先進美好,卻致命淌血:托馬斯·品欽的隱匿賽博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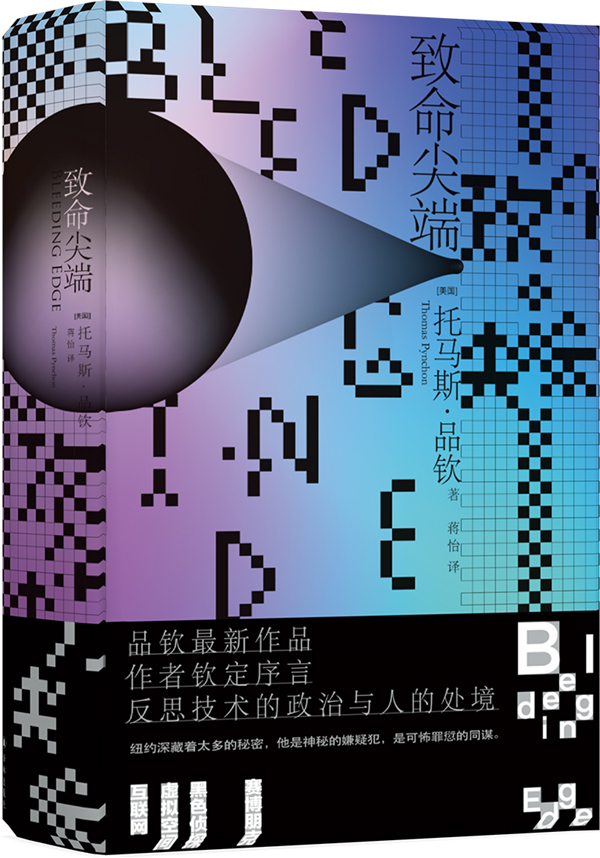
一、網(wǎng)
一生酷愛豬仔玩具的品欽,想必應該看過《夏洛的網(wǎng)》。出生時搶不上母豬奶頭而險些遭到農(nóng)場主淘汰的小豬威爾伯,頗像是品欽筆下一直記掛的“棄民”原型,而三番五次從既定的末日厄運中拯救他的,正是一張纖細而神奇的“網(wǎng)”。憑著在網(wǎng)上結出的神秘文字,“網(wǎng)”不僅成為鄉(xiāng)民和觀光客眼中的神跡,還傳遞出重審低賤生命之美的諭令。《致命尖端》(Bleeding Edge,2013)也是一部關于“網(wǎng)”的小說,只是這張網(wǎng)不是蜘蛛的唾液結成的,而是虛擬的二進制代碼、服務器、電腦終端和網(wǎng)線構成的隱匿賽博空間,如幽靈般懸掛在世貿中心遺址紀念公園的深井中。
這并不是品欽第一次在小說里“觸網(wǎng)”。在前一部《性本惡》(Inherent Vice,2009)中,私家偵探多克就通過友人的計算機實驗室見識了“阿帕網(wǎng)”(即“因特網(wǎng)”的前身)。站在20世紀60年代的終結處,嬉皮士們隱約感到一扇新的“伊甸園之門”正在開啟,網(wǎng)絡將引領人類的肉身去飛升和超越,“就像是迷幻藥,完全是另一個奇異的世界。時間,空間,所有這些都不同”。然而,品欽也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網(wǎng)絡時代的隱憂:“當年他們發(fā)現(xiàn)迷幻藥能變成一個通道,讓我們看見某些被他們禁止的東西,于是政府立刻宣布這是禁藥,還記得嗎?信息跟這個不就是一碼事嗎?”
先進美好,卻致命淌血,這正是當代社會所謂“血尖”技術的悖論。“網(wǎng)絡”及其依附的人類數(shù)字化生存,由此成為品欽小說世界中像“火箭”一樣重要的文學―科技母題。其實,以惡托邦的筆法來諷刺這個信息時代過度聯(lián)結的互聯(lián)網(wǎng)對人的異化,這在當代西方小說中并不鮮見,代表性的近作或許是大衛(wèi)·艾格斯(Dave Eggers)的《圓環(huán)》(The Circle,2013)。艾格斯在書中毫不留情地挖苦了硅谷那些科技巨頭(如谷歌、臉書和蘋果)的虛假節(jié)操,大數(shù)據(jù)時代個人隱私的消失威脅到了人的基本自由,篤信“分享即關懷”的社交網(wǎng)絡最終演變成一場全民狂歡的噩夢。相較之下,品欽對于高速信息網(wǎng)絡的態(tài)度則復雜含混得多,因為他深知互聯(lián)網(wǎng)從誕生開始,就是兩股迥異的歷史力量交纏的產(chǎn)物。
一方面,“阿帕網(wǎng)”當然屬于嚴格意義上20世紀70年代五角大樓的軍工產(chǎn)物,但另一方面,早期互聯(lián)網(wǎng)實驗室里也攜帶著20世紀60年代美國西海岸大學校園嬉皮士的自由因子。那些最早的網(wǎng)絡沖浪者,將塑造一種“極客”亞文化,他們中的佼佼者后來打造出了“硅谷”,徹底改變了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面貌。事實上,構成因特網(wǎng)基石的TCP/IP協(xié)議本身就是一種全新的通信協(xié)議文化。如曼紐爾·卡斯特在著名的《網(wǎng)絡社會》中所言,它是“通過給予別人以及從別人那里獲得而形成的協(xié)同的基礎上進行發(fā)展”,它“從根本上實現(xiàn)了不同文化之間的通信,但是不一定要共享價值觀,而要共享通信價值”。甚至如品欽在《葡萄園》(Vineland,1990)里神秘展望的那樣,賽博空間里的人類生活將是“無重量、無形狀的電子在場與缺席的鏈條”,那一長串“0”和“1”表征了更高級的人類存在方式,就像“天使,小神或UFO里的來客”。
不過,這部《致命尖端》卻更像是網(wǎng)絡時代的后現(xiàn)代啟示錄。小說以2001年春天的紐約開場,彼時穆罕默德·阿塔的劫機小組成員尚未從邁阿密動身,《老友記》中瑞秋的發(fā)型依然是城里女性競相效仿的時尚,華爾街的伯尼·麥道夫仍舊是高級投資者口中最值得信賴的生財機器。但是,一種詭異的微型末日感已悄然在紐約人腦海中盤桓。哪怕之前的“千禧蟲”危機被證明不過是虛驚一場,哪怕大部分人尚不明白在遙遠的阿富汗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意味著什么,但納斯達克的大崩盤卻足以讓曼哈頓“硅巷”的創(chuàng)業(yè)者在那個春天心驚膽寒。作為劫后余生的互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業(yè)者,小說里的電腦極客賈斯丁和盧卡斯似乎比任何人都提早意識到了這個城市、這個時代的危機四伏。
盡管《萬有引力之虹》中有過“萬物皆有聯(lián)結”這樣的名句,但品欽卻并非簡單暗示“互聯(lián)網(wǎng)泡沫”(Dot-Com Bubble)與基地組織的恐怖襲擊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聯(lián)。《致命尖端》與其他“9·11”小說最不同的敘事視角,乃是將新世紀初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的災難和世貿中心的災難放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宏大語境下。換言之,歷史從未如福山所言的那樣走向終結,“雙子塔”的倒塌既不是一個無辜城市憑空招致的無妄之災,也不僅僅是某個超級強國霸權外交的咎由自取,而是一場不斷持續(xù)的災難堆積,將本雅明式的世界歷史廢墟又壘高了一寸罷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致命尖端》并不是品欽寫的第一部“9·11”小說。早在《反抗時間》(Against the Day,2006)這部尚未譯介的皇皇巨著中,品欽就以曲折的春秋筆法,將“后9·11”的歷史之思投向了19世紀末的美國無政府主義者,投向了在威尼斯屹立千年后突然倒塌的圣馬可鐘樓,投向了發(fā)生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的通古斯大爆炸……品欽似乎習慣于從全球資本主義和現(xiàn)代性的歷史運動軌跡中,審視人類社會這些突如其來的災變、戰(zhàn)禍、暴亂、沖突和坍塌,而“網(wǎng)絡社會”或“9·11”不過是對這一連續(xù)體在當下階段的最新命名。甚至可以說,品欽并不是心血來潮才決定在晚年寫一部“9·11”小說,他畢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都在預言這類“末日”事件的不斷到來,他筆下那些形形色色的與歷史對抗的鬼魂從未真正退場,他們遲早會從邊緣悄然越界,對現(xiàn)實的中心進行轟然一擊。
二、“帝國”
閱讀《致命尖端》時可資參考的一個重要理論資源,是哈特和內格里那本極具影響力的《帝國》(Empire,2001)。這兩位左翼學者在新世紀伊始時提出,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乃是一種新形態(tài)的治理方式,它迥異于從前作為歷史征服力量的舊帝國(如古羅馬帝國、大不列顛帝國),而是一種沒有時空邊界的、超越民族國家范疇的存在。這個“帝國”并非專指今日的世界超級強國美國,甚至也不是歷史的某個分期階段,而是一種懸置歷史的力量,它試圖站在歷史之外,以“一種新的主權形式來有效規(guī)控全球交換”。哈特和內格里進一步認為,這種“解域化”的“帝國”不僅在今日的社會生活中無孔不入,而且它的主權具有高度的虛擬性(virtuality),往往以高科技的媒介技術和信息網(wǎng)絡為載體,來實現(xiàn)德勒茲所說的“控制社會”(control societies)。
既然這樣的信息帝國是全球化的晚期資本主義所呈現(xiàn)的統(tǒng)治生態(tài),那么品欽以虛擬的全球網(wǎng)絡為背景來書寫紐約“9·11”恐怖襲擊也是情理之中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9·11”不再是亨廷頓所說的西方基督教與東方伊斯蘭教之間爆發(fā)的“文明的沖突”,而是哈特與內格里所言的“帝國”與其不滿者之間的斗爭。兩位作者甚至頗具爭議地寫道,“這些(帝國的)敵人常被稱為恐怖分子,這個簡化的術語在概念上很粗糙,它根植于一種警察思維”。詭異的巧合是,《帝國》出版后不久即發(fā)生了“9·11事件”。一些批評者常將上面這句話搬出來大加鞭撻,認為是對恐怖分子的一種洗白,但也有學者認為哈特與內格里的左翼思想寫作是對全球恐怖主義時代到來的一次啟示錄式的預言。
品欽顯然希望再現(xiàn)“恐怖分子”標簽背后的極端含混性。他筆下的“9·11事件”真相撲朔迷離,各種陰謀論的敘事猶如“量子糾纏”一般鬼魅。核心的反派人物艾斯是一個四處并購的IT巨頭,利用可疑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hashslingrz在世界各地進行洗錢和金錢輸送,與之關系曖昧的既有中東的阿拉伯極端組織,也可能涉及俄國、以色列和美國政府高層之間的博弈。品欽并未在小說中將艾斯的真實背景和盤托出,也沒有確鑿說明在紐約公寓樓的天臺上那些用“毒刺”防空導彈演習的準軍事分子如何卷入了“9·11”襲擊。但毫無疑問,艾斯以及其名下鬼影幢幢的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只是站在前臺的代理,居于幕后的正是哈特與內格里書中探究的那個無以名狀的、虛擬態(tài)的“帝國”。
透過一個小說人物之口,品欽如是描述我們所處的帝國之網(wǎng):“晚期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范圍內的金字塔騙局,那種你用人類作為犧牲品一層一層摞起來的金字塔,同時還要讓那些傻瓜相信會永遠這么持續(xù)下去。”在這樣依靠虛假承諾和信心而維系的龐氏騙局中,所有的人類犧牲品就如同“帝國”每天制造出的垃圾(“瑪克欣扔掉的每一個裝滿了土豆皮,咖啡屑,沒吃完的中餐,用過的衛(wèi)生紙、衛(wèi)生棉球、餐巾紙和尿不濕,腐爛的水果,變質的酸奶的費爾威購物袋”),堆積在遠離紐約市中心的垃圾場里。然而,他們和它們并沒有憑空消失,而是“進入了集體的歷史,如同身為猶太人,發(fā)現(xiàn)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終結”。
如果說制造出這些當代棄民的,是互聯(lián)網(wǎng)驅動的全球資本主義,那么收容他們的同樣也是互聯(lián)網(wǎng)。一方面,電子網(wǎng)絡的虛擬性、即時性、匿名性和去中心化讓“帝國”可以更好地制造出超級全景監(jiān)獄,實現(xiàn)生命政治的全面控制;但另一方面,網(wǎng)絡的這些特性又幫助“帝國”的不滿者在0和1的數(shù)字世界里去反叛、去逃離。《致命尖端》告訴我們,那個熟知的因特網(wǎng)已被資本主義高度商業(yè)化,搜索引擎和各種網(wǎng)絡“后門”軟件讓我們在“帝國”里無處遁形;與這種“淺網(wǎng)”相對的是“深網(wǎng)”(Deep Web),后者是一個“結構精美的垃圾場”,那里“大多是廢棄的網(wǎng)站和斷開的鏈接”,內部則是“一套完整的具有重重限制的隱形迷宮”。
賈斯丁和盧卡斯所設計的“深淵射手”(DeepArcher)就是深網(wǎng)之中的虛擬“庇護所”:在這里,為了躲開搜索引擎的“爬蟲”程序和政府機關的監(jiān)管審查,一切的節(jié)點訪問都是匿名的,一切的網(wǎng)頁鏈接都是隨機生成的。當女主人公瑪克欣進入這個神秘的網(wǎng)絡地帶,居然發(fā)現(xiàn)那里人滿為患,到處是“探險家、朝圣者、僑居他國靠國內匯款生活的人、逃跑中的愛侶、強占他人土地者、潛逃犯、神游癥患者”。而在“9·11”發(fā)生之后,“深淵射手”又成為紐約那些死難亡靈的游魂收容站,他們以虛擬的后人類身體繼續(xù)寄居在這里。自不消說,那些尋找新的“雙子塔”進行攻擊的恐怖分子,也會選擇這樣的匿名社交網(wǎng)絡進行串聯(lián)和組織。
由此可見,品欽眼中的全球電子信息網(wǎng)絡是一把雙刃劍。它為“帝國”實現(xiàn)“控制社會”提供了史無前例的便利,也服務于全球資本主義的市場擴張,正如《致命尖端》中寫到的那樣:“在二進制的微環(huán)境里,在全球各地沿著不見天日的光纖和雙絞線,如今以無線連接的形式,穿過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網(wǎng)絡血汗工廠里的每一處地方,閃閃發(fā)亮的繡針一刻也不停歇地在那張永不平靜的帷毯上編織。”但與此同時,這張網(wǎng)又為“帝國”的反叛者提供了最佳的對抗武器,給予了那些資本主義的他者一種寶貴的自由和保護。1984年,品欽在《紐約時報書評》發(fā)表了一篇題為《做一個勒德派是否可行?》(Is It O.K. To Be A Luddite?)的文章,探討了勒德派與機器的悖論關系。在當下的時代,無數(shù)電腦組成的萬維網(wǎng)似乎就是當代勒德派分子要去抗爭的超級機器,然而信息革命又為大眾實現(xiàn)了賦權,讓他們可以實現(xiàn)從前無法想象的自由和聯(lián)結。所以,品欽無意像《圓環(huán)》那樣將互聯(lián)網(wǎng)生存諷刺為赫胥黎式的“美麗新世界”,他迫切希望我們去思考網(wǎng)絡被資本主義的工具理性所異化的危險,但同時也要將萬維網(wǎng)繼續(xù)作為對抗“帝國”的武器。
更多的開源軟件?更隱匿的網(wǎng)絡訪問方式?更多的斯諾登?更多的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精神在極客文化中復興?或許吧。品欽冷靜地提醒讀者,“深淵射手”和它所在的“深網(wǎng)”并不能一勞永逸地實現(xiàn)逃離和超越,“一旦等他們下來[深網(wǎng)]這里,一切就會被郊區(qū)化,速度比你說的‘晚期資本主義’還要快。之后一切都會跟上面淺灘里一樣了。一個接一個的鏈接,全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下,既安穩(wěn)又體面。每個角落都有教堂,所有酒吧都有營業(yè)執(zhí)照。誰還想要自由,就不得不套上馬鞍,往其他地方奔去”。
三、“大蘋果城”
在關于“帝國”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宏大敘事之外,《致命尖端》還是一部關于紐約城的黑色偵探小說。品欽雖然生于紐約長島,但常常被視為加州作家。《拍賣第四十九批》是在加州灣區(qū)的漫游記,《葡萄園》的故事發(fā)生在加州的安德森河谷,而《性本惡》的情節(jié)則是圍繞洛杉磯的沖浪海灘小鎮(zhèn)展開。按照一些真假難辨的說法,品欽正是20世紀70年代在南加州的海邊小屋寫出了那部石破天驚的《萬有引力之虹》。
“加州”之所以成為這位后現(xiàn)代小說家首選的地理坐標,當然有著深刻的文學成因。加利福尼亞有燦爛持久的陽光,有超級大都市洛杉磯,有沖浪圣手云集的海灘,有造夢的好萊塢,有沙漠、葡萄園和雪山……而與此同時,這里也有霧霾、焚風、《休倫港宣言》、瓦茨暴亂、房地產(chǎn)投機、曼森家族和霓虹燈下丑聞纏身的LAPD。或許在品欽看來,沒有哪個地方像加州這樣表里不一,永遠在最明媚光鮮的外表下掩藏著最齷齪可憎的丑惡,吸引著錢德勒筆下的私家偵探馬洛去不斷探尋黑色的傳奇故事。
那么紐約呢?這個品欽筆下極少涉及的故鄉(xiāng)之城,到底對他的文學想象而言意味著什么?據(jù)說最近二三十年,品欽一直定居在紐約市,而且和自己的文學經(jīng)理人梅蘭妮結了婚。1998年在曼哈頓街頭被記者拍到時,這位年過六旬的文學隱士正牽著自己七歲的兒子杰克遜過馬路。“9·11”恐怖襲擊發(fā)生的時刻,品欽很可能是這場城市浩劫的親歷者,并最終在十二年后寫出了《致命尖端》。對法國思想家來說,曼哈頓“歸零地”代表的是圖像與現(xiàn)實之間的后現(xiàn)代哲學關系,而雙子塔則是全球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象征性符號;但對品欽來說,紐約卻不只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提喻,它更是一座留下了他生命記憶的活生生的城。
沒有誰比《夏洛的網(wǎng)》的作者更精準地描述了“大蘋果城”的特點。在那篇廣為傳頌的《這就是紐約》(Here is New York)一文中,E. B. 懷特曾這樣寫道:
不論你身在紐約何處,都免不了與偉大時代、輝煌事功、奇人、奇事、奇聞發(fā)生感應。此刻,我坐在中城悶熱的旅館房間里——房間緊靠高樓天井的半截腰處,忍受華氏九十度的高溫。房間里沒有一絲風,然而,我仍不由得感受到周遭有什么東西撲面而來。隔二十二個街區(qū),是魯?shù)婪颉ね邆惖僦Z的遺體安葬處;隔八個街區(qū),內森·黑爾給人處決;隔五個街區(qū),歐內斯特·海明威在出版商的辦公室直搗馬克斯·伊斯曼的鼻梁;隔四英里,沃爾特·惠特曼坐在桌前,埋頭為《布魯克林鷹報》寫評論;隔三十四個街區(qū)的一條街上,薇拉·凱瑟住過,她來紐約,寫一些關于內布拉斯加州的書;隔一個街區(qū),馬塞林曾經(jīng)在競技場劇院的舞臺上插科打諢;三十六個街區(qū)外一處地方,歷史學家喬·古爾德當著眾人的面,將一臺收音機踢得粉碎;隔三十個街區(qū),哈里·索槍殺了斯坦福·懷特;隔五個街區(qū),我曾經(jīng)在大都會歌劇院為人引座;僅隔一百零二個街區(qū),老克拉倫斯·戴在主顯教堂洗去了他的罪惡。
與蔓生的“天使之城”洛杉磯相比,紐約以令人窒息的密度,在每個街區(qū)散發(fā)著各種城市傳奇的味道。它與其說是一個典型的美國都市,還不如說更像是屬于全世界的大都市,詭譎而異質。然而,透過瑪克欣的“偵探之眼”,品欽敏銳地感覺到紐約城20世紀末以來發(fā)生的變化,那種曾讓懷特心心念念的城市特質消失了。就像《致命尖端》中寫的那樣,在“朱利安尼和他那幫開發(fā)商朋友們”的合力整治下,“已經(jīng)把這個地方迪士尼化了,它變得非常貧瘠。陰郁的酒吧、賣降膽固醇和減肥藥的藥房、色情影院已經(jīng)被推倒或翻修了,邋里邋遢、無家可歸、沒有發(fā)言權的弱勢群體被趕走了,也不再有毒販子、皮條客或表演三公術的賣藝者,甚至都沒有逃學的孩子在玩彈球游戲了。都被趕走了”。
當然,新世紀的這個“潔版”紐約并未變得更加天真無害。和那些坐在雙層敞篷觀光車上的外國游客相比,以商業(yè)詐騙調查為職業(yè)的瑪克欣更清楚這些光鮮的摩天大樓背后隱藏的罪惡。品欽幾乎毫不掩飾地讓瑪克欣戲仿了《拍賣第四十九批》中的南加州家庭主婦俄狄帕,后者要偵查的是那個代表了美國遺產(chǎn)的地下郵政網(wǎng)絡,并在旅行中對20世紀60年代的南加州進行了一次認知繪圖,而前者則是試圖弄清21世紀的紐約及其虛擬的地下網(wǎng)絡如何成為“帝國”的角力場。不過,瑪克欣對于眼前的黑色城市(noir city)并沒有俄狄帕那般生澀;相反,瑪克欣在職業(yè)生涯中和紐約的三教九流打過交道(她說自己“跟收賬人、軍火交易商、如瘋狗般亂吠的共和黨人起爭執(zhí)時總能獲勝”),她所從事的財務審計行業(yè)“有一種道德感褪去后的光環(huán),一種愿意跳出法律的束縛、把審計員和稅收員的行業(yè)秘密公之于眾的令人信賴的意愿”。某種意義上,她更像是《性本惡》中那個嬉皮士私家偵探多克,將蓋茨比式的美國大亨(和他們諱莫如深的“金獠牙”企業(yè))從曖昧不明的歷史語義場中曝光出來。
這里,艾斯或《性本惡》中的烏爾夫曼都不過是品欽戲謔編織的偵探敘事中的邪惡代理人,主人公追兇之旅的終極意義指向的其實并不是具體的人,而是那個城市。對于這一點,品欽在《致命尖端》的開篇引言中就表達得再清楚不過了:“倘若紐約以角色的身份出現(xiàn)在懸疑小說里,那么它既不會是偵探,也不會是兇手。它會是那個神秘的嫌疑犯,知道事情的真相,卻不打算說出來。”這段出自紐約偵探小說家唐納德·E.韋斯特雷克(Donald E.Westlake)的話,替品欽道出了《致命尖端》中這個城市的詭異本性:“大蘋果城”深藏著太多的秘密,所有暴力與邪惡的犯罪都無法直接歸咎于它,但它似乎又并非純然無辜,而是在某種意義上屬于那些“9·11式”可怖罪愆的同謀。
四、臆想癥
對于熟悉品欽的讀者,閱讀《致命尖端》時最不陌生的元素,恐怕就是“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了。品欽的所有小說都試圖在主流歷史敘事的高塔下構建另一種影子敘事,甚至連小說家本人也被傳聞為生活中的偏執(zhí)癥患者,其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行蹤多半是為了擺脫臆想中的秘密部門的追查。本書中提到的“蒙托克計劃”,就是歷史妄想癥愛好者最愛提及的案例之一(另一個也讓他們魂牽夢繞的,大概就是神秘的內華達州51區(qū)),據(jù)說在那個巨大的軍事雷達站禁區(qū)里面,隱藏著美軍秘密研制時空穿梭旅行和心靈控制術的實驗室(順便說一個不算特別意外的巧合:蒙托克就坐落在品欽的故鄉(xiāng)紐約長島)。
對于童年時代就被蒙托克的雷達波“感應”過的品欽來說,大熱美劇《X檔案》這樣的“外星人陰謀論”并不算是科幻迷走火入魔的低智表現(xiàn)。穆德要去解開的無數(shù)懸疑背后,體現(xiàn)的是對正統(tǒng)的官方歷史敘事的不信任,人們有理由擔心在末日般災變來臨的時刻,權力的壟斷者們是否會在民眾中升起無知之幕,然后在背后交易不可告人的秘密。這些秘密可能涉及地緣政治、經(jīng)濟利益、家族權柄,甚至就是單純的活下去的機會。如果你覺得流行小報上關于“共濟會”秘密操縱世界,或五角大樓隱瞞“羅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純屬陰謀論者的無稽之談,那么“伊朗門”、“國會縱火案”或匈牙利猶太人救援委員會的卡茲納與艾希曼的魔鬼交易又說明什么呢?
有評論家認為,《致命尖端》是品欽小說中陰謀論色彩最不濃厚的一部,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能夠看到小說人物之間口口相傳的各種“9·11”陰謀論。曼哈頓恐怖襲擊會是美國政府一手策劃的“國會縱火案”嗎?恐怖襲擊發(fā)生之前,那些開著黃色出租車的穆斯林司機被預先警告遠離下城保平安了嗎?為什么在那個9月初,芝加哥交易所出現(xiàn)了一波美聯(lián)航和美航反常的看跌期權……最有意思的一個陰謀論版本,是關于“全球知覺實驗計劃”(Global Consciousness Project)。這個確有其事的實驗是以普林斯頓大學為中心,每秒不間斷地收集世界各地近百個站點的隨機事件發(fā)生器(Random Event Generator)的數(shù)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來自各地計算機完全隨機發(fā)出的“0”與“1”數(shù)值,科學家能夠以此計算它們的全球相干性(global coherence)。更通俗地說,它們是一組組毫不相干的隨機數(shù),是電腦極客們能想到的“最純粹”的任意性數(shù)字串,因此被用來作為“深淵射手”網(wǎng)站的隨機密碼,以提高該網(wǎng)站的匿名性。然而詭異的是,“在9月10日晚上出了問題,從普林斯頓得到的這些數(shù)字突然偏離了隨機特征……這種情況持續(xù)到9月11日和隨后的幾天。然后一切又神秘地回到原來近乎完美的隨機狀態(tài)”。小說并未虛構的事實是,“全球知覺實驗計劃”所統(tǒng)計的全球相干性的確在“9·11事件”發(fā)生前幾個小時出現(xiàn)了重大異常,隨機特征在重大全球災難發(fā)生前驟然消失。這似乎印證了普林斯頓科學家們提出的一個理論:“假如我們的思維都以某種方式連接在一起,那么當出現(xiàn)重大全球性事件和災難時,[征兆]就會體現(xiàn)在這些[隨機]數(shù)字中。”
以品欽對科學的專業(yè)見解,我相信他并非沒有意識到“全球知覺實驗計劃”這個泛心理學實驗本身存在的巨大爭議。在大數(shù)據(jù)的計算時代,海量數(shù)據(jù)中往往會呈現(xiàn)出無法科學解釋的相關性,它們中有相當部分被稱為“偽相關”,不適用于傳統(tǒng)實證科學中的因果分析。品欽真正感興趣的,其實是在言之鑿鑿的官方歷史敘事之外,引入更多的關聯(lián)維度,從而建立一種歷史臆想癥的思維范式,在那些被我們習慣性認知判定為“隨機”的地方(譬如自由化的金融市場,或全球互聯(lián)網(wǎng)的數(shù)據(jù)包輸送),窺見某些重要卻未知的聯(lián)結或規(guī)律特征。它們甚至可能就是人類歷史大數(shù)據(jù)中尚待揭開的“本福特定律”。所以,品欽并不是要在“9·11”小說中提煉出一種與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戰(zhàn)爭迥然相異的反敘事,而是用無盡的數(shù)字拓撲網(wǎng)絡作為象征,召喚出與單義的歷史書寫術不相容的臆想癥思維的價值。這也是他與德里羅用《天秤星座》(Libra)來重寫肯尼迪遇刺歷史頗為不同的地方。
品欽這是在繼續(xù)操練后現(xiàn)代文學理論中所謂的“歷史編纂的元小說”(historiographicmetafiction)嗎?我認為,《致命尖端》并非典型意義上的后現(xiàn)代小說,品欽也無意繼續(xù)在這樣的文學標簽下進行創(chuàng)作。品欽借用書中人物瑪奇(一個左翼的博客寫作者)這樣評價了“9·11”的意義:“‘9·11’襲擊發(fā)生后,在所有那些混沌與困惑中,美國歷史悄悄地打開了一個洞,一個管理責任的真空,人類資產(chǎn)和金融資產(chǎn)開始在里面消失。以前在嬉皮的單純歲月里,人們喜歡怪罪‘CIA’或‘某個秘密的流氓機構’。但是,這次是全新的敵人,你無法說出它的名字,也無法在組織表或預算線里找到它。天知道,說不定連CIA也怕它們。”我們也許可以效仿哈特和內格里將之姑且命名為“帝國”,但品欽卻相信這個歷史黑洞的混雜性和無法命名性。它具有太多蹊蹺和詭異的面相,唯一可以確鑿說出的,是我們在它面前的欲逃無計,對此我們無須加以后現(xiàn)代的詭辯。
進一步說,“9·11”并不是任何具有歷史紀元意義的創(chuàng)生性事件,它只是一個歷史連續(xù)體中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契機,讓紐約人從天真慵懶的城市生活幻覺中醒來,看到自己置身于“哥譚市”的現(xiàn)實。“只需一小隊形同人字雁群的飛機,立即就能終結曼哈頓島的狂想,讓它的塔樓燃起大火,摧毀橋梁,將地下通道變成毒氣室,將幾百萬人化為灰燼。死滅的暗示是當下紐約生活的一部分:頭頂噴氣式飛機呼嘯而過,報刊上的頭條新聞時時傳遞噩耗……在可能發(fā)動襲擊的狂人的頭腦中,紐約無疑有著持久的、不可抵擋的誘惑力。”同樣是在E.B.懷特1949年發(fā)表的那篇《這就是紐約》中,我們看到了半個世紀前關于“9·11”的預言。品欽并不比懷特更加樂觀,他筆下的艾斯并未被繩之以法或走向窮途末日,那個讓紐約出現(xiàn)“歸零地”式歷史黑洞的“敵人”必將再度回來。
當然,我也不認為《致命尖端》是全然悲觀的歷史筆調。相反,這部小說隱約傳遞了馬修·阿諾德那首《多佛海灘》的味道。雖然“人類苦難的渾濁的潮汐”永遠不會停歇,雖然“紛爭和潰逃的驚恐在荒原上交織/愚昧的軍隊于昏暗中在荒原上爭斗”,但我們和愛人之間依然可以用更緊的擁抱、以更真誠的愛來抵御這些注定到來的災難。小說開篇時,正是2001年的春分,“上西區(qū)的每棵豆梨樹都在一夜間綻開了一簇簇的白梨花”,而在結尾時,第二年的春天又準時來到,母親們送孩子去上學,紐約“街上的梨樹又在一夜間迸出了壓滿枝頭的朵朵梨花”。此時,倒春寒的城市依然可能再下雪,世貿中心的廢墟遠未清理完畢,但我們的女主人公瑪克欣已經(jīng)成了一個更堅韌、更懂愛的母親。
在掩卷時,讀者將發(fā)現(xiàn)暮年品欽最溫柔的時刻……
本文為美國作家托馬斯·品欽最新作品《致命尖端》中文版(蔣怡/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11月版)的序言,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