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為何要被閱讀? ——顏荻評《閱讀希臘悲劇》《奧瑞斯提亞》
我沒有見過比戈德希爾更熱愛舞臺的古典語文學家了。他不僅是劍橋擁有百年歷史的古希臘戲劇節(jié)的首席顧問,而且還曾把荷馬史詩搬上表演舞臺:在2015年,他親自發(fā)起,與六十多位英國的名演員合作(其中不乏我們熟悉的本·衛(wèi)肖[Ben Whishaw]、約翰·西姆 [John Simm]),在大英博物館當眾閱讀演繹了長達十六個小時的《伊利亞特》,這場活動陣仗之大可謂名噪一時。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本人也極具表演稟賦。他的現(xiàn)場感極強,不僅饒有興致地參演過好幾場劍橋的戲劇節(jié),即便是學術(shù)演講,也自帶辨識度極高的話劇腔,讓聽者進入講堂如同進入劇院一般。當然,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同樣能看到他對戲劇舞臺的嚴肅關(guān)注,他在2007年出版的《當今如何上演古希臘悲劇》(How to Stage Greek Tragedy Toda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就是最好的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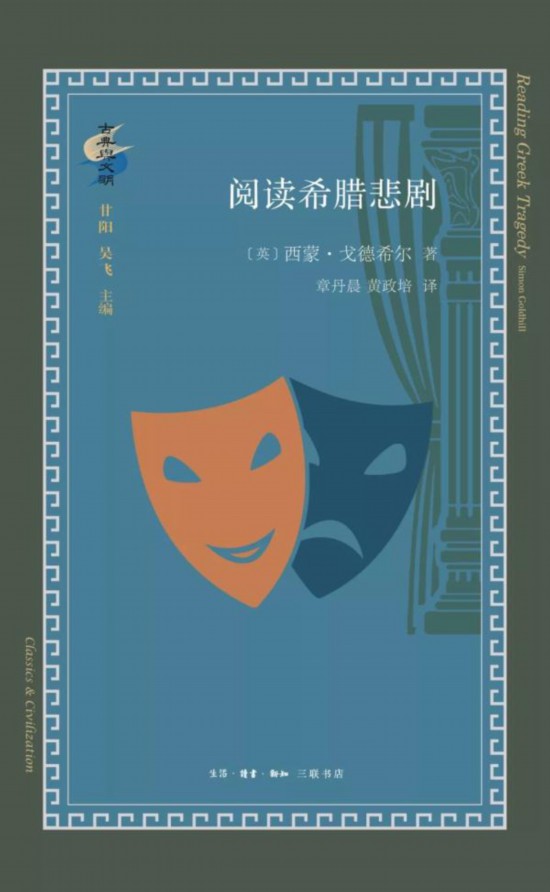
戈德希爾著《當今如何上演古希臘悲劇》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恰恰是這樣一位活躍于聚光燈下的學者將他的一部作品命名為“閱讀希臘悲劇”(Reading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此標題似乎是說:悲劇是用來“閱讀”,而非“演繹”或者“觀看”的。這個與戈德希爾熱火朝天的舞臺事業(yè)看上去頗為矛盾的書名不免讓人疑惑:他為什么認為希臘悲劇是要被“閱讀”的?他對悲劇的“閱讀”和他對戲劇作為表演藝術(shù)的熱衷又有什么關(guān)系?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需要先從戈德希爾對悲劇語言的持續(xù)關(guān)注談起。從他的第一本書《語言、性別與敘事:奧瑞斯提亞》(Language, Sexuality, Narrative: The Oreste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到后來的《閱讀希臘悲劇》《奧瑞斯提亞》(Oreste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索福克勒斯與戲劇的語言》(Sophocles and the Language of Trage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語言一直在戈德希爾“閱讀”希臘悲劇的過程中占據(jù)著核心位置。作為一部整體考量古希臘悲劇的批評性研究,《閱讀希臘悲劇》最重要的前三章便濃墨重彩地著筆于語言問題。在其早期作品中,戈德希爾時常庖丁解牛式地探討戲劇文本中某個具體詞匯的復雜語義,它們大都相互矛盾、各有所指,在不同語境中可以發(fā)展出完全不同的解釋。這種對于近乎瑣碎的語文學分析的熱愛,與戈德希爾對悲劇語言本身的理解有關(guān)。在他看來,語言并非直白的、表意清晰的符號系統(tǒng)。相反,在意義表達和接收的過程中,在能指與所指之間,語言充滿著不確定性和含混性。因此悲劇角色彼此對話時,常常發(fā)生語義沖突,導致交流的障礙和隔膜,而一旦障礙產(chǎn)生,悲劇的張力便出現(xiàn)了,繼而把悲劇推向高潮。換言之,戈德希爾認為,語詞含義間的矛盾與沖突是悲劇的靈魂——“對語言及其本身的安全感的缺乏以及確定性的錯置,是悲劇文本的關(guān)鍵動力”(《閱讀希臘悲劇》,第4頁)。對于戈德希爾,研究悲劇語言是理解悲劇意義的關(guān)鍵所在。

戈德希爾著《語言、性別與敘事:奧瑞斯提亞》
戈德希爾多次談到的一個例子是埃斯庫羅斯《奧瑞斯提亞》三連劇中對dikē一詞的使用——戈德希爾似乎特別鐘愛這個例子,不僅在《閱讀希臘比劇》,還有之后的普及性作品《奧瑞斯提亞》(1992)中都有提及。借助這個例子,戈德希爾向讀者詳細展現(xiàn)了語言的不確定性如何顛覆性地影響了我們對整部戲劇意義的理解。希臘詞dikē通常被譯為“正義”(justice)。如果大寫,Dikē,就成了我們耳熟能詳?shù)恼x女神。在傳統(tǒng)學者如基托(H. D. F. Kitto)的解釋中,《奧瑞斯提亞》三連劇呈現(xiàn)的是關(guān)于“正義”的進化論,即由克呂泰莫涅斯特拉、奧瑞斯特斯和復仇女神代表的“復仇正義”,向雅典民主城邦和雅典娜代表的“法律正義”的轉(zhuǎn)向。這個解釋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假定了語言是一個清晰、確定的符號系統(tǒng)。因為盡管從“復仇正義”轉(zhuǎn)向“法律正義”的過程中,正義的內(nèi)容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但所有角色對“正義”(dikē)一詞本身的理解卻是相同的。換言之,在戲劇中“正義”本身是一個可以被確切表述和理解的道德語匯。但戈德希爾認為,該詞在戲劇中的意義遠比傳統(tǒng)理解的要復雜、模糊,悲劇文本中的dikē充滿了沖突,這些沖突在劇中并沒有得到解決,所以《奧瑞斯提亞》的題中之義其實并不是簡單的關(guān)于“正義”的進化論,而是開放性地追問了何為“正義”。
讓我們具體來看戈德希爾筆下dikē面臨的復雜局面。戈德希爾注意到,幾乎劇中所有人都使用過dikē來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而這些角色口中的dikē意義各不相同,他們每個人都只是將該詞挪用到自己的修辭當中,來爭奪關(guān)于dikē的話語權(quán)(即《閱讀希臘悲劇》第二章所謂的“挪用的語言”)。克呂泰莫涅斯特拉說她是正義(dikē)的,因為她是作為母親在為女兒的死報仇。不過她的正義并沒有得到奧瑞斯特斯承認,奧瑞斯特斯要為父親報仇,對他而言,妻子殺丈夫是最大的不正義,他必須為父討回公道,這才稱得上是公正之舉(dikē)。然而,奧瑞斯特斯在復仇之后卻陷入了復仇女神的追殺,因為后者認為前者的血親殺戮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正義的(dikē),只有懲罰他,才能維護古老的正義秩序(dikē)。復仇女神與奧瑞斯特斯的沖突在雅典的審判中,以奧瑞斯特斯的勝訴告終,雅典的法庭支持了奧瑞斯特斯的正義觀而否定了復仇女神的正義觀。這似乎意味著奧瑞斯特斯的“正義”最終勝出了。然而戈德希爾提請所有讀者注意,審判的勝利只是民主投票的結(jié)果,六票對七票的微弱差距僅僅說明某一種正義理念險勝,因而即便到戲劇最后,關(guān)于“正義”究竟為何還是懸而未決,沒有定論。“正義”或dikē在《奧瑞斯提亞》中始終處于一種無解的、矛盾的狀態(tài),相互沖突的dikē的意涵以及關(guān)于“正義”的理解,完全沒有真正和解。這意味著,悲劇不但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解決沖突的答案,反而向我們呈現(xiàn)了沖突如何難以被解決。戈德希爾總結(jié)道:
的確,每個角色都聲稱他或她擁有正義,都對這一重要的評判詞匯做出了單方面的聲明。因此,悲劇探索了一個常規(guī)的、政治的、評判的語言在社會沖突中如何被使用,進而又如何成為社會沖突的來源。然而正是因為悲劇將人類試圖以此評判語言來相互溝通的障礙和限制戲劇化了……這不僅引起了悲劇的語言深刻的、語義上的共鳴,而且也解釋了社會評價詞匯體系中的張力與含混性。在《奧瑞斯提亞》中這一感覺最為強烈,dikē的語言——社會秩序、正義——在埃斯庫羅斯的悲劇審查中被分裂和碎片化了。(《奧瑞斯提亞》,43頁)
戈德希爾對悲劇語言的解構(gòu)性解讀是緊跟時代步伐的。在他第一本書出版前的十五到二十年,西方文學批評界經(jīng)歷了從結(jié)構(gòu)主義到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歷史性更迭。1967年德里達連續(xù)發(fā)表了《書寫與差異》《論文字學》《聲音與現(xiàn)象》,掀起了之后風風火火的解構(gòu)主義浪潮。在戈德希爾的解讀中,我們不難看到德里達和德曼(Paul de Man)的影子。尤其是他對老一代悲劇批評家如基托的批評(見《奧瑞斯提亞》第二章和《閱讀希臘悲劇》第一、二章),可謂旗幟鮮明地把矛頭指向了閉合的、系統(tǒng)的、概念性的結(jié)構(gòu)主義解讀。戈德希爾強調(diào)語詞的開放性、含混性和不確定性,這一切都與他的前輩所理解的悲劇語言背道而馳。正因此,戈德希爾認為,即使是作為表演藝術(shù)的戲劇也需要被“閱讀”(reading),而不僅僅是觀看——這就是為什么他會為自己的第二本書冠上一個看起來既矛盾又挑釁的名字——“閱讀”悲劇,他要用一個解構(gòu)性的概念,破除前人對戲劇語言平白而缺乏深度的理解,促進讀者挖掘語言本身蘊涵的張力與意義。
不過,戈德希爾對當代文學理論的青睞絕非單純?yōu)槔碚摱碚摚瑸樾鲁倍鲁薄K詫F(xiàn)代理論帶回古代研究,是因為他發(fā)現(xiàn),兩者在時空交融中有十分契合的一面,用一種解構(gòu)性的方式來解讀悲劇可能更符合當時的文化氣質(zhì)。這個文化氣質(zhì),一言以蔽之,就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文化氣質(zhì)。具體而言,它與雅典民主政治的繁榮,以及隨之而來的修辭學和智者運動的興起有著十分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在戈德希爾看來,語言在雅典是一個極為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的問題。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是直接民主,公民的日常生活便是在議會中你來我往地討論議題,在法院中就大小案件進行法庭辯論,因而說話在很多時候并不僅僅是閑談,而是直接影響政治決策的一種行為。會說話,能在辯論中勝出,是政治家基本且必要的技能。修辭學在雅典如此興盛并非偶然,它能十分有效地提高政治家的演說素養(yǎng)。戈德希爾認為,修辭學具有某種明顯的解構(gòu)性特征:它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并不追求言辭的真理,而是通過對語義的操縱和語詞的調(diào)控來達成論辯效果。不擇手段地贏得辯論才是修辭學的目的,而為了贏,一個人可以詭辯甚至撒謊(后者是對語義最大程度的扭曲)。就功用而言,修辭學有時攸關(guān)性命:在法庭辯論中,一個罪人很可能因為辯論得當而獲得釋放,一個無罪之人同樣可能因為說話不利而被置于險境(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之死便是例證);在政治決策中,一些人可以因為精妙的修辭而獲取更多利益,而戰(zhàn)爭議題上,政治家的一次煽動性演講可能決定的是一大群人的生死,甚至一個城邦的存亡。在修辭學下,語言越被賦予力量就越危險。這是戈德希爾看到的雅典民主政治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因此,作為政治參與者的公民必須對語言的力量時刻保持警醒。
對于這個問題,雅典城邦有何因應之法?在戈德希爾看來,悲劇為雅典城邦政治的自我批評和自我反省提供了一個十分適宜的場所——悲劇通過對語言(及其失控)解構(gòu)性的演繹,將危險的語言置于拷問之中。在場的觀眾(同時也是雅典公民)在悲劇的演繹中邂逅的語言——乃至整個表演——充滿著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因此,在觀看的過程中,觀眾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他們需要隨著演繹的進行,不斷解讀出戲劇隱含的不同意涵:“觀眾被放置在了一個特別的位置上。一方面,觀眾能看到詞語如何被訴諸不同的意義,這依賴于誰使用它們,以及如何使用。另一方面,觀眾能夠理解一個詞語最廣泛的含義,即便某個特定的角色只使用了這個詞語的一個特定含義。”(《奧瑞斯提亞》,43頁)所以“表演不僅能將一個有結(jié)尾的、完整的文本搬上舞臺,更是解釋文本,并將文本的解釋開放給觀眾的過程”(《閱讀希臘悲劇》,473頁)。戈德希爾認為,以閱讀的方式觀看表演恰恰是古希臘悲劇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戲劇文本成了腳本,它可以被多種方式閱讀,包括以多種方式被劇場中的觀眾解讀。而在這個解讀的過程中,觀眾充分體驗到語言的張力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巨大且令人不安的力量。就此而言,只有與“閱讀”相結(jié)合的演繹,才是有意義的演繹。對語言的解構(gòu)性理解,正是悲劇之于民主雅典的意義所在。
由此,我們看到了戈德希爾“閱讀”悲劇的一個更深層次的考量,即悲劇與雅典民主社會的關(guān)系。在他解構(gòu)主義的框架下,修辭學中危險的語言力量被暴露在悲劇的演繹之中,雅典的觀眾通過觀看,獲得了對民主政治潛在危險的警醒。當然,這種警醒不僅限于語言,盡管語言是悲劇敘事中最直接體現(xiàn)的問題。通過敘事語言的錯亂與失控,整個悲劇實際上成了一個失控的場域:無論是兩性關(guān)系的破壞(《閱讀希臘悲劇》第五章),還是瘋狂、幻象、非理性(同前,第七章),抑或是理智的陰暗面如魔法、詛咒和激情(同前,第八章),如此種種與民主社會緊密相關(guān)的議題都得到了深刻的檢討與反省。在每天從早到晚將近一周的密集觀看后,觀眾帶著警醒與反思離開劇場,再次投入日常政治活動之中。他們或許在某個政治時刻會記起悲劇中的某個行動,而這正是悲劇在雅典社會真正發(fā)生效用的時刻。對戈德希爾而言,古希臘悲劇絕不是孤立的、自治的文本,而是一種社會語言,它不僅包含了文學,還包含了儀式、宗教、政治等多個維度,所有這些維度共同定義并審問了雅典作為一個社會的社會意識與政治意識。于是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奧瑞斯提亞》一書中,為何戈德希爾要從雅典城邦開始討論,并隆重介紹戲劇節(jié)開幕式與城邦政治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四個典禮儀式(《奧瑞斯提亞》第一章)。
至此,戈德希爾悲劇理論的另一個面向——結(jié)構(gòu)主義面向——便顯現(xiàn)了出來。他將悲劇與社會文化政治關(guān)聯(lián)的做法明顯吸收了一系列結(jié)構(gòu)主義學者的思想,包括芬利(M. I. Finley)、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維達爾-納凱(Pierre Vidal-Naquet)、羅茹(Nicole Loraux)、德蒂安(Marcel Detienne)、賽特琳(Froma Zeitlin)。初讀戈德希爾,我們或許不免會對他混合了解構(gòu)主義和結(jié)構(gòu)主義的方法感到疑惑,然而在理解了他對悲劇的整體立場之后,這種疑惑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我認為戈德希爾的研究方式不僅不該被詬病(見西格爾對戈德希爾的批評,Charles Segal, “Review on Reading Greek Tragedy”, Classical philology, 1988-07, Vol.83 [3], p.234-237),反而是其對悲劇研究的真正推進之處。從社會整體來看,古希臘悲劇是對社會現(xiàn)象的反思與批評,而從悲劇的反思對象以及悲劇的呈現(xiàn)方式來看,這種批評是建立在對社會原有秩序的分析與分解之上的。恰恰因為悲劇敘事中的分解,恰恰因為悲劇對分解之后的各個對象充滿張力的演繹,悲劇才形成了一個獨立于時空的批評場域,得以對處于歷史現(xiàn)實中的社會作出一次又一次的檢討與反思。因此,戈德希爾解釋中所統(tǒng)御的兩種理論非但不是相互沖突的,而且還是自洽且必要的: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戈德希爾對希臘悲劇本質(zhì)的理解。可以說,戈德希爾為我們回答了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問題——為什么直到兩千年后的今天,閱讀希臘悲劇仍然富有意義:
正因為悲劇不能被簡單地化約為“信息”,正因為這些戲劇無法在一種閱讀或一場表演中被理解透徹,讀者們才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古代。每一時代、每一位讀者,或者每一位讀者在不同時間對希臘悲劇的回應,不僅僅是追求某種希臘悲劇的光輝所包含的永恒而固定的美,或不容置疑的真理;這些文本中包含的問題、張力和不確定性也會呈現(xiàn)在他們面前。希臘戲劇的表演和體驗,也一直都在閱讀和回應這些戲劇所提出的、始終令人不安而充滿挑戰(zhàn)的問題。(《閱讀希臘悲劇》,476-47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