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逍然:一部真正的“新”貝多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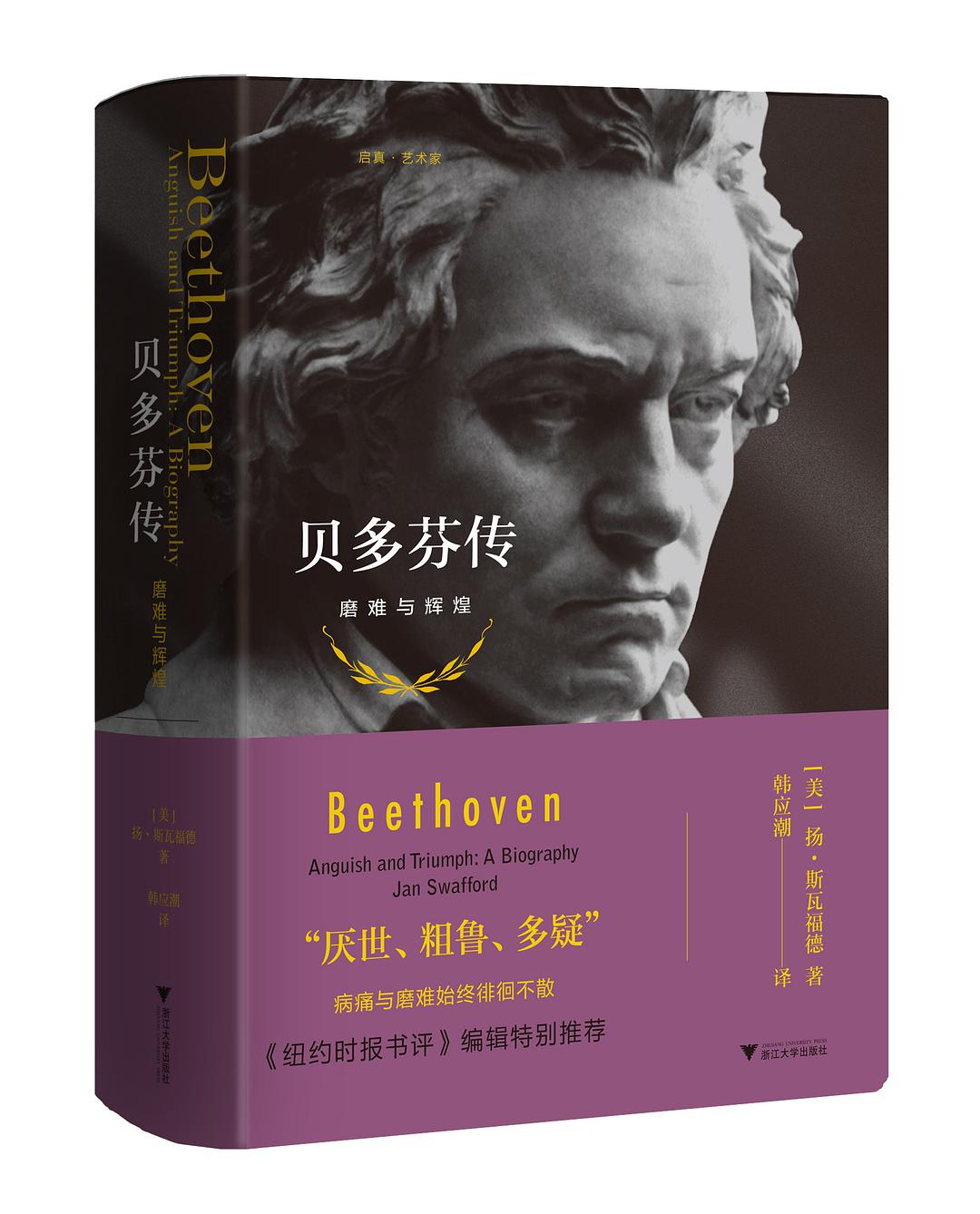
《貝多芬傳——磨難與輝煌》,[美]揚(yáng)·斯瓦福德著,韓應(yīng)潮譯,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啟真館2020年2月出版,870頁,188.00元
今年是貝多芬誕生第二百五十周年,距離他去世也已經(jīng)過去了將近二百年。盡管他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但是兩個(gè)世紀(jì)以來,歷代的學(xué)者似乎從各個(gè)領(lǐng)域、各個(gè)角度做出了幾乎所有方面的理解與闡釋,那么在今天,為什么還要寫貝多芬傳?為什么還要不斷探索貝多芬的作品?我們更可以把這個(gè)問題的范圍拓展得更為廣泛:為什么還要不斷在學(xué)術(shù)上付出努力去解讀任何過往世代的偉大作品?
一個(gè)十分明顯的回答是,我們還在不時(shí)地發(fā)現(xiàn)新的草稿、信箋等等能夠拓展我們現(xiàn)有知識(shí)與文獻(xiàn)的資料——新的發(fā)現(xiàn)在西方近代音樂學(xué)、藝術(shù)史、思想史與歷史等領(lǐng)域的確經(jīng)常出現(xiàn),舉例說來,近至2011年還有一封貝多芬所寫的六頁長信在德國被發(fā)現(xiàn)。學(xué)術(shù)是人類對知識(shí)與觀點(diǎn)的不斷更新,今天我們所掌握的許多材料往往是前輩學(xué)人無從知曉的;而前人受到時(shí)代所限而提出的某些觀點(diǎn)也需要我們今天站在新的角度上進(jìn)行修正。優(yōu)秀的學(xué)術(shù)必須是一個(gè)揚(yáng)棄的過程,不斷把錯(cuò)誤的知識(shí)與不再恰當(dāng)?shù)挠^點(diǎn)剔除,將值得重復(fù)的內(nèi)容保留并加入新的信息、提出更加符合時(shí)代的思想與理念。
揚(yáng)·斯瓦福德(Jan Swafford)的《貝多芬傳——磨難與輝煌》就是這樣一部貝多芬研究領(lǐng)域中的優(yōu)秀著作,它于2014年出版并在今年由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啟真館發(fā)行中譯本。梅納德·所羅門(Maynard Solomon)的《貝多芬傳》(1977年初版,最新的增訂版也已是將近二十年前)仍然主要致力于為貝多芬的一生還原一個(gè)真實(shí)的寫照,并成功地將許多史實(shí)與傳說區(qū)分開來,還解決了著名的“永恒的戀人”身份問題;而斯瓦福德的這部新貝多芬傳不僅整合了歷代學(xué)人發(fā)現(xiàn)并梳理出的可靠資料,更是進(jìn)而讓讀者將關(guān)注點(diǎn)放在貝多芬這個(gè)生活過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而不再是羅曼·羅蘭等作家所塑造出的那個(gè)純粹的浪漫主義英雄形象、那個(gè)“孤獨(dú)、痛苦而又不得志的理想主義藝術(shù)家”。從十九世紀(jì)初期開始,以E. T. A. 霍夫曼為領(lǐng)袖的德奧浪漫主義思想家、文學(xué)家與藝術(shù)家們?yōu)榱税l(fā)揚(yáng)自身的觀點(diǎn)與訴求,選取了貝多芬的少部分作品進(jìn)行悉心闡釋,從而將他打造成浪漫主義運(yùn)動(dòng)的偶像。但是如同斯瓦福德所說,“[沒]有誰的人生是為了被……‘闡釋’才存在的”,真實(shí)的貝多芬其實(shí)與憤世嫉俗、離群索居的浪漫主義藝術(shù)家形象相距甚遠(yuǎn)。但是由于浪漫主義的敘事影響實(shí)在深遠(yuǎn),導(dǎo)致貝多芬的這個(gè)傳統(tǒng)形象一直在全世界愛樂者的心中根深蒂固,其直接的影響首先是大量的音樂普及讀物仍然主要參照舊有的浪漫主義觀念寫成,讓我們難以跳出這個(gè)固有印象去認(rèn)識(shí)一個(gè)真正的貝多芬;其次則是我們今天的音樂圖景中仍然只有貝多芬的少數(shù)作品,廣大聽眾很難在音樂廳或媒體的明顯位置接觸到大量的其它優(yōu)秀作品。
而斯瓦福德的這部新的傳記對愛樂者來說是一個(gè)極好的契機(jī),跟隨作者的筆觸,我們能夠沿著貝多芬的生活軌跡看到他在具體的生活、人際、創(chuàng)作等問題上如何抉擇,通讀之后相信每位讀者心中都會(huì)構(gòu)建起一個(gè)立體的作曲家形象——他與我們每個(gè)人一樣,是完全獨(dú)特的,他的一生無法被重復(fù),也無法被任何刻板印象或浪漫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所歸類。貝多芬并不是道德模范,而是一個(gè)有血有肉的人,本書的全局視野為我們綜合提供了大量有關(guān)貝多芬不為人知的事情,書中告訴我們,他愛財(cái)、酗酒、待人的方式往往扭曲,但卻又真誠、堅(jiān)強(qiáng)、樂觀:他是人性的,簡直太人性的。
當(dāng)然,貝多芬的音樂才是這部貝多芬傳記的主體,對于任何熱愛音樂的讀者來說,對貝多芬的一生產(chǎn)生興趣甚至是親近之心,都是因?yàn)樗P下的那些音樂作品為自己帶來過感動(dòng)與力量。通過傳記來配合、引導(dǎo)自己對這些音樂作品的聆聽,其優(yōu)點(diǎn)是,傳記能夠?qū)⒁魳贰r(shí)代與作曲家的心路歷程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絕妙的復(fù)調(diào)。舉例說來,在寫到1802年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的那次“以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時(shí)刻為高潮的名義上的休假”時(shí),斯瓦福德對貝多芬的心理分析堪稱絕妙。在此時(shí),貝多芬已經(jīng)必須面對自己的聽力不斷惡化最終定將完全失聰?shù)默F(xiàn)實(shí),內(nèi)心之中對這個(gè)現(xiàn)實(shí)的各種防御機(jī)制也已經(jīng)全部垮塌,于是,他寫下了“海利根施塔特遺囑”。在解讀這篇著名的文獻(xiàn)時(shí),斯瓦福德指出了貝多芬的內(nèi)心是如何因絕望和苦痛而反倒充滿明晰與深刻,并且明白“從此開始,不抱希望,乃至恐懼,沒有歡樂,僅僅是生活和工作下去也需要他成為英雄……但在信中貝多芬也發(fā)誓為他的藝術(shù),伴隨著痛苦生活下去,他一直遵守著這樣的誓言”。確實(shí),這份所謂的“遺囑”并非絕望中對命運(yùn)的投降,而其實(shí)是肯定生命,戰(zhàn)勝絕望的宣言。更重要的是,斯瓦福德為讀者講解了這個(gè)階段的思想如何地改變并塑造了后來的貝多芬:“這封信后來成了他一直保存在身邊的護(hù)身符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其它都是他過去愛情的紀(jì)念品,而這封信則是他生命中失去的歡樂的紀(jì)念。很可能后來他常常將信從桌子深處取出,打開,重讀,以提醒自己如何、為何解決人生問題,以及他在創(chuàng)作出自己真正的作品之前有多么接近死亡。”至于浴火重生后,貝多芬的自我身份認(rèn)同、生活重心的轉(zhuǎn)變,以及創(chuàng)作中的“新路”,斯瓦福德不僅指出了各自的必然性,還以“復(fù)調(diào)”的形式讓這幾個(gè)層面相互補(bǔ)充,融為對貝多芬創(chuàng)作、生活與時(shí)代的整體認(rèn)識(shí)——當(dāng)然,對于貝多芬的整個(gè)生涯,斯瓦福德在本書中都是這樣做的。通過詳實(shí)的資料與史實(shí),斯瓦福德還有力地說明了他個(gè)人對貝多芬“英雄時(shí)期”創(chuàng)作起點(diǎn)所提出的新看法,他認(rèn)為并不該以“海利根施塔特遺囑”當(dāng)作分水嶺,其實(shí)“英雄時(shí)期”的開始要更早一些。通過閱讀本書的這一部分,我們明白了貝多芬思想與創(chuàng)作方向的轉(zhuǎn)變并不是在那幾個(gè)生死掙扎的日子中突然誕生的,所謂的“貝多芬1802年危機(jī)”,其實(shí)時(shí)間跨度比我們通常所想的要長得多,也正因?yàn)榇耍惗喾以诟鞣矫娴霓D(zhuǎn)變才是如此必然且成熟,由此而誕生的作品才會(huì)如此杰出。而后,話題自然而然地轉(zhuǎn)向“英雄交響曲”。從音樂學(xué)的角度來看,斯瓦福德對這部作品(以及貝多芬的絕大多數(shù)主要作品)的釋讀十分成功,盡管傳記體例的作品并不允許弗洛若斯(Constantin Floros)那樣細(xì)致入微的長篇分析,但是斯瓦福德讓自己運(yùn)用了最近二三十年的學(xué)術(shù)成果,從貝多芬筆記本上的草稿出發(fā),逐步進(jìn)入貝多芬的構(gòu)思過程,作品的主要樂思,乃至全曲的整體構(gòu)架。最難能可貴的是,跟隨斯瓦福德的指引,最為適合普通的愛樂者接觸并熟悉作品,因?yàn)闀胁]有佶屈聱牙的術(shù)語堆砌,而是重建起貝多芬在創(chuàng)作中從無到有、從小及大的思路,并且指出音樂中最為獨(dú)特之處——也就是聆聽中最需注意之處。所以,從音樂分析的角度來說,本書既是最具時(shí)效性學(xué)術(shù)成果的總結(jié)與凝練,更是適合普通愛樂者,讓我們感受到:好的學(xué)術(shù)從來都是可以接近且妙趣橫生的。

海利根斯塔特鄉(xiāng)村風(fēng)景
雖然斯瓦福德將更多筆墨灌注于貝多芬最為重要的“英雄”“命運(yùn)”“拉蘇莫夫斯基四重奏”“莊嚴(yán)彌撒”“合唱”這些里程碑作品,但是他為其它作品也做了不少介紹,足以帶領(lǐng)讀者發(fā)現(xiàn)、關(guān)注并享受那一部部可能并不算非常流行的作品。在二十一世紀(jì)二十年代的今天,無論學(xué)者還是愛樂者都需要明白,“扼住命運(yùn)的咽喉”或“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雖然的確是貝多芬作品中的核心思想,但卻遠(yuǎn)不是他通過音樂想要表達(dá)的全部內(nèi)容。斯瓦福德指出,“在帶作品編號的作品中沒有練習(xí)之作”,而他也確實(shí)認(rèn)真地對待了貝多芬每一部有編號的作品。比如貝多芬所出版的第一套鋼琴奏鳴曲(作品2)中往往被忽視的第二首(A大調(diào)),斯瓦福德指出首樂章的最突出特點(diǎn)是各個(gè)樂段之間的對比,“……這些音型,以及它們活躍、燦爛地對置的傾向,成為奏鳴曲之后的主要特征。但貝多芬馬上大膽地轉(zhuǎn)向:E小調(diào)的第二主題令音樂變得緊張,好像突然出現(xiàn)矛盾,洶涌的激情——浪漫主義。因此他在A大調(diào)奏鳴曲中的敘述方式是以歡樂定期被突然的焦慮或憂郁打斷為特征的。奏鳴曲中充滿了對比。這對比在第一樂章的結(jié)尾非常突出,音樂一開始響亮而堅(jiān)定,突然沉入柔弱和模糊的終止……”相信讀過這樣的描述,即使不熟悉這部作品的讀者也會(huì)禁不住找來聽一聽,并跟隨斯瓦福德的講解來深入其內(nèi)核。隨后,斯瓦福德以這部作品為基礎(chǔ),總結(jié)出貝多芬早期作品的標(biāo)志:表現(xiàn)力、戲劇性、獨(dú)特的音響與情感世界,并且“在繪制音畫時(shí)非常精確地表現(xiàn)心理”。
斯瓦福德并沒有像大多數(shù)貝多芬傳記的作者那樣,忽略這些“次要的”作品,而是既沒有犧牲“精”,還保證了“全”,因而這部傳記能幫助我們真正貼近這個(gè)音樂史上最深厚、最多彩的靈魂,幫助我們更多地傾聽他的聲音。也許在閱讀本書之時(shí),我們可能會(huì)從一首幾乎從來無人談及的作品里,在那最偶然而又幸福的時(shí)刻,感受到他的機(jī)智風(fēng)趣、安閑恬靜或溫暖柔情,在心靈中與他獲得親密且又獨(dú)特的連接。
無論風(fēng)格為古典還是流行,體裁為爵士、搖滾、民謠、輕音樂抑或金屬,我們音樂文化的基礎(chǔ)語言都是調(diào)性和聲體系,而貝多芬的音樂則是這套體系形成與鞏固中的核心作品,所以只要是對音樂感興趣的讀者,在對貝多芬其人與其音樂作品有了更新、更精確的了解之后都會(huì)獲益匪淺。
對于普通的音樂愛好者與音樂學(xué)界來說,本書的出版都是一大幸事。由于時(shí)代的不同,我們在面對經(jīng)典作品時(shí)所提出的問題與前人是不同的,而這也就決定了我們從作品中能夠不斷發(fā)掘出新的含義、找到新的啟示,所以,對經(jīng)典的闡釋必須隨著時(shí)代和思想的變化而發(fā)展;新的研究成果更為貼近當(dāng)前的人們,同時(shí)還會(huì)有效吸取歷代的論著,拋棄與時(shí)代不符或是已經(jīng)被證偽的內(nèi)容與觀點(diǎn),做到更為成熟且全面。就音樂類圖書的翻譯與引介來說,斯瓦福德的《貝多芬傳》是國內(nèi)能看到的少數(shù)真正的新成果之一,不僅能讓讀者從一個(gè)客觀且并無先入為主之觀點(diǎn)的角度來真正認(rèn)識(shí)貝多芬,更是收納整理了最新而且極為全面的相關(guān)史料與觀點(diǎn),相信專業(yè)與非專業(yè)的讀者都能被本書激起充分的好奇心,開始扎實(shí)有力地探索并認(rèn)識(shí)音樂史上更多的偉大人物與經(jīng)典作品。同時(shí)以本書為榜樣,我希望國內(nèi)出版界在引進(jìn)音樂類圖書時(shí)能夠開始更多地關(guān)注最新的成果,而非僅僅考慮圖書的名氣(因?yàn)槊姆e累常常需要多年的時(shí)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