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凡|“未來小說”:科幻文學的歷史和形式

摘 要:科幻文學史上,“未來小說”這一概念,演變?yōu)椴煌臍v史話語和形式。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威爾斯提出的“未來的小說”,促成了科學羅曼司到科幻小說這一新型文類的關(guān)鍵性轉(zhuǎn)變。后現(xiàn)代小說與科幻小說的疊加,呈現(xiàn)主流小說與科幻小說合流的特點,并由此誕生了種種具有“未來小說”傾向的文學變革,如以巴拉德為中心的“新浪潮運動”、斯特林的“滑流小說”宣言。結(jié)合迪克的小說分析后現(xiàn)代小說與科幻小說相互滲透的特征,結(jié)合羅伯特斯·科爾斯有關(guān)“未來小說”的結(jié)構(gòu)主義批評指明“未來小說”所具有的潛力。總結(jié)“未來小說”在新世紀的定義,結(jié)合科幻未來主義、21 世紀形形色色的理論,對“未來小說”形式上的可能性進行展望,進一步揭示未來小說的未來圖景。
關(guān)鍵詞:未來小說;威爾斯;科幻未來主義;滑流小說;科幻
“未來小說”起源于何處?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答科幻小說的起源。對科幻小說起源的回答,科幻研究者通常謹慎地采用并置討論法,即列出歷史觀點,而不下定論。較常見的有三種起源說:首先是中景裁定,前推到工業(yè)革命時代,追述至哥特文學傳統(tǒng),如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這種影響最大;其次是遠景裁定,一路而上,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幻想文學傳統(tǒng);最后是近景裁定,追溯到雨果·根斯巴克的科幻小說定義。三種裁定都具有各自明確的權(quán)力話語分配。例如,追述到工業(yè)革命和哥特文學傳統(tǒng)的目的,一是為了體現(xiàn)科學性,二是提出者為了突出歐洲大陸的文學傳統(tǒng)。再往上回溯到古希臘時代,則可以將科幻文學置于更宏大悠遠的幻想文學想象傳統(tǒng)中,拓展科幻小說的研究疆域。近景裁定,雨果·根斯巴克所定義的科幻,則為美國流行科幻小說的地位發(fā)聲,彰顯新大陸新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地位。三種裁定的爭論還將持續(xù)下去。批評家蘇文認為:“文類傳統(tǒng)的合法性是在回溯中得到確立的。”[1]回顧未來小說的歷史和多種多樣的形式,才能得以在科幻文學發(fā)展史上,確立種種不同的“未來小說”所具有的不同內(nèi)涵和外延。

科幻小說之母瑪麗·雪萊(1797 -1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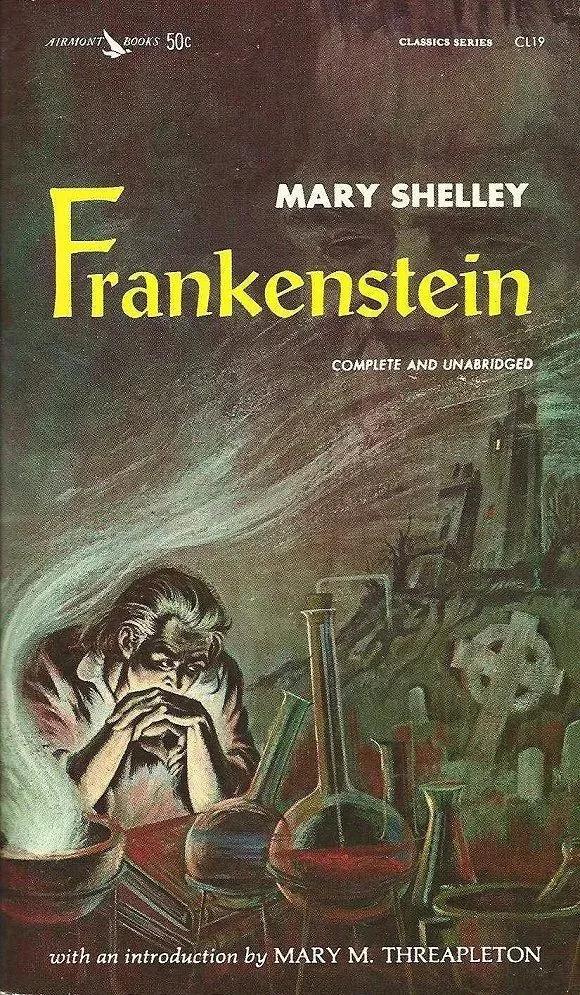
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義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1818)
一、威爾斯的“未來的小說”:從科學羅曼司到科幻小說的關(guān)鍵性轉(zhuǎn)變
未來小說肇始于作為羅曼司(romance)的科幻文學,即科學羅曼司(scientific romance)。在歐洲文學史上,存在一種鮮明的、與 19 世紀現(xiàn)實主義小說傳統(tǒng)相對立的文學形式:羅曼司。羅曼司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廣泛地存在于歐洲各國的文學傳統(tǒng)中,19 世紀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強大崛起,中世紀盛極一時的羅曼司傳統(tǒng)漸漸被遮蔽,下降到次要地位。而羅曼司,正是科幻小說的歷史淵源和史前形態(tài)。神話批評家弗萊認為,科幻小說是羅曼司的現(xiàn)代神話回歸。[2]在研究小說時,他發(fā)現(xiàn)沒有合適的詞匯來區(qū)分歷史上的小說類型,而“小說”這一概念指代混淆并縮小了敘事類型。弗萊認為,小說原本的稱呼應為“散文化虛構(gòu)”(prose fiction),這一稱謂被后起的強大名詞“小說(novel)”掩蓋,造成小說含義和外延的模糊,批評從而無以為繼。弗萊在《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1971)一書中,重新將“散文化虛構(gòu)”分為四種類型:小說(novel)、羅曼司(romance)、懺悔錄或自傳(confes-sion)、剖析體(anatomy),這四種皆為廣義的小說。狹義的小說(novel)常常與其他三種混合,并進一步產(chǎn)生不同的模式混搭,例如艾略特的早期小說,鮮明地偏向羅曼司;而后期的小說,則傾向于剖析體。弗萊進一步指出:“小說”與“羅曼司”這一概念的核心區(qū)別在于對人物塑造的觀念不同。羅曼司寫作者,并不創(chuàng)造與真實世界對應的“人物”,而在潛意識中,折射榮格所謂的集體無意識中的力比多,創(chuàng)造男女英雄的抽象人格[3]。
弗萊論點的意義在于,揭示了當代世界對“小說”這一概念的極大窄化,還原了敘事史上并行的四種傾向,小說(novel)不等于小說(fiction);更重大的意義在于,揭示出作為科幻文學先祖的羅曼司(romance),被當今強大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所遮蔽的巨大的史前樣貌。弗萊糾正了對“小說”——實際上是主流小說、特別是主流小說中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偏信與崇拜,繞開了“小說等同于 18 世紀現(xiàn)實主義小說與 20 世紀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的主流小說觀念,把斯威夫特及其之前的幻想文學作家,納入羅曼司的傳統(tǒng),從而將“羅曼司”與“小說”這一源流并駕齊驅(qū),恢復歷史上非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價值,重新界定了小說的虛構(gòu)性質(zhì)。由于科幻文學在歷史淵源上隸屬于幻想文學,弗萊對虛構(gòu)敘事的梳理、對羅曼司傳統(tǒng)的恢復,能為科幻的歷史溯源和范式定位提供理論支撐。
從羅曼司到科學羅曼司,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的時空觀念產(chǎn)生了巨變,時間上升到第一位。這一變化體現(xiàn)在,時間的觀念,作為一種權(quán)力的外化形式,發(fā)生了改變。繼古希臘羅馬人的循環(huán)時間觀,被基督教的線性時間觀取代后,再次面臨技術(shù)時代的時間觀念的挑戰(zhàn)。工業(yè)革命和科學技術(shù)的崛起,打破了教會對時間的壟斷,從宗教和皇權(quán)手中,取得了對人與自然、人與上帝的解釋權(quán)。技術(shù)主義最大的發(fā)明就是鐘表[4],鐘表象征著工業(yè)時代創(chuàng)造了一個人工的世界,它的時間體制被獨立出來,成為一個異在力量。舊的堂·吉訶德的地圖漫游模式,格列佛和魯賓遜的漂流,已不再適用于凡爾納跨越五大洲七大洋、從地球到月球、漫游太陽系的奇異的世界航程。空間上的上天入地,已不能滿足人們的漫游欲望。正如蘇文所說:“1800 年前后是科幻小說重要的分水嶺——空間失去了對陌生化地域的壟斷地位,替換世界的視野開始從空間轉(zhuǎn)向時間。”[5]
19世紀的最后十年,是科幻羅曼司的集中爆發(fā)期。據(jù)統(tǒng)計,1848-1859 年,出版了英語科幻小說23 本,1860-1869 年 23 本,1870-1879 年 91 本,1880-1889 年 215 本,而 1890-1899 年 551 本[6]。這些科幻小說有明顯的企圖,將自己的對未來的思考投入小說的形式中。承接中世紀的羅曼司傳統(tǒng),威爾斯提出了“未來的小說”(fiction about the future)概念。相較凡爾納的奇異的航程的封閉性而言,威爾斯的小說創(chuàng)作種類是擴大而開放的,他發(fā)展出成熟的科學羅曼司形式,并漸漸溢出此前的類型范式,實現(xiàn)了從科學羅曼斯到科幻小說的關(guān)鍵性轉(zhuǎn)變。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 -1946)
以威爾斯寫出《時間機器》的 1895 年而言,這一年在英語世界出現(xiàn)了 52 部科幻小說。在這些故事里,時間本體從空間化的時間中突現(xiàn)出來,也即從凡爾納的“奇異的旅行”等系列小說空間化的地圖位移,轉(zhuǎn)移到威爾的時間旅行。未來,在時間的向度上,第一次成為人類的集中向往。威爾斯指出:“科幻小說必須實現(xiàn)一種針對現(xiàn)實的幻覺,一種歷史小說的效果,一種與讀者在自欺欺人過程中的合謀。針對作家的假設(shè),作家必須在更高的維度上,擺脫現(xiàn)實世界的經(jīng)驗,發(fā)揮想象力,創(chuàng)造出最高形式的小說。”[7]
科學羅曼司這一稱呼并不能使威爾斯?jié)M意。與狄更斯以來的傳統(tǒng)有深刻的繼承關(guān)系的威爾斯,在文論里多次將自己的小說與“未來”建立關(guān)系,敏銳地發(fā)覺自己在寫作一種新形式的小說。在威爾斯的筆下,科學羅曼司傳統(tǒng)產(chǎn)生了重大的變異,那就是“未來”“科學”“烏托邦”“反烏托邦”等關(guān)鍵詞漸漸取代了傳統(tǒng)羅曼司文學的諷刺、說教和幻想游記。以前的幻想游記建立在哥白尼天文學的“新哲學”基礎(chǔ)上,已與古希臘、羅馬的奇幻想象具有顯著的不同[8],而威爾斯的科幻羅曼司,不但是一種新類型的文學運動,也是社會思想、科幻發(fā)展、工業(yè)革命在文學上的投射和反映。未來小說的第一個發(fā)展,是近代科幻小說的誕生。從文學發(fā)展史上分析,這種當時人們認為的“未來的小說”,體現(xiàn)為從羅曼司到科幻羅曼司、再到科幻小說三階段的轉(zhuǎn)變。
1895 年前后的“未來的小說”,主要分為三種類型:奇異的旅程(the extraordinary voyage)、未來的故事(the tales of future)、科學的故事(the tales of science)。
第一類“奇異的旅程”,繼承了中世紀乃至古希臘時代的羅曼司。1895 年前后,有 17 部此類作品出版,代表作有查爾斯·迪克松的《1 小時 500 英里》(Fifteen Hundred Miles An Hour,1895);古斯塔夫·波普的《火星旅程》(Journey to Mars,1894)等,人們的想象不再局限于格列佛游記式的大航海飛地,而是深入到地球中空的內(nèi)部、月球、火星和水星。“奇異的旅程”改變了以往不可為人力所左右的幻想文學的傳統(tǒng),將科學和機械工具的使用列為首要的理性探索工具和空間指南,對未來充滿確定的希望。
第二類是“未來的故事”。關(guān)于未來,凡爾納將他的故事全部設(shè)定在當下或無法逃避當下的模糊的未來,力圖展現(xiàn)科學和技術(shù)對現(xiàn)在(present)的影響力。而威爾斯的小說,既帶著基督教啟示錄和審判的預言,又受到后達爾文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的樂觀影響,悲觀的未來與樂觀的未來混合。樂觀的一面,威爾斯相信“未來”與“進步”“好的烏托邦”能產(chǎn)生疊加,但他內(nèi)心中又無法避免“惡托邦”的描寫。由于威爾斯的倡導,這類故事中,中世紀的烏托邦以科幻羅曼司的形式復活,“惡托邦”緊隨其后,先后成為世紀巨變中“未來的故事”最有力的類型,代表作有愛德華·貝拉米的《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1888),威爾斯的《沉睡者醒來》(The Sleeper Awakes,1910)。除烏托邦類型外,第二類未來的故事是“未來的戰(zhàn)爭”(future warfare),人們把“未來”當成一種正在逼近的警告。相對于小說的娛樂性和閱讀性而言,此類小說毋寧說是宣傳性的政論冊子,表達了 19 世紀末的歐洲,對即將到來的污染、人口爆炸、核戰(zhàn)爭等種種現(xiàn)代病的隱憂。第三類則是“科學的故事”,從瑪麗·雪萊的《弗朗肯斯坦》開始,即代表著科幻家形象的出現(xiàn)。科學的故事的另一種形式是發(fā)明的故事,如雨果·根斯巴克的《拉爾夫 124C 41+》(Ralph 124C 41+,1925),昭示著以“科學”為核心詞匯的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的概念深入人心,逐漸上升到舞臺的正中央。
在威爾斯的“未來的小說”體系中,威爾斯成為科學羅曼司的集大成者,也成為新文類“科幻小說”次一級文體的開拓者。他的龐大的小說類型可分為:時間旅行、外星人入侵、太空旅行、烏托邦、反烏托邦、未來的戰(zhàn)爭、宇宙巨變、科學發(fā)明等等,很多科幻小說類型第一次出現(xiàn)在科幻文類史上,或經(jīng)他錘煉、鍛造成為經(jīng)典范式。威爾斯極大地擴大了科幻羅曼司的范疇,擴充了科幻小說的題材,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融入科幻小說,極大地推進了人們的科學觀和未來觀,在多個節(jié)點上,是從科幻羅曼司到現(xiàn)代科幻小說關(guān)鍵期的轉(zhuǎn)型人物。
科幻羅曼司由此得以在威爾斯的手上,向著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轉(zhuǎn)變。正如蘇文所言:“就算科幻小說不是開始于凡爾納和威爾斯,它至少也是因為一對雙子星而開始具備了一種持續(xù)性乃至主導性。”[9]
二、未來小說與后現(xiàn)代小說的互動
20 世紀中期的未來小說,與主流小說有著復雜的互動關(guān)系。首先要界定主流小說與科幻小說的區(qū)別;并進一步論證,在此種區(qū)別下,科幻小說何以與后現(xiàn)代小說達成了某種合流或疊加。此處的主流小說主要指拋棄了 19 世紀現(xiàn)實主義的現(xiàn)代小說與后現(xiàn)代小說。
主流小說與科幻小說的區(qū)別體現(xiàn)在六大特征。第一,主體對象上,主流小說更關(guān)注人的特性、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而科幻小說更關(guān)注小說中的環(huán)境、小說中建立的世界、人與環(huán)境的交互關(guān)系。第二,寫作目的上,主流小說多揭示人物的心理世界;而科幻小說推測人類種族的潛在性、可能性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第三,世界設(shè)定上,主流小說以日常世界的生活經(jīng)驗為設(shè)定;科幻小說則以替換世界的經(jīng)驗為基本設(shè)定。第四,對作家而言,主流小說展現(xiàn)了作家經(jīng)驗世界的當下認知;科幻小說則通常發(fā)生在未來或另一星球,不能以地球的認知邏輯考察。第五,從讀者層面說,主流小說的審美,讀者與作者共享同一知識背景;而科幻小說,讀者需自我建構(gòu)相關(guān)知識背景,重新假設(shè)知識之間的聯(lián)系,從而認知文本。第六,敘事方法上,主流小說強調(diào)細節(jié)、人物性格、人物特征;而一部分科幻小說則是以人類整體作為對象的文學,從而在描述上,是宏細節(jié)而非日常心理細節(jié),是宏敘事而非日常敘事。
以主流小說的審美范式分析和歸化科幻小說,例如將科幻小說看作“真實世界的寓言式寫作”,對理解科幻小說并無任何幫助。批評家斯特林激烈地抨擊:“現(xiàn)在的問題就是,批評家們試圖減損‘科幻’,來將科幻小說歸入主流小說的分支;而這個分支,實則主流小說的作家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談論什么。”[10]
事實上,后現(xiàn)代小說與科幻小說分歧并非絕對。結(jié)構(gòu)主義批評家斯科爾斯發(fā)現(xiàn):當代的主流小說家們,例如巴斯、伯杰斯、德雷爾、戈爾丁、萊辛和品欽,在 70 年代中期,都已使用了科幻的方法和命題。[11]
斯科爾斯明確提出了“未來小說”(future fiction)的概念,并對未來小說進行了重新定位。在他的一系理論著作如《小說的本質(zhì)》(The Nature of Narrative,1966)、《寓幻家》(The Fabulators,1967)、《文學結(jié)構(gòu)主義》(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1974)、《結(jié)構(gòu)性寓幻》(Structural Fabulation,1975)等書中,詳細描述了科幻小說敘事的發(fā)生和演進。他提出了與弗萊頗為類同的重要觀念:即 18 世紀以前的小說,不在我們今天的小說觀念之內(nèi),中世紀的小說是一種寓言(fabulation,或譯寓幻),這種寓言經(jīng)過分化,隨著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興起,它們的反現(xiàn)實主義特征,被遮蔽且下降到次要地位,造成了今天我們普遍認為現(xiàn)實主義、具有摹仿論傾向的“小說”是文學中最完美的形式。斯科爾斯更進一步指出這樣幾個重要觀念:首先,在小說的誕生之初,存在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的區(qū)分,口頭文學中的“魔幻性”事件,并未表現(xiàn)出與社會的“現(xiàn)實”具有顯著的聯(lián)系[12]。其次,所謂寓幻,主要指 20 世紀以來所出現(xiàn)的,具有魔幻及后現(xiàn)代特征的反傳統(tǒng)小說創(chuàng)作,諸如巴斯和品欽這樣的作家,它們與科幻文學屬于同一譜系,科幻文學因此可以稱為“結(jié)構(gòu)性寓幻”。最為重要的是,斯科爾斯提出了一個重大觀點:未來小說并非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一種,而是經(jīng)過了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的可能的、更高的發(fā)展階段[13]。
斯科爾斯是著名的結(jié)構(gòu)主義批評家,他對“未來小說”的結(jié)構(gòu)性分析對我們今天的科幻小說敘事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弗萊并未詳細研究科幻文學,而斯科爾斯明確使用結(jié)構(gòu)主義敘事學,把科幻小說的傳統(tǒng)歸結(jié)到反現(xiàn)實主義“anti-realism”的路線,旗幟鮮明地與現(xiàn)實主義一刀兩斷;其次,在文學的敘事史上,給予未來小說很高的評價,并認為未來小說不僅是科幻小說的未來,而且是所有小說敘事的未來。最后,他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為什么一部分科幻小說具有主流小說、后現(xiàn)代文學的特征:在橫向上,科幻小說與后現(xiàn)代小說呈現(xiàn)一種交叉滲透關(guān)系;在縱向上,未來小說是比后現(xiàn)代小說更具解放力和包容性的文學形式;由此,主流小說的 20 世紀后期形態(tài)(如后現(xiàn)代主義),既生長在寓幻的歷史線路上,又成為未來小說的早期形態(tài)。
斯科爾斯顯然把未來小說當成 20 世紀 50-70 年代主流小說的彌賽亞,向他的讀者和同行們推銷“科幻小說是令人尊敬的”;科幻小說的高級形態(tài)如“未來小說”,是文學的未來。在界定過程中,他稱勒古恩為“西方世界的好女巫”,是他心目中最高等級的科幻小說。同時,他排除了很多粗糙的科幻小說,以不影響自己有關(guān)未來小說的定義。
與同情科幻小說的主流文學批評家斯科爾斯相比,科幻小說的批評家則充滿了對自身文體的不滿。從 60 年代開始,科幻小說內(nèi)部的審美發(fā)生了劇烈的轉(zhuǎn)向。美國黃金時代的科幻大師們的創(chuàng)作方法被廣遭詬病,科幻先鋒作家們要求進行探索和轉(zhuǎn)型:這種轉(zhuǎn)型包括英美新浪潮科幻(new wavescience fiction)運動、賽博朋克小說運動(cyberpunk)、滑流小說(slipstream)等概念紛紛提出。創(chuàng)作上,體現(xiàn)為巴拉德和菲利普·迪克等代表性的先鋒作家出現(xiàn);批評上,體現(xiàn)為威廉·吉布森的賽博朋克小說運動和斯特林的滑流小說宣言。
與同時代的后現(xiàn)代小說作家相比,巴拉德與迪克比后現(xiàn)代小說家更早地書寫了后現(xiàn)代科幻小說。以迪克為例,他的小說呈現(xiàn)顯著的后現(xiàn)代小說和元小說(meta-fiction)特點。例如,在科幻小說《高城堡里的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1962)中,作者營造了一個日本和德國成為戰(zhàn)勝國的二戰(zhàn)后替換世界。在替換世界中,有位高城堡里的人,正在撰寫一部科幻小說——而在這部名為《蝗蟲成災》(The Grasshopper Lies Heavy)的科幻小說里,又描述了另一個替換世界:二戰(zhàn)后的德國和日本成為了戰(zhàn)敗國。這種荒誕和諷刺,以及對敘事的敘事,鮮明地體現(xiàn)了元小說的特征。
小說中有段對于“什么是科幻小說”的對話,尤為鮮明地體現(xiàn)了元小說(元敘述)的“自我意識”特征。
“哦,不,”貝蒂反駁道,“這里面沒有科學。科幻小說寫的是未來,特別是科學的發(fā)展已遠遠超過現(xiàn)在的未來。這本書與這兩個前提都不符。”
“可是”,保羅說,“這本書寫到了可供替代的現(xiàn)在。有很多著名的科幻小說都是這一類的。”[14]
此段對話,是對書中之書《蝗蟲成災》的小說性質(zhì)的回答——它究竟是不是一部科幻小說。也是迪克對自我科幻小說敘事的清晰認識,他認為替換世界(替換現(xiàn)在或過去),比“未來”和“科學”這兩個特征更為重要。此外,在迪克創(chuàng)作的絕大多數(shù)小說中,敘事焦點的不對稱性和多變性,導致了敘事文本權(quán)力等級的分化,也體現(xiàn)了后現(xiàn)代小說解構(gòu)文本中心主義的特征。
從斯科爾斯的批評、迪克的小說創(chuàng)作可以看出,先鋒的科幻小說已兼容主流小說與類型文學的雙重特征,而主流小說也在借鑒科幻小說的遠離現(xiàn)實世界的設(shè)定。那么,主流小說與科幻小說何以形成這種相互滲透?
從歷史形式上看,在長期的科幻小說發(fā)展史上,體現(xiàn)為主流小說與通俗文學的相互斗爭和調(diào)整。科幻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從嚴肅文學(英國科幻傳統(tǒng))轉(zhuǎn)向了通俗文學(美國科幻傳統(tǒng)),兩者相互借鑒又相互抵抗。新浪潮既是一場嚴肅文學運動,它直接的革命對向是美國的黃金時代科幻,試圖重新恢復威爾斯以來的精英主義傳統(tǒng)。這種嚴肅文學傳統(tǒng)也向美國滲透,影響了美國的新浪潮寫作,迪克就被很多批評家劃為美國的新浪潮作家。80 年代賽博朋克是對新浪潮的再次反撥,試圖抵御主流小說對科幻小說的入侵,重新恢復大眾傳統(tǒng)。然而當賽博朋克運動發(fā)展到后期,滑流科幻的提出、威廉·吉布森的教父式轉(zhuǎn)型,表現(xiàn)為賽博朋克作家不甘于屈身電腦牛仔的定位。事實上,賽博朋克運動、滑流小說,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主流,乃至詹姆遜等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無法視而不見,紛紛將其作為批評的重要資源。
在主流小說界,與“滑流”相呼應,幾乎同一時間涌現(xiàn)出與“寓幻”“元小說”等具有鮮明科幻元素的后現(xiàn)代小說提法。作家如萊辛、馮內(nèi)古特、品欽、巴斯、石黑一雄等,都廣泛地采用了科幻小說的創(chuàng)作方法。無論他們被界定為哪種類型,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利用未來、新奇性、想象力為自己的小說增強形式的陌生化。
后現(xiàn)代小說與科幻小說的疊加,直接導致了滑流小說的誕生,這是一種新的未來小說的動向。1989 年,科幻作家、賽博朋克運動的旗手斯特林,敏銳地感覺到賽博朋克理論的局限:賽博朋克將自身置于科幻小說的內(nèi)部傳統(tǒng)中,無法向外擴展。斯特林由此提出了新概念“滑流小說”。滑流科幻是指那些打破了主流小說與科幻界線的嶄新類型。斯特林認為,科幻小說的技術(shù),不再能夠反映“連續(xù)的社會視域”,那些非科幻作者,反能非凡地寫出更富有想象力、更陌生化、更反現(xiàn)實主義、更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作品。在斯特林的界定中,滑流小說的代表作家有品欽、馮內(nèi)古特、托馬斯·迪什等數(shù)十人,斯特林列了一個長長的作家名單和書單,但他的這一理論并未得到廣泛采納。遲至 2006 年,第一部滑流小說集才得以出版,標題為:《感覺非常奇怪:滑流小說選集》[15]。滑流科幻小說的標簽充滿了反現(xiàn)實主義的特征:“魔幻現(xiàn)實主義”“反現(xiàn)實主義”“后現(xiàn)代”“實驗的”“超現(xiàn)實的”以及“寓幻”等。
三、未來小說作為一種新的科幻寫作資源
當代的“未來小說”,與威爾斯時代的“未來的小說”、斯科爾斯的“未來小說”、斯特林的“滑流小說”等種種歷史上的先鋒科幻小說應具有一種承續(xù)關(guān)系,保留某些共有的歷史形式特征。同時,當代的“未來小說”作為一種科幻小說新的敘事方法和寫作資源,具有面向未來的前沿性和擴展性。
什么是當代的未來小說?有學者下定義,未來小說是“從未來倒推敘述成為已然的未來,而不是純?nèi)坏念A言”的小說[16]。這是時間軸上,面向過去的定義:未來小說特指晚清、民國的社會幻想小說。
筆者更傾向于將時間軸聚焦于未來和科幻的可能性,因此在這里下一簡單定義:未來小說是科幻小說的分支,它從屬于科幻小說,但并非所有的科幻小說都是未來小說。未來小說是以科幻未來主義為明確創(chuàng)作方針,不斷追求新的科幻文學形式與審美的突破,不斷追求科幻文學中新的敘事方法展開為目標的、面向未來的、先鋒科幻文學。
在世界范圍內(nèi),各種科幻未來主義成為新的文學思潮,它們與“未來小說”這一概念緊密相關(guān):
意大利科幻作家弗朗西斯科·沃爾索提出了意大利的“未來小說”(future fiction)出版計劃;當代歐美科幻中有所謂“非洲未來主義”(afrofuturism);中國也在近幾年提出了“科幻未來主義的狀態(tài)或宣言”[17]。我們可以將種種不同的科幻動向,總結(jié)為“科幻未來主義”。各種科幻未來主義的提出,有其必然性:它是作為恰逢其時的反對話語而存在的“未來小說”的文學主張;它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對未來具有的深刻心理沖動;它描繪文學版圖中銳意創(chuàng)建的新的替換世界。
首先,未來小說是作為恰逢其時的反對話語而存在的文學主張。這種主張主要體現(xiàn)在:科幻小說內(nèi)部的形式?jīng)_突可以為未來小說的形式創(chuàng)新打基礎(chǔ),未來小說是對社會和約定文化的反對武器。批評家羅杰·羅克赫斯特指出:“一種類型文學能死亡多少次?這種死刑宣判到底能被傳遞多少代?死亡的執(zhí)行儀式又將重復多少回?……科幻文學正在死去,但科幻文學一直在死去,科幻文學的死亡從它形成之始就在一直死去。”[18]科幻文學歷史上所積累的敘事窠臼,正是阻礙科幻文學代謝、使之不能成為科幻的阻力。科幻文學的階段性死亡的內(nèi)驅(qū)力,體現(xiàn)了文類強烈的創(chuàng)造性特點。科幻小說經(jīng)常死亡,因死亡而確立其一部分屬性,另一部屬性則暗含在未來的可能性中。未來小說正是這種恰逢其時的、對敘事慣性的反對話語。
其次,未來小說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對未來具有的深刻心理沖動。現(xiàn)代人的時空觀念,打破了古人循環(huán)的時間觀和靜態(tài)的空間觀,這種時空觀的轉(zhuǎn)變,帶來了經(jīng)驗世界的重新認識。現(xiàn)代的未來意識,不但體現(xiàn)為對未至時間的預測、預期和預演,也體現(xiàn)為對空間和環(huán)境的改造的愿望。形形色色以“未來”命名的 20 世紀的斷裂運動,都是建立在時空觀念改變之上的革命性的心理沖動。在某種意義上,整個科幻文學的發(fā)生,也是未來主義運動的產(chǎn)物。人們對未來的心理沖動,體現(xiàn)為種種形式的先鋒運動,其先鋒運動的目標,是革除陳舊的形式、內(nèi)容、主題,對自我及環(huán)境展開嶄新期待。
最后,未來小說描繪文學版圖中銳意創(chuàng)建的新的替換世界。科幻小說的敘事,先天具有假設(shè)性、實驗性特征。批評家拉斯指出:“科幻文學是關(guān)于‘假如是’(what if)的文學,所有這一領(lǐng)域提出的科幻小說定義,都暗含著‘假如是’和對假定性的嚴肅解釋。科幻小說所展現(xiàn)的事物,并非性格化或日常化,而是‘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必須具備邏輯的、嚴肅的、連續(xù)的解釋。”[19]在很多科幻小說中,我們都能看到暗含可能性的思想實驗,這種實驗性甚至超越了文學,進入了烏托邦問題的政治范疇。
在敘事前景上,未來小說的先鋒性,使其可整合其他敘事策略或批評理論。這些敘事策略和批評理論,在后理論時代,在 21 世紀,具有特別的敘事學價值,例如:賽博批評(cybercriticism),鬼怪敘事(spectral narrative),(反)物敘事(material or amaterial narrative),元小說,滑流小說,非自然敘事(unnatural narrative),后人類主義(post-modernism),負人類紀(neganthropocence),種植紀(planta-tionocence),資本紀(capitalocence)、后殖民敘事,動物轉(zhuǎn)向等等[20]。
這些敘事分為兩類:一類是科幻小說已在使用的敘事手段,如女性主義敘事產(chǎn)生了大量的科幻文學作品。再如種植紀敘事中,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洪水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2009)是其突出的代表;另一類則是 21 世紀,在結(jié)構(gòu)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之上涌現(xiàn)的新的、某種程度上未經(jīng)大量作品應用的新的文化批評和敘事理論。很多文化批評雖非直接的敘事理論,但對于創(chuàng)作、具有重大的借鑒價值。這些批評理論或敘事策略之間,也是相互滲透的,例如后人類敘事,帶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法國解構(gòu)主義色彩。還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新批評,都能帶來敘事的直接變更。事實上,每一種敘事理論與未來小說的關(guān)系,都值得深入探尋,它們代表著與歷史性表述的決裂,由此成為未來主義和未來小說的潛在資源。
例如,后人類主義與賽博朋克的結(jié)合。在某種程度上,賽博格主義和后人類主義,都圍繞“身體敘事”而展開。只是,后人類相較賽博格,并不執(zhí)著于義體,對“身體”的未來想象,推測得更遠。從賽博格到后人類的概念的發(fā)展,必將呼喚新的科幻文學形式來適應對身體的超越。賽博格代表著人和機器的共生,賽博格要求自己的文化觀念與技術(shù)建構(gòu),去人類身體中心化,但它并不完全反對身體的機器載體和義肢延伸。后人類則跨過賽博格的人機共存關(guān)系,拋棄“身體政治”為核心的建構(gòu),重建“人”的內(nèi)涵和外延,直接進入“虛擬身體”范疇。在后人類時代,信息成為“身體”本身,信息即政治、倫理、道德、法律,信息以身體的形式,彌漫在人類社會的一切領(lǐng)域中。信息就是人類社會。正因為不贊同賽博格的“身體”概念,存在著對未來身體的認知不同,后人類由此提出“虛擬身體”。當身體被拋棄后,意識形態(tài)上傳到賽博空間。因為虛擬,自然也就不承擔物質(zhì)身體此前的一切政治負累。
科幻作家對“虛擬身體”有三種處理方式:一是把意識處理成污染。即上傳的意識污染整個賽博空間,成為元和一,由此取消二元對抗。另一種,保留了上傳的意識的獨立性,在賽博空間中以“獨立的個體”的意識遨游,比如電視劇《黑鏡》(Black Mirror)、電影《黑客帝國》(Matrix)中的意識體,都是這樣的分離體。第三種:意識的不同模塊,比如計算模塊,心理模塊,情感模塊……為了追求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更符人類社會的經(jīng)濟化原則(何以區(qū)別賽博空間的沒有生命的數(shù)據(jù)流),進行集成和進化:計算模塊互相尋找,構(gòu)成超級計算模塊。心理模塊集成,構(gòu)成超級心理模塊……這樣的模塊化人類社會,推演開去,又是另一種人類景觀。還有一種敘事處理:如喬內(nèi)森·瓊斯的科幻小說《鳳凰咖啡屋》(Phoenix Café,1998),作者對經(jīng)典的神經(jīng)漫游者的方式加以摒棄,反其道行之。她在小說中把以分子形式加載的虛擬世界制作成眼藥水,滴入眼中。由此,人類的心靈并未進入虛擬世界,而是虛擬世界進入心靈中。由此可見,對后人類主義推測和想象的程度、范圍,可以產(chǎn)生萬象紛呈的個人化的替換世界,對敘事和批評理論的探索和寫作實踐,可在很大程度上更新小說的創(chuàng)作方法。
四、結(jié)語
隨著科技的爆炸式增長、未來對現(xiàn)實的日益入侵,科幻小說面臨著種種危機,舊的敘事方法、題材和素材,全面落后真實世界的種種狀況。“未來小說”是在新的人類視野和科技發(fā)展水平下,調(diào)整視線和方向,展開的全新的科幻未來主義想象,諸如非洲未來主義、意大利的未來小說等,已成為世界范圍內(nèi)新興的科幻文學思潮,借助“未來小說”這一載體,構(gòu)成了新的文學潮流、心理期待和創(chuàng)新的替換世界。對“未來小說”歷史上的話語和形式進行分析、界定“未來小說”的內(nèi)涵和外延、展望新的敘事理論與“未來小說”結(jié)合的可能性,有助于重新認識科幻小說的特征和創(chuàng)新潛力,為非但是科幻小說而且是整個小說的敘事,繪制未來圖景。
注釋:
[1] Darko Suvin. 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Kent: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p.75.
[2]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64.
[3]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302-326.
[4]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作者曼福德說:“工業(yè)時代的關(guān)鍵機械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鐘表。”
[5]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 89.
[6]Edwards James. Science Fic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30.
[7]Patrick Parrinder and Robert M. Philmus. eds.,H. G. Wells’s Literary Criticism,Sussex:The Harvester Press,1980,p.249.
[8][美]羅伯特?斯科爾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阿瑟 B. 艾文斯等:《科幻文學的批評與建構(gòu)》,王逢振、蘇湛、李廣益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 年,第 168 頁。
[9]Darko Suvin. 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Kent: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p.75.
[10]Bruce Sterling.“Interviewed by Andy Robertson and David Pringle.”Interzone,15.1(1986):12.
[11]Robert Scholes. Structural Fabulation:An essay on the Fiction of the Future.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Dame Press,1975,p. 3,p. 18.
[12]Robert Scholes. James Phelan. Robert Kellogg.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 3-16.
[13]Robert Scholes. Structural Fabulation:An essay on the Fiction of the Future.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Dame Press,1975,pp.38-42.
[14]Philp K. Dick.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New York:Putnam,1962,p.103.
[15]James Patrick Kelly and John Kessel. Felling Very Strange:The Slipstream Anthology. 2006,online available.Http:< http://www.sfsite.com/10a/fs233htm>.
[16]趙毅衡:《二十世紀中國的未來小說》,《二十一世紀》1999 年第 12 期。
[17]2014 年 5 月 11 日,批評家吳巖在北京一次會議上發(fā)表演講“科幻未來主義的狀態(tài)或宣言”,這是中國科幻界第一次正式提出“東亞未來主義”。不足 500 字的“東亞來主義”包括五條綱領(lǐng):其一,為未來寫作;其二,感受大于推理;其三,思想和境界的無邊性;其四,沒有喚起的作品是可恥的;其五,創(chuàng)造力是最終指歸 。參見吳巖:《科幻未來主義的狀態(tài)或宣言》,網(wǎng)址: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84a22af0102efnc.html?from=groupmessage,發(fā)表日期:2014 年 5 月 10 日。
[18]Roger Luckhurst. "The Many Deaths of Science Fiction." in Latham R.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An Anthology ofEssential Writings. 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7,pp. 59-61.
[19]Joanna Russ,"The Image of Women in Science Fiction."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 Ed. Rob Latham. New York,NY:Bloomsbury Academic,2017,pp.200-202.
[20]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UK: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pp.3-16.
作者簡介
張凡,科幻文學博士、創(chuàng)意寫作碩士。在重慶信息學院釣魚城科幻中心擔任主任,運營的公益科幻項目有百萬獎金的釣魚城科幻大獎、與意大利科幻作家Francesco Verso、南方科技大學吳巖教授、作家阿缺聯(lián)合發(fā)起的“未來小說工坊”,運營有“科幻電影大師課”項目。現(xiàn)為中國科普作家協(xié)會科幻專委會委員,重慶科普作家協(xié)會科幻專委會副主任,中國科普研究所中國科幻研究中心特聘專家,多屆星云獎評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