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我是一部相機(jī)”
一九五四年,我曾與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在米高梅電影公司一起吃午飯。他告訴我,他剛給女演員拉娜·特納寫了一部電影劇本。主題是什么?黛安·德·波迪耶[1] 。我大笑起來(lái),他搖了搖頭。“拉娜能行的。”他淡淡地說(shuō)道。后來(lái)我們?cè)谄瑘?chǎng)里溜達(dá),我告訴他我想在電影公司找一份編劇工作,因?yàn)槲覜](méi)法再靠寫小說(shuō)的版稅過(guò)活了(而且也不想去教書(shū)),克里斯托弗用那雙明亮的、甚至有些嚴(yán)厲的藍(lán)眼睛向我投來(lái)憂郁的目光。“別,”他非常激動(dòng)地說(shuō)道,倚在一輛火車旁,葛麗泰·嘉寶飾演的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躍就死在這輛火車的輪下,“別像我一樣當(dāng)個(gè)粗制濫造的職業(yè)寫手。”但我倆都知道他只是假裝謙虛。克里斯托弗總是能按照要求給電影寫劇本,同時(shí)用自己的方式繼續(xù)自己的創(chuàng)作。那些被好萊塢毀掉的人從來(lái)不值得拯救。伊舍伍德不僅成功地為攝影機(jī)寫了劇本,而且眾所周知,在他真正的文學(xué)作品中,他本人就是一部照相機(jī)。
“我是一部相機(jī)。”小說(shuō)《別了,柏林》(一九三九)就以這幾個(gè)字開(kāi)篇,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因此出名。正因?yàn)檫@幾個(gè)字,他被視為一位自然主義作家(有時(shí)被一筆帶過(guò)),一個(gè)只記錄表象的人,一位不成功的電影導(dǎo)演。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伊舍伍德在記錄光影和進(jìn)入他視野范圍內(nèi)的獅子時(shí)往往表現(xiàn)得太過(guò)公正無(wú)私,但他也總會(huì)帶來(lái)驚喜;在看似平淡無(wú)奇的敘事中,作者會(huì)突然為正在閱讀的讀者拍攝一張寶麗來(lái)照片,他通過(guò)巧妙地使用第二人稱代詞達(dá)到這種驚人的效果。相對(duì)于伊舍伍德的作品,你永遠(yuǎn)不知道自己處在什么位置。
在半個(gè)世紀(jì)的時(shí)間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多少處在英美文學(xué)界的中心,他受到了朋友、熟人和讀書(shū)會(huì)承辦者的密切關(guān)注。隨著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回憶錄的不斷積累,伊舍伍德始終作為主要人物出現(xiàn),如果說(shuō)某些對(duì)他的描述與他本人不相稱,那是因?yàn)樗⒉皇且粋€(gè)容易描繪的角色。同時(shí),他還優(yōu)美地把自己投射在了《柏林故事》《獅子和影子》《南下訪問(wèn)》和《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類》中,任何一位想再次勾勒這頭獅子之影的人都難以無(wú)視這些作品。畢竟,再?zèng)]有比鏡子更難以描繪的東西了。
對(duì)伊舍伍德的最佳刻畫出現(xiàn)在斯蒂芬·斯彭德的自傳《世界中的世界》(一九五一)里。和伊舍伍德一樣,斯彭德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剛成年的中上層階級(jí)的一員。對(duì)于少數(shù)能進(jìn)入合適的中小學(xué)和大學(xué)的幸運(yùn)兒來(lái)說(shuō),戰(zhàn)后的英國(guó)仍然是一個(gè)自足的小社會(huì),每個(gè)人都認(rèn)識(shí)其他人。事實(shí)上,英國(guó)社會(huì)只是學(xué)校的一種延伸。但就在伊舍伍德和斯彭德這代人登上舞臺(tái)之前,校園世界里發(fā)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上一代畢業(yè)生中較優(yōu)秀的那一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喪生,而伊舍伍德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長(zhǎng)長(zhǎng)的陰影籠罩在新一代年輕人身上,那是他們死去的父親和兄長(zhǎng),也是死去的或者垂死的態(tài)度觀念。空氣中彌漫著反叛的氣氛。新的事物即將出現(xiàn)。
每個(gè)時(shí)代都有一些人物,他們?cè)谛r(shí)候就已經(jīng)顯露出未來(lái)的模樣,他們就是萌芽中的明星。人們想要結(jié)識(shí)他們、模仿他們、摧毀他們。伊舍伍德正是這樣一位人物,而斯蒂芬·斯彭德在結(jié)識(shí)他之前就已對(duì)他著迷。
十九歲的斯彭德是牛津的本科生;另一位本科生是二十一歲的威·休·奧登。而伊舍伍德本人(比奧登大三屆)已經(jīng)離開(kāi)學(xué)校進(jìn)入社會(huì)了;他故意考砸了一次筆試,使自己被劍橋開(kāi)除。他有意識(shí)地從安全舒適的大學(xué)世界中掙脫出來(lái),聰明謹(jǐn)慎的奧登十分尊敬他。斯彭德寫道:“在奧登看來(lái),[伊舍伍德]對(duì)任何事情都沒(méi)有任何意見(jiàn)。他只是對(duì)人感興趣。他既不喜歡他們,也不討厭他們,對(duì)他們也沒(méi)有贊成與否的判斷。他只是把他們視為自己的寫作素材。同時(shí),他也是奧登絕對(duì)信任的批評(píng)家。如果伊舍伍德不喜歡一首詩(shī),奧登會(huì)毫無(wú)異議地把詩(shī)毀了。”
奧登也會(huì)折磨年輕的斯彭德,“奧登不給我結(jié)識(shí)伊舍伍德的機(jī)會(huì)。”盡管寫于二十年后,斯彭德仍忍不住補(bǔ)充道,“當(dāng)時(shí)伊舍伍德并不出名。他出版了一部小說(shuō)《全是密謀家》,從出版商手中掙到了三十英鎊的預(yù)付款,書(shū)并沒(méi)有得到很好的評(píng)價(jià)。”但正如斯彭德所承認(rèn)的那樣,伊舍伍德已經(jīng)是一位傳奇人物了,世俗的成功與否和傳奇無(wú)關(guān)。最終,奧登把他們介紹給了彼此。斯彭德并不失望:
僅僅通過(guò)描述自己的生活和他對(duì)這些事情的態(tài)度,他就簡(jiǎn)化了所有困擾我的問(wèn)題……伊舍伍德有一種特別的性格,他既迷人又惹人討厭,既親切又刻薄……他的信念里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他談到自己被治愈、被拯救的時(shí)候,語(yǔ)氣之激烈不亞于任何一位救世軍成員。
在伊舍伍德最早的回憶錄《獅子和影子》(一九三八)中,我們看到了伊舍伍德對(duì)斯彭德的第一印象,那是一種反打鏡頭(斯彭德寫《世界中的世界》時(shí)已經(jīng)知道這些了):“[斯彭德]朝我們沖了進(jìn)來(lái),臉漲得通紅,大聲傻笑著,結(jié)果被地毯邊緣絆了一跤——一個(gè)身材極高、步履拖沓的十九歲男孩,一張罌粟深紅色的大臉,一頭亂蓬蓬的鬈發(fā),一雙風(fēng)信子般的藍(lán)眼睛。”攝影機(jī)轉(zhuǎn)動(dòng),捕捉整個(gè)場(chǎng)景。“剎那間,無(wú)須介紹,我們就放聲大笑,高談闊論起來(lái)……他生活在一個(gè)自創(chuàng)的、引人入勝的戲劇世界里,每個(gè)新認(rèn)識(shí)的人都立即被征召去扮演一個(gè)角色。[斯彭德]照亮了你,”(第二人稱現(xiàn)在開(kāi)始占上風(fēng)了,電影的畫外音開(kāi)始從聽(tīng)覺(jué)上引誘觀眾)“就像一位表現(xiàn)主義的制片人,使用最粗糙和最古怪的聚光燈:你變了形,變得浮夸、陰險(xiǎn)、荒唐得如此精彩或是美得令人難以置信,這取決于他對(duì)你的角色武斷的預(yù)先安排。”你,聚光燈,制片人……
在《回音廊》一書(shū)中,出版人、評(píng)論家約翰·萊曼描述了自己一九三〇年第一次與斯彭德見(jiàn)面的場(chǎng)景,說(shuō)他“談了很多關(guān)于奧登的事情,奧登和他持有許多相同的觀點(diǎn)(實(shí)際上是奧登啟發(fā)了他)。還談到了一位年輕的小說(shuō)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他告訴我此人定居在柏林,生活于赤貧之中,是一位反抗我們所在的英國(guó)的叛逆者,比他更厲害”……萊曼后來(lái)去了霍加斯出版社,為倫納德和弗吉尼亞·伍爾夫工作,他促使伍爾夫夫婦出版了伊舍伍德的第二部小說(shuō)《紀(jì)念碑》。
萊曼注意到新一代小說(shuō)家伊舍伍德:
比我個(gè)子矮很多,然而他擁有支配性的力量,智力或想象力出眾的小個(gè)子往往都有這種力量。我個(gè)人一直很喜歡這樣一種幻想:構(gòu)成我們文明存在基石的最殘酷的戰(zhàn)爭(zhēng)……是高個(gè)子與矮個(gè)子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
即便如此,“不被他吸引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我們第一次見(jiàn)面后的幾個(gè)月里……我們的關(guān)系仍然相當(dāng)正式:也許是因?yàn)楫?dāng)他的笑容消失時(shí),空氣中似乎彌漫著一種驚恐的氣氛。他仿佛流露出疑慮,懷疑自己最終還是與‘?dāng)橙恕骱衔哿恕!當(dāng)橙恕@個(gè)詞語(yǔ)中透出一股純粹的仇恨,它涵蓋了使他主動(dòng)隔絕于英國(guó)生活的一切原因”。

電影《單身男子》海報(bào)
《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類》講述了伊舍伍德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的生活。其敘述(基于日記,整體上以第三人稱寫成)銜接了《獅子和影子》的結(jié)尾“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二十四歲的克里斯托弗離開(kāi)英國(guó),生平第一次去柏林”。故事結(jié)束于十年之后,伊舍伍德移民至美國(guó)。伊舍伍德說(shuō)《獅子和影子》里寫了他“十七到二十四歲的生活。不過(guò)那書(shū)并不真是自傳性質(zhì)的。作者隱瞞了關(guān)于自己的重要事實(shí)……給角色起了虛構(gòu)的名字”。但是“現(xiàn)在我要寫的這本書(shū),將會(huì)盡量寫得坦率、真實(shí),尤其是關(guān)于我個(gè)人的內(nèi)容”。伊舍伍德的意思是他會(huì)在性生活方面坦誠(chéng);而且他確實(shí)做到了。他也是最稀有的那種人——客觀的自戀者;他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并毫不猶豫地為我們記錄下鏡子里那張臉?biāo)e累的線條以及給人格增添瑕疵的古怪影子。
我接連讀了這兩本回憶錄,發(fā)現(xiàn)在半個(gè)世紀(jì)的跨度里伊舍伍德幾乎沒(méi)什么變化,這多么奇怪。他的行文風(fēng)格從頭至尾都是一致的。從第一人稱到第三人稱的轉(zhuǎn)變并沒(méi)有影響他看待事情的方式,當(dāng)然,正是這種感知具體世界的方式,才使伊舍伍德與眾不同。他特別擅長(zhǎng)通過(guò)精心的措辭來(lái)描述外表,以暗示出人物的心理特質(zhì)。《獅子和影子》里有這樣一段:
[查莫斯]蓄了小胡子,看上去和我心目中蒙馬特的年輕詩(shī)人一模一樣,比法國(guó)人還要法國(guó)人。現(xiàn)在他看見(jiàn)了我們,朝我微微揮手打招呼,這是他的典型動(dòng)作,猶豫、羞怯、半諷刺的樣子,像是在戲仿自己。查莫斯習(xí)慣性地用零零碎碎的手勢(shì)、做了一半又放棄的動(dòng)作和說(shuō)出口的半句話來(lái)表達(dá)自己……
然后這雙銳利的眼睛轉(zhuǎn)向了敘事者自己:
走下通往餐廳的樓梯,我不再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而是一個(gè)撒旦般高傲、冷酷、不可理喻的惡魔;一位知曉一切、寬恕一切的人類救世主;一位茶幾上的福音傳道-殉難者,即使面對(duì)客廳里最殘酷的折磨,也只會(huì)禮貌地遞上抹了黃油的司康餅。
這位電影導(dǎo)演在拍攝場(chǎng)景時(shí),總會(huì)在布景的某處放上一面鏡子,這樣鏡子就會(huì)記錄下他在拍攝過(guò)程中的表現(xiàn)。
一九三八年《獅子和影子》出版時(shí),伊舍伍德三十四歲。此時(shí)他已經(jīng)出版了三部小說(shuō):《全是密謀家》《紀(jì)念碑》和《諾里斯先生換火車》。他還與奧登合寫了戲劇《狗皮人》和《攀登F6峰》。最重要的是,他筆下最優(yōu)秀的人物終于在《諾里斯先生換火車》中初次登場(chǎng);伊舍伍德毫不費(fèi)力地塑造了“伊舍伍德”這個(gè)人物。柏林故事中的“伊舍伍德”是一位多少有些乏味卻又頗為神秘的敘事者。他仔細(xì)地觀察生活,可是對(duì)任何事情都不太投入。這原本可能是敘事者的局限性,作者卻神奇地將之變成了一種美德。
斯彭德在描述柏林時(shí)期的伊舍伍德時(shí),說(shuō)他偶爾“抑郁、沉默或暴躁。有時(shí),他會(huì)和薩莉·鮑爾斯或諾里斯先生同坐在一個(gè)房間里,一言不發(fā),仿佛拒絕令他筆下的人物活過(guò)來(lái)”。但他們正是屬于伊舍伍德的角色。他的生活中“環(huán)繞著筆下人物的原型,就像一個(gè)糟糕畫家給某位作家畫的肖像,畫面中作家坐在椅子里沉思,而他小說(shuō)中的人物圍繞著他,頂著一團(tuán)用清漆繪制的臟兮兮的發(fā)光云朵”……伊舍伍德不僅拒絕了熟悉而舒適的劍橋,拒絕了倫敦的文學(xué)生活,他還拒絕了自覺(jué)的唯美主義。他選擇在柏林過(guò)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生活。斯彭德告訴我們:“他相當(dāng)貧窮,幾乎不被認(rèn)可。他的小說(shuō)《全是密謀家》被削價(jià)出售。”斯彭德再次提到了這一點(diǎn)。即便如此,斯彭德意識(shí)到伊舍伍德——
不僅僅是一個(gè)經(jīng)歷了反抗父母、反抗傳統(tǒng)道德、反抗正統(tǒng)宗教等階段的年輕叛逆者……他站在創(chuàng)造藝術(shù)作品的力量這一邊,甚至超過(guò)了他對(duì)藝術(shù)本身的興趣……他憎惡教育機(jī)構(gòu),甚至憎惡過(guò)去某些藝術(shù)作品的聲譽(yù),其實(shí)是憎惡它們阻擋在人與人之間,使人們無(wú)法直接而公正地對(duì)待彼此。
在《獅子和影子》中,伊舍伍德寫到了學(xué)校、友情,寫到了他想成為……成為“伊舍伍德”,一個(gè)尚未完全成形的角色。奧登很晚才在書(shū)中登場(chǎng),盡管他很早就出現(xiàn)在了伊舍伍德的生活中:他倆讀預(yù)科學(xué)校時(shí)就在一起了。奧登比伊舍伍德年輕,他想“成為一名采礦工程師……我對(duì)他的主要印象是頑皮、傲慢,他會(huì)因?yàn)橹酪恍a臟刺激的秘密而得意地笑,惹人干著急”。奧登已經(jīng)知道了性的奧秘,而其他人還不了解。
七年之后,奧登和伊舍伍德才再次相逢。“一九二五年的圣誕節(jié)前夕,一位共同的熟人帶他來(lái)喝茶。我發(fā)現(xiàn)他幾乎沒(méi)什么變化。”奧登“告訴我他如今在寫詩(shī):他在宣布這個(gè)消息時(shí)故意顯得十分隨便。我非常驚訝,甚至有些不安”。但隨后不可避免地,這個(gè)時(shí)代的詩(shī)人與小說(shuō)家結(jié)成了同盟。詩(shī)人給小說(shuō)家?guī)?lái)了更深的驚喜。奧登“對(duì)性的態(tài)度簡(jiǎn)單明了,毫不壓抑,令我十分震驚。他并不是什么唐璜,不會(huì)四處尋歡作樂(lè)。但對(duì)于能得到的一切,他都坦然接受,而且興致高昂,就如同他坐下用餐時(shí)展現(xiàn)出的好胃口一樣”。
藝術(shù)與性,這兩個(gè)主題在伊舍伍德的回憶錄中互相交織,但在《獅子和影子》里,我們并不知道他所謂的性到底是什么樣的,沉默的三十年代禁止人們坦率地談?wù)撍T凇犊死锼雇泻退耐悺防铮辽嵛榈绿钛a(bǔ)了這一空白;他把性和愛(ài)都講得相當(dāng)清楚。這兩位引領(lǐng)時(shí)代的詩(shī)人和小說(shuō)家對(duì)男孩們懷有的不只是欲望,還有一些證據(jù)說(shuō)明他們的行為呼應(yīng)了馬洛[2]那句偉大的臺(tái)詞:我發(fā)現(xiàn)不喜歡煙草和男孩的人都是傻瓜。
“現(xiàn)在我要寫的這本書(shū),將會(huì)盡量寫得坦率、真實(shí),尤其是關(guān)于我個(gè)人的內(nèi)容。”然后作者切換到第三人稱:“中學(xué)時(shí),克里斯托弗曾愛(ài)上許多男孩,對(duì)他們充滿浪漫的渴望。上大學(xué)時(shí),他終于成功和一個(gè)男孩上了床。這完全要?dú)w功于對(duì)方的主動(dòng)。當(dāng)克里斯托弗感到害怕,想就此打住時(shí),那個(gè)男孩鎖上了門,堅(jiān)定地坐到克里斯托弗的大腿上。”對(duì)于一個(gè)比克里斯托弗小二十二歲的美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那個(gè)時(shí)代英國(guó)人的發(fā)育滯后簡(jiǎn)直叫人震驚。在華盛頓特區(qū),青春期開(kāi)始于十歲、十一歲、十二歲,兩個(gè)孩子如果都同意,他們之間可以有喧鬧放縱、別出心裁的性關(guān)系。伊舍伍德告訴我們,他“之后還有其他經(jīng)驗(yàn),都很愉悅,但沒(méi)有一次令人完全滿意。因?yàn)榭死锼雇懈ジ械骄惺?dāng)時(shí)這在上層社會(huì)的同性戀者中并不罕見(jiàn);和來(lái)自同一階層、同一國(guó)家的人相處,他無(wú)法在性方面放松。他需要一個(gè)工人階級(jí)的外國(guó)人”。答案就是德國(guó)。“對(duì)克里斯托弗而言,柏林意味著男孩子。”奧登立刻介紹他去了“愜意角落”,一個(gè)供無(wú)產(chǎn)階級(jí)年輕人廝混的地方,克里斯托弗在那里結(jié)識(shí)了一位金發(fā)男孩布比。“在克里斯托弗的愛(ài)情神話中,布比是第一位像樣的主角候選人。”
約翰·萊曼的小說(shuō)《在純粹的異教意義上》與伊舍伍德的回憶錄不僅在時(shí)間和地點(diǎn)上有重合,還有一種相似的對(duì)性的關(guān)注。萊曼的敘事者寫道:“我癡迷于這樣一種欲望:想要與來(lái)自完全不同階級(jí)和背景的男孩做愛(ài)……”這種對(duì)身份差異的渴望并不罕見(jiàn):不管是異性戀、同性戀還是雙性戀,這場(chǎng)游戲里總是會(huì)有“門不當(dāng)戶不對(duì)”的情況。而我懷疑,中上層階級(jí)男性對(duì)下層階級(jí)青年的渴望,主要出于對(duì)自己階級(jí)的恐懼。有些男性不像伊舍伍德、奧登這樣意志堅(jiān)定,性方面的承諾可能導(dǎo)致其中一方心理崩潰。
伊舍伍德描述了他與異性的實(shí)驗(yàn):“她比他大五六歲,隨和、時(shí)髦、幽默……他覺(jué)得吃驚又有趣,原來(lái)自己這么容易就能把平常的姿勢(shì)和動(dòng)作用到這位不平常的伴侶身上。他感受到好奇和玩一種新游戲的興奮。他也感受到了情欲,但那主要是自戀……”然后:“他問(wèn)自己:我想跟更多的女人或女孩上床嗎?當(dāng)然不想,只要我能擁有男孩。為什么我更喜歡男孩?因?yàn)樗麄兊男误w,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氣味和他們行走的姿態(tài)。而且男孩可以很浪漫。我可以把他們放進(jìn)我的神話里,可以與他們相愛(ài)。女孩可以是極其美麗的,但從不浪漫。其實(shí),我覺(jué)得缺乏浪漫正是她們最可愛(ài)的地方。”這一切都透著一種清醒(即便談不上精準(zhǔn))的常態(tài)。
然后,伊舍伍德從個(gè)人轉(zhuǎn)向整個(gè)群體,他注意到社會(huì)對(duì)每個(gè)人施加的瘋狂壓力,即要求人人都是異性戀者,并不惜一切代價(jià)否認(rèn)相反的天性。由于事實(shí)證明異性戀關(guān)系對(duì)伊舍伍德來(lái)說(shuō)也很容易,他本可以加入大多數(shù)人的行列。但是叛逆的自我阻止他這樣做,他帶著馬丁·路德般的憤怒宣布:“即便我的本性和他們的一樣,我也應(yīng)該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反抗他們。假如男孩們不存在,我也必須把他們創(chuàng)造出來(lái)。”伊舍伍德對(duì)他所謂的“異性戀獨(dú)裁”發(fā)起了不懈的、令人欽佩的戰(zhàn)爭(zhēng),如今同性戀者在美國(guó)和英國(guó)“享受”到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勇敢做出榜樣、大聲疾呼的結(jié)果。
在柏林,伊舍伍德和一個(gè)叫海因茨的工人階級(jí)男孩發(fā)展出了穩(wěn)定的關(guān)系,《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類》中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是關(guān)于他們的共同生活的,當(dāng)時(shí)希特勒開(kāi)始上臺(tái)執(zhí)政,曾經(jīng)吸引了伊舍伍德的自由而舒適的柏林變得丑陋起來(lái)。因?yàn)楹R虼牡纳矸菸募袉?wèn)題,伊舍伍德和他一直不停地在歐洲更換居住地: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加那利群島、布魯塞爾。最終海因茨還是被困在了德國(guó),被迫服兵役,踏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chǎng)。但是他奇跡般存活了下來(lái)。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后,伊舍伍德見(jiàn)到了海因茨和他的妻子——對(duì)于我們這個(gè)新瓦格納時(shí)代的任何一首田園牧歌來(lái)說(shuō),這都是最令人滿意的結(jié)局。
與此同時(shí),身為作家的伊舍伍德也在不斷成長(zhǎng)。關(guān)于柏林的故事就是在這一時(shí)期寫成的;《獅子和影子》也是同樣,另外還有與奧登合作的最后幾部詩(shī)體戲劇。最終,他不可避免地墜入了電影界……這是注定要發(fā)生的事情。在《獅子和影子》里,伊舍伍德寫道:“我一直對(duì)電影很著迷……我是個(gè)天生的影迷……我認(rèn)為這與‘藝術(shù)’毫無(wú)關(guān)系;我過(guò)去就對(duì)人的外表有著無(wú)盡的興趣,現(xiàn)在依然如此——他們的面部表情,他們的手勢(shì),他們走路的姿態(tài),他們緊張時(shí)的動(dòng)作……電影把人放在顯微鏡下:你可以盯著他們看,你可以像觀察昆蟲(chóng)一樣觀察他們。”
伊舍伍德受邀為導(dǎo)演貝托特·菲爾特爾寫電影劇本。“貝托特·菲爾特爾以弗里德里希·伯格曼的形象出現(xiàn)于中篇小說(shuō)《普拉特的紫羅蘭》中,這篇小說(shuō)是十二年后發(fā)表的。”伊舍伍德和有趣的菲爾特爾一拍即合,他們一起創(chuàng)作了電影《小朋友》。從那時(shí)起,最好的英語(yǔ)散文作家就靠寫電影劇本養(yǎng)活自己。事實(shí)上,我接觸到的第一部伊舍伍德作品不是小說(shuō),而是他寫的電影《天堂怒火》,十六歲時(shí)的我覺(jué)得這部電影精彩極了。“月亮!”瘋瘋癲癲的羅伯特·蒙哥馬利吟誦道,“它盯著我,像一只巨大的眼睛。”英格麗·褒曼哆嗦了一下。我也是。
如今對(duì)文學(xué)感興趣的年輕人(他們只是極少數(shù),相比之下更多年輕人喜歡那種最平淡、最容易、最慵懶的藝術(shù)形式——電影)很難意識(shí)到,西利爾·康諾利曾將伊舍伍德視為“英國(guó)小說(shuō)的希望”,而我們這些在二戰(zhàn)中長(zhǎng)大的人則將之奉為大師。我覺(jué)得人們對(duì)伊舍伍德作品的相對(duì)忽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放棄了英國(guó)籍。在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前,他與奧登一起移居到了美國(guó),這在當(dāng)時(shí)引起了不少人的仇視(令人不齒的伊夫林·沃在《多升幾面旗》中就粗陋地諷刺了他們)。最終,奧登的聲譽(yù)幾乎沒(méi)有受到影響。因?yàn)楫?dāng)時(shí)人們覺(jué)得詩(shī)人是可以又瘋又壞、不宜閱讀的,但人們期待散文作家即便談不上有責(zé)任感,也應(yīng)該行事不出人意料才對(duì)。
在美國(guó),伊舍伍德首先受到了貴格會(huì)[3]的吸引,接著轉(zhuǎn)向吠檀多派[4]。后來(lái),他成了同性戀解放運(yùn)動(dòng)的激進(jìn)代言人。如果說(shuō)他對(duì)克里斯托弗的同類的辯護(hù)有時(shí)尖銳刺耳……好吧,在一個(gè)對(duì)同性戀深惡痛絕、盲目恐懼的社會(huì)里,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們大聲宣傳。無(wú)論如何,伊舍伍德對(duì)道德的任何一種關(guān)注都不可能使他受到文學(xué)界的青睞,因?yàn)檫@個(gè)文學(xué)界正是由老學(xué)究、猶太教徒、基督教徒、中產(chǎn)階級(jí)和異性戀者構(gòu)成的。然而他最好的一些作品正是在美國(guó)寫成的,包括讀者手中的這本回憶錄,以及小說(shuō)《單身男子》與《河畔相會(huì)》。最重要的是,他總能歪著腦袋看待世界,即便他居住在圣莫尼卡——這是一個(gè)陰郁的地方,就連同性戀家庭也像《美好家園》雜志拍攝的那些異性戀夫婦一樣,在淡褐色的太平洋天空下享用精致的早午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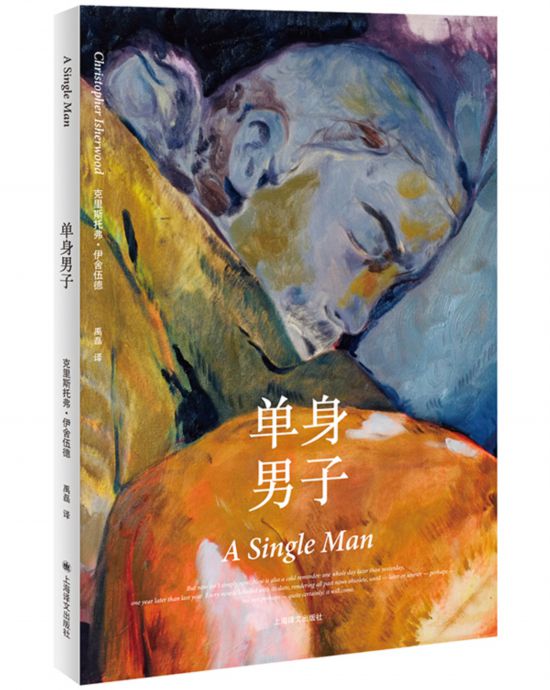
《單身男子》
在伊舍伍德的文學(xué)生涯中,最打動(dòng)我的并不是他堅(jiān)持做自己的堅(jiān)韌意志,而是他始終清晰曉暢、從不拖沓懈怠的散文風(fēng)格。伊舍伍德的句子里沒(méi)有多余之處。動(dòng)詞有力,名詞精準(zhǔn),形容詞很少。第三人稱敘事出乎意料、引人入勝,而第一人稱則是一位很好的向?qū)В瑥牟烩钼踝鲬B(tài)。
伊舍伍德的文風(fēng)是不是太簡(jiǎn)單了?西利爾·康諾利曾在《承諾之?dāng)场罚ㄒ痪湃耍┲斜硎緭?dān)憂:“[伊舍伍德]很有說(shuō)服力,因?yàn)樗侨绱苏~媚般地溫和而低調(diào),沒(méi)有什么能喚醒他,沒(méi)有什么能讓他震驚。在暗地里看不起我們的同時(shí),他又寬容得不能再寬容了……不過(guò)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jià)。伊塞伍先生——”(康諾利在探討伊舍伍德的柏林故事)“可不是一頭大傻牛,因?yàn)樗⒉皇且欢ㄒc筆下人物及其背景站在同一條戰(zhàn)線上的,而海明威出于其藝術(shù)理念則必須這么做。但是,伊舍伍德本可以更加細(xì)膩、聰慧、精于表達(dá)。”伊舍伍德回復(fù)康諾利:“在談話中,伊舍伍德……表達(dá)了他對(duì)建構(gòu)的信念,認(rèn)為這是走出困境的方法。作家必須書(shū)寫能被最大多數(shù)人理解的語(yǔ)言,大眾的語(yǔ)言,而他作為小說(shuō)家的才華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在觀察的準(zhǔn)確性、情景的合理性以及對(duì)整本書(shū)的建構(gòu)中。”
在漫長(zhǎng)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伊舍伍德一直保持著這種審美觀。當(dāng)放棄康諾利所說(shuō)的“官話式寫作”時(shí),他表現(xiàn)出了相當(dāng)大的勇氣。但后來(lái)的伊舍伍德甚至比早期的“照相機(jī)”更出色,因?yàn)樗辉偈且粋€(gè)匿名、中立的敘述者。他也會(huì)感到震驚,他也會(huì)生氣。
在《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類》中,伊舍伍德思考該以何種態(tài)度對(duì)待即將到來(lái)的對(duì)德戰(zhàn)爭(zhēng)。“克里斯托弗對(duì)自己說(shuō),假如我掌握了一支納粹軍隊(duì)的生殺大權(quán),只要按下一個(gè)按鈕就能把他們炸飛;那支軍隊(duì)里的人因折磨殺害平民而臭名昭著,只有海因茨一人例外,那么我會(huì)按下按鈕嗎?我不會(huì)——等一下,假如我知道海因茨本人因?yàn)榍优郴虻赖律鲜艿礁腥荆炎兊酶渌艘粯訅模⑶覅⑴c了他們的所有罪行呢?那我會(huì)按下按鈕嗎?克里斯托弗毫不猶豫地給出答案:當(dāng)然不會(huì)。”這就是艱難時(shí)刻一位人道主義者發(fā)出的呼聲。我們唯有希望,在克里斯托弗的生活和作品的引導(dǎo)下,他真正的同類會(huì)越來(lái)越多,即便他們(我們)如此明智地拒絕繁衍。
注釋
1.Diane de Poitiers(1499-1566),法國(guó)國(guó)王亨利二世的情婦。
2.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國(guó)劇作家、詩(shī)人。
3.Quakers,興起于17世紀(jì)中期英國(guó)及其美洲殖民地的一個(gè)宗教教派,具有神秘主義色彩。
4.Vedanta,印度傳統(tǒng)六派哲學(xué)中的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