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浪漫傳奇中,都有一個虛榮的主人公
虛榮是亙古不變的人的哲理。但虛榮是否成為一個問題,這就是時代的問題了。
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甚至中世紀(jì)時期,虛榮的神、人、角色大有人在。但虛榮又不是他們最重要的特質(zhì),虛榮也沒有從諸多特質(zhì)中浮現(xiàn)。因此,虛榮者是不存在的。那時的人,所擁有的幾乎是全部的倫理。
虛榮屬于貴族。即使到了莎士比亞時期,仍然如此。看看莎士比亞的描述:“輕浮的虛榮是一個不知饜足的饕餮者,它在吞噬一切之后,結(jié)果必然犧牲在自己的貪欲之下……”很顯然,莎士比亞并沒有打算將虛榮的品質(zhì)放在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身上,甚至莎士比亞從未真正將注意力放在貴族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辛白林》中,虛榮似乎成了女人的專屬。
不過,自文藝復(fù)興以降——由于體裁的原因,莎士比亞在某種程度上屬于一個例外——事情發(fā)生了變化,“人的發(fā)現(xiàn)”洶涌而來。人,也從其完整的世界走了出來。技術(shù)極速進步,生活以新月異,自然從周遭消失,人的喜怒哀樂也從其毛細(xì)管中集聚在一頭一面。
從文學(xué)的發(fā)展上看,普羅旺斯的抒情詩、波斯一帶的箴言詩歌、中國的詩詞曲、日本的宮廷文學(xué)、整個宗教世界的經(jīng)典文本,被世俗的、通俗的、不易流行的文學(xué)和作品取而代之。由此,虛榮的人、虛榮的角色,來到了這個世界。
虛榮如何進入這個世界?
虛榮,屬于七宗罪中的驕傲,喬叟的堂區(qū)長的劃分被引用至今。“從驕傲派生出來的枝枝節(jié)節(jié)罪孽究竟有多少……虛榮指喜歡塵世的權(quán)位和豪華,并因這種世俗地位感到光彩。”喬叟進而將驕傲分為兩種:一種藏在心里,一種顯露在外。言下之意,有一種內(nèi)心的虛榮,也有一種外顯的虛榮。與之對應(yīng)的,喬叟提供了相對應(yīng)的救治方法,即謙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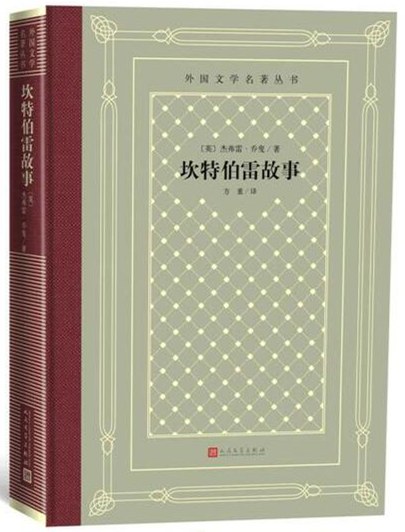
《坎特伯雷故事》
在薄伽丘和喬叟的時代,虛榮心應(yīng)和著世俗奇情,純粹、狡黠、環(huán)環(huán)相扣。《坎特伯雷故事》中就有一個極虛榮的管家。管家經(jīng)營著一個磨坊,他很不老實,四處坑蒙拐騙,居民都叫他霸王。故事很簡單。約翰和阿倫到磨坊,研磨自家的谷物,可一不留神就丟了馬和谷物。空手的約翰和阿倫只好睡在磨坊,他們心思一動,和管家的女兒和老婆通奸。虛榮的磨坊主遭受了極大的懲罰。
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虛榮不是普遍的?虛榮,作為一種人格和特質(zhì),被重新書寫了。它被安置在普遍的人之上,而不再只是養(yǎng)尊處優(yōu)的人。
在文藝復(fù)興之后,虛榮,愈發(fā)沿著兩個路徑衍發(fā),但不是喬叟所說的向外和向內(nèi)。其一是現(xiàn)實主義,其一是浪漫主義,或者說,其一是實用主義,其一是理想主義。前者是樂觀的、貴族式的,后者是悲觀的、基督教式的。
從倫理學(xué)出發(fā),早期的現(xiàn)實主義遠(yuǎn)不同于我們所認(rèn)知的平均的現(xiàn)實主義,或者之后處在巔峰時期的、作為集大成者的現(xiàn)實主義。在十八世紀(jì),甚至十九世紀(jì)早期,小說還不是嚴(yán)肅的文學(xué)類型,但它們的倫理傾向卻比后來的大多數(shù)現(xiàn)實主義作品要嚴(yán)肅得多。
湯姆·瓊斯是一個君子化的流浪者和主人公,他并不完美,但從未被放棄。瓊斯天性美好,處事輕薄,犯下了很多錯誤。但瓊斯卻有一種平衡,這種平衡很難說是他本身擁有的,而不如說是菲爾丁賦予他的。菲爾丁給瓊斯以虛榮,也給了他真正的榮譽,虛榮使其迷悟,榮譽使其成為一個理想紳士。下面這段在《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中的話,足以回答菲爾丁或者瓊斯的虛榮觀:
“盡管造物決不會在每個人的氣質(zhì)里摻和等量的好奇心和虛榮心,可是世上恐怕不會有人分到的竟是那樣少,以致他不需要什么技巧,不費什么周折就能把二者克制或隱藏起來——然而對任何一位稱得起聰穎或者教養(yǎng)好的人,這種控制是必不可少的。”
他們渴望榮譽,甚至虛榮,但這對于他們,對于事情的發(fā)展并沒有傷害。他們的榮譽、虛榮,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早期的資本主義的特質(zhì),發(fā)展后的資本主義很快就拋棄了它。
以浪漫主義方式表現(xiàn)的,卻是另一種虛榮。浪漫主義的虛榮,比現(xiàn)實主義的虛榮,要來得久遠(yuǎn)一點。在史詩、典雅愛情故事、巴洛克傳奇中,虛榮幾乎是其中最大的道德設(shè)定。故事中常常有一個愛慕虛榮的女人,通常是上流身份,和一個追求女人以實現(xiàn)虛榮的男人,通常是騎士身份。
幾乎所有浪漫傳奇中,都有一個虛榮的主人公。唐璜或許是這一系列虛榮者中最耀眼的人物。唐璜有著一系列的變形。為人所知的版本是莫里哀和唐璜和拜倫的唐璜。有些唐璜過于典型,在此便不再展開,只拿出D.H.勞倫斯的一句話:做一個唐璜似的人是多么痛苦,既不能獲得歡愛后的安寧,又不能讓那團小小的火焰在歡愛中變成烈焰,也不能在間歇時像一條清流那樣貞潔。
虛榮如何充溢這個世界?
夏多布里昂之后,虛榮的問題滲透到幾乎所有作家的筆下。財富的問題、愛情的問題、生命的問題,經(jīng)由虛榮,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現(xiàn)。虛榮,在那個年代,是美好的事。虛榮,還沒有變成一個巨大的怪獸,它和榮譽之間還存在著密切的關(guān)系。雖然虛榮不能像榮譽那樣,成為必要且崇高的品質(zhì),但是它仍然有巨大的游戲空間。
在廣義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中,大多數(shù)角色都不是標(biāo)準(zhǔn)的正派人物,他們或是病態(tài)的,或耽溺某種偏頗。特別重要的是,他們不得不置身于復(fù)雜的社會和巨大的關(guān)系網(wǎng)之中,這在今天都是難以想象的。虛榮,是多么重要的喜劇元素。
像浪漫傳奇中的設(shè)定一樣,簡·奧斯丁也將虛榮分配了女性,而不是男性。這一次,虛榮屬于伊麗莎白,《傲慢與偏見》的女主角。達西和伊麗莎白,一位是紳士,一位是紳士的女兒,是故事中僅剩的般配的人,他們最終牽手成婚。達西是傲慢的,他很體面,在意教養(yǎng)。這樣的傲慢在伊麗莎白心里一直是一個癥結(jié),她對達西有很大的偏見。傲慢,在奧斯丁的視野中,是一樁好品質(zhì),她反諷地說:只要你果真聰明過人——你就會傲慢得比較有分寸。起初,讀者會介意達西的傲慢或者教養(yǎng),他看起來無法成事,可是隨著事情開展,讀者就會改變主意,興許還會認(rèn)為教養(yǎng)是最大的美德。
不過,伊麗莎白的虛榮,或許也是恰到好處的。而且如果沒有達西的驕傲,伊麗莎白的虛榮,或許會大打折扣。在這樣的故事中,傲慢是有教養(yǎng)的,虛榮也是有教養(yǎng)的。這樣的虛榮,很微妙,但常常是誤解和錯誤最大的源頭。讓我們聽一聽故事中,伊麗莎白自己的說法:
“我還一向自鳴得意地認(rèn)為自己有眼力,有見識呢!我還常常看不起姐姐的寬懷大度,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總是無聊或是無稽地胡亂猜疑。這一發(fā)現(xiàn)真讓我感到羞愧啊!然而我也活該感到羞愧!我即使墜入情網(wǎng),也不會盲目到如此可鄙的地步。不過我最蠢的,還不是墜入情網(wǎng)的問題,而是虛榮心在作怪。我起初認(rèn)識他們兩個的時候,一個喜歡我,我很得意,一個怠慢我,我就生氣,因此,在對待他倆的問題上,我抱著偏見和無知,完全喪失了理智。我到現(xiàn)在才有了點自知之明。”
在現(xiàn)代主義的框架下,另一個方式是集體的、放肆的、暴露狂式的虛榮。這種方式濫觴于法國文學(xué)。虛榮者之所以充斥法國文學(xué),主要是因為法國文學(xué)在其原有的宮廷文學(xué)基礎(chǔ)上再生了新的文學(xué),這區(qū)別于英國文學(xué)由資產(chǎn)階級思想再造的局面。再加上,法國文學(xué)長期是世界文學(xué)的宗主,這就給虛榮者提供了某種土壤。正如拿破侖在其回憶錄中所說:啊,共和國!今天,肯為公眾利益犧牲一切的只有一個人,而圖享受求虛榮的,卻何止千千萬萬。
《紅與黑》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虛榮者,同樣的,巴爾扎克筆下的人物也幾乎都是虛榮者。于連在所有故事的角色中或許是最浪漫的,最具有幻想的。另一個例子是愛瑪·包法利,她的幻想有著同樣的力量,只不過福樓拜拒絕這樣做。于連夢想著成為新的拿破侖,夢想著情婦溫柔體貼,夢想著……于連也如愿以償,成為“一個貝藏松年輕女子心目中的英雄。她們?yōu)榱四悖咽裁炊纪耍B政治都忘了……”不過,司湯達所接受的終局仍然是賀拉斯的:“象牙、大理石、繪畫、銀盆、雕像、紫衣, /無數(shù)人認(rèn)為這些東西必不可少, /但也有人并不為之所動。 ”
虛榮的故事在雨果、凱瑟琳·曼斯菲爾德、路易莎·奧爾科特、托馬斯·哈代、列夫·托爾斯泰也以幾乎同樣的方式發(fā)生著。所有這些作家在書寫虛榮的時候,總是以一種特殊的、微妙的、批判或反諷的方式呈現(xiàn)的,區(qū)別在于不同作家的虛榮量表是不同的。
虛榮是如何衰落的?
在十九世紀(jì)末和二十世紀(jì)初之后,虛榮的問題不再是一個問題。更為準(zhǔn)確的說法是,在現(xiàn)代現(xiàn)場和后工業(yè)裝置中,虛榮的問題被排除在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菲茨杰拉德,以各自的方式,展示了虛榮的衰落和退場,以及虛榮為何退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曾經(jīng)是一個極度虛榮的人,或者說,他曾經(jīng)生活在一個虛華的世界。可是他退休后,把自己鎖在環(huán)境惡劣的地下室,生活在苦索、墮落之中。這位退休文官,悉悉嗦嗦,耽于軍官為何侮辱他的榮譽。他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俄國式的浪漫主義者,他洞察一切,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妥協(xié),緊盯著有利的、實際的目標(biāo)。當(dāng)然,陀思妥耶斯基如此寫,用意是在希望讀者對此有所反應(yīng)。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意不在軍官和虛榮,而在讀者,抑或說,普遍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地下室人的口吻進行自我解剖:
“我對自己的臉深惡痛絕,覺得它丑陋不堪,甚至還懷疑它上面有某種下流無恥的表情,因此……我此時害怕并非由于膽小如鼠,而是漫無邊際的虛榮心。”
稍微理解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們就明白,他所講的是現(xiàn)代人所面臨的境況,至少也是俄國人的境況。只要把自己帶入地下室人的角色,我們就很容易明白,虛榮的現(xiàn)代人被囚禁在所謂理性境況之中,而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達和暗示的:
“如果讓我們單獨留下,遠(yuǎn)離書本,我們就會立即陷入歧途、驚慌失措——我們將無法搞清,我們追隨什么,我們依靠什么,愛什么和恨什么,尊重什么和蔑視什么。我們甚至連做人——做一個真正的、有著自己血肉的人——都會感到有一種不堪承受之重;我們將對此深感羞愧,視為奇恥大辱,并且竭力成為某種主觀臆造的一般性的人。”
以幾乎同樣的方式,卡夫卡戳穿了人身上最后的那一點可信性,那一點虛榮。圍繞虛榮而展開的敘事,諸如愛情、名利、犯罪傾向、人道精神,都破產(chǎn)了。現(xiàn)代容不下一點點有緣由的浪漫。
蓋茨比的故事,可以看作是虛榮之巨艦最后的沉落。蓋茨比帶領(lǐng)現(xiàn)代人經(jīng)歷了一個浮華的故事。蓋茨比自然是一個虛榮者,但他正直、坦蕩、渴望愛情。但布坎南夫婦不是,他們虛榮,但他們更虛偽。蓋茨比的故事就是虛榮毀于虛偽的故事。現(xiàn)代人的虛偽藏匿在現(xiàn)代人的人情味、科層制、資本主義等等之中。在這些龐大固埃的虛偽面前,虛榮是極其脆弱的。蓋茨比的不幸和死亡,正是一種虛榮的死亡,乃至于福柯意義上的“人之死”。
尤其是那句名言:每當(dāng)你要批評別人,要記住,世上不是每個人都有你這么好的條件。它所呈現(xiàn)的只是一種赤裸裸的虛偽,它在真實面前無所依附。
虛榮的衰落和消失,歸根結(jié)底是因為,某種人的消失,那種扎實的、在社會系統(tǒng)中游走的人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獨自面對赤裸裸的世界的人。與此同時,虛榮的位置被虛偽取代了。
最后讓我們回顧一下,圣埃克蘇佩里所寫的一個情節(jié),他所寫的虛榮在今日已成為了過去式:
“真的嗎?”小王子問,他沒有完全聽明白。
“你拍拍手吧,”虛榮的人指點他說。
小王子拍了拍手。虛榮的人拿起帽子,謙虛地表示感謝。
“這比剛才訪問國王好玩多啦,”小王子心里想。他又拍了拍手。虛榮的人再次舉起帽子致意。
經(jīng)過五分鐘的練習(xí)之后,小王子厭倦了這個單調(diào)的游戲。
“如果要讓你把帽子摘掉,”小王子問,“該怎么做呢?”
但虛榮的人聽不見他的話。虛榮的人只聽得見贊美。
“你真的非常崇拜我嗎?”他問小王子。
“崇拜是什么意思呀?”
“崇拜我就是承認(rèn)我是全世界最優(yōu)秀、穿的衣服最漂亮、最富裕和最聰明的人。”
“但你的星球上只有你一個人啊。”
“幫幫忙吧。請你崇拜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