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簡史
兩千多年前,荒誕已于軸心時代初露端倪。無論在古希臘神話中,還是中國的莊子哲學中,都依稀可見荒誕的神秘蹤影。在西方語境中誕生的“荒誕”一詞(absurd),源于拉丁文absurdus,意為不合曲調(out of tune)或無意義(senseless),其前綴ab作用是加強語氣,后綴surdus意思是deaf(耳聾)、unheard(聽不見的)、silent(沉默的、無意義的)、dull(感覺麻木的,乏味單調的,無精打采的)。因此, absurd 就是完全耳聾,一點也聽不見,感覺麻木,乏味單調,令人厭煩苦惱,提不起精神。這個原意為“樂曲不和諧、不協(xié)調”的音樂術語,在后來的歷史中慢慢引申為不真實、不合理、不合邏輯、不可理喻,并逐漸從歷史的陰暗一角走向世界和人生舞臺的中央。
被遮蔽的荒誕
古希臘時期,世界被視為一個秩序井然、和諧一致、依照系統(tǒng)的規(guī)則邏輯建立起來的天地,事物各從其類、各歸其位、在宇宙中各有固定的準確的位置。這似乎是希臘思想對世界的一個重要貢獻,即將哲學領域、自然界、政治領域和道德領域視為一個規(guī)律體系。正如英國學者基托對希臘精神的總結:“萬物一體的觀念,或可說是希臘精神最典型的特性……現代精神分裂為某些范疇,專門化為某些范疇,以某些范疇進行思考,而希臘人的本性與此相反,他們采取最寬廣的視角,將萬物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這正是中國古人所推崇的“萬物并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生活境界。
掌管世界的不是神或命運,而是規(guī)律。人與世界和諧共處,世界對人(人的意識、人的行動)是敞開的,人生于其中感覺不到自身與自然世界的尖銳差異。人與世界的和諧關系使人類有一種“在家”的感覺,人可以從任何一方,無論是從世界中還是于自身中皆能感受到和諧與秩序,以及人的尊嚴和價值——尤其是從神話斯芬克斯之迷對人的生命歷程的外在描述,到四處宣揚“認識你自己”的蘇格拉底對城邦人的生活、道德、美和善惡的研究,從伯利克里對“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勞動成果”的大聲宣告,到普羅泰戈拉對“人是萬物的尺度”大旗的高舉,從柏拉圖對純粹理性哲人的推崇,到亞里士多德對人進行全方位的把握,這一切的一切都讓荒誕失去了立足之地。
基督教廣泛傳播之后,西方進入了漫長的中世紀。盡管希臘的世界觀、宇宙觀發(fā)生了變化,但是人并沒有成為被拋棄的存在,沒有成為世界的局外人。不同于古希臘的和諧觀念,中世紀時期強調奧古斯丁所謂“上帝之城”與“魔鬼之城”的對立,認為人可選擇其一而居。從此,基督教神學牢牢地緊箍著人們的心靈,一切世俗文化均被納入神學范疇,禁欲主義扼殺了人們的自然欲求,蒙昧主義剝奪了人們借科學認識自然、世界及自我的權利。人被迫放棄一切世俗的觀念,主動承認自己的無能、卑下和原罪,并忍痛受苦,努力贖罪,以求來世進入天堂享受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進入萬劫不復的地獄。
由此,人否定了自己作為“人”,人把自己的本質對象化給上帝,正如費爾巴哈所言:“人在上帝身上肯定了他在自身中加以否定的東西”。人失去了整個世俗世界和自我的完全性,由一個幻想中的上帝來主宰自己的人生。古希臘文明中映照出的人的健康形象被神學教會污染得面目全非,而被宗教鴉片麻醉了的人們對此卻一無所知,并心甘情愿地任其擺布。盡管失去了對人、人性、人的意志自由和獨立人格力量的追求,基督教依然可以保護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因為上帝拯救人類,人的存在價值在神的庇護中得以確立。因此,荒誕無法在上帝的強烈光芒中現身。
一言以蔽之,荒誕被遮蔽了。
荒誕的去蔽
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理性的旗幟得以高揚,荒誕恰恰是人類理性發(fā)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這也解釋了荒誕在中國古代歷史的長期缺席)。16世紀上半葉,法國作家拉伯雷的《巨人傳》(五部陸續(xù)出版于1532-1564年)引發(fā)轟動,翻開這部小說,滿眼盡是荒誕不經的內容:先是高康大(龐大固埃之父)的出生令人匪夷所思——從母親的耳朵里跑出來,然后是龐大固埃每頓飯能喝下四千多頭奶牛的奶,接著是龐大固埃朋友的頭被敵人砍下來后,巴奴日竟通過外科手術將其頭和身體連接起來,并使之復活。而這位朋友復活后就講述他在地獄里的見聞:歷史上大名鼎鼎的英雄們到了地獄都在從事各種卑下的行當等。作為荒誕文學的遠祖,拉伯雷在寫作這部作品時,正是人們走下神壇轉而開始關注人自身的時代,書中的內容雖然荒誕離奇,實則揭露社會的黑暗,并從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fā),熱情贊頌了人文主義理想,高康大和龐大固埃的巨人形象正是對人的力量和智慧的肯定。
幾乎就在《巨人傳》出版的同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科學革命也一觸即發(fā)。1543年,波蘭天文學家尼古拉斯·哥白尼出版了《天體運行論》,其中提出的“日心說”一舉顛覆了統(tǒng)治幾千年的“地心說”理論,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類也不再是宇宙的主宰。哥白尼革命動搖了人類對世界的想象,人被驅逐出了世界的“伊甸園”,被拋向無限的宇宙,人不再感到安全。面對著截然不同的存在處境,人被重新拋回了自身,他們發(fā)現自己在軟弱、孤獨等方面與其它生物無異。在探索世界的歷史過程中,人類逐漸失去了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并日益痛苦地發(fā)現世界變得如此陌生,人與世界的距離如此之大,它已經不再是人類的家園。這一深刻的精神危機使人類產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和虛無感,當個人將自身與他人、與外界區(qū)別開來,人的陌生感和斷裂感由之而生。
16至17世紀,現代性開始萌芽。蒙田的隨筆、笛卡爾的哲學、帕斯卡爾的信仰構成了現代性的三大源頭,它們代表了一個人面對自我和世界時的三種態(tài)度:我懷疑,我知道,我相信。笛卡爾試圖以“我思故我在”找回科學意義的確定性,帕斯卡爾試圖以“我相信”找回宗教意義的確定性,但蒙田的“我懷疑”才代表了西方思想發(fā)展的趨勢,不可知論和懷疑論成為這一時期西方哲學思潮的主流,并預示了后來的非理性主義和存在主義思潮。從此,人類開始意識到理性的局限性,認識到人的有限性、存在的偶然性,荒謬這朵被遮蔽了兩千年之久的奇葩開始慢慢展露出它的真容。換言之,荒誕乃是理性發(fā)展到較高階段后所達到的一種對世界和人生的深度體驗與清醒意識——這份體驗既是對僵化思維模式的搖撼解構,也體現著主體意識對既有理性邏輯的超越與揚棄。數百年后,法國哲人阿貝爾·加繆這樣定義荒誕:清醒的理性對其局限的確認。可謂一語中的。
隨著18世紀末浪漫主義的運動開啟,非理性元素越來越多的登上歷史舞臺,人們開始推崇直覺、想象力和感覺,這既是對啟蒙運動時期絕對理性的反動,也是一曲個體自由的贊歌。這在那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可見一斑:從夏多布里昂《勒內》(1802)的“彷徨苦悶”,到拜倫《曼弗雷德》(1817)的“世界悲哀”,再到繆塞《一個世紀兒的懺悔》(1836)的“迷茫絕望”……這些浪漫主義時代無所適從、焦躁不安的靈魂,其所共同表達的正是孤獨、無聊、焦慮、虛無、絕望等種種非理性的生命體驗。科技飛躍和宗教式微讓個人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自由巨大的局限性又讓人困惑,它猶如一道強光,將明暗閃爍的荒誕完全照亮。人們意識到,自由既是權利也是責任,作為要承擔后果的責任,意味著自由本身并不自由。不止如此,人既向往自由,但又逃避自由,甚至喜歡奴役或被奴役。正如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的感嘆:“人懸于‘兩極’:既神又獸,既高貴又卑劣,既自由又受奴役,既向上超升又墮落沉淪,既弘揚至愛和犧牲,又彰顯萬般的殘忍和無盡的自我中心主義”。
和理性及其局限一樣重要,自由的悖論是解讀荒誕的一把鑰匙。絕對自由開啟的虛無釋出荒誕,自由本身的悖謬導出荒誕,而荒誕同時也解開了所有成規(guī)的束縛,解放了自由。原來,“自由”與“荒誕”是一對孿生兄弟。
荒誕的爆發(fā)
進入20世紀后,荒誕迎來了舉世矚目的超級大爆發(fā),風頭之勁甚至超過了它的孿生兄弟——自由。經歷了“上帝之死”(尼采語)的信仰崩潰、弗洛伊德怪誕的“潛意識”理論以及兩次世界大戰(zhàn)帶來的絕望氣息,在無盡黑暗中摸索的人們開始深入地反思。風起云涌的存在主義哲學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聚焦于荒誕,其中執(zhí)“荒誕”牛耳者無疑是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加繆。正是他,有史以來第一次將荒誕提升到了哲學和美學高度,并對之后所有的文學和藝術流派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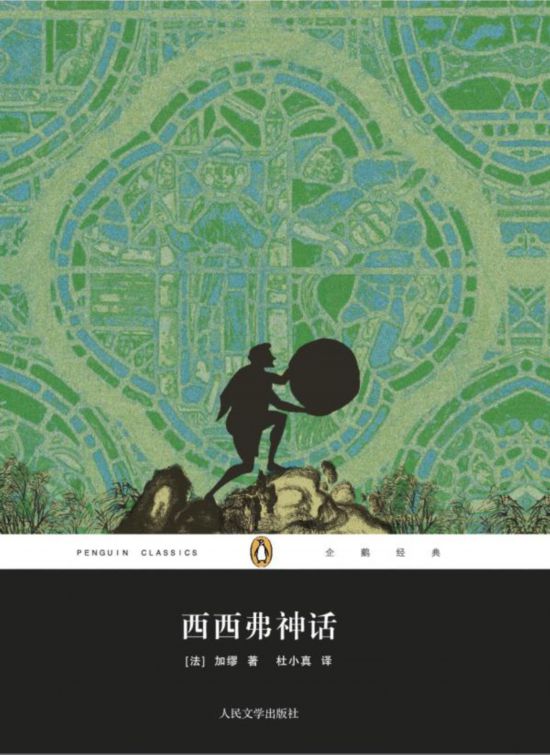
《西西弗神話》
在著名的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1943)中,加繆對荒誕進行了精微獨到的論述。首先,他清醒地指認了作為感覺的荒誕的無處不在:荒誕感,在隨便哪條街上,都會直撲隨便哪個人的臉上。這種荒誕感就這般赤裸裸叫人受不了,亮而無光,難以捉摸。更為荒誕的是,一切偉大的行動和一切偉大的思想,其發(fā)端往往都微不足道。偉大的作品往往誕生于街道的拐彎處或飯店的小門廳。歸根到底,機械般的日常生活所引發(fā)的厭倦、無聊和憂慮觸發(fā)了這種人生的荒誕感,這便有了加繆那段著名的文字,他用最普通的現代人的生活圖景絕妙地表述了西方人生存狀態(tài)的荒誕性:
起床、乘電車、工作四小時、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依靠同樣的節(jié)奏重復下去。不過某一天,“為什么”疑問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這種略帶驚訝的百無聊賴中開始了。
當然,身為文學大師的加繆并不滿足于從理論上闡釋荒謬,他在同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著名小說《局外人》(1942)讓人更加真切地體認和觸摸到荒誕的真面目。小說主人公默爾索作為生活的“局外人”,深感生活的虛幻、無聊和厭倦,對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抱著漠然的態(tài)度,他已然成為自己的陌生人。母親的死亡,情人的愛戀都不能激起他內心的波瀾(《局外人》的著名開頭是: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他對自己的生命抱著聽之任之的冷漠態(tài)度。這是人類意識到自身存在的荒誕性,卻又無可奈何而被迫采取的一種消極的生命姿態(tài),冷漠的表象下透射出對世界的荒謬本質的徹悟。然而,正是對荒誕的醒悟使默爾索的麻木、消極和冷漠獲得了高度的哲學意味,荒誕感被人格化了。
由此,加繆展現了人與世界的疏離關系乃是荒誕感的本質特征。一個人與周遭世界的疏離、隔閡與格格不入,乃是源自于他對社會通行準則的蔑視,從而成為社會中的“異己”,這正是加繆所推崇的“反抗哲學”。他說:“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這種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與布景的分離,正是荒誕感。荒誕本質上是一種分裂,它不存在于對立的兩種因素的任何一方。它產生于他們之間的對立……它不在于人,也不在世界,而在兩者的共存。”看來,荒誕感乃是麻木不仁的反義詞,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加繆在《局外人》序言中對默爾索的積極評價:“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zhí)著而深沉的激情,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
由此,放眼20世紀的文學作品,荒誕可謂無處不在。在卡夫卡冷峻筆觸所建構的永遠也到達不了的《城堡》(1926)中,在薩特以日記體沉思人對世界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的《惡心》(1938)中,在博爾赫斯現實與虛構交錯、幻影與夢境交織的《環(huán)形廢墟》(1944)中,在貝克特夢囈般對白所希冀到來卻永遠都是進行時的《等待戈多》(1953)中,在尤內斯庫科幻氣質與狂熱敘事并進中人退化為動物的《犀牛》(1960)中,在約瑟夫·海勒“只有瘋子才能獲準免于飛行”的《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1961)中……荒誕以絕望、惡心、虛無、異化、黑色幽默等各種面目不斷出現,猶如川劇中的變臉,令人目不暇接,但它們對荒誕的表達都指向同一個中心,即意義的缺席。作家們筆下的種種負面情感如冷漠、恐懼、孤獨、徒勞、惡心、厭倦和絕望等,都圍繞著這一中心作著不同姿態(tài)的旋轉。
是的,在一個上帝已經歷史性退場的世界上,荒誕迎來了大爆發(fā),因為人生的意義被取消了。人的生存沒有了目的性、必然性、神圣性和無限性,非目的性、偶然性、瑣屑性和有限性成了生存的真相(這些特點甚至一直延續(xù)到了21世紀的今天,并在碎片化的微時代呈現放大的趨勢)。荒誕文學無情地抹去了詩意的神話,殘忍地揭示了人類生存的真相——生存降格為活著,而這活著就是活著的唯一依據。這無疑沉重地打擊了人類的自尊,以非理性的重炮摧毀了人類幾千年來建立起來的形而上學的精神大廈。
如今,荒誕文學的熱潮早已褪去,但荒誕依然在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的各個角落隨處可見,在這個碎片化的微時代繼續(xù)變幻著它的面目。這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人類在經歷了理性的二度高漲,以及非理性的蓬勃發(fā)展之后,面對世界時的清醒意識和冷靜姿態(tài)。當然,面對無處不在的荒誕,冷眼旁觀或一笑而過都是不夠的。進而言之,加繆反對自殺的反抗哲學在任何時代都顯得彌足珍貴,在荒誕中找尋永恒,從虛無間生發(fā)意義,向無聊處借取靈感,問閑暇時可有創(chuàng)新,乃是貫穿現代人一生的真正課題。
尾聲:回歸荒誕的本義
1802年10月,飽受耳疾困擾的青年貝多芬正經歷著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時期,他在痛苦已極中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遺書》,其中寫道:“六年以來我的身體何等惡劣……可是我不能對人說:‘大聲些,我是聾子’……這感官在我是應該特別比別人優(yōu)越……我不致自殺是因為藝術留住了我。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不能離開這個世界。”在此,荒誕罕見地展現出了它的原始面目——deaf(耳聾)、unheard(聽不見的)、silent(沉默的、無意義的),貝多芬在面對這一巨大的荒誕時(成為一名真正的音樂家是其唯一志向,卻遭遇了玩笑般的失聰厄運),想到了加繆所謂的“肉身自殺”,但鋼鐵般的意志讓他選擇了“扼住命運的咽喉”,以奮振之姿反抗荒誕。
在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震古爍今的交響曲(如“英雄”、“命運”、“田園”等)、鋼琴奏鳴曲、鋼琴/小提琴協(xié)奏曲等杰作之后,晚年貝多芬徹底喪失了聽力,且因病重而長時間臥床不起,他躲進了自己隱蔽的聲音世界里。在他最后的五首鋼琴奏鳴曲、六首弦樂四重奏、迪亞貝利變奏曲以及六首小品中,貝多芬毫無顧忌地拋棄了那種平均的、古典的風格,不斷赤裸裸地表露出不和諧與兩極化的傾向,直至取消了調性。它們的現代感并非以19世紀20年代的標準來評判,而是一個世紀之后的標準。這些晚期作品尤其是弦樂四重奏幾乎像是令人尷尬的私生活,又像是他自己在紙上研究一些折磨腦袋的心智游戲,或把他自己從難以忍受的哀傷中抽離出來。貝多芬大部分的同儕友人并不了解,是什么原因造就出這些四重奏作品,這就好像一百年后的人搭乘時光機回到1826年,然后面對著困惑的聽眾演奏充斥著不協(xié)和音的20世紀音樂一樣。
我們猛然想到,荒誕這個原意為“樂曲不和諧、不協(xié)調”的音樂術語,或許正是解開貝多芬偉大的晚期杰作的秘鑰。以弦樂四重奏為突出代表的這些晚期作品,都有一種音樂上的疏離感,一種沒有溫暖的強度,一種難以言喻的孤獨,過去數十年來音樂的歡愉準則行將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不計任何代價要去試驗和聲可能性的急迫感:那是一種惴惴不安的美。無論是迪亞貝利變奏曲(Op.120)第21號變奏的瘋瘋癲癲,還是第32號鋼琴奏鳴曲(Op.111)第一樂章“C小調心境”(從早年的“悲愴”鋼琴奏鳴曲(Op.13),到協(xié)奏曲的里程碑——第三號鋼琴協(xié)奏曲(Op.37),再到堪稱完美的“命運”交響曲(Op.67),以及第九交響曲的先聲——合唱幻想曲(Op.80)貫穿始終)的最后展現,抑或第16號弦樂四重奏(Op.135)末樂章的“非如此不可”,我們都可以感受到晚年貝多芬在獨自一人面對荒誕時的孤冷、偏執(zhí)與抗爭,他在用生命最后的激情反抗糾纏其一生的荒誕,并在這些遠遠超越其時代的偉大作品中與荒誕達成了最終的和解。
由此看來,是貝多芬而不是加繆,有史以來第一次將荒誕上升到美學高度,無怪乎貝氏曾言之鑿鑿地宣稱:“音樂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學更高的啟示”。換言之,在加繆所創(chuàng)造的光輝燦爛的哲學和文學之前,荒誕在貝多芬的晚期音樂中得到了最完美、最透徹的詮釋(我們幾乎可以從中聆聽、感受和觸摸到荒誕的所有面目),無論是以其最原始的含義,還是最現代的含義,都是如此。
(謹以此文紀念路德維希·凡·貝多芬誕辰25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