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gòu)”在中國的可能
當(dāng)下中國“非虛構(gòu)”寫作在2010年前后由《人民文學(xué)》雜志倡導(dǎo)出場(chǎng),區(qū)別于“虛構(gòu)”,也區(qū)別于傳統(tǒng)意義的“報(bào)告文學(xué)”。“非虛構(gòu)”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書寫和反思當(dāng)代生活現(xiàn)場(chǎng)的能力,也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人言說和闡釋當(dāng)下生活的能力。這就要求寫作者即“行動(dòng)者”。所以,所謂的“非虛構(gòu)”是精神站位、進(jìn)入路徑和文體、修辭的合體。
而現(xiàn)在“非虛構(gòu)”顯然已經(jīng)出圈,大眾傳媒把所有標(biāo)榜“記錄”的都增容到“非虛構(gòu)”之中,包括日志、真實(shí)故事、 素人寫作、短視頻等等。國民以空前的熱情記錄生活投入于寬泛意義的非虛構(gòu)生產(chǎn),即便它們對(duì)真正意義的審美創(chuàng)造并無多少建樹,但一些記錄個(gè)人生活史意義的寫作實(shí)踐可以作為觀察時(shí)代風(fēng)習(xí)的樣本。
在“非虛構(gòu)”被增容和泛化的當(dāng)下,需要重新回到2010年前后倡導(dǎo)“非虛構(gòu)”寫作的問題意識(shí)和精神原點(diǎn),在“非虛構(gòu)”的汪洋大海中澄清和強(qiáng)調(diào)有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和審美創(chuàng)造的“一種”非虛構(gòu)。這是一種有難度和門檻的寫作,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歷史學(xué)和專業(yè)的深度調(diào)查為抵達(dá)真實(shí)和真相提供了精神、路徑和方法,但它們對(duì)世界和人性復(fù)雜性的勘探,以及修辭和文體又是“文學(xué)”的。
更重要的是,以文學(xué)而論,被寄以厚望的“非虛構(gòu)”能不能鑿穿文學(xué)和中國現(xiàn)實(shí)秘道?能否有更大的空間和可能?所謂中國“非虛構(gòu)”既指當(dāng)下中國現(xiàn)場(chǎng),也是指一種進(jìn)入中國現(xiàn)場(chǎng)的實(shí)踐性文體;而“非虛構(gòu)”中國強(qiáng)調(diào)的是立場(chǎng)和路徑,就是以“非虛構(gòu)”這種直面現(xiàn)實(shí)方式來把握、理解當(dāng)代中國。在2020年的“上海-南京雙城文學(xué)工作坊”第四期上,社會(huì)學(xué)和人類學(xué)家鄭少雄、非虛構(gòu)平臺(tái)“三明治”主理人李依蔓、媒體人呂正,帶來了他們對(duì)這個(gè)主題的實(shí)踐與思考。
——主持人 尹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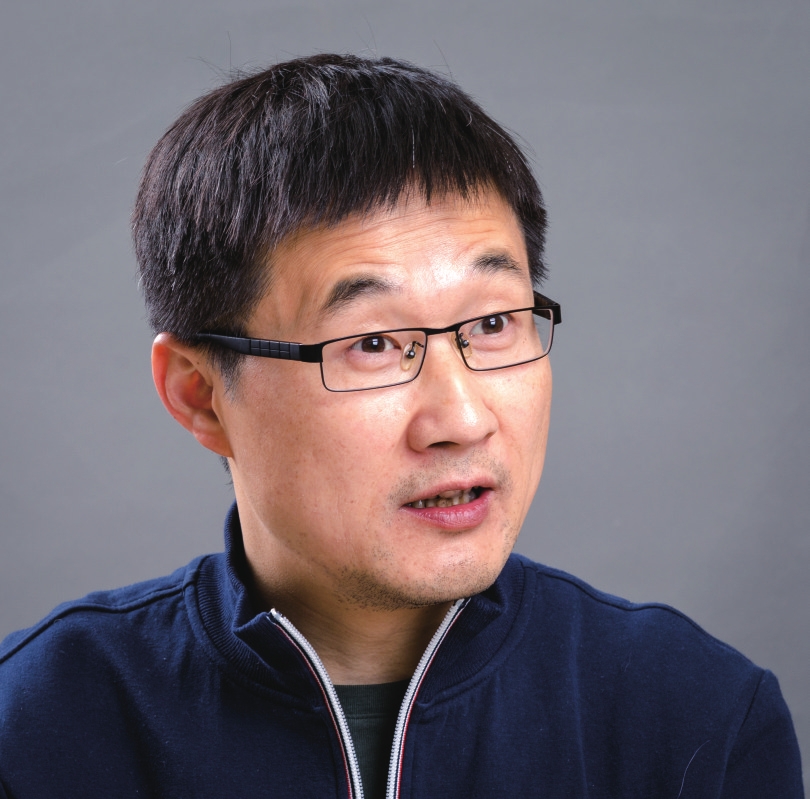
《瞻對(duì)》:關(guān)于非虛構(gòu)文本的人類學(xué)見解
鄭少雄
作為一名人類學(xué)者來討論“非虛構(gòu)”寫作問題,和學(xué)科間相互啟發(fā)的需要有關(guān),也可能是因?yàn)槲易罱鼛啄暝陉P(guān)注阿來的寫作。我自己做過康區(qū)土司研究,寫過一本《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展開研究之前,當(dāng)然已經(jīng)讀過阿來的《塵埃落定》,書稿完成后我意識(shí)到阿來很深地影響了我的思考框架。但在我的書里,阿來是隱匿的,甚至都沒有作為參考文獻(xiàn)出現(xiàn)過。為什么人類學(xué)者不能坦承文學(xué)的貢獻(xiàn)呢?為了彌補(bǔ)這個(gè)缺失,我后來相繼做過一些對(duì)阿來的再閱讀和寫作,算是遲來的致敬。更何況,阿來其實(shí)還是一位對(duì)民族理論、政策和實(shí)踐有自己獨(dú)到見解的知識(shí)分子,《瞻對(duì)》出版后,他與一位主管民族政策的高級(jí)干部有過一場(chǎng)對(duì)話,曾經(jīng)引起很大反響。
《瞻對(duì)》是阿來最著名的一部非虛構(gòu)作品。2013年《人民文學(xué)》非虛構(gòu)大獎(jiǎng)的頒獎(jiǎng)詞說:“作者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申歷史,并在敘述中融入了文學(xué)的意蘊(yùn)和情懷。”這段話涉及了“歷史”與“文學(xué)”兩個(gè)關(guān)鍵詞,可以看做是對(duì)非虛構(gòu)文學(xué)之歷史功用的肯定。
從長(zhǎng)篇小說《塵埃落定》到非虛構(gòu)作品《瞻對(duì)》,在阿來筆下,康區(qū)土司除了在小的尺度上,相互之間合縱連橫、征戰(zhàn)殺伐外;在大的尺度上,既有依賴、協(xié)同內(nèi)地征剿西藏的一面,也有與西藏聯(lián)手,共同對(duì)付清廷和民國政府的一面。簡(jiǎn)言之,土司及其追隨者是一些鐘擺人,善于在政治結(jié)構(gòu)中間拿捏、回旋。民國時(shí)期前輩學(xué)者林耀華、馬長(zhǎng)壽、陳永齡等人也嘗稱嘉絨在漢藏之間“首鼠兩端”。雖然這個(gè)框架并非阿來首創(chuàng),但是通過虛構(gòu)及非虛構(gòu)寫作,他把這個(gè)雙向互動(dòng)過程鋪陳得非常磅礴、精細(xì)。可以看出,其一藏族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并非鐵板一塊;其二就像阿來曾強(qiáng)調(diào)的,“作家表達(dá)一種文化,是探究這個(gè)文化‘與全世界的關(guān)系’”。當(dāng)然,近年來國內(nèi)人類學(xué)也已經(jīng)較多實(shí)踐王銘銘等人所推動(dòng)的“關(guān)系主義人類學(xué)”了,可見阿來的直覺和眼界具有學(xué)者式的精準(zhǔn)。
阿來用近似紀(jì)年的手法記述了清廷發(fā)動(dòng)的七次瞻對(duì)戰(zhàn)爭(zhēng)。從乾隆開始,就要依靠西藏地方政府助戰(zhàn),到了全書用力最著的貢布郎加叛亂時(shí)期,更是依靠藏軍才最終平息,因?yàn)橹Ц恫黄鹞鞑剀婐A,而把瞻對(duì)賞賜給西藏,在康區(qū)地面上形成了犬牙交錯(cuò)的政治局勢(shì),一直到清末川邊新政以后才由中央直接設(shè)縣治理。我們看到貢布郎加既挑戰(zhàn)西藏的權(quán)威,又挑戰(zhàn)中央王朝的權(quán)威,而受到貢布郎加欺凌的其他土司和百姓,在打箭爐清衙門告狀未果,便又向西藏爭(zhēng)取噶廈政府的干預(yù)。可見阿來寫瞻對(duì),包括余下很多篇幅寫整個(gè)康巴,都是把它放到清代開始的整個(gè)區(qū)域性政治局勢(shì)中、相互關(guān)系中來寫的,是符合歷史事實(shí)的,這個(gè)框架完全經(jīng)得起學(xué)術(shù)檢驗(yàn)。
有些評(píng)論認(rèn)為,從《瞻對(duì)》所使用的正史材料,主要是清代官方檔案文書的真實(shí)性上看,是歷史的、非虛構(gòu)的;而從對(duì)材料的文學(xué)化組織和運(yùn)用方式來看,則是主觀的,小說家言的。這個(gè)見解固然不錯(cuò),但是他們還認(rèn)為,因?yàn)榘硗瑫r(shí)選擇了地方筆記、方志、民間故事、口頭傳說等材料,所以更顯出虛構(gòu)的特征。這個(gè)說法一方面沒有意識(shí)到在《瞻對(duì)》中阿來雖然努力深入田野、兼聽兼信,但實(shí)際上帝國檔案被廣泛采信,民間材料則被貶抑;另一方面本質(zhì)化了歷史,對(duì)歷史學(xué)來說,任何材料都是有意義的,核心在于如何展開“文本分析”,發(fā)問的落腳點(diǎn)在文本“到底想說些什么?”以及“為什么這樣說?”
雖然前后延續(xù)了200多年,但在當(dāng)代瞻對(duì)口傳材料里,幾乎所有事跡最后都錯(cuò)誤地疊加在貢布郎加一人身上,他也被稱為惡魔或護(hù)法神,有各種暴力神異的傳說。顯然,這些材料并非事實(shí),而且從敘事方式來說是反邏輯的。阿來將之稱為地方的“敘事迷宮”,造成“時(shí)空交錯(cuò)的魔幻之感”,以此來說明藏區(qū)的落后、循環(huán)與歷史停滯。但反過來,從藏族歷史敘事風(fēng)格來看,把惡魔收伏為護(hù)法神,意味著藏傳佛教征服原始苯教、教化藏地全境的過程;與此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貢布郎加對(duì)佛法僧三寶的不敬,對(duì)瞻對(duì)來說,也是在表明一種宗教和政治意義上的地方性和多樣性,這是一對(duì)永恒的糾纏和張力。本地材料顯示,瞻對(duì)上中下三個(gè)土司家族都是從一個(gè)叫喜饒降澤的僧人開始,跟隨西藏的八思巴去北京覲見忽必烈,由于在忽必烈面前展示了獨(dú)特法力,受職回家,稱為“瞻對(duì)本沖”,這是瞻對(duì)地名的來歷。這個(gè)起源敘事相當(dāng)精巧,隱含的真相是,既有佛教化過程,也有與西藏及中央王朝的直接關(guān)聯(lián),且這種關(guān)聯(lián)是等級(jí)性的。這個(gè)結(jié)構(gòu)也分明地顯示了一種歷史人類學(xué)家王明珂所說的“英雄祖先”和“兄弟祖先”歷史心性的結(jié)合,加上關(guān)于瞻對(duì)“夾壩”(劫掠)的描述,反映了藏區(qū)較為惡劣的人類生態(tài)。而口傳資料對(duì)貢布郎加傳奇的反復(fù)強(qiáng)化,反映出來的現(xiàn)實(shí)是,在國家政治一體、藏區(qū)文化相似性之下,中心與邊緣、民間與廟堂、樸蠻特質(zhì)與文明教化之間的辯證距離。尤其在歷史上藏區(qū)雙重多封眾建的背景之下,這種塑造地方強(qiáng)人和主體性的敘述結(jié)構(gòu)就更明顯。
理解非虛構(gòu)寫作需要分辨事實(shí)、真相和現(xiàn)實(shí)。王明珂指出,事實(shí)是真實(shí)存在的;真相是為事實(shí)所做的注解或進(jìn)一步的描述,是事實(shí)與現(xiàn)實(shí)之間的交錯(cuò)關(guān)系,是主觀、模糊以及飽含爭(zhēng)議的;現(xiàn)實(shí)則是一個(gè)社會(huì)中存在的、普遍的、受政治權(quán)力建構(gòu)與維持的人群區(qū)分體系,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習(xí)俗、常識(shí)、社會(huì)規(guī)范以及審美觀。現(xiàn)實(shí)讓事實(shí)(或者非事實(shí))產(chǎn)生社會(huì)意義。
一直以來,許多評(píng)論者都糾結(jié)于阿來身份的復(fù)雜性和模糊性。但評(píng)論者未必注意到的另一個(gè)維度是,阿來的身份認(rèn)同也在發(fā)生變化。通過仔細(xì)梳理,我把阿來創(chuàng)作史約略分為三個(gè)階段:2000年以前作為藏族作家的阿來;2000-2008年退守到康巴、嘉絨本位上;2008年以后傾向于強(qiáng)調(diào)中華民族乃至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當(dāng)然這些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是由一系列標(biāo)志性事件構(gòu)成的,個(gè)人身份認(rèn)同也并非瞬息劇變且在每一個(gè)階段都是相對(duì)混雜的。《瞻對(duì)》是第三階段的作品。從阿來自己的表述可以看出,寫作本書的核心目的之一,是要揭示并防止內(nèi)部(族裔性)民族主義的興起導(dǎo)致削弱多民族共同的國家意識(shí)。所以,阿來固然也批評(píng)王朝和國家的種種不足,但主要還是針對(duì)舊時(shí)代政治哀其不幸、怒其不爭(zhēng)的批判,從而對(duì)比并反思新時(shí)代以來的成就。因此就文類的選擇來看,采用“非虛構(gòu)”形式是明確地表明歷史是不容虛構(gòu)的。在這里,非虛構(gòu)寫作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象征。
進(jìn)一步說,就論與“非虛構(gòu)”最直接相關(guān)的事實(shí)層面來看,敘事尺度的選擇會(huì)產(chǎn)生完全不同的歷史結(jié)果。在紀(jì)錄片《文學(xué)的故鄉(xiāng)》里,阿來說自己連導(dǎo)演都不算,最多只算是舞美師,其實(shí)是暗指自己是一個(gè)客觀、中立的觀察者,他只設(shè)置時(shí)間和空間,而不干預(yù)人物和事件。但從空間尺度來看,寫瞻對(duì)戰(zhàn)爭(zhēng)如果只寫到康巴土司的內(nèi)部關(guān)系,或只寫到川藏之爭(zhēng),或者像《瞻對(duì)》一樣最終放到中印英俄的區(qū)域世界關(guān)系中來談,產(chǎn)生的歷史感是完全不一樣的;從時(shí)間來看,正如王明珂舉例的,美國“歷史”是從印第安人、“五月花”、非裔、或是亞裔到達(dá)美洲寫起,臺(tái)灣“歷史”是從原住民、閩粵移民、或是“國府”遷臺(tái)寫起,盡管都是事實(shí),但其導(dǎo)致的歷史記憶和對(duì)當(dāng)下族群關(guān)系的看法,會(huì)大相徑庭。《瞻對(duì)》敘事是截面式的,開篇第一句“那時(shí)是盛世。康乾盛世”,無疑已經(jīng)奠定了籠罩性的帝國(國家)視角,自然也就易于最終推出一切都是大勢(shì)所趨的結(jié)論。
總而言之,就如海登·懷特提出的“作為文學(xué)虛構(gòu)的歷史文本”,或者后現(xiàn)代人類學(xué)所反思的“作為詩學(xué)與政治學(xué)的民族志”,既然歷史學(xué)和人類學(xué)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關(guān)于真實(shí)性的質(zhì)疑辯難之中,我們對(duì)文學(xué)非虛構(gòu)與否的關(guān)注,可能更應(yīng)該落腳在共情地理解文本背后的作者面對(duì)何種真相與現(xiàn)實(shí)、嘗試傳遞何種歷史觀念上。

個(gè)人生活史的寫作實(shí)踐
李依蔓
10年前,三明治還是一個(gè)獨(dú)立媒體平臺(tái)和創(chuàng)新人群社群,三明治這個(gè)名字來源于“三明治一代”(The Sandwich Generation)這個(gè)發(fā)源于美國的文化概念,形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但我們把“三明治”的意涵擴(kuò)大到家庭結(jié)構(gòu)之外,指代一種像三明治一樣的“夾層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往往同時(shí)體現(xiàn)在個(gè)人生活和時(shí)代特征上。
10年前,30歲左右人群出生于1980年左右,他們的成長(zhǎng)伴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的進(jìn)程,之后是國企改革或企業(yè)重組引發(fā)“下崗潮”,“鐵飯碗”整齊劃一和穩(wěn)定的生活方式成為過去,技術(shù)引發(fā)的第一波互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業(yè)熱潮剛剛開始,市場(chǎng)和社會(huì)為年輕人提供了比父輩更多的選擇和機(jī)會(huì),但也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和風(fēng)險(xiǎn)。
因此對(duì)于他們而言,可以選擇相對(duì)安穩(wěn)的生活,努力建立和維持“三十而立”的傳統(tǒng)中產(chǎn)身份,但所受的教育和全新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又讓他們不甘于此,于是很多人開始思考與父輩生活不同的可能性,并思考“我是誰”,要過怎樣的生活,并嘗試作出創(chuàng)新生活的實(shí)踐。雖然這種實(shí)踐充滿了挑戰(zhàn)和困難,他們普遍處于一種“夾層狀態(tài)”中,像一只三明治。當(dāng)時(shí),“三明治”提出的口號(hào)是“三十明志”,以個(gè)人生活史的寫作實(shí)踐,是用以“明志”的最主要行動(dòng)。
最初4年,個(gè)人生活史寫作的實(shí)踐主要通過三明治獨(dú)立媒體團(tuán)隊(duì)來完成。我們用人物報(bào)道、新聞特稿的方式,記錄30歲上下人群探尋自我、生活創(chuàng)新和進(jìn)行困局突圍的真實(shí)故事和深度文化觀察。但僅由團(tuán)隊(duì)觀察并記錄的人群和時(shí)代切片終究是少數(shù),并且我們希望三明治成為一個(gè)“寫作+行動(dòng)”的充滿變化和可能性的創(chuàng)新文化平臺(tái),讓更多的青年人用寫作來書寫自己的真實(shí)生活。
從2015年開始,三明治的個(gè)人生活史書寫實(shí)踐從狹義的“我們寫”變成了更廣泛意義上的“我們寫”,倡導(dǎo)每一個(gè)珍視文字和寫作的普通人來寫,試圖呈現(xiàn)更多元的中國當(dāng)代個(gè)人史和社會(huì)文化的切片記錄。
我們通過這些寫作者看到了更多元和豐富的中國面貌。有關(guān)于時(shí)代和社會(huì)的,比如中國人如何在非洲賣手機(jī)、緬甸華人的真實(shí)生活狀況、一位跨性別者如何找到裝在男性身體中的女性;有關(guān)于年輕人生活選擇的,比如兩個(gè)年輕人決定合作生養(yǎng)孩子但不結(jié)婚、網(wǎng)絡(luò)女主播的愛恨江湖;有關(guān)于家庭的,比如一位酗酒的父親、一位和阿茲海默癥斗爭(zhēng)的婆婆、一個(gè)家庭20年的下崗人生。當(dāng)這些寫作者在寫作時(shí),就在進(jìn)行一種溫和的生活突圍。
然而寫一篇達(dá)到一定完整度的作品,對(duì)于未經(jīng)過專業(yè)文學(xué)訓(xùn)練的寫作者來說,是有一定挑戰(zhàn)的。于是我們推出了更輕盈的、側(cè)重社交的寫作項(xiàng)目——每日書,每天記錄300字,連續(xù)寫30天。參與者可自由確定記錄的主題,無論是寫生活日常,還是寫某一段重要的經(jīng)歷或故事。寫作者們的背景非常多元,他們可能是媒體人、公務(wù)員、設(shè)計(jì)師、創(chuàng)業(yè)者、全職媽媽、老師、互聯(lián)網(wǎng)運(yùn)營(yíng)、品牌公關(guān)、銀行職員、咖啡師、醫(yī)生護(hù)士……一位護(hù)士回憶2003年自己參加抗擊SARS疫情的經(jīng)歷,一個(gè)民宿主人寫下自己在家鄉(xiāng)湛江硇洲島開民宿的經(jīng)歷,一個(gè)媽媽寫下孕期最后30天迎接孩子到來的心情,一個(gè)微信重度依賴者記錄自己卸載微信30天的變化。
我們還發(fā)起了不同主題的寫作工作坊,以及寫作項(xiàng)目短故事學(xué)院,由編輯和寫作者一對(duì)一地進(jìn)行溝通并指導(dǎo),幫助每一個(gè)想寫自己的某段經(jīng)歷和故事的寫作者,把一個(gè)想法落地成一個(gè)好故事。其中比較有話題性或者社會(huì)價(jià)值的作品,我們會(huì)挑選出來再進(jìn)行編輯,在平臺(tái)發(fā)布。
在三年來發(fā)表的短故事作品中,我們得以更系統(tǒng)地窺見當(dāng)代中國人真實(shí)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也有許多隱而未見的故事浮出水面。很多時(shí)候我們都會(huì)為作者們自我袒露和剖析的勇敢和坦誠所震撼。每個(gè)人都可以為自己發(fā)聲,每一段經(jīng)歷、每一個(gè)故事都重要,有的對(duì)個(gè)體重要,有的有更大的在社會(huì)層面探討的價(jià)值,讓那些 “The Unrepresented Voice”(未被代表的聲音)顯露出來。寫作這個(gè)行動(dòng)以及它們匯集起來的聲音,聯(lián)結(jié)起了我們當(dāng)下的這個(gè)時(shí)代。
我們是怎樣的一代人?在一個(gè)什么樣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生長(zhǎng)起來,受到了怎樣的影響?面臨著哪些困境?在三明治過去幾年記錄下的故事中,我們得以窺探到一些痕跡。
比如和10年前相比,出生于獨(dú)生子女政策下更年輕的一代人,似乎擁有更優(yōu)越的物質(zhì)條件、社會(huì)資源,有更多選擇機(jī)會(huì)和可能,但他們更多地陷入一種原子化的孤獨(dú),他們面臨著更強(qiáng)大的控制,這種控制來自于家庭,也來自于更強(qiáng)力、更無孔不入的資本和商業(yè)浸透。我們也面臨著社會(huì)飛速發(fā)展帶來的巨大撕裂,城鄉(xiāng)的撕裂,階級(jí)的撕裂。他們面臨更頻繁出現(xiàn)的無力感,虛無感,意義的消解,理想主義的崩塌,許多人缺乏愛與被愛的經(jīng)驗(yàn)和能力。當(dāng)被迫以成年人的身份面對(duì)社會(huì)時(shí),很多人往往展現(xiàn)出一種未戰(zhàn)先怯的姿態(tài),典型的一些說法如“喪”、“社畜”,自我在社會(huì)的巨大齒輪之間變成了碎片式的存在,商業(yè)價(jià)值成了壓倒性的成功標(biāo)準(zhǔn)。
寫作者們?cè)谖淖种姓宫F(xiàn)出強(qiáng)大的自省感知力,通過書寫去重新構(gòu)建關(guān)于自我和生活的意義,去觸發(fā)更多的行動(dòng)可能。這些故事就是鮮活跳動(dòng)著的時(shí)代脈搏。接下來,我們希望借助一些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以及個(gè)人生活史書寫實(shí)踐,繼續(xù)對(duì)這一代三明治的心靈圖景進(jìn)行研究和分析,去不斷提出問題,并嘗試作出回應(yīng)。
每一代人,都一定會(huì)找到和當(dāng)下時(shí)代交手的方式。這一代年輕人也會(huì)找到不同可用的、好用的方法和路徑,去達(dá)成對(duì)自我的梳理、確認(rèn)、接納,去和他人建立更深層次的理解和連接,去生成更持久、更有意義和影響力的社會(huì)行動(dòng),去進(jìn)行向內(nèi)和向外的探索,去“突圍”。而真誠地寫下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和故事,形成一些相對(duì)完整而不是碎片化的敘事,可以是一切行動(dòng)中一個(gè)有力的開始,也是讓我們看見自己在時(shí)間之河中身在何處的錨。

非虛構(gòu)如何書寫城市
呂 正
“非虛構(gòu)”在中國這些年經(jīng)歷了橫空出世到遍地開花的過程。這個(gè)過程就像大家以前只喜歡看《動(dòng)物世界》,人們?cè)陔娨暀C(jī)前——隔一個(gè)安全距離看動(dòng)物們廝殺、捕獵,一個(gè)畫外音平靜地告訴我們發(fā)生了什么。很快我們變得不滿足,要開始看《荒野求生》,看貝爺從飛機(jī)上跳下來,看人吃蟲子……挺刺激的。
“上海相冊(cè)”是一個(gè)很新的非虛構(gòu)項(xiàng)目,首季創(chuàng)作在2020年8月間刊發(fā)完畢。在參與這個(gè)項(xiàng)目之前,我剛結(jié)束在“武康大樓口述史”項(xiàng)目的工作。我在撰寫“武康大樓”相關(guān)報(bào)道時(shí),收到了老同事許海峰的邀請(qǐng),他提議做一個(gè)城市寫作與攝影交叉、跨界的“非虛構(gòu)”項(xiàng)目,項(xiàng)目需要一位特約編輯,熟悉作家,懂圖片,而他知道我一直在推動(dòng)城市題材的創(chuàng)作。2020年3月,我們啟動(dòng)了“上海相冊(cè)”,許海峰開始挑選攝影師的作品,而我開始向身邊的作家發(fā)出邀約。
“上海相冊(cè)”的第一期是作家于是的《天臺(tái)造城記》和攝影師徐昕的攝影作品“the Metropolis大都會(huì)”。“上海相冊(cè)”一共找了22位上海在地作家,根據(jù)22位上海在地?cái)z影師每人一組的攝影作品進(jìn)行創(chuàng)作。“在地”是指長(zhǎng)期生活、工作、創(chuàng)作在上海的作家,當(dāng)然這其中有不少是土生土長(zhǎng)的上海人。“上海相冊(cè)”也自帶了創(chuàng)作者的時(shí)差感,攝影作品和文字是有對(duì)話和對(duì)望意味的。攝影師的作品本身創(chuàng)作跨越的年份非常大。有些作品是拍攝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也有些作品就是拍攝于2020年,包括新冠疫情中的上海。參加項(xiàng)目的攝影師普遍的年齡是“50后”,我們也有選擇“80后”的攝影師馬良、周仰,“90后”的攝影師徐昕。在挑選作家的時(shí)候,我有意識(shí)地選擇“80后”、“90后”,也有“70后”。比如走走、于是、王若虛、吳越、栗鹿、陸茵茵、錢佳楠、三三、負(fù)二等作家參與“上海相冊(cè)”的寫作,他們中有長(zhǎng)期從事純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從事翻譯創(chuàng)作的,也有專欄寫作較多的。
這個(gè)項(xiàng)目沒有那么多的官方色彩,更像是澎湃新聞和上海作協(xié)《萌芽》雜志藝術(shù)性的探索和嘗試。描繪上海這個(gè)重要的命題,離不開攝影和文字共同的努力。許海峰和我一開始就想,一定要堅(jiān)持盲寫,作家是以“盲寫”的方式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作家首先并不知道拿到的攝影作品是誰拍的。作家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理解或者想象自由發(fā)揮。有一位參加項(xiàng)目創(chuàng)作的作家叫btr,他本人很“跨界”,在后來的作家和攝影師見面會(huì)上,他揶揄“盲寫”的行為很像在“相親”,于是我們笑稱我們的項(xiàng)目是“上海相親”。而btr拿到的那組照片是關(guān)于上海的公園的,上海的公園非常出名的功能就是“相親”,這是雙響炮式的巧合。
我覺得,作家和攝影師的非虛構(gòu)跨界合作,就像宇宙中的引力場(chǎng),攝影師的作品先在那里,以恒星、星體做比喻,有光有熱,那是看得見的,還有看不見的,需要意會(huì)的,那就像引力。作家的創(chuàng)作可以是如行星圍繞,也可以如彗星,出發(fā)漫游。比如在面對(duì)攝影師朱鋒的《上海零度》系列作品,作家王若虛寫道:什么樣的城市看不見呢?是未來的城市。城市會(huì)自我繁殖,自我膨脹,那些“生活開拓者”往往生活在都市的最外沿,你這一刻走過的荒蕪和蒼涼,幾年后或許就是平地起高樓,或許就是燈火通明,就是交通擁堵。而過來人多半只會(huì)感慨昔日的蒼涼,不會(huì)去懷念它。如果人類的基因里都有懷念它的部分,那么今天也就沒有那么多城市,而是人人都想做個(gè)荒野獵人。這是他對(duì)攝影作品的個(gè)人理解。所以,在這個(gè)非虛構(gòu)項(xiàng)目里,照片各有特色,文字也各有殊異,有的像讀后感,有的像散文詩,有的像短篇小說。有些圖文比較協(xié)調(diào),有些似乎兩不相干,誰也無法預(yù)料這個(gè)項(xiàng)目到底會(huì)有怎樣的結(jié)果,然而這正是實(shí)驗(yàn)的應(yīng)有之義:勇于探索,大膽嘗試,用創(chuàng)造性思維打破畫地為牢。
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首先是“有趣”。幾乎每個(gè)參加這個(gè)項(xiàng)目的作家、攝影師都是抱著這樣的態(tài)度來嘗試;其次是“距離感”,因?yàn)樽骷抑安]有看過這些照片,一些人覺得這是一次“實(shí)驗(yàn)”,更多的人說這是一次“冒險(xiǎn)”。項(xiàng)目第一季收官的時(shí)候,我們舉辦了一場(chǎng)“握手會(huì)”,請(qǐng)大家交流創(chuàng)作感受。攝影師和作家相見的時(shí)候會(huì)小心翼翼地試探。攝影師尋求的答案是:你讀懂了我的照片沒有?你是不是表達(dá)了我要拍的意圖?當(dāng)“解讀”有可能等同于“誤讀”時(shí),我想“有感而發(fā)”也基本等同于“跑題”了。正如作家三三在《異化,或時(shí)間秩序的重置》中說的:“這一瞬間不供應(yīng)任何意義,僅作為一個(gè)停頓。樟樹舉著一身鱗片似的葉,由于風(fēng)的參與,日光變得輕盈多動(dòng)——當(dāng)你凝視這一切時(shí),你與這些日常景象的交流也投影到鏡頭里,而你的自我也留存其中。”
2018年上海雙年展項(xiàng)目總協(xié)調(diào)、策展人施瀚濤先生談到他對(duì)這個(gè)非虛構(gòu)項(xiàng)目的理解,他覺得作家并不是以“評(píng)論”的視角去看待攝影作品,而是從“創(chuàng)作者”的視角進(jìn)行再創(chuàng)作。“激發(fā)和刺激了不可預(yù)期的圖片與文字的新關(guān)系,有著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雖然這樣的跨界合作在其他地區(qū)國家有著很多版本,但落地上海書寫上海城市文化,依然有著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我們希望“上海相冊(cè)”可以成長(zhǎng)為一個(gè)具有實(shí)驗(yàn)性的非虛構(gòu)平臺(tái),給予讀者開放性的閱讀體驗(yàn),讓人各取所需獲得更多的啟發(fā)。我希望呈現(xiàn)的是一個(gè)有體溫、有細(xì)節(jié)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