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半個多世紀(jì)后 為自己最負(fù)盛名的小說劃上句號 ——評最新引進(jìn)出版的約翰·勒卡雷小說《間諜的遺產(chǎ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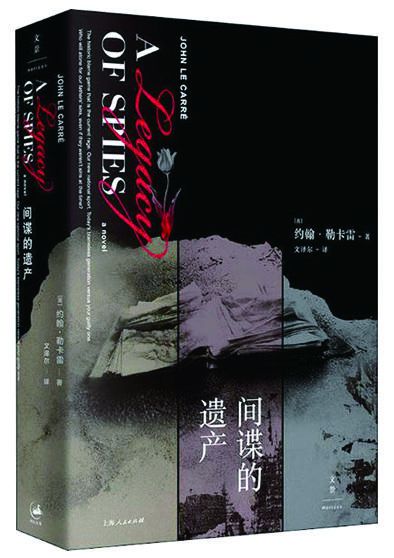
1999年9月11日,一位滿頭銀發(fā)的英國老太太在位于倫敦東南角貝克斯利希斯的自家花園開了一場簡短卻引人注目的新聞發(fā)布會。這位寡居多年的老婦人名叫梅利塔·諾伍德,當(dāng)時已經(jīng)87歲高齡,慈眉善目、戴著老花鏡,對著蜂擁而至的媒體讀了一份簡短的聲明,承認(rèn)自己曾是間諜,代號是“霍拉(Ho l a)”。在1972年退休前,她一直是英國有色金屬研究協(xié)會的秘書,有機(jī)會接觸大量涉及英國核研究的機(jī)密文件。于是,在遠(yuǎn)離英國有色金屬研究會和間諜生涯近30年后,梅利塔的真實(shí)身份被突然曝光,乃至引發(fā)媒體關(guān)注和意外的政治風(fēng)波。
翻開最新引進(jìn)出版的英國作家勒卡雷的小說《間諜的遺產(chǎn)》,很容易聯(lián)想到梅利塔的故事。一位退休幾十年的老間諜,卻因?yàn)橐粋€偶然事件被重新牽扯進(jìn)當(dāng)年的不堪往事。在小說開頭,隱居法國、金盆洗手多年的彼得·吉勒姆為了自己的退休金,不得不重返“圓場”。在那兒,他無奈地接受了“馬戲團(tuán)”年輕一代有關(guān)60年前“橫財(cái)行動”細(xì)節(jié)的種種問詢。而所謂“橫財(cái)行動”正是勒卡雷在代表作《柏林諜影》中所講述的那樁詭譎悲劇。縱然過去了數(shù)十載,但那場悲劇依舊“陰魂不散”,受害者的后人們居然找上了門。而21世紀(jì)的“圓場”年輕一代卻只是想把這個陳年的“老麻煩”丟給同樣老邁的彼得·吉勒姆,讓他發(fā)揮“余熱”充當(dāng)組織的替罪羊。
盡管《間諜的遺產(chǎn)》被宣傳為《柏林諜影》的續(xù)作,但其實(shí)也可以稱其為《柏林諜影》的前傳。年逾九十的勒卡雷新作中的大量篇幅都是為《柏林諜影》故事所做的鋪墊,而五六十年后的故事與其說是“續(xù)集”,莫不如說是一場事與愿違的追憶。另一方面,若沒有讀過《柏林諜影》又或是“史邁利系列”的前作,倒還是可以直接捧起《間諜的遺產(chǎn)》。雖然會錯過一些致敬前作的典故和無關(guān)主旨的細(xì)節(jié),但同樣也可以回避掉一些敘述邏輯和常識上的“硬傷”,例如史邁利的登場。
在此之前,史邁利的上一次出現(xiàn)還得追溯到1990年出版的《史邁利的告別》(又譯為《神秘朝圣者》)。在《間諜的遺產(chǎn)》中,2015年時彼得·吉勒姆本人已經(jīng)是78歲的老人,但依舊可以跟新同事們玩“捉迷藏”的間諜游戲。若根據(jù)《召喚死者》中的描述,身為大學(xué)生的史邁利是1926年加入了“馬戲團(tuán)”,那么他應(yīng)該是在1905年前后出生的。這就意味著在《間諜的遺產(chǎn)》的故事中,史邁利高齡已經(jīng)超過110歲。而在《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勒卡雷把史邁利加入的年齡推遲到了1937年,但即便如此,史邁利在《間諜的遺產(chǎn)》中也成了一位超過100歲的超級壽星。
有鑒于此,新讀者的一大優(yōu)勢就是在閱讀時可以不用背負(fù)這類前作設(shè)定上的尷尬,只需享受文字和智識上的冒險。勒卡雷也巧妙地將《柏林諜影》的故事折疊塞入了新作之中,讓人有了重溫當(dāng)年這部經(jīng)典之作的興趣。
初看起來,《間諜的遺產(chǎn)》可能是勒卡雷諸多作品中,較為好讀的一部,以至于能讓人產(chǎn)生可以一個晚上輕松翻完的錯覺。然而,若細(xì)細(xì)探究,卻能發(fā)現(xiàn)作者布下的暗線與沖突。例如小說中,往往以檔案文件和私人回憶彼此交織的方式來回溯五六十年前的那個冷酷故事。因此你甚至可以把《間諜的遺產(chǎn)》當(dāng)作一本“書信體小說”來讀。檔案與回憶之間彼此補(bǔ)充,卻又充滿矛盾,而所謂“真相”似乎就隱藏其中,但又讓人時不時掩卷思考與質(zhì)疑。而現(xiàn)實(shí)的情報(bào)工作,除了極少部分“剝頭皮組”那樣的外勤任務(wù)外,絕大部分都是在文字、言辭、回憶和互相比對中查找線索,進(jìn)而抽絲剝繭發(fā)現(xiàn)如碎片般的些許“真相”。在小說中,彼得·吉勒姆即便曾目睹、經(jīng)歷過當(dāng)年柏林冷夜中發(fā)生過的一些事,但確實(shí)很難窺得全貌。即便是在幾十年后,重讀檔案,他也不過是嘗試著拼湊歷史碎片。真正洞悉整個事件的只有當(dāng)年的“老總”和史邁利本人。然而,你也別指望在小說的最后就能抵達(dá)勒卡雷間諜世界的終點(diǎn),整個故事可能就是一個周而復(fù)始的循環(huán)旅程,亦如他之前回憶錄的書名《鴿子隧道》。
勒卡雷間諜小說的懸疑背后實(shí)則都隱藏著一個母題:極端環(huán)境下,每個人的道德選擇及其代價。哪怕已經(jīng)過去半個多世紀(jì),哪怕檔案都已殘缺不全,哪怕當(dāng)代人早已淡忘,但他筆下的人物依舊要為當(dāng)年的選擇承擔(dān)后果,或早或晚付出各自的代價。沒有信念支撐的犧牲在“圓場”年輕一代看來,自然也是無法理解的。他們對冷戰(zhàn)時代的種種幾乎一無所知,以至于在“審訊”吉勒姆時可以輕松地吐槽:在你們那個時候,無辜者的死亡或許是可以接受的,但如今情況不同了。背負(fù)這個“詛咒”的吉勒姆卻是直面背后冷酷的老特工,而能解除這項(xiàng)道德枷鎖者正是他當(dāng)年的上司史邁利。
在勒卡雷的小說中的“叛國者”都不是為了金錢,正如現(xiàn)實(shí)中的“劍橋五杰”、梅利塔·諾伍德,大多都是處于信念與理想而選擇此道。2005年,梅利塔·諾伍德以93歲高齡去世,死前也從未對自己的間諜行為表示后悔。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我之所以會做這些事并不是為了金錢,而是為了阻止一個新制度的失敗”。其實(shí),他們與史邁利終究都是同一類人,只不過是選擇了不同的出口。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縱然立場水火不容,但史邁利、吉勒姆或許反而會能理解梅利塔們當(dāng)年的動機(jī)。面對帝國衰敗的現(xiàn)實(shí),試圖力挽狂瀾的情報(bào)機(jī)關(guān)自身也在不斷地墮落,變得更加卑劣與虛偽。借彼得·吉勒姆之口,勒卡雷還吐槽了如今的“圓場”。在他看來,如今“圓場”的情報(bào)工作無非是官僚化的重復(fù),喪失靈魂與信念。經(jīng)歷、目睹這一切的史邁利或許真需要有一種“歐洲精神”來支撐自己的信念。
勒卡雷本人曾經(jīng)在原版《間諜的遺產(chǎn)》的新書發(fā)布會上直率表達(dá)他對當(dāng)今西方世界的憂慮。在他看來,“某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正在發(fā)生,我們理應(yīng)清楚意識到這一點(diǎn)”。他口中的“糟糕之事”包括了英國脫歐、民粹主義興起以及民眾對歐洲精神的背離,也可能還有他對當(dāng)代英國人喪失崇高目標(biāo)感的失望。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臺的采訪時,勒卡雷指出:2016年英國公投決定脫歐讓他感到非常失望,而他寫這本小說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為歐洲辯護(hù)。
不過,也如《經(jīng)濟(jì)學(xué)人》評價的那樣:在勒卡雷的《間諜的遺產(chǎn)》中,雖然史邁利一再強(qiáng)調(diào)他身負(fù)歐洲精神的寶貴價值,但他所表現(xiàn)出的依然是一個地道的英國紳士形象。
(作者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xiàn)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