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圖內(nèi)斯《審查官手記》:以患病形式“沾染”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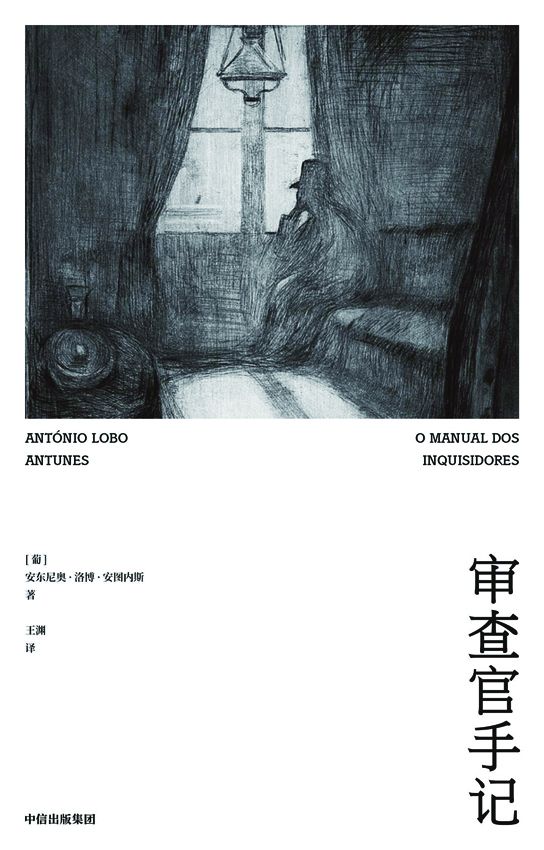
《審查官手記》是一部奇異晦澀,“挑釁”讀者的“怪杰之作”。作者安圖內(nèi)斯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一樣,堪稱當代葡萄牙語文學的“雙子星”。從某種角度看,安圖內(nèi)斯屬于跨界寫作,作為長期研究心理學的醫(yī)師,他對人性異化與社會病態(tài)抱有抑制不住的診斷激情。可以說,他讓小說變得更像“病例報告”。《審查官手記》里的回憶與敘述充滿反常的扭曲變異,偏離與混亂,正是對敘事可能性的極端實驗。在作家看來,清晰可辨的意象、敘事節(jié)奏的穩(wěn)定、人物和情節(jié)的秩序,不過是經(jīng)過理性壓抑、自我審查的結果。
安圖內(nèi)斯正是想提供一種“原生文本”:充滿矛盾狐疑、閃回跳接,沉默躁郁反復交替的敘述,就像夢、醉與病的三位一體。《審查官手記》被稱為作家最黑暗的作品,直抵人類無意識的幽暗之地。不正常的文本,需要非常態(tài)看待。敘述者的“失控”,意味不再受作家“審查”,而是向所有讀者敞開的虛空。這或許是“審查官”(召喚讀者批評)之謂的真實意圖。小說的“述評體”頗為獨特,“共分為五個報告,每一篇分為六小節(jié),一位主要人物分三次敘述,另外三人各有一次評論的機會”。(《譯后記》)這讓我想起循環(huán)賽制,結構與程序的均衡之美,與敘事的繁雜迷亂,造成幾近怪異的反差。
其潛在意圖很明顯:即使人物的身份地位有云泥之別,但在敘事話語上卻顯露平等制衡。部長弗朗西斯科與兒子若昂、女管家蒂蒂娜、私生女保拉、情婦米拉這5個敘述者,和外圍14個評論者,完全超越了復調(diào)小說的多聲部合奏。因為安圖內(nèi)斯的諸多敘事者,并非聲音的簡單疊加聚合。相反,眾聲喧嘩的“離散型”與“非和諧”壓過了慣常的和聲。而紛亂嘈雜,或許是作家意欲呈現(xiàn)的敘述生態(tài)。
盡管作家反感原型批評和歷史分析,但評論家們依然發(fā)現(xiàn)了某種現(xiàn)實映射。作品文本風格與作家批判的現(xiàn)實生態(tài),恰好是協(xié)調(diào)互生的。他用小鎮(zhèn)帕爾梅拉上的一個莊園,衍射整個葡萄牙社會的歷史圖景。歷史上,經(jīng)濟學教授出身的薩拉查,統(tǒng)治葡萄牙近半個世紀,他將對外殖民與國內(nèi)農(nóng)業(yè)傳統(tǒng)結合起來。小說里的莊園就是溝通農(nóng)業(yè)社會和政治時局的空間隱喻。部長弗朗西斯科和少數(shù)寡頭在這里關起門來,玩弄社會政治。這種家國宗法的高度同構,移植并擴散成一種關系,即部長弗朗西斯科對雇工仆人的任意處置,與父權制的獨裁政府之間本質(zhì)相同。
有意味的是,安圖內(nèi)斯強調(diào)小說的催眠、致幻功能。這是很多作家都未曾重視的接受心理。“你們需要陷入這些作品表面上的漫不經(jīng)心、暫停和冗長的省略,沉溺在陰影覆蓋的波浪搖擺之中,一點一點地,文本就會把你們帶去和致命的黑暗相見,這對精神的再生與革新至關重要。”“我提議的真正冒險,需要敘述者和讀者一同在無意識的黑暗和人性的根基處進行。”作為早年就研究醫(yī)學、成為作家后仍舊從事精神分析醫(yī)師工作的安圖內(nèi)斯,把“職業(yè)后遺癥”也帶入到創(chuàng)作里。你甚至有種直覺:小說是把葡萄牙社會當作病院環(huán)境,將一群人物當成需要治療的“病例”。
近于精神分析一樣的文本召引,相信自然而然能誘引讀者進入無意識層,探查人性的基底。從而,我們理解了作家所謂放棄“討論主題”的真實意圖。那就是讓讀者脫離“意識層”的控制,進入不加設防的無意識。作家將這種接受過程稱為“以患病的方式沾染書”,而非閱讀。只有經(jīng)歷“感染”,才會在康復時(合上書,回歸自身時)滿載而歸。若昂少爺?shù)淖园拙驼f明了敘事的虛空。“無我”是行為的條件,人物的透明性得到突顯。“婚后他們請我去銀行上班,條件是在月末的工資單上簽字,條件是我不許異想天開,不許搞什么項目,不許在會議上發(fā)言,也不許去工作,事實上,條件就是我不再存在,對我的岳母來說不存在,對我的妻子來說不存在,對我的孩子們來說不存在。”
小說如同精神錯亂的囈語,是一堆不同時空生活場景的“混剪”,強制拼貼。博士老爺在莊園的墮落淫亂,法庭打離婚官司的若昂少爺,岳母打橋牌時的輕蔑……這些印象成了倒帶循環(huán),不斷重現(xiàn),就像壞掉的光碟,總跳不過故障影像。如老爺說:“她們要怎樣,我都會做,但我從不摘下帽子,這樣別人才知道誰是主人”;岳母對女婿的蔑視,“你是真蠢還是裝傻”。這些口頭禪似的句子,被作家循環(huán)插播,指認出人物最難抹除的無意識印痕。
管事女兒只有在黑夜的長明燈里才能看到幸福寧靜,白日卻是死亡重來的時刻。黑白顛倒,惡魔就在白日(現(xiàn)實里)伸出魔爪。老爺欺辱一切可被奴役的女性,看待她們?nèi)缤︷B(yǎng)母畜。女人與奶牛的描寫拼接,正有如此用意。這暗示我們一種罪惡邏輯:暴力已超出階級壓迫的奴役性,轉(zhuǎn)變?yōu)槿藢Α吧蟆钡牧枞琛H舭荷贍斒且娮C父親不堪獸欲的敘事者。“我從沒有母親,沒有兄弟姐妹,我是獨生子。”在我看來,“猜母親”或許是小說的游戲,聽上去像荒謬惡作劇,卻是罪惡的果實。“而這張照片里的女人很像那位女管家,她會開著燈在我身邊‘小若昂、小若昂’,直到我入睡。‘會是女管家嗎’?”
如果我們按作家提示,用“符號”、“私語”或“幻覺”來看待故事,就會發(fā)現(xiàn)更多寓言象征。如部長造訪時,不僅對人下達高壓禁令,甚至對亂叫的烏鴉也大肆射殺。那只阿爾薩斯狼犬的狂吠,也是犬牙幫兇的符號表達。排除異己和噪聲,追求絕對的死亡寂靜,是葡萄牙獨裁時期的精神寫照。甚至暴力也滲透于日常,如管事女兒的受迫害狂,持續(xù)出現(xiàn)的幻聽幻視,意味暴力的后遺癥更為恒久。“害怕廚娘會抓住我的脖子,拿刀把我的喉嚨割斷,害怕廚娘像博士老爺在畜棚里那樣扼住我的脖子。”“博士老爺?shù)钠砷_,背心敞著,大腿夾住我的腰,一邊笑一邊將小雪茄的煙霧吹到我的頸背,別動,小姑娘。”
博士老爺?shù)耐嗍桥c統(tǒng)治階層聯(lián)結,“合體”實現(xiàn)的。他與樞機主教大人、海軍上將、薩拉查教授、教皇的合影照片,說明是利益勾結的同盟。安圖內(nèi)斯實現(xiàn)了文本的復仇,他讓老爺從一個施暴者、強權者徹底蛻化成被人擺布的失能者。女護工把老爺當成“垂老的嬰兒”、稻草人、一個舊玩偶。“她們解開父親睡衣的布袋,打開襟門的拉鏈,在他極度消瘦、除了毛就是骨頭的雙腿間擺上便盆”,“我的父親下巴下垂,屁股綿軟,正嘗試用顫抖的袖子擤鼻涕”,“我的父親一言不發(fā),百依百順,一無是處,沒有小雪茄,沒有假牙,沒有嘴唇,沒有帽子,他像稻草人一樣躺在床墊上。”一個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之人,曾肆意發(fā)泄獸欲,蹂躪女人。這種近乎報應的“審判”,有種天然快感,它達到了小說內(nèi)在敘事倫理的制衡。沉默、順從、又無用,一切獨裁暴力都有衰落頹敗的殘局。
“博士老爺”的形象是暴戾腐壞的象征,他的中風代表貴族獨裁的坍塌,莊園毀棄就是隱喻。“博士老爺在如今的大廳里,沒有帷幔,沒有沙發(fā),沒有壁畫,沒有棋桌,沒有吊燈,沒有家具,露臺朝著荒廢的莊園傾倒,花壇近乎枯萎,鴿棚只剩殘垣,車庫里沒有輪胎的汽車慢慢腐朽。”虛構的部長老爺和現(xiàn)實獨裁者薩拉查都充滿對權力的迷戀。即使中了風,還忘不了恐怖統(tǒng)治的威權。“獵槍完了,威脅結束了,子彈沒了。”是否暗指那場沒怎么流血的“康乃馨革命”?事實上,安圖內(nèi)斯對革命的態(tài)度依舊是懷疑。他并不認為存在歷史進步。資本家佩德羅奪取莊園,成為新貴,取代老舊政治勢力。但本質(zhì)上,這并未改變社會的病態(tài)、異化與強權,前景依然混亂迷茫。
安圖內(nèi)斯成為福克納風格的承襲傳人,無論是風格、主題還是技法形式。《審查官手記》與《喧嘩與騷動》的親緣關系,如同直系血親。小說采用的述—評模式,可以視為一種內(nèi)在性“交互對話”,它在每個敘事小單元里都能實現(xiàn)小說動力上的“內(nèi)循環(huán)”。這種經(jīng)營設置,把不同人物的情感、判斷和視角高度壓縮,形成“沉積巖”一般的斷面。它們或相互補述,參差互見;或相互闡釋,相反相成;或在自我獨白和事件評價中,彰顯故事本身的多維分裂與意義褶皺。福克納多重人物敘事、罪惡與不幸的代系輪回,以及如河網(wǎng)稠密的意識流動,都在安圖內(nèi)斯的文本里得到“復刻”。他與塞利納的相似,則更多如姻親般“合體”。癔癥般的長句,不加標點,就像哮喘患者的呼吸困難,病態(tài)、骯臟和頹喪的氣氛雜糅,如同冷血動物的膚質(zhì),黏膩且潮濕。
作家反感那套社會學式的外部評論,它把小說直接“降維”成一堆問題的佐證注腳。這恰恰是全書最零散、最不重要的方面:“國家、男女關系、身份問題和對其的搜尋、非洲和殖民剝削的殘忍等等,也許在政治、社會或者人類學角度上,這些主題十分重要,但它們和我的作品一點關系也沒有。”這或許是對動輒大談后殖民、種族、性別、身份等“學院批評”的嘲諷。評論家們甚至會惶惑,如果不談這些主題,該怎么“下嘴”去談作品。安圖內(nèi)斯給出的答案是放棄自己的鑰匙,放棄每個人都有的萬能鑰匙,“只使用文本提供的鑰匙”。
這意味著不要濫用外部理論闡釋,要用文本批評保證一種內(nèi)在性、自足性和純粹性。不要把小說當成歷史背景簡單的回聲返照。安圖內(nèi)斯把作品視為“虛構幻想的實體化象征”,小說淪為虛像,“話語只不過是私密情感的符號,而人物、場景和情節(jié)只不過是表面的托詞,我只是引領走向靈魂背面的深處。”換言之,作家在意歷史幻象里的“意識界真實”。如果耽溺考證和比對,從小說里找尋“歷史批評”,顯然舍本逐末,并不明智。鮮有作家會在小說前大談“讀法”,但這看似自負的提醒卻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