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書環(huán)游地球︱紐約:《雨王亨德森》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huán)游地球》,既是重構(gòu)世界文學(xué)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dāng)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十六周 第四天
紐約 索爾·貝婁 《雨王亨德森》
跟巴黎一樣,紐約也一直是移民心目中的圣地,尤其是那些滿懷抱負(fù)的作家們。很多作家來到紐約追尋文學(xué)夢,這里云集了眾多美國出版社。甚至很多外地作家會定期造訪。1969年,就是在他的一次定期造訪時,我認(rèn)識了索爾·貝婁(Saul Bellow),彼時距離他獲諾貝爾獎還有七年。他那次來和出版作品或推廣活動有關(guān),但還有個浪漫的目的,他當(dāng)時和瑪格麗特·斯達(dá)茨(Margaret Staats)在一起,他正想娶她做第四任貝婁夫人(最終有五任)。他們曾訂婚過一段時間,后來瑪格麗特改變了主意。她給貝婁看了一篇我的日志,然后在一個星期六的早上,約我去跟貝婁見面。見我對十八世紀(jì)文學(xué)感興趣,貝婁建議我更廣泛閱讀當(dāng)時的作品。正因為他,還有我哥哥,同為文學(xué)學(xué)者的李奧(Leo),我才讀到了菲爾丁、笛福、理查遜和斯摩萊特。他還慷慨地為我的日志寫了一些夸贊的評語,“警告”說我可能成為一名作家。
貝婁被形容成那種“把書當(dāng)氧氣”的人,他是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等十九世紀(jì)偉大作家的作品長大的。他不僅被源于現(xiàn)代西班牙早期的流浪漢小說傳統(tǒng)所吸引,還喜愛十八世紀(jì)的書信體小說和諷刺作品。所以他讓我去讀理查遜和斯摩萊特并非巧合,不是每個人書單里都有斯摩萊特,但他的《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Expedition of Humphrey Clinker)是復(fù)調(diào)書信體創(chuàng)作的偉大試驗之一。就在我與他見面的數(shù)年前,貝婁已經(jīng)獲得了國家圖書獎,獲獎作品《赫索格》(Herzog,1964)還上了熱賣圖書榜,這本書的大部分都以雜亂無章的書信形式呈現(xiàn),全是貝婁筆下無休無止的,牢騷滿腹又糊里糊涂的主人公寫給各色想象中的收信人的信。說是想象的收信人是因為赫索格從來沒真的把這些長信發(fā)給老朋友、老情人和前妻們,而那些寫給類似于像尼采、上帝的信,他想發(fā)也發(fā)不出去。
貝婁上一本小說《雨王亨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1959)最有可能的模本是十八世紀(jì)的作品《老實人》,在《雨王亨德森》里,非洲取代了伏爾泰想象中的巴西,在這里,主人公遭遇一個全然非西方的文明,和當(dāng)?shù)卣軐W(xué)家一樣的國王進(jìn)行討論,并逐漸理解自己的世界。如同對伏爾泰筆下埃爾多拉多(El Dorado傳說中的黃金國)的再現(xiàn),瓦瑞瑞(Wariri)的首都就藏在群山中,與世隔絕,而國王達(dá)福(Dahfu)甚至有一支“亞馬遜女武士”組成的侍衛(wèi)隊。和伏爾泰一樣,貝婁從未踏足過他筆下的異域世界,但他的知識卻不止是來自那些旅行者的故事。他在西北大學(xué)獲得人類學(xué)學(xué)士,又去威斯康辛大學(xué)繼續(xù)攻讀碩士,所以不同于《老實人》,他的小說有扎實詳細(xì)的人類學(xué)背景。《雨王亨德森》中很多部落習(xí)俗,以及其中一些段落,都直接取自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茨(Melville Herskovits)的《東非的牛情結(jié)》(The Cattle Complex in East Africa,1926),這本書出版十年后,貝婁就在作者的指導(dǎo)下,在西北大學(xué)完成了自己的畢業(yè)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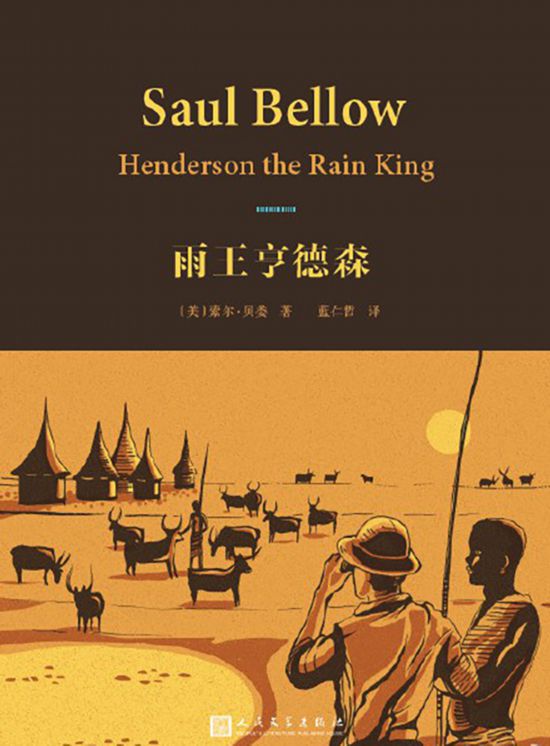
一般認(rèn)為,貝婁是個典型的芝加哥小說家,但創(chuàng)作《雨王亨德森》時,他住在紐約。他的主人公尤金·亨德森(Eugene Henderson)是小提琴家,也是一個養(yǎng)豬場主,他莫名其妙地在他康涅狄格州的莊園里開了養(yǎng)豬場。養(yǎng)豬場離紐約不遠(yuǎn),他還去紐約市57街找一個“叫哈珀以的匈牙利老頭”去修小提琴。貝婁筆下的紐約滿是像他一樣的移民。亨德森甚至用自己的身體比做紐約地圖:“我的臉就像是個終點站,就像中央車站,我是說——高高的鼻子張大的嘴,可以直達(dá)鼻腔,而眼睛就像隧道。”當(dāng)他跑到非洲去尋找自我時,仍然用紐約的參照物來給自己定位。所以當(dāng)聽到國王達(dá)福的聲音里帶有一點低沉的嗡嗡聲時,“讓我想起了悶熱夜晚紐約十六街發(fā)電站的聲音。”
對自己的突然出走,亨德森最好的解釋就是:“我心里有種騷動,一個聲音總在那兒喊,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這個聲音每天下午都會響起。”在非洲,亨德森在兩個部落生活過,分別是和平的阿諾維和好戰(zhàn)的瓦瑞瑞。這樣兩個對立的部落精神正是亨利·莫頓·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那套帝國話語的必備內(nèi)容。亨利的任務(wù)是平撫或消滅那些戰(zhàn)士,以及掠奪和平的部落。但令人吃驚的是,亨德森在兩種社會中都沒有建立起帝國式的掌控。
有一些章節(jié)講述了亨德森在阿諾維村寨里的時光,小說在此轉(zhuǎn)向我們八十天旅程中最后一次瘟疫敘事。因為缺水,牛紛紛渴死,漫長的干旱還在繼續(xù),而非同尋常的是,因為來了一群青蛙,村寨為干旱準(zhǔn)備的蓄水塘卻被廢棄了。正如亨德森跟他們說的:“我相信自己非常明白遭受一場瘟疫是怎樣的痛苦,也很同情他們。然后我意識到,他們只能把眼淚當(dāng)面包來度日,我希望我不會給他們麻煩。”
出于同情,亨德森無法抗拒作為白種人的使命,挺身而出去幫忙解決當(dāng)?shù)厝说膯栴}。他做了一個愚蠢而驚人的方案,他制作了一個小炸彈,扔到蓄水塘里,想炸死那些青蛙。結(jié)果是蓄水塘被炸破,水都流光了。尷尬的亨德森就此離開了。他遲疑缺少決斷,建立帝國式掌控的那些嘗試都失敗了,然后他來到了瓦瑞瑞的地盤,在這里他搬動了一個沉重的雕像,之前部落里從未有人能舉起來過,以至他短暫地成為圣戈(Songo),或者叫“雨王”。當(dāng)他搬起雕像之后,雨神奇地落下來。其實他這個勝利是被國王達(dá)福的敵人安排好的,他們想除掉國王,還需要一個繼位的人。誰能比一個無知的,他們能控制的外人更合適呢。
國王達(dá)福交游廣泛、熟習(xí)藥理,英語也很流利,在這些事件發(fā)生之前,亨德森已經(jīng)很依賴于他。就像休·洛夫廷筆下的棒破王子一樣,達(dá)福說著一口過于詳盡的英語(“我估計你非常強(qiáng)壯。噢,太強(qiáng)壯”)。但貝婁不是在取笑達(dá)福,他將國王的話作為神諭,富于廣泛閱讀后獲得的哲理。(“詹姆士的《心理學(xué)》是本非常吸引人的書”,他順道對亨德森評價說)。達(dá)福對整個人類,以及對亨德森這個人,都有非常深入的見解。
“你闡釋了很多東西”,他說:“對我來說,你是一個闡釋道理的寶藏。我不會責(zé)備你的外貌。我只是從你的體格中看到了世界。在我對醫(yī)學(xué)的學(xué)習(xí)里,這是對我來說最具魅力的部分,我曾獨自對各種體型做過透徹的研究,形成了整套分類系統(tǒng),比如有,痛苦型、貪食型、固執(zhí)型……狂笑型、書呆子型、好斗反擊者型,啊,亨德森-松戈,多少種類型啊,數(shù)也數(shù)不清!”
漸漸地,達(dá)福聽著越來越像貝婁在紐約的精神科醫(yī)生:“想象在你身上起了作用,它雖然閉塞,卻是強(qiáng)力而原初的……你是各種暴烈力量的非凡融合。”在他養(yǎng)獅子的地窖里,達(dá)福給亨德森安排了一系列費(fèi)力而危險的任務(wù),迫使亨德森脫光了去觸碰自己內(nèi)心的野獸。這聽起來像是個詭異的東方主義幻想,但實際上,貝婁曾接受過萊克學(xué)派醫(yī)生的心理輔導(dǎo),有兩年時間,醫(yī)生都要求他在心理輔導(dǎo)中全身赤裸,而小說正是對這段經(jīng)歷的戲仿和強(qiáng)化。
盡管這些心理輔導(dǎo)讓人惱火,但和貝婁一樣,亨德森也開始對自己,對美國有了新的感知,并能在回到家后讓生活重回正軌。不再無止境地去“成長”了,他決定:“且看當(dāng)下!打破靈魂的沉睡。醒來吧,美國!讓專家們瞠目結(jié)舌。”貝婁的非洲是從紐約化身而出的,是紐約的倒影——一個也許能將美國驚醒的翻轉(zhuǎn)鏡像。
貝婁把《雨王亨德森》稱作他最愛的作品,還說相較于筆下的其他角色,他在亨德森身上傾注了最多的自我。這樣的判斷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畢竟像莫斯·赫索格和薩姆勒先生那樣的角色更直白地表現(xiàn)出跟作者的相似。但就像筆下的非洲,貝婁用反轉(zhuǎn)來創(chuàng)造了他的主人公:他自己是個窮猶太移民,而亨德森是個美國白人新教徒,還是個百萬富翁,住在從父親那里繼承的康涅狄格農(nóng)場;貝婁雖然瘦小,但靈活英俊,而亨德森是個高大丑陋,力量驚人的摔跤手。通過將紐約、康涅狄格轉(zhuǎn)換為非洲,將自己轉(zhuǎn)化成形體、文化的對立面,貝婁找到了能把自己和國家看得更清楚的距離。他在巴黎待了幾年之后回到美國,在巴黎,他和詹姆斯·鮑德溫成了朋友,那時他已經(jīng)準(zhǔn)備好探索世界了。正如他心目中的達(dá)福,“在離家這么遠(yuǎn)的地方竟能遇上這樣一個人物。是啊,旅行是值得推薦的。相信我吧,世界就是一個意識。旅行是思維上的游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