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xué)新動(dòng)向|新加坡文學(xué)獎(jiǎng)與打工詩(shī)人
文學(xué)新加坡:新加坡文學(xué)獎(jiǎng)、謝裕民、打工詩(shī)人
8月27日,新加坡文學(xué)獎(jiǎng)線上揭曉。華文組的獲獎(jiǎng)情況如下:黃凱德以《豹變》、謝裕民以《建國(guó)》獲小說(shuō)獎(jiǎng);黃凱德以dakota獲非虛構(gòu)寫(xiě)作獎(jiǎng);吳耀宗以《形成愛(ài)》獲詩(shī)歌獎(jiǎng)。英文組的獲獎(jiǎng)情況如下:阿什塔·南達(dá)(Akshita Nanda)與詩(shī)人黃毅圣(Ng Yi-sheng)獲小說(shuō)獎(jiǎng);陳瑞琳(Marylyn Tan)以Gaze Back獲詩(shī)歌獎(jiǎng)。淡米爾組的小說(shuō)和詩(shī)歌獎(jiǎng)均被西蘇拉·龐拉吉(Sithuraj Ponraj)摘得。
本屆新加坡文學(xué)獎(jiǎng)主題是“#WhyWeWrite”(為何寫(xiě)作),探討作家的寫(xiě)作初衷。本屆獎(jiǎng)金由往屆的1萬(wàn)元減少至3000元。新加坡文學(xué)獎(jiǎng)的歷屆得主主要有:英培安、謝裕民、希尼爾(謝裕民哥哥)、尤今、吳耀宗。其中,英培安四獲新加坡文學(xué)獎(jiǎng),目前是歷屆最多,分別是在2004年、2008年、2012年、2016年。
《建國(guó)》此前曾入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說(shuō)。《建國(guó)》綜合了兩種敘事方式,其一是以“建國(guó)”為主線的歷史故事,其一是“SG50詞典”的新聞式連載。兩種敘事交織重合,構(gòu)建了新加坡建國(guó)后復(fù)雜的國(guó)家故事、人物流動(dòng)、全球局勢(shì)。

謝裕民
此前,謝裕民對(duì)《聯(lián)合早報(bào)》表示,《建國(guó)》就是一個(gè)男人在嘮嘮叨叨,也許就像伍迪·艾倫電影里的中年男人的牢騷。“日常的牢騷最難寫(xiě)。日常像細(xì)沙,一抓,它便不斷從指間溜走”,謝裕民表示。謝裕民認(rèn)為一般作家從一樓升到三樓,天才作家一下子就跳到第四、第五樓。靠努力的人,1之后甚至只能是1.1、1.2、1.3……“60歲之后發(fā)現(xiàn),其實(shí)0跟1之間,就很多學(xué)問(wèn),已經(jīng)夠你活了,不用去到2和3。我寫(xiě)過(guò)一個(gè)極短篇,寫(xiě)井底之蛙不需要太大的天空,當(dāng)它跌下來(lái)的時(shí)候才發(fā)現(xiàn),井里面還有一個(gè)小洞,那里更寬闊。”
作家林高稱謝裕民的文筆貼地氣,“語(yǔ)言到了你手里都能隨人物身份、環(huán)境氛圍、題材可能潛藏的信息等因素作適當(dāng)?shù)恼{(diào)整。譬如《放》的敘事語(yǔ)言,讀者能感受到那年代的心理氛圍,這是你著力之處。”
于2006年獲得新加坡文學(xué)獎(jiǎng)的《重構(gòu)南洋圖像》,在黃曉燕看來(lái),是慣于都市書(shū)寫(xiě)的謝裕民開(kāi)始嘗試文化尋根之旅的重要轉(zhuǎn)型之作。《重構(gòu)南洋圖像》聚焦于“我”隨父親去印尼馬魯古群島的安汶島尋找十世祖父和曾祖父的歷程,穿插荷印殖民時(shí)期的東印度公司的歷史。于2010年獲新加坡文學(xué)獎(jiǎng)的《m40》寫(xiě)的是一個(gè)40歲的都市男人“你”面對(duì)都市文化和苦悶及其他的尋根癡想,“不知道會(huì)不會(huì)像你爸爸,在所有記憶被連根拔起后枯萎掉”。有人視之為“尋根文學(xué)”。
謝裕民祖籍廣東揭陽(yáng),1959年生于新加坡,1995年受邀參加美國(guó)愛(ài)荷華國(guó)際寫(xiě)作計(jì)劃。他曾任《新明日?qǐng)?bào)》文藝副刊編輯,現(xiàn)為《聯(lián)合早報(bào)》副刊組資深高級(jí)編輯。2019年,謝裕民獲頒泰國(guó)王室主持的東南亞文學(xué)獎(jiǎng)(2017年),同時(shí)頒發(fā)的還有余王敬瑩(2016年)、吳彼得(筆名Peter Augustine Goh,2018年),東南亞文學(xué)獎(jiǎng)因泰王逝世延期兩年。
此前,在新加坡疫情蔓延,國(guó)家采取一級(jí)防范,工人受劣待的情況下,《亞洲藝術(shù)觀察》(Art Review Asia)發(fā)表了新加坡建筑監(jiān)理Zakir Hossain Khokan的詩(shī)作。
《初稿》
……
政府已經(jīng)聲明,
戴口罩是強(qiáng)制性的。
但他們沒(méi)有口罩。
宿舍,政府,公司——
有誰(shuí)會(huì)給他們口罩?
他們被禁止外出。
如果他們沒(méi)有口罩,他們?cè)趺创骺谡郑?/span>
他們目瞪口呆地看著自己。
他們無(wú)法理解是誰(shuí)在輕視誰(shuí),
在這個(gè)生命的鏈環(huán)中。
……
他們很焦慮。
他們知道高級(jí)專員公署在那里
把他們的尸體裹回家。
……
有時(shí)候文人和知識(shí)分子也會(huì)拜訪他們。
他們鼓勵(lì)他們閱讀、發(fā)言、寫(xiě)作、繪畫(huà)、攝影、拍電影,
但強(qiáng)調(diào)他們的藝術(shù)應(yīng)該是冷靜的,而不是爆炸性的。
……
Zakir Hossain Khokan生于孟加拉國(guó)達(dá)卡,畢業(yè)于孟加拉國(guó)立大學(xué),于2003年到新加坡工作。目前,他在建筑行業(yè)任質(zhì)量控制項(xiàng)目協(xié)調(diào)員。自2014年、2015年連續(xù)兩次獲獎(jiǎng)后,他就成了新加坡移民工人群體的代表人物。他已經(jīng)出版了兩本詩(shī)集。他是新加坡孟加拉移民詩(shī)人詩(shī)集《移民故事集》(Migrant Tales)和《呼喚與回應(yīng):移民/本地文集》(Call and Response: A Migrant/Local Anthology)的聯(lián)合編輯。2015年,Zakir Hossain Khokan受邀做了一場(chǎng)Ted演講,名為《口袋里的詩(shī)歌》(Poems from my pocket),歡迎觀看。
阿莉·史密斯和她的季節(jié)四部曲
阿莉·史密斯季節(jié)四部曲以《夏》收尾,它表現(xiàn)了身臨其境的怒火、熱情、高調(diào)。此前,《秋》《冬》《春》分別出版于2017年、2018年、2019年。《夏》從2020年2月開(kāi)始,其時(shí)新冠新聞?wù)跊坝浚?020年5月結(jié)束,世界各地都在不同程度的封鎖中。另外,史密斯還帶我們回到了二戰(zhàn)時(shí)期,像其他三部那樣,一段相得益彰的歷史時(shí)期和現(xiàn)在當(dāng)下構(gòu)成了一個(gè)平行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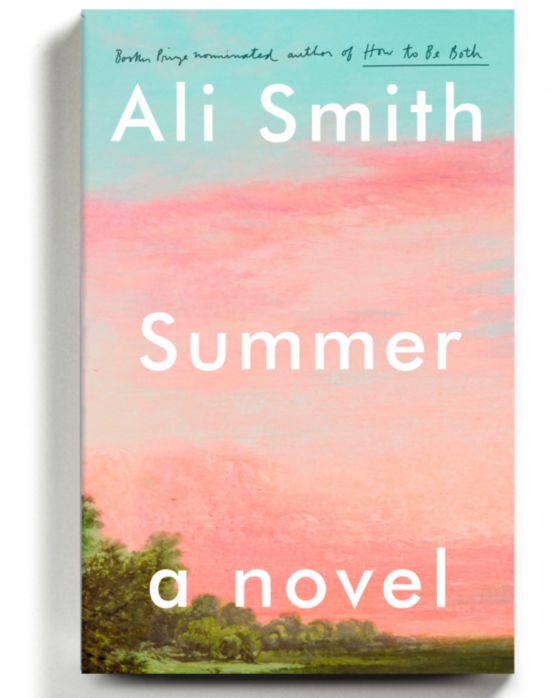
《夏》
在《夏》中,史密斯帶我們重溫了脫歐、特朗普、澳大利亞森林大火、新冠病毒等等一系列世界重大危機(jī)事件。事情是糟糕的,生活是復(fù)雜的。“全英國(guó)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見(jiàn)證了謊言,看到了施加在人類和地球之上的虐待,他們還發(fā)了點(diǎn)聲音,游行、抗議、書(shū)寫(xiě)、投票、交談、激進(jìn)主義、播客、電視、社交媒體、推特、一頁(yè)又一頁(yè)…… ”這里還有卓別林、保利娜·博蒂、塔西塔·迪恩、芭芭拉·赫普沃斯、莎士比亞、狄更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史密斯借書(shū)中的人物說(shuō),“夏天,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想象的結(jié)局。我們本能地沖向它,好像它一定是有什么含義。”
《夏》以薩莎·格林勞(Sacha Greenlaw)的視角展開(kāi)。薩莎試圖保持清醒,她從不乘坐汽車,因?yàn)樗褂没剂稀5艿芰_伯特很調(diào)皮,他崇拜有暴力傾向的電子游戲。在這個(gè)夏天,各種各樣致命的事情發(fā)生了。再次出現(xiàn)的人物丹尼爾·格魯克(Daniel Gluck)將我們帶到上世紀(jì)四十年代,關(guān)于崩解、戰(zhàn)爭(zhēng)、夢(mèng)想破滅。像詹姆斯·伍德此前在《紐約客》為其《冬》寫(xiě)的書(shū)評(píng)里面寫(xiě)道的那樣,史密斯尋找到了一種并置:英國(guó)式的奇思妙想與蘇格蘭式的后現(xiàn)代主義;傳統(tǒng)資產(chǎn)階級(jí)小說(shuō)的現(xiàn)實(shí)情節(jié)與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實(shí)驗(yàn)主義、無(wú)政府主義元素的拼貼。
詹姆斯·伍德認(rèn)為史密斯是當(dāng)代小說(shuō)中最癡迷于雙關(guān)語(yǔ)的作家,勝于托馬斯·品欽。雙關(guān)語(yǔ)的應(yīng)用給她的作品一種擴(kuò)展和延綿的可能性。在歡快的語(yǔ)調(diào)之下是現(xiàn)實(shí)的不堪和臃腫。史密斯是高智商的,但她放棄高雅和舒適,而她的人物也往往是不那么體面的紳士。更重要的是,在史密斯看來(lái),這個(gè)世界不再有高貴了,這個(gè)世界是“骯臟的、英式的、矮小的”,起碼這是它目前的基本狀況。在《夏》中,薩莎致信一個(gè)被拘留的人,“現(xiàn)代意義上的英雄正在照亮那些需要被看到的東西”——這正是我們需要關(guān)注的。崇高,在今天比任何時(shí)候都顯得更為迫切和重要。
史密斯1962年8月24日生于一個(gè)蘇格蘭工人家庭。她曾在阿伯丁大學(xué)讀書(shū),后來(lái)又在劍橋紐納姆學(xué)院攻讀愛(ài)爾蘭現(xiàn)代主義的博士。大學(xué)期間,史密斯寫(xiě)了很多詩(shī)歌。她曾短暫在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xué)教過(guò)書(shū),但事與愿違,不久就離開(kāi)了這所學(xué)府,從此以寫(xiě)作為生。1995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shū),是一部短篇小說(shuō)集,此后連出幾本短篇小說(shuō)集。史密斯從未獲得過(guò)重量級(jí)獎(jiǎng)項(xiàng),除了橘子小說(shuō)獎(jiǎng)(現(xiàn)在更名為女性小說(shuō)獎(jiǎng))和科斯塔文學(xué)獎(jiǎng)——這兩個(gè)獎(jiǎng)項(xiàng)并不為我們所熟知。2007年,史密斯當(dāng)選英國(guó)皇家文學(xué)學(xué)會(huì)會(huì)員。史密斯對(duì)《新政治家》表示,如果一切重來(lái),她會(huì)做好交際的隱士、鳥(niǎo)類學(xué)家、貓語(yǔ)者、街頭藝人、煲湯大師、清潔工人,并非理想意義上的,而是現(xiàn)實(shí)意義上的,史密斯當(dāng)過(guò)服務(wù)員,她的自我認(rèn)可也是正像她所言的。
史密斯并不認(rèn)可互聯(lián)網(wǎng),在她看來(lái),算法只是一個(gè)簡(jiǎn)化的系統(tǒng),而語(yǔ)言——并不是文學(xué)意義上的語(yǔ)言——是一個(gè)意義系統(tǒng)。這個(gè)觀點(diǎn)應(yīng)該為我們所見(jiàn)證和警醒。“當(dāng)政治語(yǔ)言把我們和自己簡(jiǎn)化為數(shù)據(jù)或者社交媒體的關(guān)注/被關(guān)注,而不是這個(gè)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公民時(shí),我們身上的各個(gè)方面的悲哀的事情就會(huì)發(fā)生……并不是說(shuō)社交媒體不美好。所有的連接方式都是美妙的,直到它們習(xí)慣服務(wù)于機(jī)器而不是人類。”
愛(ài)麗絲·奧斯瓦爾德:牛津詩(shī)歌教授、園藝師、水的樂(lè)師
在最新一期《詩(shī)歌》雜志中,Kit Fan發(fā)表了一篇關(guān)于英國(guó)詩(shī)人愛(ài)麗絲·奧斯瓦爾德(Alice Oswald)的新作《無(wú)名者》(Nobody)的評(píng)論。文中說(shuō),“紙上的音樂(lè)引發(fā)了一連串的氧氣狀和策略性的停頓,這些停頓可以重塑意義…… ”在他看來(lái),奧斯瓦爾德的詩(shī)歌因其詞和意的模糊和雙重,恰恰為閱讀和欣賞提供了一種助力。
《無(wú)名者》是對(duì)《奧德賽》的改寫(xiě),延續(xù)了奧斯瓦爾德對(duì)于水的熱愛(ài),這種熱愛(ài)讓她對(duì)海洋有一種即興的、富有色彩的想象。同時(shí),她對(duì)荷馬——既是古典學(xué)的荷馬,又是自然意義上的荷馬——的熱愛(ài)也表現(xiàn)了出來(lái)。她試圖傳遞給我們這樣的信念,“在巨浪之下,人只是一個(gè)無(wú)名者”。“一個(gè)人有塵土的性格/另一個(gè)人有一個(gè)箭頭代表靈魂/但他們的故事都結(jié)束了//在某個(gè)地方//在海里”。愛(ài)麗絲·奧斯瓦爾德
在一次新書(shū)發(fā)布會(huì)上,奧斯瓦爾德稱自己的詩(shī)歌為“聲雕”(sound carvings)。所謂聲雕,大概是在人與世界間的那張已死的紙張。死亡、消失、溶解,愛(ài)麗絲·奧斯瓦爾德寫(xiě)得最多,對(duì)她來(lái)講,所有腐爛的跡象似乎蘊(yùn)含著生命、生機(jī)。她會(huì)和音樂(lè)家合作,她喜歡這樣,這涉及她對(duì)詩(shī)歌的理解。同樣的,她在意詩(shī)歌呈現(xiàn)在紙上和書(shū)中的質(zhì)感,關(guān)于裝幀、設(shè)計(jì)、排版、色彩。
奧斯瓦爾德并非強(qiáng)調(diào)聲音,而是強(qiáng)調(diào)詩(shī)歌的可能性。在答《白色評(píng)論》的訪談時(shí),奧斯瓦爾德表示,“詩(shī)歌不需要假定它會(huì)被朗誦。詩(shī)歌必須有能量來(lái)創(chuàng)造自己的必需品……口頭詩(shī)歌,比如《奧德賽》,甚至沒(méi)有A4紙,只有氣息。這樣才能讓詩(shī)人集中精神。我感興趣的是,怎樣才能恢復(fù)現(xiàn)代詩(shī)人的壓力——拿走所有的道具和類別,讓詩(shī)歌自生自滅。”安格·姆林科(Ange Mlinko)在7月刊的《紐約書(shū)評(píng)》中表達(dá)了同樣的觀點(diǎn)。
作家珍妮特·溫特森將奧斯瓦爾德視為特德·休斯的最佳繼承人。他們都訴諸自然,共享了相似的語(yǔ)調(diào)。奧斯瓦爾德反駁了類似的評(píng)判。她說(shuō),“我并不是大自然的詩(shī)人。的確,我喜歡植物,但落實(shí)到詩(shī)歌,我喜歡的自然詩(shī)歌形而上的部分。”她的楷模是荷馬、奧維德、莎士比亞,這些人把人與非人囊括在自身的語(yǔ)言里。不管她多么拒絕和特德·休斯扯上關(guān)系,讀者還是很自然這樣想。特別是在她的作品《野草和野花》獲得特德·休斯獎(jiǎng)后,她更加擺脫不了這一聯(lián)系。《野草和野花》無(wú)疑是她的園藝事業(yè)的一部分。在這部書(shū)里,她將24種花草記錄在案,包括百合、石竹等。
這樣的目錄后來(lái)發(fā)展成了《紀(jì)念札:〈伊利亞特〉的一個(gè)版本》。像紀(jì)念碑熔鑄了死魂靈一樣,《紀(jì)念札》將《伊利亞特》里死去的人一一銘記、一一憑吊。里面大多是“除了死亡一無(wú)所有”的士兵。《紀(jì)念扎》是《伊利亞特》的翻譯,它完全繼承了荷馬史詩(shī)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恢宏描寫(xiě)和隱喻表達(dá)。《紀(jì)念扎》又是《伊利亞特》的再創(chuàng)造,它不講故事,它講述的是死亡的政治,是多聲調(diào)的民主。按詩(shī)歌類型判斷,《紀(jì)念扎》是一首地地道道的哀歌,它的主題既是死亡,又是新生。
奧斯瓦爾德生于1966年,父親是著名的園林設(shè)計(jì)師。奧斯瓦爾德在牛津修習(xí)古典學(xué),畢業(yè)后她從事園藝工作。目前,她和丈夫子女定居在德文郡。她于2012年獲得了艾略特詩(shī)歌獎(jiǎng),于2017年獲得了獎(jiǎng)金豐厚的格里芬詩(shī)歌獎(jiǎng)。
2019年6月21日,奧斯瓦爾德被授命為下一任牛津大學(xué)詩(shī)歌教授。在最后的投票中,她以1046票的壓倒性優(yōu)勢(shì)贏得了這個(gè)席位。從當(dāng)年10月1日開(kāi)始,她將在牛津?qū)W府進(jìn)行為期五年的兼職授課。牛津大學(xué)詩(shī)歌教授講席是1708年開(kāi)始設(shè)立的。馬修·阿諾德(兩任)、W. H. 奧登、謝默斯·希尼、保羅·默頓、杰弗里·希爾等著名詩(shī)人都曾在這個(gè)席位為學(xué)子講授詩(shī)歌。
在很多場(chǎng)合中,奧斯瓦爾德反復(fù)講述了一個(gè)故事。八歲那年,她一個(gè)人熬過(guò)了整個(gè)夜晚,望著黎明前的藍(lán)天白云,她驚訝得說(shuō)不出話。如果說(shuō)八歲時(shí)的黎明將其渡化為詩(shī)人,那么她寫(xiě)《提托諾斯》所經(jīng)歷的黎明則是一次永不復(fù)歸的旅行。這是一首46分內(nèi)的配樂(lè)即興之作。完成后,她再也沒(méi)有重讀它。故事講的是一場(chǎng)凄美的愛(ài)情故事,抑或是生命故事。厄俄斯愛(ài)上美少年提托諾斯,她請(qǐng)求父親宙斯賜予他長(zhǎng)生,但卻忘記說(shuō)賜予他青春。厄俄斯最終離他而去,而衰老的提托諾斯一直在相思、一直在等待。
奧斯瓦爾德的住處從不缺植物,它們通常是些瘋長(zhǎng)的蕁麻。鄉(xiāng)居旁邊就是達(dá)特河,她常年在這里游泳嬉戲。為她贏得T·S·艾略特詩(shī)歌獎(jiǎng)的詩(shī)集《達(dá)特河》就是獻(xiàn)給這條河流的。在《達(dá)特河》中,詩(shī)人將詩(shī)歌和散文雜糅結(jié)合在了一起,這個(gè)形式雖然特殊,但已經(jīng)有很多詩(shī)人以這樣的形式來(lái)創(chuàng)作。在不得不暫離舊居時(shí),愛(ài)麗絲為她的河作了一首長(zhǎng)詩(shī)《重創(chuàng):給一條干枯的河流的詩(shī)歌》:
“極細(xì)的、凋敝的、幾乎干涸的
一個(gè)骨頭造就的羅馬寧芙
脫力從石灰?guī)r里喚起一條河”
《回響》:一本粵語(yǔ)文學(xué)雜志
7月,華語(yǔ)世界第一本粵語(yǔ)雜志《回響》在香港發(fā)行。它的發(fā)行有賴于眾籌,籌得目標(biāo)金額五倍以上。第一期在發(fā)出兩周后告罄,第二期也于上月下旬發(fā)行。
《回響》由粗通文學(xué)的“山城豬伯”主編,他希望憑一己之力改變市場(chǎng)。刊物本名《粵刊》,足見(jiàn)其野心。“山城豬伯”曾對(duì)“文學(xué)性”頗有微詞。他接受立場(chǎng)新聞的專訪時(shí)批評(píng):“香港文壇偏重文學(xué)性,故事性強(qiáng)的作品受到貶抑”,而他以“賺到錢”為《回響》日后成功的指標(biāo),相信做旺“巿場(chǎng)或者產(chǎn)業(yè)”就能“推廣文學(xué)”。
陳子謙撰文指出,《回響》團(tuán)隊(duì)的角色就好似一個(gè)策展人,或是一個(gè)中間人,將文學(xué)同大眾、通俗同嚴(yán)肅的文學(xué)放在一起,建立起整個(gè)閱讀文化。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山城豬伯”觀察到愈來(lái)愈多香港人用粵語(yǔ)文字表達(dá)自己,甚至成為身份象征,正如“你見(jiàn)到寫(xiě)繁體中文字,通常都會(huì)assume佢系(是)臺(tái)灣人”。
《回響》也有爭(zhēng)議存在。作家黎國(guó)威質(zhì)疑“書(shū)面語(yǔ)”和“口語(yǔ)”是否可以二分,像《回響》主編所言的那樣。作家沐羽撰文指出,雜志漠視前人耕耘,“舉著立意良善的旗幟先踩別人幾腳,再吹奏自己踩的角度多么精準(zhǔn)”,結(jié)果“一開(kāi)口就得罪大半個(gè)文學(xué)場(chǎng)域的人”。
陳智德認(rèn)為,粵語(yǔ)入文早已有之,不必強(qiáng)調(diào)用了粵語(yǔ)才能代表香港文學(xué),至于近五六年對(duì)“粵語(yǔ)文學(xué)”的提倡和討論,其實(shí)是一種反彈。“討論這個(gè)現(xiàn)象,要把政治情結(jié)和學(xué)術(shù)分開(kāi),我擔(dān)心混淆它和學(xué)術(shù),會(huì)扭曲了文化的問(wèn)題。”
陳子謙撰文指出,粵語(yǔ)入文,在香港起碼可以追溯至晚清。黃仲鳴在訪問(wèn)中說(shuō),“粵語(yǔ)入文,一開(kāi)始無(wú)非為了吸引更多讀者。第一個(gè)應(yīng)該是清末的鄭貫公,他本來(lái)崇拜康有為,后來(lái)跟從了孫中山的革命派。為了讓百姓更容易接受,他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唯一趣報(bào)有所謂》(簡(jiǎn)稱《有所謂報(bào)》)加入了廣東話,結(jié)果比孫中山的《中國(guó)日?qǐng)?bào)》銷量更高,可見(jiàn)粵語(yǔ)入文真的能夠吸引讀者。”
現(xiàn)在在世的作家中,董啟章、黃碧云、飲江都有大量的粵語(yǔ)入文的嘗試。飲江表示,“我在粵語(yǔ)環(huán)境長(zhǎng)大,自然會(huì)講粵語(yǔ),但其他人呢?比如維特根斯坦,會(huì)怎樣說(shuō)?特朗普又會(huì)怎樣說(shuō)?我就會(huì)模擬、想像,借此活化自己的想法,也在語(yǔ)言里和他們打個(gè)照面。我有些頑皮,而粵語(yǔ)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比較自在,可以來(lái)一點(diǎn)無(wú)稽、非份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