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個瘋子》:瘋狂中真實的現(xiàn)實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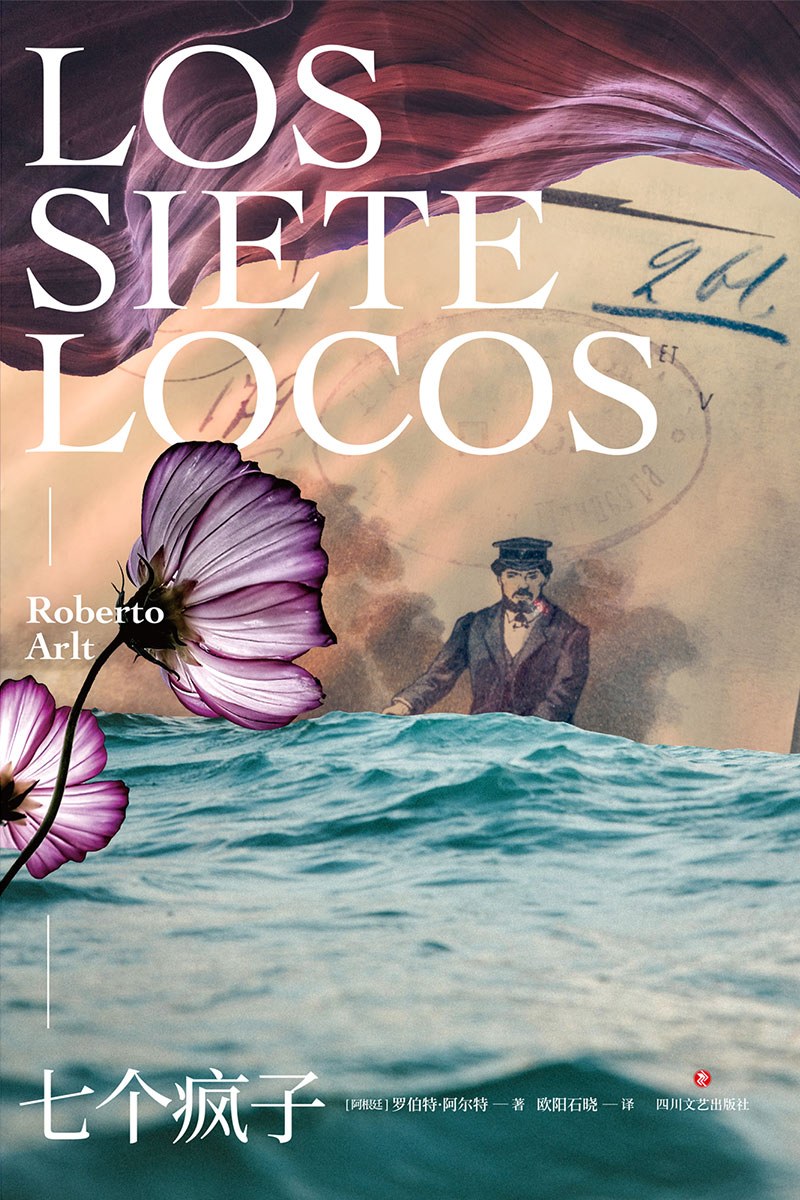
當(dāng)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拉斯埃拉斯(Las Heras)大街的一家書店向店員請教,除了博爾赫斯、科爾塔薩、皮格利亞這樣世界聞名的大師,阿根廷還有什么更“不為人知”的本土作家嗎?店員給了我一本羅伯特·阿爾特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速寫》(Aguasfuertes Porte?as),這本書的選題和用詞果然非常“本地”,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部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十分“接地氣”的小說。
阿爾特出身底層移民家庭,如千千萬萬住在大雜院里的移民一樣,扎根在這個新構(gòu)建的民族國家,終身沒能擺脫貧困,獲得社會晉升。還有誰能比他更知道底層阿根廷人的所思所想?讀罷《七個瘋子》,我更想說,有誰比阿爾特更了解阿根廷人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呢?
阿爾特1900年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他16歲離家,換過各種工作。他熱愛寫作,寫就了《憤怒的玩具》、《七個瘋子》、《噴火器》、《魔幻之愛》等小說和一些故事集。同時,作為記者,他游歷了烏拉圭、巴西、西班牙和北非,寫出了2000多篇報刊短文,收錄在上文提到的《速寫》中。他的文筆不拘一格,喜歡在行文中夾雜各國方言俚語;而一旦譯成中文,其中的趣味就消失了。某種程度上,阿爾特小說的神髓也在于翻譯中丟掉的“街頭神韻”。在阿根廷文學(xué)中,阿爾特地位崇高卻常常被研究者和普通民眾忽視,這與他“接地氣”的行文有關(guān),也與他人生和創(chuàng)作中蘊含的各色矛盾息息相關(guān)。
在阿爾特的作品中,《七個瘋子》是一本奇書。在整部小說中,現(xiàn)實、幻想和瘋狂混在一起。該書的出版距離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大爆炸”還有二三十年,卻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了類似的特點。但是,阿爾特并非“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家。他真的在寫“真實”。只有讀完這本書才能體會到,在看似瘋狂的思想和舉動之下,居然真的能剝離出當(dāng)時的社會現(xiàn)實和未來的社會現(xiàn)實。只能說,所謂虛幻,不過是因為你不相信罷了。況且,現(xiàn)在不會發(fā)生的事情,將來可能會發(fā)生,這并非一種簡單的“未來學(xué)預(yù)測”,恰恰凸顯了阿爾特作品之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以至于能夠穿透荒誕現(xiàn)實的表面,預(yù)見事物發(fā)展的趨勢。
小說的主人公埃爾多薩是個失敗的底層人物。他在糖廠做收銀員,因婚姻不幸和窮困潦倒,開始偷工廠的錢,遭到妻子表弟巴爾素特的舉報。工廠要求他在24小時之內(nèi)還錢,不然就要辭退他。當(dāng)妻子背叛他、離他而去,他的世界開始坍塌,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想要殺死巴爾素特,勒索一筆巨款,支持他朋友“占星家”的一個瘋狂的計劃,即創(chuàng)建一個秘密社會,推翻現(xiàn)有的世界。這個計劃一共召集到七個人——這也是標題“七個瘋子”所指,暗喻基督教中的七宗罪,是世界末日釋放出的上帝的憤怒。
故事行文色彩暗淡,從小說各章的標題中就能看出來——“街上的恐怖”“憎恨”“層層黑暗”“受辱者”等。但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阿爾特幾乎沒有給這些黯淡絕望的生活以一點救贖的光明,只有無盡的貧困、齟齬、卑微、屈辱、墮落,這些都是一個底層移民家庭出身的阿爾特耳濡目染的。除了這幾個來路不明的瘋子,書中其他的人物也是殺人犯、妓女、皮條客、賭徒、無賴等底層人物,甚至與他們相關(guān)的也是梅毒、肺結(jié)核、麻風(fēng)之類的窮人病。與上層社會不同,他們常常受到巫師、占卜者這類人物的影響,因而,“占星家”這樣的人物能成為他們的首領(lǐng)也就不足為奇了。
社會的逼仄和墮落激發(fā)了埃爾多薩瘋狂的行動,他一開始只想殺人,后被“占星家”的計劃說服——他召集七個人,想通過一個秘密社會和革命來推翻現(xiàn)有的秩序。可是,這一“革命”卻是以犯罪和殘酷剝削為基礎(chǔ)的,他們資金來源居然是開妓院剝削女性;誘騙工人來礦上做工,用鞭子打死那些不愿意做工的人(第151頁)。他們的“高尚”是以殘暴為基礎(chǔ)的。小說中的高尚與卑微總是很微妙,即便生發(fā)于卑微,高尚還是帶著陰暗的光。
這樣吊詭又強烈的矛盾,還體現(xiàn)在新社會的制度設(shè)計上。無神論與資本主義將人變成了懷疑一切的魔鬼。小說的主人公們認為,20世紀最大的惡就是“非宗教性”,科學(xué)與信仰之間的鴻溝越大,人們的悲慘也越多。因此,這個秘密社會的主要目的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恢復(fù)丟失的信仰,即崇拜上帝。至于秘密社會的形式,尤其是意識形態(tài),則是一片混亂。“我不知道我們的社會是布爾什維克還是法西斯的社會。也許最好的選擇是做一道連上帝都搞不明白的俄式沙拉。”(第31頁)“我們中將會有布爾什維克派、天主教徒、法西斯主義者、無神論者、軍國主義者。”(第154頁)正如文中兩人討論對“占星家”的看法,“有時候您會覺得在聽一位反動派講話,另一些時候又會覺得他是左派。說實話,我覺得連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第46頁)在續(xù)集《噴火器》中,“占星家”在律師的逼問下,最終將立場搪塞為共產(chǎn)主義。在此,矛盾再次出現(xiàn):為了反對無神論和資本主義,“占星家”卻選擇其所謂的“共產(chǎn)主義”作為意識形態(tài)。他認為,立場最終是愚弄和欺騙年輕人的,意識形態(tài)不重要。羅伯特·阿爾特
阿爾特對阿根廷的政治形式做出了驚人的預(yù)判。這本書寫于1929年,同年10月出版社進行編輯,而書中已預(yù)言到了1930年發(fā)生的軍事政變和阿根廷將要面對的一系列政治動蕩和革命嘗試。他精確模擬了軍隊的口吻,對政壇中充斥著道德淪喪、賣國求榮的各色人等進行了強有力的抨擊。(第166頁)盡管將這一法西斯性質(zhì)的秘密社會比作庇隆政府較為牽強,但阿爾特對阿根廷政治文化缺乏固定的意識形態(tài)的判斷是非常精辟的,這一特點縈繞在阿根廷的主流政治派別之中,揮之不去。
更讓人震驚的是,這種以其所謂的“共產(chǎn)主義”有神論反抗“資本主義”無神論的潛意識,在三十年后誕生的阿根廷最大的一支城市游擊隊——蒙托內(nèi)羅身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蒙托內(nèi)羅脫胎于革新天主教運動,在一片混亂之中卻舉起了共產(chǎn)主義的旗號。他們的失敗不僅僅來源于他們的組織和斗爭策略,更根源于其意識形態(tài)的飄忽不定。如“占星家”設(shè)想的同出一轍,他們發(fā)出了一種脫離了社會現(xiàn)實和底層利益的呼聲,只動員了中產(chǎn)階級青年,沒能動員生產(chǎn)性力量。阿爾特甚至設(shè)想了具體的恐怖襲擊手段,如綁架行動,靠幾個人控制一個城鎮(zhèn)等等(第167頁),這些都被游擊隊一一執(zhí)行,除此之外,他還預(yù)想到了七十年代的軍政府采取的恐怖鎮(zhèn)壓。
“占星家”支持軍政府的另外一個理由,是軍隊對工業(yè)化的支持。20世紀初,阿根廷社會開始信奉工業(yè)發(fā)展,認為工業(yè)化是文明進步的必經(jīng)之路。對工業(yè)化的迷戀在故事中被不斷強調(diào),如主人公對銅鑄玫瑰花的癡迷,秘密社會的工業(yè)發(fā)展計劃,女性對化學(xué)與工業(yè)生產(chǎn)的崇拜,“占星家”對“工業(yè)會帶來黃金”的堅信(第149頁)。故事中由惡棍貴族組成的上層,想要推翻資本主義,卻想發(fā)展工業(yè)。他們認定,為了大力發(fā)展工業(yè),殘酷剝削下層是有理的,因為軍政府如此有效率,是推動工業(yè)的最佳選擇。如他所料,阿根廷后來真的不斷陷入軍政府的統(tǒng)治無法自拔,大部分軍政府也果真秉持大力發(fā)展工業(yè)的立場。
欲知這秘密社會的結(jié)局和七個瘋子的經(jīng)歷,需要等到續(xù)集《噴火器》的出版。我們只能說,這場“革命”沒有成功。在幾十年后的阿根廷,各種革命嘗試不斷爆發(fā),同樣沒有成功。《七個瘋子》想象中瘋狂的烏托邦,在阿根廷的歷史中真切地存在過,只是在故事講完之后才發(fā)生而已。不得不說,這些瘋狂中帶有真實的現(xiàn)實主義。歷史就如阿爾特和他的小說一樣,充斥著矛盾和悖論,既偉大又被忽視、既瘋狂又現(xiàn)實、既卑微又高尚、既混亂又有序、是可能的歷史也是預(yù)言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