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終歸是一件與人為善的事情 ——2019年法國小說創(chuàng)作回顧

趙丹霞 法語文學博士,中國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學》編輯部副編審,主要關注領域為法語現(xiàn)當代文學。
內(nèi)容提要 2019年法國新出版的小說作品中,涌現(xiàn)不少以社會問題、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人生況味等為主題的佳作。無論是對時代和社會問題的思考,還是將歷史事件融入家族個體的敘事,或是對人生對時間的體察,作家們多是從人心和人性的角度來探索,顯示出了鮮明的人道主義關懷。
關鍵詞 法國年度文學研究 性侵 默許 難民 沉默 人生況味
在2019年的法國文學回歸季中,女作家的作品或是女性主題的作品在各出版社的新書推介中非常搶眼,質(zhì)量和數(shù)量均不俗。雖然女作家作品的主題并不一定是女性,而以女性為主題的作品并不只是由女性作家來寫,但放眼望去,“到處是女性”——不少以此為標題的新書推介概括出了2019年回歸季最顯著的特點。從年度新書的題材來看,時代痼疾、女性生存困境、家族敘事、人生況味等主題均有上乘作品出現(xiàn)。本文將介紹并嘗試解讀以上主題的幾部作品,以期能反映出2019年法國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側(cè)面。
一、一樁性侵案:社會與人性的全息投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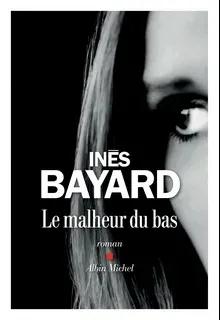
《下半身的災禍》,圖片源自Yandex)
#Metoo運動在全球開展以來,法國出現(xiàn)了不少與之呼應的文學作品,比如女作家巴亞爾的《下半身的災禍》和品若的《緘口》,這兩部作品都涉及性侵事件中權(quán)力與性、女性受害者在心理上的無助等問題,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社會對性侵這一現(xiàn)象的姑息態(tài)度。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開展的如火如荼的#Metoo運動,在法國曾出現(xiàn)過不同的聲音。2018年1月9日,《世界報》刊發(fā)了一封以法國為主的約百位歐洲女性名流簽署的公開信,信中認為大規(guī)模開展#Metoo等反對性騷擾運動有可能會矯枉過正,而她們“捍衛(wèi)人們求歡的自由”,認為這是“性自由”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法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女性主義所強調(diào)的“性自由”和“性魅力”對法國女性在兩性關系上的觀念依然有較大影響,這就造成了 “默許”問題——在“性侵”界定上的一個難點——在法國顯得更值得討論。這一難題在女作家特耶的新作《人的事》中就有所反映。

作家特耶,圖片源自Yandex
概括來說,《人的事》是通過一樁性侵案及其所引起的社會震蕩來描繪社會和人性中的種種死結(jié)。書中的主人公之一讓·法雷爾是一位政治記者和電視專欄節(jié)目主持人,他的妻子克萊爾是一位以女權(quán)運動的介入者聞名的作家,他們的兒子亞歷山大剛剛從名校畢業(yè),這樣一個家庭因為兒子被訴性侵而跌下高壇……小說大致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是對主要人物的素描,每個人的內(nèi)里都是其光鮮表面的反面。讓和克萊爾這對年齡差距二十七歲的夫妻貌合神離,讓在其多年的情婦——曾獲阿爾伯特·倫敦新聞獎的記者弗朗索瓦絲——之外,又與一位女實習生有染;克萊爾在兒子長大后,正打算搬去情人那里;優(yōu)等生亞歷山大內(nèi)心一直緊張苦悶,在一次晚會上,侵犯了母親情人的女兒米拉……作者描寫了三口之家里的每個人為維持“成功”的表面所承受的壓力、焦慮和恐懼;同時暴露了政界、出版界、媒體圈子里權(quán)力與性的糾纏;還通過刻畫二十多歲的米拉,四十多歲的克萊爾和六十多歲的弗朗索瓦絲,講述了三代女性各自的生存困境。
小說后半部分是庭審實錄般的書寫,對話成為主要的敘事方式,調(diào)查、傳喚、質(zhì)詢、交鋒。被輿論操縱的媒體和司法,人性中灰色地帶的模糊和矛盾都在敘述者的“實錄”中凸顯:由于這樁性侵案發(fā)生在韋恩斯坦事件后不久,再加上被告亞歷山大的特權(quán)家庭出身,使得此事在社交媒體上以驚人的速度被發(fā)酵,無論是被韋恩斯坦事件震驚的民眾,還是厭惡特權(quán)的正義人士,甚至一些“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的吃瓜群眾,都有“被告有罪”的心理預設。司法機關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以讓亞歷山大謝罪而設計的問題帶有很強的傾向性和誘導性,法庭似乎成為某種“輿論暴力”的幫兇……但形成這種“輿論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難道不是對長期存在的對性暴力姑息態(tài)度的反動嗎?甚至可以說是前者對后者的一種“以暴制暴”,或者說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矯枉過正。然而同暴力十足的性侵案相比,此案的具體情況又有微妙的不同:案發(fā)前,米拉欣然接受“男神”亞歷山大做晚會女伴的邀請,晚會上在酒精和大麻的作用下與之發(fā)生了性關系,米拉當時的心理有多少愿與不愿?事后狀告亞歷山大又受到多少外來因素的影響?在這里,如何界定性侵中的“默許”問題浮出水面,“默許”和“性侵”間的界限在哪里?這一問題因為涉及人性的復雜多變而變得無法找到真相,但“真相”又是什么呢?就像書中陪審團的主席所言:“不是只有一種真相。我們可以在同樣的場景下,看到同樣的事情,卻用不同的方式闡釋。”作為女權(quán)主義者的克萊爾和作為母親的克萊爾眼中的真相是否相同?人的事何其復雜!作者以旁觀者的立場,把社會與人性的各個側(cè)面與層次通過一樁性侵案充分展開,使作品成為一個具有諸多面向的批判性文本。
二、和解:移民問題的終極想象
法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由于它曾經(jīng)的殖民帝國高度集中在阿拉伯和非洲的伊斯蘭世界,因此法國是穆斯林移民最多的歐洲國家。據(jù)預測,二十五年之后,穆斯林人口將占法國人口的一半以上。穆斯林風俗文化在法國影響力的擴大,使得近年來在法國出現(xiàn)了“法國伊斯蘭化”的疑懼,移民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的困擾也是“黃馬甲”運動的深層原因之一。素有法國社會預言師之稱的作家維勒貝克2015年出版的《臣服》被認為是對伊斯蘭沖擊法國社會的預言。在2019年初,他又推出預言“黃馬甲”運動的《血清素》,描述了法國社會深層的憤怒與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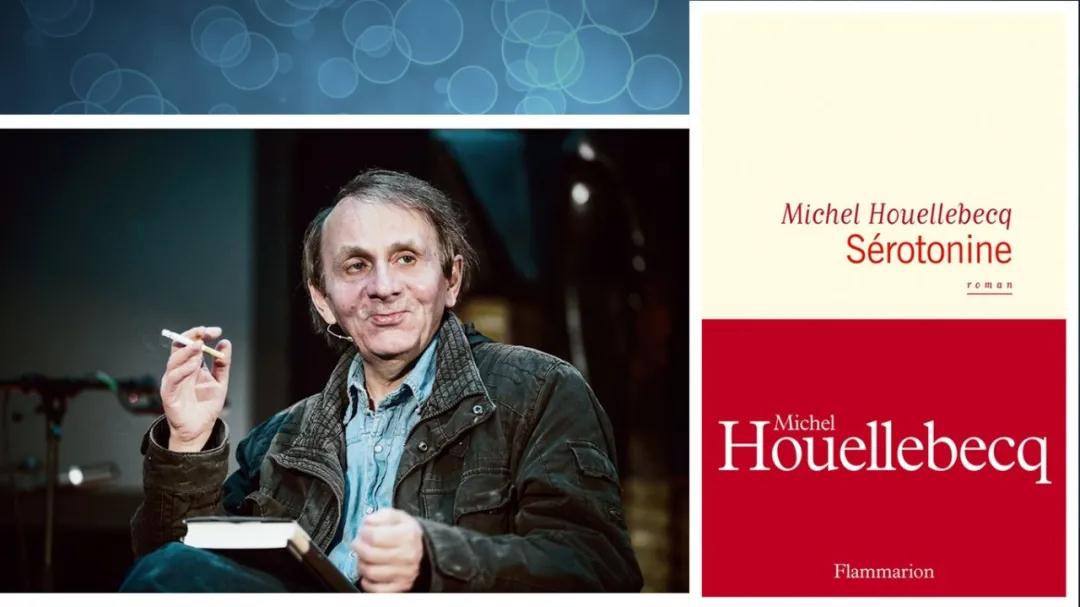
作家維勒貝克和《血清素》,圖片源自Yandex
維勒貝克在《臣服》中想象了2022年的法國,那時法國已被代表伊斯蘭溫和派的“穆斯林兄弟會”統(tǒng)治,并誕生了法國歷史上第一位穆斯林總統(tǒng)。2019年,喀麥隆法語作家米阿諾的新作《皇后紅》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與維勒貝克對起了山歌,她構(gòu)想了一個2100年繁榮而統(tǒng)一的非洲國家“卡帝歐帕”,那里是不堪移民重負的舊歐洲人趨之若鶩的地方。這些被稱為“弗拉斯”的歐洲人由于固守自己的文化和血統(tǒng)而變得孤立貧窮……圍繞著歐洲移民難題,“驅(qū)逐”和“融合”兩種思路的博弈在國家元首伊隆卡和他的紅顏知己——大學教師博婭之間展開,最終“融合”說服了“驅(qū)逐”。作者米阿諾試圖通過這種“換位思考”的方式來表現(xiàn)移民問題中的身份、記憶、傳承等難題和對“世界大同”的渴望。
相比于米阿諾在想象中訴說愿望的快意,法國女作家達里厄塞克意欲以法國當下的集體難民問題為主題的創(chuàng)作卻遭遇了六年的難產(chǎn)。幾年來,達里厄塞克曾多次對難民進行實地采訪,但了解得越深入,她就越難下筆。難民的背景、經(jīng)歷、訴求各個不同,使她無法塑造出具有代表意義的形象,甚至該怎么命名這一人群都是問題:難民?流亡者?尋求庇護者?這些名稱都不能完全代表這些試圖離開故土到歐洲尋夢的人。另外,解決難民問題的現(xiàn)實困難也讓女作家無法給她的難民故事一個指向。達里厄塞克還看到,普通法國人在談論難民時,會有不同的站隊,但是當他們和個體的難民打交道時,反應和立場經(jīng)常是另外一回事。于是女作家放棄了塑造典型形象的執(zhí)念,選擇講述一種并不典型的“偶遇”來呈現(xiàn)法國難民問題這一“時代大事”。她的新作《大海的另一面》(2019)就這樣誕生了。

作家達里厄塞克,圖片源自Yandex
小說女主人公羅絲是一位兒童心理治療師,在一次帶孩子的游輪旅行中,偶然看到游輪搭救了一艘偷渡船上的尼日利亞難民,其中一位叫約拿斯的少年激起了她的母性,在剛把兒子的手機借給他使用后,約拿斯就被意大利海警帶下了船。羅絲一直通過手機自動定位功能來追隨少年的蹤跡,并在他需要幫助時,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最后成功幫他去了英國。羅絲是作家2013年的小說《克萊芙》中的一個人物,她在《大海的另一面》中深陷中年危機,出于自己本能的熱心腸幫助了約拿斯,這一舉動使她的注意力和經(jīng)驗都脫離了慣常軌道,內(nèi)心發(fā)生了一系列改變,不知不覺間從“小我”的內(nèi)心危機中走出,成為“贈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受惠者。作者似乎將一部難民主題的小說寫成了一部中年女性的心靈成長小說,但也說明了作家試圖從人本的角度,從一個更小更具體卻更切實的角度,來反映當今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zhì)、人與人之間愛與分享的本質(zhì),而這一角度或許也是解決難民問題的一種本質(zhì)角度。
三、寫作:創(chuàng)傷的救治
2019年,法籍阿根廷裔作家阿米戈雷納的《內(nèi)心的牢籠》和法國作家戈阿塔列穆的《人子的那一份》均寫到了因戰(zhàn)爭創(chuàng)傷造成的家族長輩的沉默,這一“沉默”給后輩帶來的心理創(chuàng)傷以及他們試圖通過寫作來自我療救的努力。《人子的那一份》更因?qū)ζ洹跋胂蟆敝凶娓感蜗蟮目坍嫬@得了以捍衛(wèi)“小說營造”為宗旨的吉奧諾獎。
戈阿塔列穆的祖父1943年因一封捏造的匿名告密信被蓋世太保帶走,后被送到法國和德國的集中營,自此杳無音訊。這一事件成為家中的談話禁忌,作者的父親皮埃爾用噤聲的方式對抗幼年失父的恐懼與無助,逐漸成長為一個用沉默來埋葬自己悲傷的人。對戈阿塔列穆來說,這一禁忌造成的缺憾卻讓他成為一名以“找尋”為創(chuàng)作主題的作家:他的作品總在尋找他處、他者、陌生人、失蹤的人,對曾與祖父一樣在中南半島客居過的高更和謝閣蘭格外留意,似乎是想通過這樣的靠近,來填補心中的“黑洞”。
在十多部作品之后,戈阿塔列穆終于想要靠近“黑洞”的中心,寫一部關于祖父的小說,但父親不愿給他提供任何線索,堅持用沉默作為自己的哀悼。戈阿塔列穆去市政府的檔案館,去警察局,去法國和德國的集中營,一路調(diào)查和追尋祖父的蹤跡,得到的卻只是一些零星的、相互矛盾的線索。它們會不會給出錯誤的引導?再加上真相經(jīng)常隱身在很多“不說”的身后或者不同“話語”角度的背后,那么,是不是應該繼續(xù)“沉默”?但父親的憂郁,祖母眼睛里“望不到盡頭的迷茫”,自己如影隨形的缺失感不斷在提示戈阿塔列穆,“沉默”只能是逃避的港灣,卻無法成為痛苦的解藥。他決定在有限資料的基礎上,虛構(gòu)出祖父的經(jīng)歷,因為“只有確切的詞語能激活他”。在書中,戈阿塔列穆將自己的猶疑和詢問如實寫下,嘗試與祖父、與那個時代、與那些和祖父同命運的人建立起對話,給無數(shù)像祖父一樣湮沒在塵埃中的普通人無法還原的生平一個文學的命運。這是一場過程比結(jié)果更重要的找尋,在與祖父虛構(gòu)的對話中,戈阿塔列穆找到了最切膚的完整感,并最大可能地連綴起家族敘事中缺失的那一環(huán)。比起固守沉默卻無法因沉默而療愈的父親,戈阿塔列穆在救治的道路上向前邁出了一步。
四、況味:人生的重與輕
2019年,法國的兩大文學獎——龔古爾獎和費米娜獎的獲獎作品都是講述“沒故事”的普通人的人生感受,作者著力刻畫的似乎是人生中的某種精神狀態(tài)。
獲龔古爾獎的《大家并不是以同樣的方式活在這世上的》書名雖長,故事卻簡單:在蒙特利爾的監(jiān)獄里,一個名叫保羅的囚犯用對逝去親人的回憶來捱過漫長的牢獄時光……敘述在冰冷的現(xiàn)實和美好的回憶間往返。
作者杜布瓦多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叫保羅,雖然此保羅非彼保羅,但這些作品大多是在講保羅們?nèi)松性?jīng)的努力和幸福,以及最終的失敗和幻滅。在這部小說里,熱愛汽車的祖父死于車禍,癡迷于水上飛機的伴侶韋羅娜死于飛機事故,做牧師的父親娶了嬉皮士風的母親,一個善良的人因失手打傷對他百般刁難的小頭目而獲刑……命運的荒唐撥弄似乎是杜布瓦作品的底色,但在這“人生無望”的底色上,杜布瓦用細膩的筆觸,寫出了人實現(xiàn)自我的努力、在無常的生存際遇中對生存意義不懈的追求,描繪出“生而為人的美與希望”。在小說中,保羅和他的親人們都因自我實現(xiàn)而幸福過:祖父母和伴侶雖然都被其所愛奪去了生命,但他們的一生都因為能夠愛其所愛而幸福;保羅“68一代”的母親堅持在自己的先鋒劇場放映情色片《深喉》,雖然此舉成為她婚姻終結(jié)的導火索卻不曾后悔;保羅在父親去世后,選擇去做老年公寓管理人的工作,希望能在這座“俗世修道院”里體會到“助人為樂”的幸福……杜布瓦憐惜人性在艱難人生中的“扭曲”,共情人在困境中的選擇,贊嘆人心中那一縷對美善的向往:保羅的父親中年時癡迷博彩,但仍兢兢業(yè)業(yè)地完成一個神父應盡的職責,他在最后一次布道時說:“……我想請你們在腦海中存放這樣一句話——我的父親在原諒人的過錯時常用——大家并不是用同樣的方式活在這世上的。”作者選取這句話作為書題,顯示了他的作品悲憫的人道主義內(nèi)核,也奠定了其小說哀而不傷的敘事語調(diào)。雖然保羅們的人生常常是如西緒弗斯般一次次徒勞地重建失去的平衡的過程,但或許作家想要傳達的是——在注定要失敗的人生旅途中自有生命的生機和情感的溫暖,我們可以藉此幸福地走向自己的悲劇。
杜布瓦的保羅們經(jīng)歷了人生難以承受之重,而普呂多姆獲費米娜獎的《在路上》寫的卻是身處“歲月靜好”中的年輕人在“存在之輕”中的選擇與承受。
全書以十七世紀法國利穆贊地區(qū)一位無名行吟詩人的詩句“時間去了又來,轉(zhuǎn)了彎”開頭,道出了“時間”這一讓主人公薩沙在寫作和生活中縈懷的主題。小說中,生活在巴黎的作家薩沙渴望一種能夠有利于寫作的寧靜和孤獨,將他在流逝的時光中體會到的種種微妙、悖論、歡樂和痛苦在紙面上拓展和理解,于是移居到法國西南的一座小城。在那里,他竟與十五年前一起搭順風車的舊友重逢,這位朋友盡管娶妻生子,卻一直沒有停下“搭順風車”的腳步。小說從薩沙的視角,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方式來講述自己和“搭順風車的人”當下的日復一日,寫了穿行在生活中的時間,寫了友誼的美,愛情的層次,欲望的明暗,寫了平淡生活中內(nèi)心的小音樂……像是沒寫什么,又像是寫了很多。
“愿望”是這部小說內(nèi)在的主線,除了寫作的愿望和出發(fā)的愿望,書中還有各種大大小小的愿與欲:愛的愿望,身體的欲望,對美的向往……在追求愿望的實現(xiàn)中,魚與熊掌的選擇無處不在:“搭順風車的人”每到一處必要寄回家的照片和明信片、他遵照妻兒為他安排的搭車路線等行為透露出他“既想要出發(fā),又想要留下”的矛盾心理;薩沙和“搭順風車的人”的妻子瑪麗志同道合,兩情相吸,但出于對曾照亮過舊日時光的友情和愛情的尊重,他們心照不宣地各自退后一步,將之轉(zhuǎn)化成海闊天空的友誼;薩沙和讓娜兩性相悅后心態(tài)上微妙的盈與虧等等;作者將人物的“愿望、選擇、承受”等心理引發(fā)的豐沛情感都外化在豐富細膩的動作情態(tài)描寫和柔和安靜的語調(diào)里:他寫彌散著橄欖油香味的廚房、寫顫抖的肌膚的溫柔、寫心有靈犀后瞬間的對視、寫搭順風車沿途所見的森林、海鷗、百態(tài)的世相、百樣的人生……
這本情節(jié)不多的小說被讀者闡述出了眾多的主題:希望、自由、創(chuàng)造、愛情、風光……但或許主題之一,是對待生命的態(tài)度。小說中,作者借人物之口說出對人生的看法——“從來都是同樣的事情。生命在過去。時間在溜走。就是這么簡單,從來都沒有什么精彩發(fā)生”。全書沒有一個問號和感嘆號,吻合了人物對待生命不疑不驚的了然態(tài)度。然而,在明瞭生命的虛空本質(zhì)之后,依然能夠認真對待和珍視生活,恐怕是“在路上”的西緒弗斯另一種“舉輕若重”的樣貌吧。
從以上對2019年幾部法國小說的介紹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對時代和社會問題的思考,還是將歷史事件融入家族個體的敘事,或是對人生對時間的體察,作家都把目光轉(zhuǎn)向了人心和人性,顯示出了鮮明的人道主義關懷。或許,寫作,終歸是一件與人為善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