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爾丘克:在“怪誕”的文學(xué)罐頭里想象未來(lái) ——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新書《怪誕故事集》云首發(fā)
2018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新作《怪誕故事集》的中譯本,日前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由十篇風(fēng)格各異的短篇小說(shuō)組成。這十個(gè)故事打破人與自然,人與物質(zhì)世界的界限,超越時(shí)間和空間,以宏大的文學(xué)視野,帶讀者進(jìn)入既怪誕又溫柔,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其中每一個(gè)故事,都潛藏著對(duì)加速變化著的社會(huì)生活的隱喻和對(duì)未來(lái)的某種想象。

活動(dòng)現(xiàn)場(chǎng)
8月3日晚7點(diǎn),《怪誕故事集》云首發(fā)活動(dòng)在單向LIVE直播間舉行。第十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作家李洱,《世界文學(xué)》主編、翻譯家高興,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歐洲語(yǔ)言學(xué)院院長(zhǎng)、教授、翻譯家趙剛,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波蘭語(yǔ)教研室主任、《怪誕故事集》譯者李怡楠,在直播間與讀者一同分享托卡爾丘克的新作,以及她怎樣以文學(xué)的形式提出關(guān)于當(dāng)下這個(gè)世界的種種問(wèn)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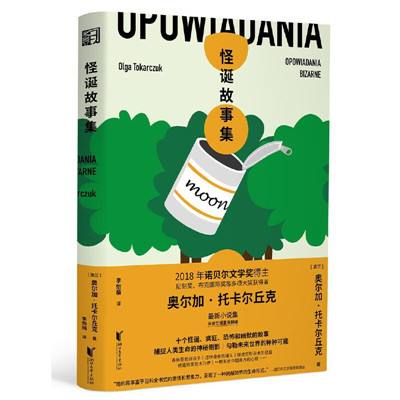
《怪誕故事集》書影
“怪誕”非荒誕,是對(duì)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的延伸
托卡爾丘克在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進(jìn)入波蘭文壇,作品形式多變,善于融合民間傳說(shuō)、神話、宗教故事、科幻等元素來(lái)觀照波蘭的歷史與人類生活。曾憑借《云游》和《雅各布之書》兩次榮獲波蘭權(quán)威文學(xué)大獎(jiǎng)尼刻獎(jiǎng),六次獲得尼刻獎(jiǎng)提名;2018年《云游》獲布克國(guó)際獎(jiǎng);2019年《雅各布之書》榮獲法國(guó)儒爾·巴泰庸獎(jiǎng),同年《犁過(guò)亡者的尸骨》入圍布克國(guó)際獎(jiǎng)短名單,由該小說(shuō)改編的電影《糜骨之壤》曾獲2017年柏林國(guó)際電影節(jié)銀熊獎(jiǎng)。《怪誕故事集》是托卡爾丘克出版于2018年的新作,中文版由李怡楠從波蘭語(yǔ)直接翻譯。

李怡楠
李怡楠在現(xiàn)場(chǎng)分享了自己翻譯《怪誕故事集》的經(jīng)歷。她回憶到,自2016年起每年都會(huì)關(guān)注波蘭文學(xué)的年度動(dòng)態(tài)。2018年,她在整理當(dāng)年波蘭文學(xué)的年度動(dòng)態(tài)時(shí),關(guān)注到《怪誕故事集》。當(dāng)時(shí)因?yàn)闀r(shí)間有限,沒有讀完全書,但看了不少書評(píng)。后來(lái)她在院長(zhǎng)趙剛的辦公室又看到《怪誕故事集》,表達(dá)了想翻譯的意愿。李怡楠介紹說(shuō),“怪誕”(bizarne)這個(gè)詞在標(biāo)準(zhǔn)波蘭語(yǔ)中找不到,是托卡爾丘克結(jié)合法語(yǔ)詞根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法語(yǔ)詞匯“怪誕”(bizarre)意思是“奇怪的、多變的、可笑的、超乎尋常的”。除了“怪誕”,《怪誕故事集》里還出現(xiàn)了不少托卡爾丘克自己生造的詞,像《變形中心》里的“變形中心”、《拜訪》里的“愛工”、《人類的節(jié)日年歷》里的“雷控”等。

李洱
結(jié)合閱讀經(jīng)驗(yàn),李洱認(rèn)為,“怪誕”并非我們平時(shí)所說(shuō)的奇幻或魔幻,而是指這個(gè)時(shí)代不斷增加的各類信息超出日常認(rèn)知后導(dǎo)致的一種不可控制的、不斷分裂的感覺。托卡爾丘克的小說(shuō)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蘑菇”這一意象,在訪談中,她也提到過(guò)蘑菇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動(dòng)物,而是一種菌類。李洱把“蘑菇”看成解讀托卡爾丘克小說(shuō)的關(guān)鍵詞,“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把她(托卡爾丘克)的小說(shuō)看作一種蘑菇,一種介于動(dòng)物和植物之間、介于神話思維和日常思維、介于人物傳記和童話之間的故事類型。”
李怡楠在閱讀和翻譯《怪誕故事集》時(shí),經(jīng)常一身冷汗,譯完好多天都不敢校對(duì)譯稿,得先緩一緩。但她也提醒讀者注意,托卡爾丘克小說(shuō)中的情節(jié)雖然荒誕、不可思議,但都是現(xiàn)實(shí)中會(huì)發(fā)生的事情。“托卡爾丘克真正想表現(xiàn),或者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東西,其實(shí)就是我們身邊的東西。”
碎片化時(shí)代,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書寫
《怪誕故事集》由十篇圍繞“怪誕”這一核心主題展開的短篇故事組成:《旅客》講述“我”在長(zhǎng)途旅行中遇到的男子述說(shuō)他幼年經(jīng)常在床邊看到的 “鬼魂”竟是老年時(shí)的自己;《綠孩子》發(fā)生在1656年的波蘭,身為國(guó)王御醫(yī)的“我”遇到兩個(gè)和自然渾然一體的“綠孩子”,仿佛獲得了治愈的解藥;《接縫》里的主人公在衰老時(shí)突然發(fā)現(xiàn)世界的一切都變了;《變形中心》里的姐姐選擇變成一匹狼,回歸森林;在《拜訪》里,世界仿佛沿著時(shí)間的軌跡在蝸牛殼里爬行,智能“愛工”的存在使世界變得精密、完美卻也乏味;《萬(wàn)圣山》里的神秘心理研究揭開了關(guān)于修道院里木乃伊的一段陰暗歷史……這些故事涵蓋科幻、童話、史詩(shī)等多種文體類型,除了內(nèi)容的豐富和雜糅之外,寫作風(fēng)格和手法也多種多樣。

高興
“托卡爾丘克的開放性和豐富性讓人驚訝。”高興稱托卡爾丘克為一位博聞強(qiáng)識(shí)的作家,能在各個(gè)領(lǐng)域順暢地騰躍、跨界,幾乎每部作品都構(gòu)造了一個(gè)獨(dú)特的世界。“托卡爾丘克厲害就厲害在,她似乎掌握著十八般武藝,而且她的作品中,涉及到的學(xué)科領(lǐng)域太多了:人類學(xué)、心理學(xué)、植物學(xué)、醫(yī)學(xué)……真的是需要一顆百科全書式的頭腦才能創(chuàng)作出這么多奇妙的作品。”高興將托卡爾丘克的小說(shuō)歸納為“合成的文學(xué)”,并提到,托卡爾丘克小說(shuō)中呈現(xiàn)的碎片化,絕對(duì)是一種精心安排的結(jié)果,給讀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間。“她實(shí)際上教會(huì)我們用怎樣的方式看待這個(gè)世界,她特別強(qiáng)調(diào)視角的轉(zhuǎn)換,視角變化可能讓讀者看到一個(gè)不同的世界。所以托卡爾丘克的很多長(zhǎng)篇如同紙牌那樣,可以不斷組合,然后在這種不斷組合的基礎(chǔ)上獲得新的意義。”
“托卡爾丘克的小說(shuō),用一個(gè)詞形容的話,就是強(qiáng)烈的綜合性。”綜合性也是李洱觀察到的小說(shuō)在世界范圍內(nèi)近20年來(lái)發(fā)展的一種潮流。“從文體上看,托卡爾丘克的小說(shuō)雜糅了游記、日記、童話、神話等多種形式,呈現(xiàn)出一種綜合性特征。思維方式上,托卡爾丘克認(rèn)為神話故事從未發(fā)生過(guò),但神話思維一直留存于人間,她的小說(shuō)帶有強(qiáng)烈的溢出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的思維方式。”李洱尤其注意到,托卡爾丘克的小說(shuō)彼此之間有鑲嵌作用的故事片段,通過(guò)相互“擠壓”產(chǎn)生了化學(xué)反應(yīng)。“這有點(diǎn)類似于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流行的一種碎片化,甚至可以說(shuō)用原始思維寫成的故事。看上去虛構(gòu)的故事,卻帶有某種非虛構(gòu)的色彩,這可以看成是托卡爾丘克對(duì)這個(gè)時(shí)代的寫作做出的一種調(diào)整。”
李洱將當(dāng)下形容為一種信息紛亂、不斷向我們提供一些負(fù)面的惡的時(shí)代,他認(rèn)為托卡爾丘克的碎片化寫作與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大眾傳媒的發(fā)達(dá)密切相關(guān),“現(xiàn)在所有作家都要面對(duì)這樣一個(gè)現(xiàn)實(shí),這個(gè)現(xiàn)實(shí)就是如何面對(duì)網(wǎng)絡(luò)、手機(jī)等現(xiàn)代通訊手段對(duì)人的沖擊和擠壓,以及傳統(tǒng)的敘事方式在不斷受到挑戰(zhàn)的情況下,如何做出調(diào)整。”李洱覺得,托卡爾丘克既迎合了這個(gè)碎片化時(shí)代,又通過(guò)寫作對(duì)時(shí)代提出了質(zhì)疑,表現(xiàn)出了一個(gè)作家的良知和本能。“如何認(rèn)識(shí)這個(gè)時(shí)代,如何把握這個(gè)時(shí)代,如何用小說(shuō)的方式應(yīng)對(duì)這個(gè)時(shí)代,托卡爾丘克確實(shí)可以作為一種方法。我們來(lái)認(rèn)識(shí)她,從而來(lái)審視自己。”
李怡楠提到,托卡爾丘克本人非常推崇短篇小說(shuō),她在波蘭專門倡導(dǎo)短故事文學(xué)集。接受采訪時(shí),托卡爾丘克曾談過(guò)長(zhǎng)篇小說(shuō)和短篇小說(shuō)的區(qū)別:長(zhǎng)篇小說(shuō)讓讀者進(jìn)入一種縹緲的狀態(tài),融入到整個(gè)長(zhǎng)篇中;短篇小說(shuō)對(duì)作家要求更高,作家要有能夠創(chuàng)造所謂“妙語(yǔ)金句”的能力。“托卡爾丘克還是很熱衷于進(jìn)行碎片化的短篇小說(shuō)的創(chuàng)造,她在當(dāng)今時(shí)代的文學(xué)叢林找到一條新的道路。她不一定用這種方式迎合碎片化的時(shí)代和碎片化的閱讀方式,但這種方法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她的標(biāo)簽之一,她的短故事背后其實(shí)蘊(yùn)藏著許多深刻的思考。”
正如托卡爾丘克在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受獎(jiǎng)演說(shuō)《溫柔的講述者》中所說(shuō),“也許我們應(yīng)該相信碎片,因?yàn)樗槠瑒?chuàng)造了能夠在許多維度上以更復(fù)雜的方式描述更多事物的星群。我們的故事可以以無(wú)限的方式相互參照,故事里的主人公們會(huì)進(jìn)入彼此的故事之中,建立聯(lián)系。” 這或許就是托卡爾丘克所提出的“第四人稱講述者”的要義:搭建某種新的語(yǔ)法結(jié)構(gòu),而且有能力使作品涵蓋每個(gè)角色的視角,并且超越每個(gè)角色的視野,看到更多、看得更廣,以至于能夠忽略時(shí)間的存在。
既有波蘭性,又具有非波蘭性
托卡爾丘克是波蘭歷史上第五位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作家,此前已有顯克維奇(1905年)、萊蒙特(1924年)、米沃什(1980年)、辛波絲卡(1996年)等四位作家獲獎(jiǎng)(此處不包括從波蘭移居美國(guó)的艾薩克·辛格)。為什么在短短一百多年時(shí)間里,波蘭走出了五位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現(xiàn)場(chǎng)作家、評(píng)論家對(duì)此做了一番交流。趙剛認(rèn)為這與波蘭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有關(guān)。像許多中東歐國(guó)家一樣,波蘭也是傳統(tǒng)的歐洲價(jià)值觀和現(xiàn)代文明的擠壓的一塊土地。在過(guò)去幾百年,甚至是一兩千年,波蘭以及很多中東歐國(guó)家一直在歐洲文明圈的邊緣,政治上的腥風(fēng)血雨時(shí)常在此發(fā)生,東西方文明在此碰撞和交融。“他們內(nèi)心一方面非常珍惜和懷戀所生長(zhǎng)的鄉(xiāng)村自然環(huán)境;另一方面,他們又被卷入或帶入現(xiàn)代文明的軌道上。包括米沃什等作家都曾深刻地反思這個(gè)問(wèn)題。有擠壓才會(huì)迸發(fā),在重重重壓的內(nèi)心糾結(jié)的狀態(tài)下,他們的文化達(dá)到了一種高度。”

趙剛
趙剛將波蘭文學(xué)分成兩種流派。其中一個(gè)流派以密茨凱維奇、顯克微支、萊蒙特等正統(tǒng)作家為代表,特點(diǎn)是有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用作品來(lái)表現(xiàn)民族精神,為國(guó)家代言。另一個(gè)流派是像貢布羅維奇、布魯諾·舒爾茨、辛波斯卡等現(xiàn)當(dāng)代作家,他們的作品對(duì)波蘭的民族性格和特點(diǎn)、波蘭的歷史和文化有客觀而冷靜的反思和批判。“如果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潮流存在的話,波蘭文學(xué)很難走到今天這樣一個(gè)高度。恰恰有多元共存的現(xiàn)象存在,給波蘭文學(xué)創(chuàng)造了一方肥沃的土壤。” 在趙剛看來(lái),托卡爾丘克便誕生在這方沃土之上,同時(shí)在諸多方面突破了波蘭文學(xué)的傳統(tǒng)框架。“在托卡爾丘克的視野里,人和自然不是對(duì)立的,也說(shuō)不上人的世界和非人世界的區(qū)別,它是一個(gè)逐漸過(guò)渡、逐漸變化的過(guò)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個(gè)融合的世界。”
高興表示,波蘭出現(xiàn)一批享有世界聲譽(yù)的杰出作家,完全在情理之中。他將趙剛提到的波蘭文學(xué)兩條不同的創(chuàng)作思路簡(jiǎn)單地稱為“波蘭性”和“非波蘭性”,并認(rèn)為托卡爾丘克綜合了兩者。“托卡爾丘克既有波蘭性,又具有非波蘭性。“顯克維支那種具有震撼的歷史細(xì)節(jié)描寫能力——她有,貢布羅維奇怪誕的那種想象力——她有,舒爾茨那種變形——她有,以及那種巧妙的暗喻——她也有。”在高興看來(lái),托卡爾丘克與波蘭其他當(dāng)代作家相比更具文學(xué)性,是當(dāng)今中東歐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溫柔地邀請(qǐng)讀者進(jìn)入她的文學(xué)世界
作為一位帶有先鋒性質(zhì)的當(dāng)代作家,托卡爾丘克并不拒絕講故事。在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受獎(jiǎng)演說(shuō)中,她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講故事對(duì)解構(gòu)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的重要作用。“文學(xué)是為數(shù)不多的使我們關(guān)注世界具體情形的領(lǐng)域之一,因?yàn)閺谋举|(zhì)上講它始終是心理的,我覺得這里的心理其實(shí)關(guān)乎靈魂的意思,它重視人物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和動(dòng)機(jī),揭示其他人以任何其他方式都無(wú)法獲得的經(jīng)歷,激發(fā)讀者對(duì)行為的心理學(xué)解讀,只有文學(xué)才能使我們深入一個(gè)人的生活,理解他的觀點(diǎn)、分享他的感受、體驗(yàn)他的命運(yùn)。”
高興認(rèn)為托卡爾丘克是一個(gè)建構(gòu)者,而不是一個(gè)解構(gòu)者。她的很多作品故事中有新的故事,講述故事的方式是中斷舊故事、然后再講新故事。高興說(shuō),世界和生活的真相有時(shí)候就是這樣,不斷地被打斷,我們不可能完整去聽一個(gè)故事,講述一個(gè)故事。如果仔細(xì)閱讀的話,托卡爾丘克的小說(shuō)可以拼成很多完整的故事,這個(gè)需要讀者的互動(dòng)。“進(jìn)入托卡爾丘克的文學(xué)世界,可能比較容易。但是要真正地深入領(lǐng)略她的文學(xué)世界,則需要讀者有一定的藝術(shù)修養(yǎng)、藝術(shù)境界、人生閱歷,以及對(duì)世界復(fù)雜性和豐富性的準(zhǔn)確看法。”

托卡爾丘克
高興表示,托卡爾丘克是一個(gè)具有靈魂意識(shí)的作家,這種意識(shí)使她能夠成為一個(gè)溫柔的寫作者。“托卡爾丘克是強(qiáng)調(diào)意義的,強(qiáng)調(diào)每部作品、每本小說(shuō)起碼都要圍繞著一定的意義,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種迷人的、貼心的光澤。托卡爾丘克是一個(gè)絕對(duì)有魅力、有個(gè)性的作家,始終以一種溫柔的、親切的方式邀請(qǐng)我們進(jìn)入她的文學(xué)世界。如果我們能夠應(yīng)她親切溫柔的邀請(qǐng),走進(jìn)她的世界的話,肯定會(huì)發(fā)現(xiàn)一個(gè)極為豐富、極為復(fù)雜的文學(xué)天地,同時(shí)又能讓我們多多少少捕捉到世界和人生的真正意義。”
“托卡爾丘克是一個(gè)特別值得去細(xì)讀的作者。”李怡楠補(bǔ)充道,“可能世界上每一個(gè)角落的讀者,都可以通過(guò)閱讀她的文字或者她的作品,找到自己的故事,找到自己對(duì)于托卡爾丘克寫的某一句話或者某一個(gè)詞的一種對(duì)應(yīng)的理解。”
《怪誕故事集》里,便有來(lái)自世界不同角落的十種生命經(jīng)驗(yàn)。在今天這樣一個(gè)信息泛濫、碎片化的時(shí)代,托卡爾丘克繼續(xù)用她瑰奇的想象力,提醒著我們“文學(xué)”和“講故事”的重要性。在托卡爾丘克看來(lái),文學(xué)是“為數(shù)不多的使我們關(guān)注世界具體情形的領(lǐng)域之一”,文學(xué)還保留著怪誕、幻想、挑釁、滑稽和瘋狂的權(quán)利。可以說(shuō),文學(xué)賦予了碎片以意義和存在感,重構(gòu)了我們的生命經(jīng)驗(yàn),并成為我們對(duì)抗日益膚淺化和儀式化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一劑解藥。
據(jù)悉,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將推出的托卡爾丘克作品全系列(共九部),包括長(zhǎng)篇小說(shuō)《犁過(guò)亡者的尸骨》(即《糜骨之壤》)《最后的故事》《雅各布之書》等,以及小說(shuō)集《衣柜》《鼓聲齊鳴》等。該系列作品均從波蘭語(yǔ)直接翻譯,譯者包括著名波蘭語(yǔ)文學(xué)翻譯家、學(xué)者張振輝、烏蘭、茅銀輝、李怡楠、林歆等。除《怪誕故事集》外,8月下旬還將出版小說(shuō)集《衣柜》,長(zhǎng)篇小說(shuō)《犁過(guò)亡者的尸骨》和散文《玩偶與珍珠》也計(jì)劃于年內(nèi)與讀者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