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聊天記錄》到《正常人》:怎樣在突破自我的愛中尋回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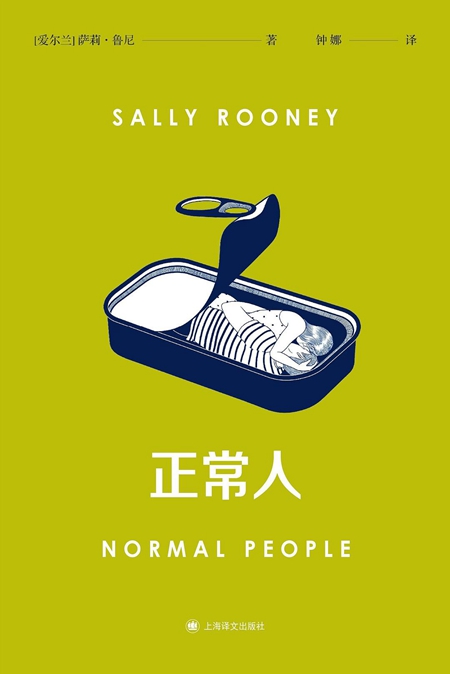
在第一部小說《聊天記錄》里,薩莉·魯尼引用弗蘭克·奧哈拉的話開場:“在危機(jī)時,我們都必須一次又一次地決定,我們究竟要愛誰。”這句話的重點在于“決定”和“要”,似乎愛被迫成為一種選擇得到或者選擇給予的能力,選擇自己還是選擇他人,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薩莉·魯尼筆下的角色們。《聊天記錄》的結(jié)尾,弗朗西絲選擇放棄種種對自身的構(gòu)建,重新投入與尼克的戀情中去。《正常人》里的瑪麗安和康奈爾在一次次分離和重聚中,經(jīng)受這種選擇的考驗,無論結(jié)果如何,都將為彼此帶來持久的影響。小說《正常人》是薩莉·魯尼的第二部作品,講述瑪麗安和康奈爾在戀情中彼此成長的故事,今年夏天,根據(jù)小說改編的同名劇集再次將這個故事帶回觀眾的視線。
小說的初始背景在愛爾蘭的一個虛構(gòu)小鎮(zhèn),瑪麗安和康奈爾是同學(xué),瑪麗安高冷不合群,是眾人眼里的怪人,康奈爾性情溫和,善于跟周圍的人打成一片。兩人在小說開始的那段對話里率先表露出彼此間輕微的敵意,瑪麗安用審視的態(tài)度打量康奈爾,局促不安的康奈爾只想著快速離開,這里也交代了兩人背后的另一層關(guān)系:康奈爾的母親是瑪麗安家的女傭,每周兩次去這座豪宅里打掃衛(wèi)生。從性格和家庭背景上說,他們都分屬不同的世界。魯尼的角色總是如此,《聊天記錄》里的弗朗西絲用種種理念武裝自己,免遭傷害。出生在富裕家庭的瑪麗安,與母親和哥哥一起生活,母親對她態(tài)度冷漠,時常無視哥哥對瑪麗安的語言暴力,過世多年的父親也曾毆打過瑪麗安。成長于這樣缺乏關(guān)愛的環(huán)境,瑪麗安身上的高冷與古怪同樣是一種應(yīng)對外界的方式:筑起情感的高墻,抵擋傷害,也隱藏自身的敏感、自卑和脆弱。
至于魯尼的男主角們都帶有一種軟弱的善良,他們是這個不夠健全的環(huán)境里相對中庸的性別產(chǎn)物,不夠好,也不會壞到像瑪麗安的哥哥和父親。出生于貧民家庭的康奈爾沒有父親,與母親關(guān)系和睦,身邊朋友眾多,即便他的朋友不像他喜歡閱讀和思考,他也討厭朋友對女性的評頭論足,但他依然選擇了一種溫和、沉默的入世方式——似乎同樣出于自我偽裝的目的,來獲取所需的人際關(guān)系和情感交流。當(dāng)目睹瑪麗安孤立在人群之中,無視校規(guī),頂撞老師,發(fā)表著刻薄又獨(dú)到的觀點,已經(jīng)融入人群的康奈爾在感到不安的同時多出一絲敬畏。在這個正常的世界里,他與瑪麗安是不夠正常的兩個人,像背道而馳的兩列車,一列逃往更不正常的方向,一列努力奔向正常。
當(dāng)瑪麗安和康奈爾相愛時,小說似乎步入一個俗套、主流的敘事模板:富家女與窮小子打破偏見和束縛,在完成這段充滿戲劇感和浪漫色彩的戀情后必將收獲眾人的掌聲與祝福。薩莉·魯尼的處理可以說是對這一敘述模板從內(nèi)向外的重寫。
《正常人》的開場引用了來自喬治·艾略特的《丹尼爾·德龍達(dá)》的一句話:“對我們當(dāng)中許多人來說,無論天或地都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啟示,直到某種個性同他們的相碰,帶來一種不同尋常的影響,并迫使他們接受它。”——正如上面提到的,她延續(xù)自己在《聊天記錄》中對角色心理細(xì)膩、深入的洞悉,幾次對話過后,瑪麗安和康奈爾逐漸識別出他們內(nèi)在同質(zhì)的、敏感又纖細(xì)的天性,這種天性將他們吸引在一起,也迫使他們分離。英劇《正常人》劇照
例如小說里,康奈爾害怕這段關(guān)系的公布會對自己造成影響,與瑪麗安始終保持著地下戀情。天性中的敏感未能壓倒自私,也未能對抗外界的目光。
來到大學(xué),康奈爾變成了與人群格格不入的那個,瑪麗安活躍于各種社交活動,變成了另一個康奈爾。
薩莉·魯尼善于在她的小說中探討人際關(guān)系與性別、階級意識之間的互相作用。無需刻意構(gòu)建,這些意識已經(jīng)自然地融入到瑪麗安與康奈爾德這段關(guān)系中,也使得兩人之間搖擺于友誼和愛情之間的關(guān)系變得愈為復(fù)雜和模糊。而在一次次嘗試撕開這種模糊表象的努力中,薩莉·魯尼將瑪麗安和康奈爾裸露在真實的肉體關(guān)系中,他們享受過短暫、純粹的歡愉,也因為時常要回到模糊之中感受刺痛。
不同的階級帶來金錢與地位觀念的差異。對于同為優(yōu)等生的瑪麗安和康奈爾來說,一份獎學(xué)金代表完全不同的意義,瑪麗安將其看作是一種榮譽(yù),對自身能力的認(rèn)可,證明自己比別人聰明。康奈爾的觀點更實用,獎學(xué)金意味著他不用擔(dān)心房租,不用努力打工賺學(xué)費(fèi),他可以用一下午的時間欣賞一幅名畫。
康奈爾和瑪麗安在大學(xué)復(fù)合后的一次對話,堪稱完美地展示了這種觀念差異與敏感天性組合起來會產(chǎn)生怎樣的破壞力。起因是康奈爾負(fù)擔(dān)不起房租,試探性地告訴瑪麗安自己要搬家,內(nèi)心其實希望獲得后者的幫助。對于從未陷入金錢窘境的瑪麗安來說,她自然意識不到康奈爾背后羞于啟齒的需求。對話開始跑偏,兩人都以為對方想再次結(jié)束這段關(guān)系,康奈爾為自己感到可悲,他甚至覺得瑪麗安“想要那種家里能帶她假期去滑雪的男朋友”。
薩莉·魯尼在小說里同樣審視了不同形式的親密關(guān)系及其可能帶來的后果。分別之后,康奈爾遇到跟自己貌合神離的海倫,他認(rèn)可這段關(guān)系最合拍的部分:“忠誠,總體上實用的人生觀,希望被視作好人的愿望。”也會因為海倫無法理解自己傷神。瑪麗安在與兩個偏執(zhí)、暴力的男性交往中,被壓迫式的親密關(guān)系剝奪著對愛的渴望,她重新找回冷漠的家庭環(huán)境中養(yǎng)成的自我認(rèn)知:自己不能像正常人一樣,不能讓別人愛自己。
即便在分別過程中,瑪麗安和康奈爾依舊保持通信和偶爾的肉體關(guān)系,薩莉·魯尼似乎將小說中少有的浪漫都濃縮在這樣一個跨越時間和距離的場景中,當(dāng)身處愛爾蘭的康奈爾因抑郁癥失眠,遠(yuǎn)在瑞典的瑪麗安開著視頻陪他入睡。瑪麗安回到愛爾蘭后,康奈爾也幫助她擺脫了來自家庭的壓迫。
或許正是從這里開始,經(jīng)由不間斷的分離與重聚,反復(fù)體驗過選擇的得失后——是愛自己,被性別、階級、與生俱來的環(huán)境和天性圍困,還是在嘗試淡化這一切、理解這一切的基礎(chǔ)上給予他人,瑪麗安與康奈爾的關(guān)系朝向一個健康、正常的方向發(fā)展。薩莉·魯尼那個關(guān)于植物的比喻凸顯出無與倫比的精妙,她的原話是這樣——
這些年來,他們就像一盆土中的兩株植物,環(huán)繞彼此生長,為了騰出空間而長得歪歪扭扭,形成某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姿態(tài)。
小說結(jié)尾,康奈爾與瑪麗安重新走到一起,又因為康奈爾要前往紐約求學(xué)再次面臨分離,他們欣然接受。這種分離與以往相比產(chǎn)生截然不同的意義,他們騰出空間,是為了幫助對方成為更好的自己。而所謂的“正常”再也無關(guān)于世界和他們對“正常”界定的爭奪,成長的姿態(tài)會以自己的方式給出問題新的答案,這個答案只有他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