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巨擘 科幻傳奇 研究先鋒——葉永烈科普科幻創(chuàng)作綜述
葉永烈從11歲開始發(fā)表作品,少年時期便走上文學(xué)道路,后來歷經(jīng)幾多職業(yè),身份幾經(jīng)變換。他是導(dǎo)演,著有介紹電影制作過程的《電影的秘密》,拍攝過《紅綠燈下》,獲得過最佳科教片獎;他是記者,遠赴自然條件惡劣的羅布泊,零距離追蹤科學(xué)事件,拍攝大量照片并持續(xù)報道,寫下《追尋彭加木》這樣的紀實文學(xué);他是編劇,寫過《美猴王》《神筆大俠》《中華五千年》等劇本;他是專業(yè)作家,風(fēng)格多變,既寫科普又寫科幻,還寫游記和傳記,有35篇文章被選入各種版本的中小學(xué)語文教科書;他是研究者,對科普科幻的研究碩果累累,言前人之所未言,學(xué)術(shù)觀點嚴謹周到。他處處涉獵又能處處開花,很難定位哪個領(lǐng)域的成就是其人生的巔峰。但可以明確一點,他是當(dāng)代以來,中國科普與科幻創(chuàng)作的奠基者之一。不同年齡段的讀者受其啟發(fā),循著他的作品走進對科學(xué)的探索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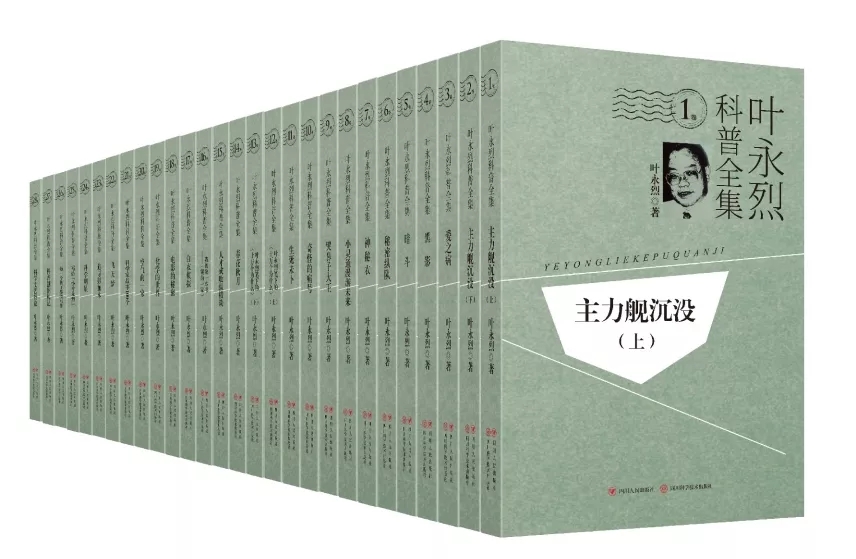
對于中國當(dāng)代科普科幻文壇來說,葉永烈這個名字有著多重意義,他的寫作之路、諸多成就、對社會的影響、引起的爭論等幾乎是中國當(dāng)代早期科普科幻發(fā)展的縮略圖。他的筆下,有對高科技與美好未來的憧憬,有面向大眾普及科學(xué)的執(zhí)著與熱情,有對新敘事形式的探索與嘗試。暢銷、鮮花、褒獎、榮譽以及質(zhì)疑、批判、嘲諷、打擊,一個科幻作家所能遭遇的,他都經(jīng)歷過。毫不夸張地說,我們可以從葉永烈身上讀到一部中國當(dāng)代早期科普科幻發(fā)展史和思想發(fā)展史,他的經(jīng)歷與中國獨特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科技緊密相連,完整地閱讀葉永烈便意味著開啟了一次中國當(dāng)代科普科幻之旅,研究葉永烈的科普科幻創(chuàng)作,對于重新審視中國當(dāng)代思想發(fā)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科普創(chuàng)作
葉永烈的創(chuàng)作歷程自科普起步,可以追溯至1959年。當(dāng)時,他還只是一個19歲的學(xué)生,便已在報紙上發(fā)表了數(shù)十篇科學(xué)小品,第二年將其結(jié)集為《碳的一家》,這便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書中以碳元素為中心,介紹與其相關(guān)的物質(zhì),例如,由碳元素構(gòu)成的金剛石、石墨、煤、二氧化碳、石灰石、石油、糖等,它們分別具有何種特性以及它們之間的差別;碳元素與其他元素反應(yīng)得到的新物質(zhì),這些物質(zhì)在生活中的形態(tài)等。內(nèi)容由淺入深,妙趣橫生,為人們打開了一個新異而奇妙的世界。當(dāng)時政治氛圍濃厚,適合青少年的讀物異常稀缺,可想而知這樣一部脫離政治語境又通俗易懂、活潑有趣的科普書籍受到了怎樣的喜愛。
后來,葉永烈的科普創(chuàng)作一發(fā)而不可收,靈感頻頻,俯拾皆是,揮灑自如,步履輕盈。其科普讀物、科學(xué)小品、創(chuàng)作理論等大面積覆蓋閱讀界,尤以參加《十萬個為什么》的編著為代表。這套叢書在國內(nèi)幾乎家喻戶曉,引起了社會極大反響,總印數(shù)超過1億冊,激發(fā)了讀者“對科普讀物的興趣”, 甚至“影響了他們以后的人生選擇”。北京大學(xué)化學(xué)系畢業(yè)的經(jīng)歷為葉永烈提供了創(chuàng)作 的知識儲備與專業(yè)眼光,那些信手拈來的數(shù)理化知識也令人大開眼界。然而,科普創(chuàng)作并非易事,僅有知識儲備是不夠的,還需要知識的更新、精進,更要懂得寫作的技巧,擺脫教科書式的宣教。縱觀葉永烈的科普作品,大致可用以下幾點概括。
(一)博與新
題材之“博”之“新”是葉永烈科普創(chuàng)作的一大特色,其寫作范圍之廣令人驚異,幾乎包羅萬象、無所不納,其科學(xué)視野的寬廣與敏銳的發(fā)現(xiàn)眼光令人感嘆,同時也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了作家的勤奮與思索的深入,這是優(yōu)秀科普作家必備的特質(zhì)。他像一個孜孜不倦的解謎者,不斷剝開大自然的神秘外衣,露出內(nèi)部真實的肌理,通過一個個常見的現(xiàn)象讓人們探求其背后的原因。
他要求自己“做一個科學(xué)雜家”,閎覽博物,認知遼闊的科學(xué)疆域。上至天文航空、下至地理考古、中曉物理化學(xué),世界萬物都能引起他的好奇,成為其關(guān)注的對象。他寫植物、寫動物,介紹種子的組成部分,發(fā)芽的必要條件,寫蝌蚪變青蛙的過程及捕蟲本領(lǐng),寫染料、香料、化學(xué)元素、塑料、皮革,還寫熊貓、風(fēng)箏、集郵、火花、青苔和海鷗。除此之外,1981年,葉永烈在創(chuàng)作《黑影》《暗斗》等“金明系列”驚險科幻小說時,因深入警方生活,了解了許多現(xiàn)代偵破技術(shù),竟產(chǎn)生出一部厚厚的“副產(chǎn)品”——《白衣偵探》。書中講述了種種現(xiàn)代科技偵破技術(shù),如通過指紋、唇紋、聲紋、血型和頭發(fā)等細節(jié)破獲案件,剖析眾多實證 案件的蛛絲馬跡,不是科幻卻更加精彩,讓人手不釋卷。這也是一次大規(guī)模的科普與公安偵破題材結(jié)合的嘗試。
體裁之“博”同樣引人注意。可以說,在科普創(chuàng)作這一大背景下,沒有哪一種體裁是他沒有嘗試過的。他率先提出“科學(xué)雜文”“科幻童話”“科學(xué)寓言”三種體裁,在 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了國內(nèi)第一本科學(xué)雜文集、第一本科幻童話集和第一本科學(xué)寓言集。除了人們熟知的《十萬個為什么》中以問答形式出現(xiàn)的知識條目類和由某一主題生發(fā)開去的科學(xué)小品外,他還寫過科學(xué)散文、科學(xué)隨筆、科學(xué)詩、科學(xué)相聲、科學(xué)家傳記和科幻電影分析等,努力將科學(xué)知識與多種文學(xué)體裁結(jié)合以尋找最佳的表達方式。作家偏離自己擅長的風(fēng)格,時常轉(zhuǎn)換體裁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冒險,因為這是一種“揚短避長”。但葉永烈的嘗試卻令人敬佩,他不怕失敗,只希望用更多的文學(xué)形式表達科學(xué)的內(nèi)容,豐富科普傳播的手段。他在科學(xué)相聲中反復(fù)思忖怎樣“寓科學(xué)于笑聲”,如何甩出科學(xué)“包袱”,從科學(xué)本身挖掘笑料;在科學(xué)寓言中探索怎樣避免不倫不類,不失去寓言的味道;在科學(xué)詩中專注科學(xué)內(nèi)容不影響詩的本質(zhì);在科學(xué)童話中從不偏離兒童視角,這些都體現(xiàn)了勇敢的創(chuàng)新精神。
葉永烈的科普作品注重“新”,提倡文章的時效性,提倡及時了解最新的科學(xué)發(fā)展與應(yīng)用,常對當(dāng)下的科技成果做出最快的反應(yīng)。他批評中學(xué)教科書中的內(nèi)容沒有及時更新,向?qū)W生灌輸著舊知識;批判有的作家信息滯后,“把早已實現(xiàn)的科學(xué)技術(shù)仍當(dāng)作科學(xué)幻想來寫”;提醒科普作家不能把老化的知識寫進科普文章,為此應(yīng)“消息靈通”,要 “懂得外文,能夠直接涉獵外文科學(xué)期刊”,這樣便省去了等待國內(nèi)翻譯的時間。
他閱讀科學(xué)雜志、收集科學(xué)資訊,將世界領(lǐng)先的種種新科學(xué)、新技術(shù)、新成就、新動態(tài)匯編收錄,如其1959年收錄的《科學(xué)珍聞三百條》,后來成為《小靈通漫游未來》的核心內(nèi)容。他建議科普作家應(yīng)隨時留意科技領(lǐng)域的更新,一些舊有數(shù)據(jù)如化學(xué)元素的相對原子質(zhì)量、長江黃河的長度、珠穆朗瑪峰 的高度等,都應(yīng)采用最新測量公布的數(shù)據(jù)。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幾年,中國還未擺脫其造成的傷痕,沉浸于控訴與批判的滾滾洪流時,葉永烈已寫到在模擬艙中體驗航天員的太空生活,開始了航天之夢;寫到紅外線的應(yīng)用:紅外照相機、紅外望遠鏡、紅外顯微鏡、紅外測溫儀;寫到換心術(shù)、換頭術(shù)、器官移植、人造器官、人機對弈等高科技領(lǐng)域。近40年后的今天,當(dāng)這些科技有的已廣泛運用于生產(chǎn)、生活或軍事等領(lǐng)域 時,我們才赫然發(fā)現(xiàn)作者對它的描述是多么超前。
(二)理與真
“理性”與“真實”是葉永烈科普作品 嚴格遵守的法則。其作品中的科學(xué)原理往往反復(fù)推敲,言說有據(jù)。不主觀、不虛妄、不夸大、不渲染,剔除時代因素影響,剔除個人好惡,按照事物本來的樣貌描寫,按照高度的理性精神分析是其科普作品的第二個特色。
他主張數(shù)據(jù)、引用一定要準確,從網(wǎng)絡(luò)上查閱下載的數(shù)字常常不準確,需要認真核實。謹慎、辨?zhèn)巍⑶笳妗⒗硇允强破談?chuàng)作的關(guān)鍵。普及已知的、正確的科技知識,即便要把正在探索、爭論的問題寫入科普作品,也應(yīng)如實說明各種不同的學(xué)術(shù)見解,去除自己的主觀傾向性,因為“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在《辨?zhèn)巍敺酪杂瀭饔灐分校~永烈批評英國嚴肅雜志《新科學(xué)家》在愚 人節(jié)拋出牛肉與西紅柿雜交的玩笑,批評望文生義誤傳很廣的“詹天佑鉤”,他認為去偽存真、有效辨別是科普創(chuàng)作必須遵守的,即使對名家的觀點也不應(yīng)過于迷信,而應(yīng)核實準確無誤后再加以引用。
為了弄清干擾素的奧秘,他特意去軍醫(yī)大學(xué)向教授請教;聽說某儀表廠試制成功 “電子鼻”,馬上去實地了解情況;某市辦起了“揚子鱷繁殖研究中心”,立即動身訪問;為了研究科學(xué)小品創(chuàng)作,查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許多報刊,復(fù)印了數(shù)百篇文章。1972年,葉永烈讀到《考古》雜志中考古學(xué)泰斗夏鼐的論文,認為“西晉無鋁”的理論依據(jù)不足,觀點不能成立,于是寫信質(zhì)疑, 1982年再次發(fā)表文章反駁,1983年第三次引用事實材料反駁,1993年第四次深入論爭,其間多次與夏鼐本人、雜志編輯部和其他相關(guān)者信件往來,并寫出了萬字以上的論文。從科學(xué)的角度予以辨析并和專家觀點對峙,這樣的理性求真態(tài)度令人折服,也使他的科普作品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觀不實,達到了對細節(jié)錙銖必較的境界。
他曾嚴厲批評收入中學(xué)語文教材的文章 《悲壯的兩小時》,指出這篇科普性文章犯了常識性錯誤,同時提供了權(quán)威資料進行佐證。他認為宇宙飛船返回大氣層花費兩小時落到地面不可能,兩小時內(nèi)與地面一直保持通話也不合常識,文章作者沒有經(jīng)過推敲便隨意編篡,有悖于科學(xué)精神,應(yīng)該立即從教材中 刪掉并告訴學(xué)生文章錯在哪里。有理有據(jù)的批駁引發(fā)了社會多層面的討論,使教材編選體制成為社會熱點。
(三)趣與深
“趣味”與“深入探索”是葉永烈科普創(chuàng)作的第三個特點。怎樣把僵硬的科學(xué)知識變成一篇篇妙趣橫生的文章,既不失科學(xué)之真,又要擺脫說教、羅列和枯燥之弊;怎樣不流于淺嘗輒止,而能由淺入深,把書寫對象放在顯微鏡下仔細打量,這些都是葉永烈科普作品關(guān)注的重點。
《漫話空間技術(shù)》一文中,葉永烈以李賀的《夢天》、蘇軾的《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起筆,點出古人遨游太空的夢想,接著從古代神話、敦煌壁畫等角度寫古人對遠離地球限制的向往,詩意十足,文學(xué)意味濃厚。然而,提倡趣味并不意味著浮光掠影、不求甚解。一篇好的科普作品,應(yīng)既能以趣味性吸引初級讀者,也能禁得起高級專業(yè)人士對其的打量與推敲。還以《漫話空間技 術(shù)》為例,文章在趣味性充分體現(xiàn)的同時,繼而轉(zhuǎn)入介紹人造地球衛(wèi)星發(fā)展史、用途分類、各種衛(wèi)星的獨特之處、航天員的太空生活、中國自己的空間實驗室等。有淺有深,有面向外行的淺表介紹,也有面向內(nèi)行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和專業(yè)分析。
關(guān)于趣味,他說“千萬不要以為科學(xué)總是嚴肅的”,“科普作家要善于把科學(xué)的趣味寫出來”,遇到讀者不熟悉的知識硬塊時,就要換一種思維方式和寫法,使之更加生動。即使是“死”數(shù)字也要寫活,將之形象化,否則會讓人感到枯燥。科普創(chuàng)作離不開科學(xué)原理、專用名詞、科學(xué)定律等,這些全都是一幅幅僵硬的面孔,不易理解、不易親近,需要通過有序、有趣的文字描述才能變得明白易懂又極具閱讀價值。為了提高這些科普讀物的趣味性,葉永烈努力擺脫“理科男”敘述的僵化單調(diào),更多關(guān)注科普知識的講述方式,與教科書式的宣講劃清界限。
他會在科學(xué)小品中穿插俗語、諺語、寓言、詩詞、故事、民間傳說、影視情節(jié)、生活現(xiàn)象、衣食住行常識等,使它們與生物遺傳、航天、天體物理、考古、計算機、海洋學(xué)、機器人等科學(xué)領(lǐng)域的知識交叉互滲,以達到文理結(jié)合、虛實結(jié)合、古今結(jié)合、中外結(jié)合,文氣縱橫捭闔,書寫汪洋恣肆,在同一主題下,通過多學(xué)科、多維度、多側(cè)面地打量,深挖細掘予以全方位詳盡解析,將無趣的科普知識巧妙地鑲嵌在輕盈華麗的絲綢之下,撫之如水,捻之如云。
無論博與新、理與真、趣與深,葉永烈的科普創(chuàng)作特色無不源于他對作品明確的價值取向定位。1982年2月,葉永烈在《科普作品的社會功能——“銀鏡”中之我見》中因自己的作品被讀者肯定并幫助了他們的生活而感到欣喜,意識到“科普作品應(yīng)面向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面向生活,使讀者長知識”。科普是要起作用的,這一點不同于散文的浪漫、小說的虛構(gòu)、詩歌的抒情,只有在生活中切實發(fā)揮作用,給予讀者實實在在的啟迪與幫助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因此,他會在意各種各樣的“生活中的科學(xué)”,寫日常用品、衣櫥、廚房、天氣、電影院,寫人們忽略的衣食住行中的科學(xué),帶有廣為播撒的普世性啟蒙色彩。他的科普作品為一代代青少年打開知識的大門,引領(lǐng)他們走入五彩繽紛的科學(xué)世界。擺脫無知、愚昧、庸常,走向智慧、澄明與思索。
除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他那顆誠摯而堅定的科普之心,那種對科普深入骨髓的熱愛。《十萬個為什么》以篇計費,但他的稿費卻比別的編者低了一半——他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嚴寒與緊張的政治氛圍中,他冒著危險躲在上海一間11平方米的破舊小屋里寫作——他忍受;下放到“五七干校”種水稻做植保員,3年中天天跟蟲子打交道他不以為苦,竟還苦中作 樂地寫下了科普作品《治蟲的故事》;寫作不能領(lǐng)到1分錢稿費只收到樣書亦“萬分高興”……這些在當(dāng)代人看來不可想象的事情,都折射出葉永烈感人至深的精神追求。
科幻創(chuàng)作
葉永烈的科幻小說數(shù)量較多,一些名篇如《小靈通漫游未來》《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愛之病》《暗斗》《腐蝕》等廣為流傳, 一版再版。除此之外,在同時代的科幻作家中,葉永烈是能被主流文學(xué)接納并予以肯定的極少數(shù)類型文學(xué)作家之一,首發(fā)于1981年 《人民文學(xué)》的《腐蝕》便證明了這一點。縱觀其數(shù)量龐大的科幻作品,大致可從主題、結(jié)構(gòu)、敘事等方面分析,揭示其別具一格的創(chuàng)作特色。
(一)“為現(xiàn)實”的主題
葉永烈科幻小說的主題相對集中而洗練,如同車輻集中于車轂,其小說無論篇幅的長短、人物形象的差異、敘述風(fēng)格的不同,都可涵蓋在同一個大主題之下,那就是——“為現(xiàn)實”。數(shù)量龐大的小說指向較為統(tǒng)一的主題,輻輳出明確的價值取向,這些主題體現(xiàn)了作家對科幻作品的終極定位,即科幻作品應(yīng)與現(xiàn)實相關(guān),每一個科幻創(chuàng)意都應(yīng)作用于生活并有益于生活。這一點上,其科幻作品與科普作品是殊途同歸的。
(二)“科”以致用
科學(xué)應(yīng)正向作用于生產(chǎn)、生活,而非阻遏、損害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這是葉永烈大量科幻小說中體現(xiàn)出的觀點。歌頌人類通過科技手段掌握世界和自然的能力,使自然具有更多人化特征,將人類從必然王國提升至自由王國。主人公始終在法律與道德允許的范疇內(nèi)合理運用科技,使其沿正確方向運行,發(fā)揮積極作用,只有對現(xiàn)實產(chǎn)生正向推動作用的發(fā)明和研究才值得肯定與推廣,它 們必須使人們的生活更美好、更方便、更快捷,這是葉永烈小說毫不含糊的前提設(shè)定。
在葉永烈的科幻作品中,幾乎很少見到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顧均正《北極底下》、威爾斯《莫洛博士島》、劉慈欣《魔鬼積木》等小說中的瘋狂科學(xué)家形象,他們利用高科技手段進行反人類行為,是地地道道的利己主義者甚至社會罪人。葉永烈小說中出現(xiàn)了許多在生活中能夠大大提高生產(chǎn)效率、提高生活水平的科幻創(chuàng)意。
例如在《鮮花獻給誰》中,作為醫(yī)生的“我”給馬師傅移接了手臂和腳,把他從殘疾人變成運動員;《“大馬”和“小馬虎”》中,楊大夫和同事從蠑螈和蜥蜴身上提取出“蠑蜥劑”,即再生刺激劑,給人注射后可以長出新的器官;《舊友重逢》中,老同學(xué)老余發(fā)明“X-3”藥水,用人工方法改變鮭魚洄游路線,游到人們指定的區(qū)域;《飛檐走壁的奧秘》中,爸爸仿照壁虎的腳做成“走壁鞋”“走壁手套”,供消防員救火及工廠、建筑工地使用;《傷疤的秘密》中從蜂蜜里提煉出鉭,將人的頭骨修補得天衣無縫;《奇妙的膠水》中藤壺分泌出的“膠水”可粘牢各種東西,甚至地板、鋼板;《奇怪的蜜蜂》中研究蜜蜂的語言,增加蜂蜜的產(chǎn)量;《“逃會教授”的秘密》中通過單性繁殖,培育出和陶惠教授一模一樣的人,代他出席各種會議,使其從“會海”中脫離出來,把精力用在科學(xué)研究上;《喜新厭舊》中抽屜式的建筑,可以隨時搬家,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科”以致用的集大成者是著名的《小靈通漫游未來》,小說中所有的新事物、新發(fā)明無不體現(xiàn)著科學(xué)對人類的有用、有益性,以人類的得失判斷科學(xué)的好壞成為作者毫不掩飾的評價標準。
(三)“科”以報國
愛國主義是葉永烈科幻作品的重要主題之一,忠于祖國與忠于科學(xué)像兩條并行不悖的繩索,深深嵌入各種長長短短的科幻敘事中。這是“科”以致用的合理延伸,是其在政治和民族意識上的體現(xiàn)。
葉永烈塑造的科學(xué)家形象往往較為一致,都有一身錚錚鐵骨,執(zhí)著于科學(xué)探索,滿懷一腔報國之志,希望將自己的科學(xué)研究獻給祖國,在個人與國家的利益沖突中,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實現(xiàn)其“科學(xué)愛國”“科學(xué)救國”的人生理想,雖死而未悔。《生死未卜》中的科學(xué)家施宏樂,《神秘衣》里客居熱帶島國的華僑楊林生,《弦外之音》中的歐陽予清等均是這一理念的體現(xiàn)者。
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的主題并非葉永烈獨有,而是中國科幻進入當(dāng)代后的一個集體選項,鄭文光1957年的《火星建設(shè)者》、童恩正1960年的《古峽迷霧》與1978年《珊瑚島上的死光》、王國忠1963年的《黑龍?zhí)柺й櫋返榷季o緊圍繞愛國主題進行架構(gòu),在和平時期對未來的科技戰(zhàn)爭做出預(yù)想,分析戰(zhàn)爭過程中可能受到的高科技攻擊,這些均反映出國家處于經(jīng)濟相對貧弱落后時期作家的憂患意識。走在時間前面,為國分憂,危機意識成為當(dāng)科幻小說家的共同取向。
跳出個人、集體、國家的范圍,在更為宏闊的背景下則是“科”以救世。科學(xué)應(yīng)對 整個世界產(chǎn)生積極意義,這體現(xiàn)了科學(xué)的大 愛。《演出沒有推遲》中,中國科研人員將 自己辛苦研制新疫苗的方法向全世界公布;《愛之病》中,中國毫無保留地向世界公布 “反滋一號”技術(shù)以共同面對全人類的敵人, 都顯示出科學(xué)的至善境界——拯救人類。
(四)結(jié)構(gòu)與敘事
在“為現(xiàn)實”的明確主題下,無論“科” 以致用、“科”以報國還是“科”以救世,作者對矛盾沖突的描寫常采用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模式。是非對立、善惡對立、真假對立、美丑對立、正邪對立、敵我對立、愛國與叛國的對立等,雙方態(tài)度鮮明、此消彼長,在你死我活的對峙中反復(fù)較量,最終正確戰(zhàn)勝錯誤、善戰(zhàn)勝惡、美戰(zhàn)勝丑、正戰(zhàn)勝邪、我戰(zhàn)勝敵、愛國戰(zhàn)勝叛國,缺點得以改正,陰謀得以粉碎,科學(xué)成果得以載譽回國。“為現(xiàn)實”的主題下,矛盾的設(shè)置及最終化解都不復(fù)雜,雖然也注重懸念的先聲奪人、情節(jié)的起伏跌宕和明線暗線的彼此交叉等,但圓滿成功的結(jié)局卻無一例外。
《腐蝕》便是典型的“是非對立”二元模式。獻身科學(xué)的李麗、杜微、方爽與功利主義的王璁的對立,無論是腐蝕菌的科幻創(chuàng)意還是對科研工作者不同個性的描述均屬上乘,但人物性格的一百八十度轉(zhuǎn)變卻顯得過于簡單,人性的復(fù)雜并未得以彰顯。自私自利的王璁進入沙漠實驗室后,目睹了方爽的遺書和尸體,馬上受到精神感召,一下子從利己主義的懸崖上勒馬而回,自動留在沙漠獻身科學(xué)研究以洗滌自己的靈魂。這種頓悟式的轉(zhuǎn)變過于突然,缺乏必要的合理性及性格邏輯性,反而不如王璁之前的自私寫得精彩。
然而在眾多單一結(jié)構(gòu)和傳統(tǒng)敘事手法外,有些篇目的結(jié)構(gòu)與敘事卻達到了令人驚嘆的超前地步,似無人駕駛汽車出現(xiàn)在一片原始馬車之中,跨越“傷痕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改革文學(xué)”“尋根文學(xué)”等這些中國相繼出現(xiàn)的文學(xué)思潮,提前數(shù)年與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先鋒文學(xué)相銜接。令人遺憾的是,目前為止任何文學(xué)批評包括科幻批評都未注意到這一點,不得不說,當(dāng)前中國的科幻批評與主流文學(xué)批評相比滯后了很多。這一點概源于進入當(dāng)代后科幻批評的方向所致,它們更多聚焦于科幻創(chuàng)意或小說的科普功能,極少引入純文學(xué)的評判體 系,科幻批評與主流文學(xué)批評始終保持著橋歸橋、路歸路互不交叉的態(tài)勢。事實上,葉永烈早年創(chuàng)作的科幻小說中便已開始敘事的創(chuàng)新,不僅重視“寫什么”,而且非常在乎 “怎么寫”,對形式的關(guān)注并不亞于對內(nèi)容的關(guān)注。
寫于1978年的《飛向冥王星的人》較早運用了“多視角敘述”與“多時空并置” 的手法。這種敘事手法在當(dāng)時極為罕見,因為過于超前并未引起評論界足夠的關(guān)注,而讀者感興趣的是吉布雪藏之后奇跡般的復(fù)活,29歲的他與85歲的妻子相見時的違和感。小說共分為5節(jié),每節(jié)都采用不同的敘述視角。第一節(jié)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交代飛向冥王星的載人宇宙飛船實況轉(zhuǎn)播;第二節(jié)以珠瑪?shù)目谖堑谝蝗朔Q視角向觀眾講述她和吉布的愛情與遭遇;第三節(jié)楊大夫向觀眾講述吉布是如何被發(fā)現(xiàn)的;第四節(jié)趙院長講述吉布的人工復(fù)活過程;第五節(jié)盛所長講述吉布復(fù)活后的情況與自愿申請飛向冥王星。五個敘述視角你我相連,互相補足,彼此說明,前后相繼,共同勾勒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閱讀時會被不同的敘述者帶入到不同的情境中,領(lǐng)略那些特別的場面和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21世紀的今天,當(dāng)主流文學(xué)批評操縱著“多視角敘述”“敘事藝術(shù)”“敘事時間” 這些時髦的理論術(shù)語,熱烈探討著福克納的 《喧嘩與騷動》等作品時,我想他們或許并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不久后葉永烈早已開始嘗試,只因作品被歸為科幻類型而未引起主流文學(xué)的足夠重視,不得不說是批評界的遺憾。
另一篇《剪刀加糨糊》在其眾多的科幻小說中并不起眼,但其敘事策略卻頗具匠心,成為科幻小說問鼎先鋒敘事技巧的先行者。
小說篇幅不長,由作者說明、5張剪報、后記及編者注組成。作者說明中作家以真正的身份出現(xiàn),無論姓名、職業(yè)、生活習(xí)慣及與編輯的交往都真實無誤,這些可以通過作家的創(chuàng)作談得以證實,對構(gòu)思過程、寫作過程的暴露也坦率真誠。中間插入了4位作者的5張剪報,以純客觀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剪報內(nèi)容有的毫無關(guān)聯(lián),有的則互相抵牾、彼此駁斥,其中不僅有作者的署名,甚至還細心地寫出了刊物名稱和發(fā)表時間,看起來真實可靠。內(nèi)容分別為小兒麻痹癥患者言之鑿鑿地稱自己爬上了自由女神像的22層;別人的質(zhì)疑;年輕的歷史專業(yè)研究生到元朝體驗生活等。而在小說結(jié)尾,卻并未給出這些事件孰真孰假,有何關(guān)聯(lián),只在剪報五中介紹了“三如電影”,至于“三如電影”與前面幾篇剪報的關(guān)系,讀者必須自己思考才能最終領(lǐng)悟,富有開創(chuàng)性的將“可讀的文本”變?yōu)椤翱蓪懙奈谋尽保粲踝x者的參與意識。
在這個不長的文本中,綜合了“拼貼結(jié)構(gòu)”“元敘事”“開放式結(jié)尾”等前衛(wèi)敘事 技巧,這在1980年前后尚不多見。其對敘事策略的關(guān)注已遙遙領(lǐng)先于當(dāng)時的文壇,顛覆了科幻小說的簡單模式,成為獨樹一幟的存在。當(dāng)然,這種創(chuàng)新對當(dāng)時的讀者而言尚屬新鮮事物,讀來頗為懵懂。以至于作者在小說尾部加上了后記,用編者注的形式表明 “這是作者行文的一種方法,那些‘摘文’ 并非真是他人之作”。敘事的真真假假、虛實難辨、迷離惝恍在當(dāng)時甚是少見,直到后 來先鋒文學(xué)的各種敘事技巧亂花迷眼時,馬原、余華、蘇童等人的作品中才將這些技巧作為常用的敘事手段,不再刻意加以注釋。
10年后,先鋒小說已成氣候,批評家與讀者都驚異于馬原、余華作品中各種各樣的“拼貼”和“敘事圈套”,并不知道這些技巧10年前在科幻作家葉永烈手中早已運用純熟。如果不是1983年冬他因長篇科幻小說《黑影》遭到不公正批判,痛下決心遠離科普科幻,轉(zhuǎn)型至純文學(xué)領(lǐng)域,我們對葉永烈的敘事創(chuàng)新還可滿懷期待,然而時間無法倒流,這種遺憾也只有深深埋在心里了。
除了以上的創(chuàng)新,葉永烈讀了美國科幻小說《酷肖其人——一個無性生殖的人》 后,沿用原故事及人物寫出了續(xù)篇《自食其果》,之后有人為《自食其果》寫了續(xù)篇 《適得其反》,再之后又有人向下續(xù)寫了《勝似其人》。4篇共同構(gòu)成一部接龍式科幻小說,如海浪般各有峰谷卻又能連成一片,這在國內(nèi)科幻界尚無先例。
科普科幻研究
許多年來,無論讀者還是研究者,幾乎都毫無爭議地把葉永烈定位為科普作家、科幻作家,很少有人稱之為學(xué)者,對其在科普科幻領(lǐng)域的研究工作視而不見,主觀忽略。這多半是因為其科普科幻作品數(shù)量龐大之故,如同達·芬奇在眾多的身份中,往往以畫家身份傳世,其他領(lǐng)域的貢獻并不為公眾所熟知。然而毫不夸張地說,葉永烈在科普科幻領(lǐng)域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在理論研究、史學(xué)梳理、往事鉤沉、術(shù)語定義、文獻發(fā)掘及中外科幻文學(xué)對比方面,均有獨到之處。
他重視且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和尋找答案,極有耐心地埋頭于舊資料中尋找證據(jù)、追本溯源,一些發(fā)現(xiàn)已成為科普科幻領(lǐng)域的首創(chuàng)或奠基性觀點。為了考證中國科幻小說的起點,他埋頭在上海圖書館里反復(fù)查閱古籍,最終在1904年的《繡像小說》雜志上,發(fā)現(xiàn)了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這是比《新法螺先生譚》(1905年出版)更早的科幻小說。接著,葉永烈又向上海的“掌故大王”鄭逸梅求證荒江釣叟究竟是誰,由于鄭逸梅也說不清楚才只得作罷。從1981年12月21日這一發(fā)現(xiàn)在《文匯報》上第一次披露,至今已過去30多年,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無數(shù)次在各種中國科幻經(jīng)典賞析中作為第一篇目出現(xiàn),被科幻界公認為是中國第一篇科幻小說,1904年則是中國科幻小說的誕生元年。
只要與科普、科幻相關(guān),便能激發(fā)起葉永烈的研究興趣。他考證出顧均正發(fā)表于1940年的《和平的夢》是國內(nèi)第一篇驚險科幻小說,鉤沉出1920年陳衡哲(莎菲女士)的科學(xué)童話《小雨點》是中國最早的科學(xué)童話。他探求“科學(xué)小品”一詞何時在中國誕生,出自誰人之口,科學(xué)相聲的出現(xiàn)緣由。為了考查“科學(xué)小品”的來歷,他請教陳望道、高士其,查閱舊期刊,寫下了《科學(xué)小品探源》《讀“科學(xué)小品”源流再探》等考證文章,最終將中國“科學(xué)小品”的發(fā)軔定 位于1934年上海創(chuàng)刊的《太白》雜志,認為科學(xué)小品“是時代的產(chǎn)物,是集體的創(chuàng)造”,而非出自某一作家或編輯,目前這一觀點廣泛被業(yè)內(nèi)學(xué)者接受。
他深入研究中國科幻文壇,從古代至近代、現(xiàn)代、當(dāng)代,分析每個時代科幻作家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還進一步探討這些作家間的異同。例如,對《太白》作家群的分析便切中肯綮,認為“顧均正科學(xué)小品的特點是內(nèi)容新,常常把當(dāng)時科學(xué)的最新成就告訴讀者,而高士其、周建人、董純才、賈祖璋則偏重于基礎(chǔ)知識,尤偏重于生物基礎(chǔ)”。他分析賈祖璋的《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從立意、科學(xué)原理、結(jié)構(gòu)、創(chuàng)作特色等層次多方面予以打量,引導(dǎo)讀者更加深入地理解科普文章。選取諸如老舍、童恩正、肖建亨、劉興詩、宋宜昌、魏雅華、金濤等知名科幻作家的經(jīng)典篇目逐篇解讀,對一些同時代的科普科幻作家進行創(chuàng)作訪談,為他們寫傳記,就某個科普科幻問題聽取他們的觀點,并對中國科幻現(xiàn)狀和科幻批評提出建設(shè)性意見,這些都奠定了中國科普科幻研究史的基礎(chǔ),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他關(guān)注國外科幻創(chuàng)作與研究,分析凡爾納、威爾斯、法布爾、伊林、海因萊因各自的特色,分析國外經(jīng)典科幻作品和電影;與國外科幻文壇保持密切聯(lián)系,將中國科幻引出去,國外科幻引進來;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種研究與科普科幻社會活動中,不遺余力地推廣傳播著科學(xué)思維,無數(shù)次面向社會各階層進行科普科幻的培訓(xùn)與演講。
葉永烈的創(chuàng)作始于科普科幻但并未受其局囿,以文學(xué)的視角看科學(xué),以科學(xué)的視角看文學(xué),將二者融會貫通,取長補短,使科普科幻創(chuàng)作更為豐滿而又不喪失自身的特色。我想,中國科普科幻創(chuàng)作及研究領(lǐng)域會記住葉永烈這個名字,因為他是無可替代的,無論是現(xiàn)在還是將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