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通論》:阿瓜盧薩的虛構(gòu)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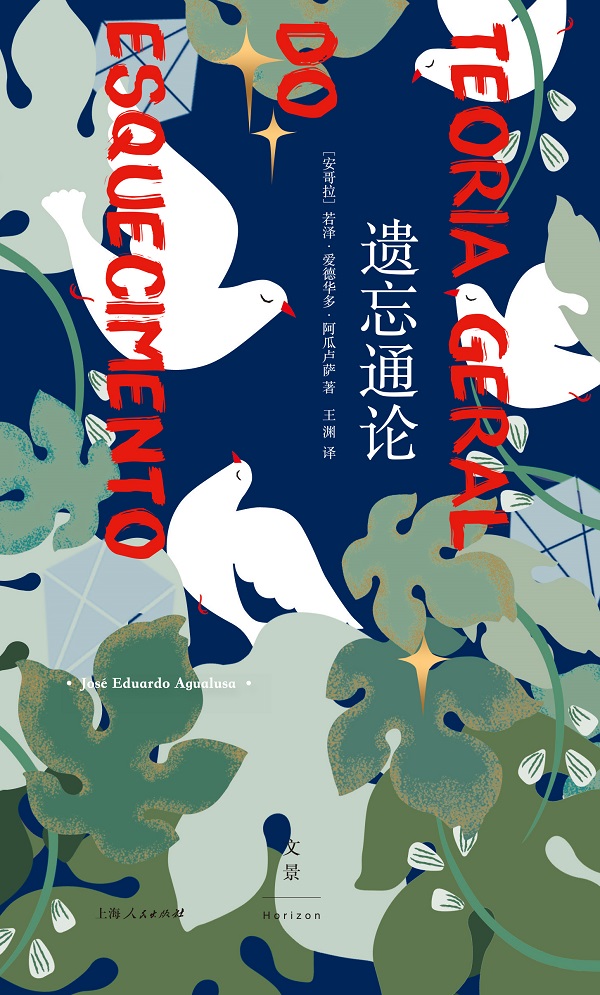
一般來說,以“通論”“總論”“概論”為名的書籍應(yīng)該闡釋某個(gè)主題的原理和價(jià)值。但在這本關(guān)于遺忘的通論里,作者卻否認(rèn)了遺忘的可行性,反過來強(qiáng)調(diào)記憶的重要性。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書中的人物參與了個(gè)人或集體的遺忘,但作者的觀點(diǎn)卻是人需要記憶來實(shí)現(xiàn)理解,進(jìn)而原諒,最終達(dá)到自我救贖。盧多需要薩巴魯喚醒她壓抑多年的情感,喚起她塵封已久的記憶,從而打破讓她動(dòng)彈不得的遺忘之網(wǎng)。而對(duì)本書作者阿瓜盧薩來說,文學(xué)事業(yè)就是他的薩巴魯,他選擇了將自己的身份與寫作這一行為交纏,便是為了對(duì)抗遺忘,實(shí)現(xiàn)他個(gè)人和社會(huì)的救贖。
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1960年出生在西非國家安哥拉,父母分別是來自巴西與葡萄牙的移民。他的母親在萬博市的國立中學(xué)教授文學(xué)和法語,而身為公務(wù)員的父親則為鐵路上的工人們擔(dān)任短期教師。年少時(shí),阿瓜盧薩常常會(huì)隨父親沿著鐵路旅行,一去就是兩三個(gè)月。多元的家庭背景,加上與各個(gè)地區(qū)人民的親身接觸,讓阿瓜盧薩體會(huì)到身份的流動(dòng)性和認(rèn)同的復(fù)雜性。因此,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對(duì)身份的探究是最為核心的問題。各式各樣的群體概念界限模糊又交叉重疊,為了找準(zhǔn)自己的位置,他沒有選擇像文中的盧多一樣封閉自己,而是盡其所能,親身以腳步丈量葡萄牙語世界的遼闊,再用紙筆揣摩全球文學(xué)傳統(tǒng)的廣博。他的足跡遍布葡語世界的各個(gè)角落,而他的創(chuàng)作也并不局限一地,而是包含東帝汶、印度果阿等極少出現(xiàn)在文學(xué)地圖上的地點(diǎn)。作為一名多產(chǎn)作家,其寫作范圍涵蓋報(bào)紙專欄、書評(píng)、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戲劇和兒童文學(xué)。與此同時(shí),他還積極參與社會(huì)議題,對(duì)政治腐敗、種族歧視、拼寫規(guī)則等問題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近年來,有多位葡語作家的文字得到引進(jìn),從而與中國讀者見面。他們風(fēng)格各異,如薩拉馬戈和安圖內(nèi)斯善用長句搭建框架,米亞·科托通過重構(gòu)語詞推陳出新,克拉麗絲則借助女性哲思發(fā)人深省。相比之下,阿瓜盧薩的作品行文平實(shí),主旨鮮明,故事性強(qiáng),閱讀難度并不高。但是,如果僅僅讀過阿瓜盧薩的單部作品,就容易忽略這位安哥拉作家的一大特質(zhì),那就是其創(chuàng)作宇宙中的互文性。在旅行小說《果阿陌客》(Um estranho em Goa)當(dāng)中,面對(duì)記者“為何寫作”的提問,敘述者回答說是因?yàn)樗胫澜Y(jié)局。對(duì)于好奇心旺盛的阿瓜盧薩來說,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小說結(jié)尾并不代表人物和故事真正的結(jié)局,發(fā)生在“全書完”之后的精彩需要借助其他文本進(jìn)行補(bǔ)完。在1997年的小說《克里奧爾國度》(Na??o Crioula)當(dāng)中,作家就續(xù)寫了弗拉迪克· 門德斯的故事。弗拉迪克是個(gè)花花公子旅行者的形象,最初由葡萄牙現(xiàn)實(shí)主義大師埃薩· 德· 奎羅斯創(chuàng)造。在自己的小說中,阿瓜盧薩填補(bǔ)了原著一筆帶過的情節(jié),詳細(xì)描述了他在安哥拉和巴西之間尋找真愛和心安之處的旅程。在此之后,隨著阿瓜盧薩本人作品不斷增多,其內(nèi)部的互文愈發(fā)明顯,用葡萄牙著名書評(píng)人托爾卡托· 塞普爾維達(dá)的話說,阿瓜盧薩“正在創(chuàng)造一個(gè)獨(dú)立的虛構(gòu)世界”。不同作品之間共享的宇宙,就此成為這位多產(chǎn)的旅人在遺忘幽谷里孜孜以求的一點(diǎn)微光。
因此,這篇文章希望能帶來更新鮮的信息,通過介紹《遺忘通論》與作家其他作品的內(nèi)在對(duì)話,期待向中文讀者勾勒出一個(gè)更為立體的阿瓜盧薩。
1、作為上帝的壁虎
“‘我死了,’熱雷米亞斯想著,‘我死了,那只壁虎是上帝。’”(《遺忘通論》,第59 頁)
在阿瓜盧薩的名作《販賣過去的人》(O vendedor de passados)當(dāng)中,主要敘述者就是一只小壁虎:“我什么都能看見。在這家里我就是黑夜的小上帝。白天,我睡覺。”動(dòng)物敘述者一般用來展現(xiàn)畸形社會(huì)中人的異化,尤其是由人變成的動(dòng)物,卡夫卡《變形記》中變成甲蟲的格里高爾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在《販賣過去的人》中,比壁虎更具“變色龍”性質(zhì)的其實(shí)是形形色色的新貴階層。在社會(huì)動(dòng)蕩、記憶斷裂的背景下,這些人找與壁虎同居一室的文圖拉偽造身份,從而在社會(huì)地位和財(cái)富的再分配中提升自身的話語權(quán)。而在《遺忘通論》中,傭兵熱雷米亞斯誤將壁虎當(dāng)成上帝,則發(fā)生在他重獲新生之時(shí)。由于瑪達(dá)萊娜的搭救,大難不死的傭兵雖然失去了言語能力,卻在土著居民身邊找到了存在的意義,成為部落和牛群的保護(hù)者。同樣是改頭換面斷尾求生,兩書人物的區(qū)別主要體現(xiàn)在他們對(duì)待記憶的態(tài)度,因?yàn)闊崂酌讈喫箾]有擁抱遺忘,而是在最后向盧多坦承自己殺死了她的姐姐和姐夫,從而獲得了對(duì)方的原諒,也由此與記憶達(dá)成和解。
2、監(jiān)獄里的女詩人
“在庭院里,他發(fā)現(xiàn)一位備受尊敬的女詩人坐在緬梔樹蔭里,她的名字在歷史上和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聯(lián)系在一起。和他一樣,詩人也是在獨(dú)立后不久被捕,被控支持一股知識(shí)分子批評(píng)政黨前進(jìn)方向的潮流。小酋長詢問瑪達(dá)萊娜的下落。她幾個(gè)星期前被釋放了。警察沒能證明她和任何指控有關(guān)。‘真是不一般的女人!’女詩人補(bǔ)充道。她建議小酋長不要離開監(jiān)獄。在她看來,這次暴動(dòng)會(huì)很快被鎮(zhèn)壓,逃犯被抓后會(huì)被酷刑折磨然后槍決,‘會(huì)有一場血洗。’”(《遺忘通論》,第76 頁)
這位女詩人指的是《雨季》(Esta??o das chuvas)一書的主人公莉迪亞· 杜· 卡莫· 費(fèi)雷拉,一位阿瓜盧薩虛構(gòu)出來的女詩人及歷史學(xué)家。與《遺忘通論》聲稱以真實(shí)人物日記為底本類似,《雨季》也模糊了現(xiàn)實(shí)與虛構(gòu)的界限。盡管事實(shí)上莉迪亞并不存在,而是許多現(xiàn)實(shí)人物的結(jié)合,但阿瓜盧薩塑造的這個(gè)形象太深入人心,以至于甚至有人對(duì)作家表示,自己曾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見過莉迪亞。在接受《巴黎評(píng)論》采訪時(shí),唯一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葡語作家薩拉馬戈曾經(jīng)表示,我們會(huì)把原本只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經(jīng)典形象當(dāng)成真人,就好像世界的總?cè)丝谠黾恿艘粯印_@樣的人物不單是對(duì)他們創(chuàng)作者的最高褒獎(jiǎng),同時(shí)也承載了與其他作品的互文可能。在《遺忘通論》中,這一經(jīng)典人物已經(jīng)不再需要莉迪亞這個(gè)名字,“小酋長”離開前與她長久擁抱,則讓人感受到跨越文本界限的溫情。而盡管《遺忘通論》并非如敘述者所宣稱的那樣根據(jù)真實(shí)事件改編,但在此書出版之后,莫桑比克有一對(duì)同樣與世隔絕數(shù)十年的夫婦被人發(fā)現(xiàn),從而再次證明阿瓜盧薩把握政治時(shí)局與人性選擇的能力。這位文字的魔法師似乎擁有非凡的能力,能夠讓人物在虛構(gòu)與真實(shí)的網(wǎng)絡(luò)中任性穿插。
3、秘密警察蒙特
“蒙特不喜歡審訊。就在今天他還回避了這個(gè)話題。他避開的內(nèi)容包括回憶七十年代,那時(shí)候?yàn)榱吮Pl(wèi)社會(huì)主義革命,他們被允許—用政治警察喜歡使用的委婉說法—稍微過點(diǎn)火。他對(duì)朋友們坦承,在獨(dú)立之后恐怖的數(shù)年里,在審訊派系分子、和極左有關(guān)聯(lián)的青年過程中,他對(duì)人性有了足夠的了解。他表示,童年幸福的人心理防線更難被打破。”( 《遺忘通論》,第71 頁)
對(duì)熟悉阿瓜盧薩的讀者來說,殘暴的秘密警察蒙特是個(gè)老熟人了。同樣是在《雨季》中,莉迪亞入獄時(shí)就曾遭到蒙特“稍微過點(diǎn)火”的審訊。他一直在說自己不喜歡暴力審訊,但“總有人要做這事兒”。在2007年的小說《我父親的妻子們》(As mulheres do meupai)中,蒙特也以類似的形象出現(xiàn)。除了擔(dān)任特務(wù)和私人偵探作為主業(yè),他還是詩人和企業(yè)家,業(yè)余時(shí)間喜歡收集蝴蝶和甲蟲。就像《辛德勒名單》中彈鋼琴的納粹軍官一樣,這些暴力機(jī)器的個(gè)人藝術(shù)造詣?dòng)撸荏w現(xiàn)人性的割裂。蒙特在葡萄牙語中意為“大量,大堆”,暗指在因內(nèi)部斗爭而異化的社會(huì)中,如蒙特與納粹軍官般割裂的人物絕非個(gè)例。唯一能讓讀者在共情之余聊以慰藉的是,蒙特和他現(xiàn)實(shí)中的原型一樣,都擁有一個(gè)戲劇般的結(jié)局:被電視天線砸死。
4、記者丹尼爾· 本希莫爾
“丹尼爾· 本希莫爾收集安哥拉的失蹤故事。任何種類的失蹤都行,盡管他更偏愛飛行器的失蹤。比起被大地吞噬,永遠(yuǎn)是被天空拖走更有意思,就像基督耶穌和他母親一樣。”( 《遺忘通論》,第115 頁)
在2017年的新作《不情愿的做夢(mèng)者團(tuán)體》(A sociedade dos sonhadores involuntários)當(dāng)中,阿瓜盧薩將《遺忘通論》中的次要人物丹尼爾· 本希莫爾提升到主角的位置,并對(duì)他的背景故事展開細(xì)化。丹尼爾年輕時(shí)因?yàn)榘l(fā)表批評(píng)祖國的文章丟掉工作,其后逐漸脫離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變成腐敗政權(quán)的沉默幫兇。但在女兒入獄后,丹尼爾又經(jīng)歷了從妥協(xié)到抗?fàn)幍男乱惠嗈D(zhuǎn)變。雖然這本小說因政治議題壓倒文學(xué)性而頗受非難,但作者選擇原有人物進(jìn)行擴(kuò)充的手法值得一提。阿瓜盧薩想要表達(dá)的并不是對(duì)非凡英雄的贊頌,而是普通人團(tuán)結(jié)起來就能帶來變革。從舊時(shí)代故事的收集者到新時(shí)代故事的參與者,丹尼爾的轉(zhuǎn)變也許正是阿瓜盧薩對(duì)安哥拉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期許。
5、消失的“新希望”
“編輯部沒有人對(duì)新希望消失的消息感到不安。主任馬塞利諾· 阿松桑· 達(dá)· 博阿· 莫特發(fā)出一陣大笑:
‘那部落不見了?在這個(gè)國家什么都會(huì)消失。也許整個(gè)國家正在慢慢消失,這里一個(gè)村莊,那里一個(gè)小鎮(zhèn),等到我們留意時(shí)就什么都不剩了。’”( 《遺忘通論》,第120—121 頁)
在阿瓜盧薩出生后,他的祖國安哥拉先是經(jīng)歷了1961年至1974年反抗葡萄牙殖民統(tǒng)治的戰(zhàn)爭,獨(dú)立后又旋即陷入長期內(nèi)戰(zhàn)與動(dòng)亂之中。革命與政權(quán)交替帶來的希望之光愈來愈昏暗,很多人不再相信祖國有走上正軌的可能。在地圖上消失的小部落“新希望”正是這個(gè)動(dòng)蕩社會(huì)的縮影。
在完成《遺忘通論》的次年,阿瓜盧薩發(fā)表了反烏托邦小說《天上的生活》(A vida no céu),對(duì)“消失”這一概念展開進(jìn)一步的探索。在這部作品中,遭遇空前災(zāi)難的地球只剩下數(shù)百萬人,幸存者生活在少數(shù)幾個(gè)浮空城和氣球組成的村莊當(dāng)中,穩(wěn)定的大地僅僅存在于老年人的記憶之中。人們通常向往天空而鄙夷塵世凡間,而《天上的生活》顛倒了這一關(guān)系,隱喻著非洲人不應(yīng)只艷羨其他大洲的富足,而應(yīng)腳踏實(shí)地耕耘自己的祖國,這才是非洲發(fā)展的新希望。
我國的文學(xué)傳統(tǒng)自成一體,視野大多內(nèi)向而非放諸域外。被時(shí)代的大潮驚醒之后,在從救亡圖存走向民族復(fù)興的歷程中,我們依舊吝嗇于關(guān)注長期貧窮落后的非洲大地,似乎只有光鮮亮麗的歐美與東洋才是唯一值得重視的文化產(chǎn)出者。然而,在我自己的閱讀體驗(yàn)中,反倒在非洲葡語文學(xué)身上體會(huì)到最意外的親切感。無論是政治道路上的曲折反復(fù),還是在文化問題上的交鋒爭鳴,萬里之外非洲人民的所思所想似乎都能在我國的歷史進(jìn)程里找到對(duì)應(yīng)。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讀者與學(xué)者也應(yīng)當(dāng)參與到阿瓜盧薩等非洲作家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xué)宇宙中。無論是要海納百川,還是要推動(dòng)自己的文化走出國門,都無需只盯著高高在上的西方國家。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用技術(shù)將我們連接在一起,但想要達(dá)到更高層次的理解乃至大同,還需要將我們各自書寫的篇章相互勾連,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希望中國讀者與《遺忘通論》的邂逅,能夠像盧多與薩巴魯?shù)南嘤鲆话惚舜顺删汀?/p>
(本文為《遺忘通論》后記,小說中文版日前由世紀(jì)文景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