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時(shí)代的年輕作家 如何給未來留下有共識(shí)的經(jīng)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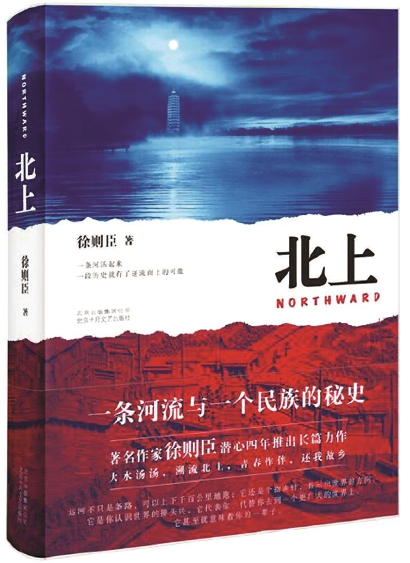
《北上》 徐則臣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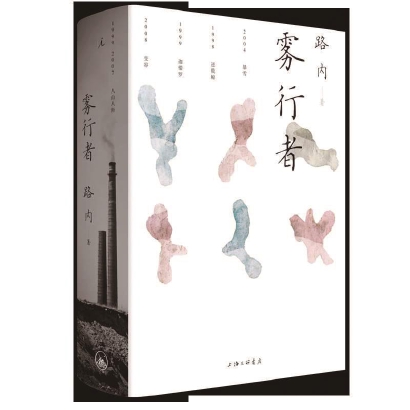
《霧行者》 路內(nèi)著 上海三聯(lián)書店

《譬若檐滴》 朱婧著 譯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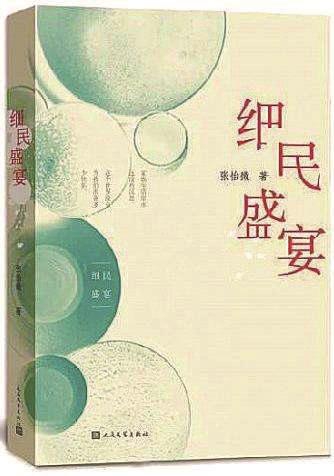
《細(xì)民盛宴》 張怡微著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歷史感、現(xiàn)實(shí)感的匱乏和經(jīng)驗(yàn)的同質(zhì)化,成為新一代作家面臨的普遍質(zhì)疑
不拘泥于“十”或者“五”年劃分出一個(gè)代際,我更愿意把改革開放前后出生和成長的數(shù)代人稱為改革開放時(shí)代的兒女們。如果考慮到學(xué)校教育對一個(gè)人精神上成人的意義,我們可以把生于1970年以后的都放在這個(gè)群體里看,因?yàn)椴畈欢嗍菑母母镩_放元年,1970年出生的孩子開始進(jìn)入學(xué)校念小學(xué)。
從1920年代出生的汪曾祺、林斤瀾、高曉聲、陸文夫等到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格非、遲子建、畢飛宇、麥家、東西、艾偉等,即便不溢出他們的生理年齡,他們書寫改革開放時(shí)代都有“改革開放之前”被帶入進(jìn)來,無論是《李順大造屋》《美食家》,還是《生死疲勞》《秦腔》《空山》《繁花》《活著》《兄弟》《平原》《春盡江南》《越野賽跑》等等,莫不如此。對他們而言,“改革開放之前”和改革開放時(shí)代同在一個(gè)綿延的歷史邏輯之上。而之后的一代年輕作家則不同,如果也要像前輩們建立過去和現(xiàn)在的歷史邏輯,則是回溯式的,弋舟的《隨園》、徐則臣的《北上》、葛亮的《朱雀》《北鳶》、笛安的“龍城三部曲”、孫頻的《松林夜宴圖》、張悅?cè)坏摹独O》、默音的《甲馬》……這些小說都涉及到在家族世系或者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史之上識(shí)別“我是誰?”
2019年,《中華文學(xué)選刊》向活躍于文學(xué)期刊、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及類型文學(xué)領(lǐng)域的117位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青年作家發(fā)去調(diào)查問卷,提出了10組問題。其中問題八:“是否認(rèn)同歷史感、現(xiàn)實(shí)感的匱乏與經(jīng)驗(yàn)的同質(zhì)化是當(dāng)代青年作家普遍面臨的問題?你認(rèn)為自己擁有獨(dú)特的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嗎?”1985年和1970年,中間隔了15年。提問者和回答者想象的“歷史感”似乎都理所當(dāng)然的是“卻顧所來徑”,即年輕作家能不能寫超出他們生命長度和經(jīng)驗(yàn)的“過去”。而且,按照我的揣測,問題的設(shè)計(jì)者可能還預(yù)設(shè)了對年輕作家不寫“過去”的質(zhì)疑和詰問。
但需要辨析的是,所謂的“歷史”既可能是“過去”,也有可能是同時(shí)代的歷史邏輯和肌理。因此,寫當(dāng)代也有可能就是寫歷史。
至于現(xiàn)實(shí)感的匱乏,則可能涉及我們?nèi)绾慰创F(xiàn)實(shí)?如何計(jì)量輕與重?單單說年輕作家不寫“現(xiàn)實(shí)”顯然不符合“現(xiàn)實(shí)”。“匱乏”一定意義是參考了文學(xué)史和審美慣例,我注意到批評(píng)家經(jīng)常會(huì)指責(zé)越是年輕的作家們越沉溺于小確幸、小憂傷。我們的文學(xué)傳統(tǒng),計(jì)量一個(gè)作家書寫現(xiàn)實(shí)的重量所取的單位可能是各種所謂的“大”,而且在過去和現(xiàn)在對比上,也習(xí)慣強(qiáng)調(diào)現(xiàn)在和民族記憶等量之“重”。一旦年輕作家的“現(xiàn)實(shí)感”不能在這兩個(gè)重量級(jí)上滿足想象,可能就會(huì)被詬病為“匱乏”和“同質(zhì)化”。
和前輩作家們將當(dāng)代作為過去迤邐而來的當(dāng)代不同,年輕作家在當(dāng)代寫當(dāng)代
和前輩們相比,什么是年輕作家理解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班宇認(rèn)為:“一個(gè)人的變革可以由外部催生出來,那些荒誕的景觀、動(dòng)蕩的時(shí)代,確實(shí)值得書寫,但也可以完全是個(gè)體精神上的,這種也很劇烈。卡佛、耶茨、厄普代克所身處的那個(gè)時(shí)代,看起來也沒什么大的波動(dòng),但他們對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做了深入挖掘。”這種個(gè)人化、內(nèi)傾化和精神性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孫頻定義為“共同的隱秘的傷痛感”。可以簡單地對照下,班宇、孫頻等最近小說中的“下崗”,和1990年代后期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沖擊波”的“大廠小說”,或許就能理解年輕一代的文學(xué)觀。
從審美革新的角度,予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個(gè)人化、內(nèi)傾化和精神性,可以有效節(jié)制“時(shí)代”成為標(biāo)簽。標(biāo)簽化進(jìn)入到文本的“時(shí)代”可以舉郭敬明的《小時(shí)代》做例子。或者說,郭敬明只是某個(gè)時(shí)段的文學(xué)癥候。大都市的“時(shí)代”被標(biāo)簽化,在郭敬明之前的衛(wèi)慧、棉棉和安妮寶貝都曾經(jīng)這樣去做,只是郭敬明更赤裸裸更無所不用其極而已。《小時(shí)代》把有可能的新興城市的洞見換成利益的精明,棱角粗糲的“時(shí)代”也被精心地打磨成“時(shí)代的貼片”。
并不都是《小時(shí)代》這樣的“時(shí)代的貼片”,近幾年青年作家的小說有一些把時(shí)間標(biāo)志得特別清楚,而且有的時(shí)間跟時(shí)代都對應(yīng)得特別緊,比如路內(nèi)的《霧行者》、周嘉寧的《基本美》、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逍遙游》、七堇年的《平生歡》、孫頻的《我看過草葉葳蕤》《鮫在水中央》、張玲玲的《嫉妒》,等等,這可能是一個(gè)值得關(guān)注的現(xiàn)象。為什么他們普遍地不去曖昧?xí)r間?一批小說都有了類似的東西不是很偶然的現(xiàn)象,我們需要思考每一個(gè)具體的時(shí)間對作家的文本究竟意味著什么?這里面有些可能是小說技術(shù)層面的,涉及年輕一代作家對大時(shí)代大歷史之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史、命運(yùn)史和精神史的處理,這可以說是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1980年以來“新歷史”“新寫實(shí)”等文學(xué)遺產(chǎn)的回響。但也許更重要的是,不只是這些時(shí)間確鑿的文本,包括所有他們對自己所處時(shí)代的觀察和表達(dá),這些年輕作家似乎正在努力命名他們自己生焉在焉的同時(shí)代。進(jìn)而,我們應(yīng)該意識(shí)到,和前輩作家們將當(dāng)代作為過去迤邐而來的當(dāng)代不同,這些年輕作家在當(dāng)代寫當(dāng)代。
個(gè)人的小編年史和“微觀的精神事件”,如何獲得與稠人廣眾休戚與共的命運(yùn)感
假如不拿既有文學(xué)尺度來丈量他們的寫作,需要文學(xué)批評(píng)和研究回應(yīng)的是,這些年輕作家是否提供了屬于他們時(shí)代的新的審美經(jīng)驗(yàn)?而就像參與上述問卷的小說家遠(yuǎn)子所說:“當(dāng)然也有很多人在寫所謂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網(wǎng)絡(luò)上、文學(xué)期刊上有大量這樣的作品。但這種萬無一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其實(shí)是完全與現(xiàn)實(shí)脫節(jié)的主義。比如,他們所寫的農(nóng)村,其實(shí)是由一代人共同構(gòu)建出來的‘文學(xué)場景’,而老一輩作家和他們帶出來的徒弟還在這上面苦心經(jīng)營;再比如,他們已經(jīng)有了一套農(nóng)民該怎么說話,工人該想些什么,官員該怎么做事的標(biāo)準(zhǔn)。你不這樣寫,就是不夠‘現(xiàn)實(shí)’,‘不接地氣’。就是說他們所秉持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原則,恰恰是導(dǎo)致現(xiàn)實(shí)感匱乏的根源。”當(dāng)年輕作家仿照前輩作家將他們的同時(shí)代作為改革開放前那個(gè)“過去”的附屬物,而且如果那些“過去”不是建基于深入的田野調(diào)查和文獻(xiàn)功夫的文學(xué)轉(zhuǎn)化,僅僅是遠(yuǎn)子所說的這種拙劣的復(fù)刻,文學(xué)史譜系、審美的慣例和套式反而更有可能滋生“匱乏”和“同質(zhì)化”。
為什么改革開放時(shí)代的年輕作家書寫的與他們生命等長的同時(shí)代不可以是他們所理解的“大時(shí)代”?我們姑且也回望下“在當(dāng)代”寫當(dāng)代,而不是把當(dāng)代作為過去歷史的附屬物,一直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重要傳統(tǒng)。迷信歷史感的豐盈只能存在于物理時(shí)間的過去,這應(yīng)該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但即使是史詩性的長篇小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優(yōu)先消化的幾乎是同時(shí)代的“當(dāng)代”。
我曾經(jīng)給朱婧的短篇小說集《譬若檐滴》寫過一個(gè)評(píng)點(diǎn),說她從早期的《連生》《消失的光年》到《安第斯山的青蛙》再到最近的《水中的奧菲利亞》《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是一部1980年代出生人從大學(xué)生活到為人妻為人母,從清白純粹的理想到細(xì)小瑣碎的現(xiàn)實(shí),從整一到裂碎的小編年史,一以貫之地將微小的日常生活發(fā)展成反思性與個(gè)人和時(shí)代關(guān)聯(lián)的“微觀的精神事件”。因此,所謂“歷史感”不應(yīng)該絕對化地理解為線性的過去和現(xiàn)在的關(guān)系邏輯之上的。即使不去擬想他們未曾經(jīng)歷的過去,年輕作家所建構(gòu)的他們同時(shí)代的歷史邏輯也當(dāng)然可以獲得豐盈的“歷史感”。比如魏微從《大老鄭的女人》到《沿河村紀(jì)事》、徐則臣從“北漂”“花街”系列到《耶路撒冷》《北上》、魯敏從“東壩”系列到《九種憂傷》《荷爾蒙夜談》、梁鴻從《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到《梁光正的光》《四象》、付秀瑩從《陌上》到《他鄉(xiāng)》、雙雪濤從《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獵人》、周嘉寧從《荒蕪城》《密林中》到《基本美》、張怡微從《家族實(shí)驗(yàn)》到《細(xì)民盛宴》……如果我們研究者愿意細(xì)細(xì)考察,他們每一個(gè)人都是人和時(shí)代遭逢的悲欣交集的小編年史。
改革開放時(shí)代的年輕作家如何消化和書寫他們的同時(shí)代——以文學(xué)之發(fā)現(xiàn)、發(fā)微同時(shí)代的歷史邏輯,發(fā)明并命名“改革開放時(shí)代”?個(gè)人的小編年史和“微觀的精神事件”如何獲得與稠人廣眾休戚與共的命運(yùn)感?又如何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激蕩、沛然涌出時(shí)代的精神長河?令人遺憾的是,當(dāng)下的文學(xué)貌似并不匱乏的現(xiàn)實(shí)感和歷史感,可能恰恰是喪失了想象和建構(gòu)“過去”的興趣和能力。同時(shí),“現(xiàn)在”或者“同時(shí)代”也散成碎片般浮光掠影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一點(diǎn)所“感”。據(jù)此,我們有理由批評(píng)年輕作家放任自以為發(fā)達(dá)的“感”而敷衍的窮極無聊的“故事會(huì)”,他們真正匱乏理性反思、哲學(xué)思辨、時(shí)代文體創(chuàng)造以及“文學(xué)的國語”發(fā)明的能力。如此等等。一茬又一茬的年輕作家會(huì)不再年輕,“他們都老了嗎?”共識(shí)的經(jīng)典又留有幾部?也正據(jù)此,我上面對年輕作家所做的辯護(hù),或許恰恰成為辯無可辯護(hù)再難護(hù)的匱乏。
(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