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之時讀《中間的英格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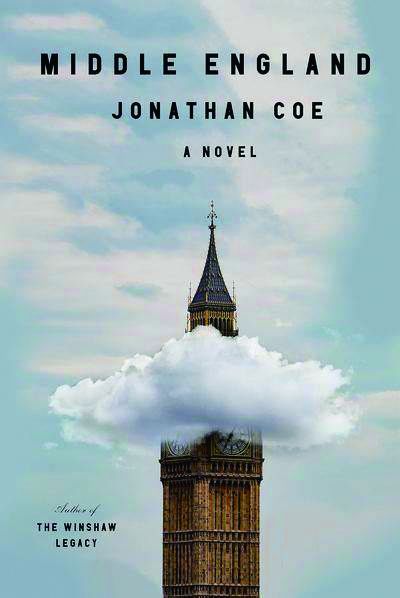
2019年秋,英國的議員還在為脫歐吵吵嚷嚷,每晚的議會都上演一場牽動民眾血壓的政治連續(xù)劇。在普通人家,親人間也因立場的不同,爭執(zhí)、隔閡、怨恨。在不少夫妻之間,脫歐成了忌諱不提的話題,或者成了徹底散伙的導火線。
在早一年的2018年秋,喬納遜·科伊出版了《中間的英格蘭》(Middle England)。他沿用了之前作品中的人物,《二混子俱樂部》(The Rotters’ Club)和《小圈子》(The Closed Circle)中的本杰明、道格拉斯、克里斯托弗等,鎮(zhèn)靜地拿起了脫歐這個滾燙的話題。前兩部集中于這些上世紀70年代就讀于伯明翰文法學校的孩子的人生經歷,而《中間的英格蘭》則是借這些人物來表現社會、政治、歷史的圖景,被評論者稱為“國情小說”(state-of-the-country fiction)。
2019年科斯塔圖書獎的評委認為《中間的英格蘭》是“應和當今時代的最佳小說”,獲得了科斯塔年度小說獎。《中間的英格蘭》剖析的是現時的新傷,從2010年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執(zhí)政開始,經過盛行多元文化、舉辦倫敦奧運會的2012年,最后推向2016年6月那場歷史性的脫歐公投。之后,時代大震的余波毫不減弱地繼續(xù)回蕩著。
作為“國情小說”,書名中的“Middle”涵括了地理、社會、政治、歷史等多種層面。“中”指的是地理位置上的英格蘭中部、社會政治含義上的中產階級,以及年齡階段上的中年。地理概念上的英格蘭中部地帶,由東西兩部分組成,包括伯明翰、萊斯特、諾丁漢等城市。這一帶繼承了18、19世紀工業(yè)革命時期的傳統(tǒng),是英國經濟文化的重要地帶。可是,媒體表現中的英格蘭地域形象,經常以南北來分別,南部屬于穩(wěn)定規(guī)范的建制,人多富裕;北部則是勉力維持生計,以工人階級為主。中部則成了不南不北也是可南可北的一帶。貫穿英國南北的主干道M1,從離倫敦一小時車程的密爾頓·凱恩斯開始,便以南、北來標識,仿佛中部并不存在。倫敦人的地域偏見更是視倫敦以北皆為北方了。在倫敦任教的索翰招呼從伯明翰過去的朋友索菲,“天哪……你看起來臉色蒼白,病蔫蔫的。一定是那可怕的北方天氣給害的。”
而社會政治含義上的中產指向典型的英格蘭城郊和鄉(xiāng)村,傳統(tǒng)的文化、連綿的綠地和紅磚的屋。科伊在開篇描繪了中部沿途的風景:“他們駕車穿越英格蘭中部的中心地帶,一路大致循著塞文河,經過布里奇諾斯,埃爾維里,夸特,大溫洛克,克雷塞奇。這一路平淡無奇,不會讓人留下任何印象,唯有的一些句點是沿途的加油站、酒館和園藝中心。還有一些文化遺產的棕色路標,在無聊的行路人的前方晃悠著更遠處的誘惑——那兒有野生動物園、國家信托的老宅大院,還有植物園。每一個村子的入口豎著村名的標牌,閃著限速的提醒。”
這些典型的英格蘭中部中產的村子里的人口構成以白人為主,過著相對舒適穩(wěn)定的生活。政治傾向上也基本在中間的兩側,稍左稍右,或是視情形左右搖擺。
中年的英格蘭50來歲,在年齡上的承前繼后,夾在保守的上一代和反叛的下一代之間。大選臨近,本杰明還沒決定該給哪個政黨投票,而他八十幾歲的父親毫無例外地繼續(xù)支持保守,大學生珂麗則是社會主義者工黨領袖科爾賓社團的積極分子。這一代中年人經歷過的半個世紀,他們出生于漸漸擺脫了二戰(zhàn)陰影的60年代,成長于連續(xù)罷工動蕩的70年代、社會分裂加深的80年代。到工黨執(zhí)政的1997年左右,他們初為父母。
這部從4月開始的小說,無法讓人不想起艾略特《荒原》的首句,“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這個混合著“記憶和欲望”的季節(jié),“攪動著”不知什么樣的舊土,催發(fā)什么樣的新芽。小說三部分的章節(jié)名都指向悠久地盎然著綠意的英格蘭:“快樂的英格蘭”“深處的英格蘭”“古老的英格蘭”。三者意思相近,反復喚起那懷舊的烏托邦,工業(yè)革命現代化列車飛速駛來之前的田園風光,是華茲華斯的詩、哈代的小說、康斯太勃爾的畫、拉爾夫·沃恩·威廉斯的音樂。小說一開頭已經借用一場老人的葬禮、一曲《再見了,古老的英格蘭》道過別,而這首挽歌似乎余音縈繞不去,以空為實,提醒人們缺位的存在。現時的英格蘭處在對過去的“記憶”和未來的“欲望”之間,或許也可被認作是又一層含義的“中段”。
寫脫歐這場時代風潮的作家,不止科伊。伊恩·麥克尤恩的《蟑螂》(The Cockroach)以卡夫卡式的怪誕寫了一出荒唐的鬧劇,諷刺退歐強硬派。而科伊本人雖然留歐的立場鮮明,但小說的描述卻是幾近社會學教材的寫實,不失公正理性,慎重地以“中”為軸線,方方面面地呈現、闡釋南北、左右、退留和老中青等的立場背景。科伊借助一個次要情節(jié),不失自嘲地指出作家的尷尬。本杰明幾十年的心血,一部長達5000多頁的小說,砍掉了歷史背景和音樂創(chuàng)作的后現代元素、變成了一部叫做《無刺的玫瑰》的自傳體愛情小中篇,卻得以進入主流的文學殿堂——布克獎入圍名單。
作為文學體裁的小說,無論是什么主題,總是要落實到個體的人。《中間的英格蘭》可以被讀作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卷軸,可上面的人物性情姿態(tài)各異,演繹著人類有關親情、愛情和友情的永恒主題。中年的作家寫中年人特別讓人笑得含淚。本杰明想回到青春愛戀、血脈僨張的一刻,躲入納尼亞式的“魔衣櫥”,走進時光的隧道。科伊也忍不住借用他創(chuàng)造的人物來療愈脫歐給這個國家?guī)淼膭?chuàng)傷。倫敦的索翰去了英格蘭北部的達勒姆,他在倫敦金融區(qū)工作的愛人也尾隨而去。左傾留歐派的大學老師索菲和工人階級退歐派的丈夫也復合了。也許科伊讓英格蘭重新聚合的愿望太強烈,忍不住寫了一個預產期在脫歐日2019年3月29日的寶寶。
“美麗”的寶寶可能誕生了,但脫歐沒有按時發(fā)生。直到年底,鮑里斯·約翰遜贏得提前大選,坐穩(wěn)首相職位后,脫歐進程才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開始。這本當是退歐進程占領頭版的春天,忽然因了一場不明緣由的疫情,被禁了足,宅在了家中。在病毒這一人類共同的敵人面前,“社會”重新回歸到人類共同體的概念。4月5日晚上,快94歲的英國女王出來講話,感謝工黨于1945年創(chuàng)立的國民醫(yī)療體系,感謝保證生活基本運作的工作人員,也感謝乖乖待在家中不亂跑的民眾。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疫情面前,政治分歧擱置了,喚起二戰(zhàn)期間的全民團結,宣揚“自律、含蓄的幽默感和同情心”的民族共同性。《再見了,古老的英格蘭》末句唱道:“我曾經坐過自己的馬車,有著仆傭替我駕乘。這下我在獄牢,不知道該往何處轉身。”音韻還在回響,歷史從不會缺席。解封后,英格蘭會往何處走。在這最殘忍的4月,我們只能等待會有美麗的新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