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地域性及歷史留痕 ——關(guān)于呂翼小說《比天空更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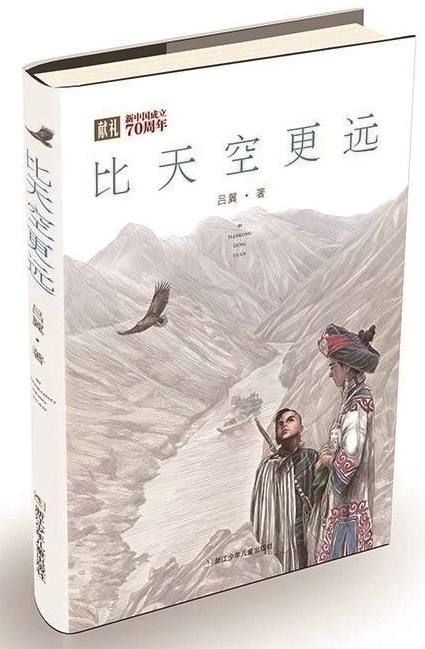
作家要為人類的歷史長河進行文字記錄,這個過程,因為不需要史學(xué)家那樣詳實嚴(yán)謹(jǐn)?shù)挠洈ⅲ虼耍谋镜氖褂每梢杂蟹翘摌?gòu)或虛構(gòu),也可以有非虛構(gòu)與虛構(gòu)交織融會。但不管如何展示,都不會完全脫離作家本人的根性源頭,那就是,作品最終會烙下與作家有關(guān)的民族性、地域性及歷史留痕。作家呂翼應(yīng)是最具有以上特征,且自覺肩負起本民族責(zé)任的彝族作家。
《比天空更遠》是一部長篇小說,歸屬兒童文學(xué),是呂翼的最新力作。作家屬于從小接受漢語言教育,不會使用本族母語和文字的人,所以,他的漢語書寫,沒有民族母語作家那種需要通過母語成句,再進行自我翻譯而造成語言思維轉(zhuǎn)換障礙的過程。小說的敘事跌宕起伏,情感豐沛,語言通暢、生動。《比天空更遠》的故事真實采用的是新中國解放前,劉伯承將軍率隊過彝區(qū),與彝族果基家支首領(lǐng)小葉丹歃血結(jié)盟的歷史事件及其派生出的后續(xù)影響。作品為忠于歷史的時間線,全書采用1956年前彝族的舊稱“夷”。(1956年,毛澤東主席建議將 “夷”改為“彝”,遂稱彝族,意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絲”、有吃有穿,象征興旺發(fā)達)。書中以白彝少年覺格的視角,講述了上世紀(jì)50年代初,在蒼茫的大涼山區(qū),一個叫苦蕎地的彝族寨子,發(fā)生的黑彝、白彝和娃子間的內(nèi)部糾葛,以及與國民黨駐扎軍隊的外部斗爭。最終,覺格阿爸曲木率領(lǐng)的解放軍,感化了黑彝羅火頭人,完成了苦蕎地寨子的和平解放。
《比天空更遠》在小說的敘事中,有極強大的民族性體現(xiàn)。作家在小說開始,就對彝族階層起源做了詳細描述,將當(dāng)?shù)鬲毺氐拿褡逭w生存形式躍然于紙,從中說明了彝區(qū)的政治生態(tài)。這也意味著告知讀者,彝人自古分階層的價值觀、世界觀、生活觀將直面革命性的改變。作家以彝族這個特定的等級制度為出發(fā)點,讓作品發(fā)展的走勢被整體帶動。由族群歷史淵源發(fā)散而成的枝節(jié),為小說中白彝少年覺格與黑彝少女史薇之間的友情,與阿媽的母子親情,以及彝人曲木和漢人鐘皓的兄弟情,鋪設(shè)了故事延續(xù)的復(fù)線型情節(jié)安排,這樣的寫作姿態(tài)很符合昆德拉的復(fù)雜多樣性范式。
優(yōu)秀的民族文學(xué)作品,必定會如實描摹民族日常、宗教信仰、族群生命觀、民族意識及部族文化,其目的,是為達到民族性的綜合展示。本小說在形式上不算特別新穎,作品中,白彝覺格和黑彝史薇依本民族習(xí)俗不能上學(xué),小說就此以兒童視覺呈現(xiàn)出解放戰(zhàn)爭中少數(shù)民族悲歡離合的生活畫卷,書寫了彝族地區(qū)的少年兒童蒙昧混沌的苦難和對美好生活的熾熱向往。新中國的建立和新生活的到來,必將徹底改變彝家對世界的理解和對未來的認(rèn)知。民族性的強調(diào),民族語言的準(zhǔn)確使用,是小說故事起伏及向外延伸的支點,還是故事中各橋段啟、承、轉(zhuǎn)、合的中心。如果背離了彝族特有的民族元素,這個小說的構(gòu)建就會失去光亮和意義。身為彝族后裔,呂翼清楚知道這些元素符號的使用與闡釋,他自然地將小說文本植入其間,完美地達到了書寫經(jīng)驗帶來的、不需要猜測和臆想的結(jié)構(gòu)進程。一部反映民族徹底摧毀奴隸制的小說,如果沒有澎湃的民族性,就將失去根基。呂翼以他生活的烏蒙大地為基點,把目光溯回和放遠,于是,他字里行間的族群天空就寬廣無限。他與族群對視,與族群交談,與族群相守,之后,落筆處必定是族群的存在。所以,在寫出族群和自己的民族生命體驗中,如此水到渠成,又如此令人難以釋懷。
《比天空更遠》中,地域性描寫的體現(xiàn)也是作品成功的綜合保障。我曾說過,小說是呂翼在文學(xué)世界里存在的方式 。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不屬于先鋒范圍,中規(guī)中矩,典型的傳統(tǒng)小說,一直追求全知的敘述視角。小說的人物、時間、地點、物件、專稱都有現(xiàn)實寫照,這在民族文學(xué)作品中,文體的自覺性應(yīng)該就是其特有的地域性界定。我讀過呂翼以母族為載體創(chuàng)作的幾部小說,前有《疼痛的龍頭山》《馬嘶》《馬腹村的事》,近有《比天空更遠》,這些作品的地域性描寫都非常明顯。眾所周知,彝族在我國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區(qū))的高原與沿海丘陵之間。其中,大涼山地區(qū)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地,也是直接從奴隸社會跨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地區(qū)。其特有的地域性事物眾多,小說就涵蓋了多方面的講述,如:神話傳說中,天神叫恩梯古茲、生育神叫格非神、惡鬼叫阿多納;稱蕎麥為蕎子;將肉切成坨塊清水煮,叫坨坨肉;男人頭頂留著天菩薩;男女都披羊毛披氈;畢摩念的驅(qū)鬼經(jīng)是:“你若要回來,/除非騾子下兒,/烏云生菌子,/石頭開鮮花/騾子長尖角……”除穢經(jīng)是:“妖魔鬼怪出不出?/兇星邪神出不出?/窮鬼餓鬼出不出?/三魂七魄出不出?”等等。這些大涼山彝區(qū)特有的區(qū)域說詞,被作家用各種不同的日常組件還原進文本,就是為增強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地域性重量。通過這些說詞的原形描述,讓讀者產(chǎn)生回顧或問詢,并再現(xiàn)出此地域環(huán)境里人與事與物的活動場景,強調(diào)了此地域的文化內(nèi)涵,構(gòu)成了語言、思想、社會矛盾的內(nèi)在沖突和外向爆發(fā)。
地域性是一個民族繁衍生息的區(qū)域內(nèi)各種要素總稱,地域、環(huán)境能夠?qū)γ褡逦膶W(xué)作品的整體風(fēng)格產(chǎn)生影響,由此能讓作品具有其鮮明的個性特征。例如,小說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火塘,就是地域性特征的代表之一。彝族的信仰里包含火崇拜,是一個火的民族,自視為火的子孫。家里的火塘永遠不能熄滅,那是火神居住之地,是祖先神靈取暖的地方。所以,當(dāng)鄧白嘴在火塘上躥來躥去時,立刻引起了爾沙管家的憤怒,這為后續(xù)羅火頭人接受和平解放的理念埋下了伏筆。在以苦蕎地寨子為代表的大涼山,頭人、家支、蕎麥、雄鷹等詞語,傳遞出來的是彝區(qū)自古固守的常態(tài)延續(xù)。小說是漸變與激變的戲劇性藝術(shù),地域性元素引起的演化,能夠激發(fā)小說內(nèi)在戲劇性的發(fā)展。呂翼在以上意義之下完結(jié)了他的小說建設(shè),這個故事的走向也成就了作品打造的存在感。小說中講述的族群過往,真正成為了新中國發(fā)展建立過程中,彝族社會意識變革的縮影。從這個層面來看,這部小說也是一部民族進化史。呂翼通過這些地域性元素的放送,表現(xiàn)了奴隸社會時期大涼山彝族民眾愛國意識的覺醒,也同時重溫了彝族人民對新中國解放事業(yè)的巨大貢獻。
在大涼山當(dāng)時的社會制度下,參加解放軍的成員,或參與解放工作相關(guān)事宜的進步人士,主要以彝族階層中地位略為低下的白彝為主,黑、白彝的階層不同,個體思想的思考狀態(tài)就不同,而更底層的娃子,盡管已對黑彝奴隸主產(chǎn)生不滿情緒,但仍然沒有擺脫壓迫的覺悟,仍然在慣性思維中把黑彝視為自己的主子而效忠。小說豐富的歷史內(nèi)容的梳理,是為更好完善人物的靈魂、意識和心理動態(tài),并且能突出作品的寫實技巧,使故事的敘述更為合理。這與注重探索形式的先鋒小說區(qū)別明顯。作家在作品里的心靈呈現(xiàn)和人性探索,對大多數(shù)讀者來說,更契合眾生現(xiàn)實主義審美感受。
與西方文學(xué)的理性相比,中國文學(xué)更側(cè)重抒情,這是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審美影響的結(jié)果,作家會以自己的情感牽制作品的走向,這是優(yōu)點,也是劣勢。尤其在歷史體裁的作品中,過度的情感會削減作品深度。還好,呂翼沒有落入這種俗套。
作家在歷史細節(jié)蘊含的事物中尋找意義,從更深刻的歷史意識源頭用歷史發(fā)展的延續(xù)性,把握歷史精神中的重要關(guān)系,以深刻的邏輯定位和情感投射出多層次多維度的構(gòu)境空間,以歷史人物事件間的關(guān)聯(lián)網(wǎng)絡(luò),在歷史條件下形成動態(tài)關(guān)系和生活結(jié)構(gòu)。社會現(xiàn)實文化的建構(gòu),是與歷史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記憶,這就是本部小說里歷史留痕在作品中體現(xiàn)的作用。因此,歷史是一個與文化、意識、語言、行為不可脫離的范疇,對歷史的理解,不能等同于線性進化。
這部小說緊緊扣動了歷史的脈絡(luò),將因為語言與地理因素等造成的大涼山地區(qū)的落后、蒙昧,從社會體制上進行剖析,對作品人物的設(shè)計就不只局限于本民族。從歷史進化的角度來看,正是不可抵擋的現(xiàn)代文明的介入,使得彝區(qū)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進入到現(xiàn)代社會,瞬間完成了政治歷史的變革。
長篇小說的寫作,可以讓作家熱烈奔放,小說的枝節(jié)也可以長出許多,這能讓小說的大樹更為粗壯。呂翼近年來對不同的小說人物刻畫、情節(jié)設(shè)計更趨于深刻及豐富,作品的語言節(jié)儉、大量使用短句式,加快了作品節(jié)奏。作品越來越精致和豐滿,體現(xiàn)了作家的自我成熟。他真正做到了以文脈去與世界溝通,讓作品與眾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