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戲劇的雙重隱形結(jié)構(gòu):“回溯”與“闖入”
原標題:“回溯”與“闖入”——論曹禺戲劇的雙重隱形結(jié)構(gòu)
摘要:曹禺的前期創(chuàng)作都運用了“回溯”和“闖入”雙重隱形戲 劇結(jié)構(gòu)。“回溯式”結(jié)構(gòu)能夠展現(xiàn)個體的生命歷程和內(nèi)在心理糾葛,承載現(xiàn)代的個人悲劇主題,這種結(jié)構(gòu)與易卜生的分析戲劇有著高度相似。“闖入式”結(jié)構(gòu)能夠容納更多的社會問題之討論,是從霍普特曼 的社會劇開始確立的戲劇結(jié)構(gòu)。同時,曹禺試圖用“哀靜的詩”來統(tǒng) 轄“回溯”與“闖入”的雙重隱形結(jié)構(gòu),這與梅特林克式“靜的戲 劇”及其日常生活的悲劇性的觀念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在結(jié)構(gòu)上的內(nèi)在相似性,體現(xiàn)出曹禺前期戲劇一 以貫之的雙重主題:個人悲劇與社會悲劇。
關(guān)鍵詞:曹禺 現(xiàn)代悲劇 回溯式戲劇 “闖入式”戲劇 雙重隱形結(jié)構(gòu)
曹禺作為最重要的中國現(xiàn)代劇作家,他的幾部戲劇作品《雷雨》《日出》 《原野》《北京人》的題材各有不同,《雷雨》中帶有專制色彩的資產(chǎn)階級家庭 矛盾和階級沖突,《日出》展現(xiàn)的中國上層社會的荒淫墮落和下層社會的血淚苦 難,《原野》中被凌辱與迫害的仇虎以荒蠻方式進行的反抗與復仇,《北京人》 中一個“詩禮傳家”大家庭的敗落與離析,這些都指向現(xiàn)代中國的種種社會問 題。而曹禺的幾部戲劇又以各個不同的戲劇藝術(shù)形式為人矚目,《雷雨》由多重 戲劇時間構(gòu)成的套狀戲劇結(jié)構(gòu),《日出》群像式的人物展現(xiàn)方式,《原野》的原 始色彩和象征主義手法,《北京人》的“靜的戲劇”與“北京人”的象征色彩, 這些也都引起讀者與研究者的關(guān)注,已有相當多的論述分別加以辨析。那么,在 曹禺的創(chuàng)作中,是否有一以貫之的戲劇觀?這幾部戲劇之間是否存在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在表面看來迥然不同的戲劇作品中是否存在著某種整體性和一致性? 初看起來,曹禺前期四部戲劇有著兩種不同的結(jié)構(gòu)方式,論者往往認同《雷雨》《原野》是鎖閉式結(jié)構(gòu),《日出》《北京人》是開放式結(jié)構(gòu),而這兩種戲劇 結(jié)構(gòu)被認為是戲劇結(jié)構(gòu)最基本的兩種方式。1 顧仲彝認為,除了鎖閉式結(jié)構(gòu)和開 放式結(jié)構(gòu)外,近現(xiàn)代戲劇還發(fā)展出了一種人像展覽式結(jié)構(gòu),這三種戲劇結(jié)構(gòu)是戲 劇史上最常用、最主要的結(jié)構(gòu)形式,而《日出》就屬于人像展覽式結(jié)構(gòu)。2 和小說、散文不同,戲劇文體本身對結(jié)構(gòu)的要求很高,戲劇結(jié)構(gòu)不僅和戲劇的外在形 式有關(guān),本身也聯(lián)系著戲劇的內(nèi)在主題。曹禺是內(nèi)行的劇作家,在戲劇結(jié)構(gòu)上尤 其著力,他在多篇創(chuàng)作自述中曾多次涉及這個問題。曹禺曾談到《雷雨》“太像 戲”,《日出》有著“結(jié)構(gòu)的統(tǒng)一”,《北京人》更好地在融合西方戲劇藝術(shù)的 同時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的風格,等等。如果說從《雷雨》到《北京人》,戲劇結(jié)構(gòu) 發(fā)展變化是一個不斷揚棄的過程,那么,這中間有沒有始終不變的曹禺式內(nèi)在戲劇結(jié)構(gòu)? 《雷雨》的序幕和尾聲保留與否,曾經(jīng)引發(fā)不同的爭議,如何理解作家要保留這一結(jié)構(gòu)的自辯?《日出》的第三幕是否有“生硬插入”之嫌,方達生的人物 設(shè)置是否僅僅充當作者的代言人?《原野》結(jié)尾帶有神秘色彩、象征主義傾向的 對仇虎幻覺的描寫,是否是對奧尼爾《瓊斯皇》的簡單模仿?《北京人》以寫實 的方式展現(xiàn)大家庭的中落,為何要加上象征色彩濃郁的袁任敢一家和一個現(xiàn)代工 人裝扮成的北京猿人?這些“曹禺式”的戲劇形式是否能夠從曹禺創(chuàng)作的整體考察中得到說明?這些獨特的戲劇結(jié)構(gòu)方式和曹禺的戲劇觀有何關(guān)聯(lián),是否形成了 統(tǒng)一的曹禺式內(nèi)在戲劇結(jié)構(gòu)?如果這些聚訟不已的問題有一個總體的解答,那么 就可以成為理解曹禺前期創(chuàng)作的重要基點。

曹禺
將曹禺三四十年代這四部代表作品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可以看到在各不相同的戲劇形式中存在著共性,那就是始終如一的“回溯式”和“闖入式”的雙重隱形戲劇結(jié)構(gòu)。勞遜曾經(jīng)指出,戲劇中動作的統(tǒng)一性和主題的統(tǒng)一性其實是同 一樣東西,而這兩者之間的結(jié)合正是通過戲劇結(jié)構(gòu)來實現(xiàn)的。3 可以說,概而言之的鎖閉式結(jié)構(gòu)和開放式結(jié)構(gòu),更多地描述了曹禺戲劇的外在結(jié)構(gòu)形式及戲劇形 式的轉(zhuǎn)變,而聯(lián)系著戲劇主題的“回溯式”與“闖入式”隱形戲劇結(jié)構(gòu),則證明 著曹禺戲劇一以貫之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和主題,以及這兩個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和主題之間的矛盾與張力。正是這種矛盾和張力,使曹禺戲劇的形式與主題顯現(xiàn)出某種曖昧、神秘 和爭議性,也塑成了曹禺戲劇的現(xiàn)代性品格。“回溯與闖入”的雙重隱形結(jié)構(gòu)背 后,是曹禺獨特的現(xiàn)代戲劇觀與悲劇觀。曹禺的戲劇結(jié)構(gòu)與戲劇觀,則需要放在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易卜生、斯特林堡、梅特林克和霍普特曼為代表的西方現(xiàn)代 戲劇轉(zhuǎn)型的視野中,才能得到更為清晰的體認。
一、回溯式結(jié)構(gòu)
曹禺戲劇表現(xiàn)的內(nèi)容都較為復雜,而且往往涉及長時段的人物經(jīng)歷,可以 說,他選擇的戲劇題材往往是長篇小說的容量,那么,如何將這樣多的內(nèi)容熔鑄 到表演時間不超過一個晚上的話劇舞臺形式中?曹禺采取回溯式戲劇結(jié)構(gòu),解決 的就是這一問題。

《雷雨》為人津津樂道的“發(fā)現(xiàn)”與“突轉(zhuǎn)”的戲劇技巧,背后就是典型的回溯式戲劇結(jié)構(gòu)。第一幕開場的時候,戲劇中關(guān)系人物命運的重要事件幾乎都已經(jīng)發(fā)生。三十年前周樸園對侍萍和大海的遺棄,三年前蘩漪和周萍的私情,半年來周萍和四鳳的相戀,幾天前周樸園礦上以大海等人為工人代表的工人罷工,這些事件在結(jié)構(gòu)上可以視為戲劇“前情”,在戲劇主題上卻不僅僅是“前情”那么 簡單,而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是通過“發(fā)現(xiàn)”的手法逐漸呈現(xiàn)出 來的,整部戲從結(jié)構(gòu)安排來看則可以視為回溯式戲劇。
這種回溯式戲劇往往被認為是由易卜生創(chuàng)造并發(fā)揚光大的。彼得·斯叢狄 在《現(xiàn)代戲劇理論(1880 — 1950)》一書曾經(jīng)敏銳地指出易卜生戲劇的“分析 技巧”,并且將運用這種技巧的劇作稱為“分析戲劇”。分析戲劇的結(jié)構(gòu)方式正是回溯式戲劇結(jié)構(gòu)。所謂“分析戲劇”,真正的情節(jié)在戲劇開始前就已經(jīng)發(fā)生,并且在戲劇展開過程中逐漸揭示出來,換句話說,戲劇是從結(jié)局開始的,作為前 因的主要戲劇事件并不直接呈現(xiàn)在戲劇舞臺上。分析戲劇是斯叢狄從內(nèi)容和形式 兩個方面考察得出的戲劇類型,這種戲劇的內(nèi)容和形式互為表里、互相決定。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社會支柱》《群鬼》《海上夫人》《羅斯莫莊》《野鴨》 《建筑師》《博克曼》《當我們死而復醒時》這些重要的作品,采取的都是這種 分析技巧和回溯式戲劇結(jié)構(gòu)。關(guān)于這一點,焦菊隱《論易卜生》也有類似發(fā)現(xiàn),他指出易卜生戲劇有“濃縮的力量”:“自從戲劇一開始,動作就一直是緊張的,有時一開幕便是‘高潮’。因此讀者和觀眾,當戲一開始時就被其集中的濃 縮的力量所吸引。而他的戲劇的外部的動作太少。外部的動作雖少,內(nèi)部的涵量 卻是飽滿、密集的。” 4 這顯然也是拜回溯式戲劇結(jié)構(gòu)所賜。
論者嘗謂《雷雨》模仿、借鑒了《群鬼》開頭,都以仆人間的對話(父親追問作為女仆的女兒和少主人的關(guān)系)來引出懸念,甚至認為這是用“頗為陳舊的方法”來“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5 。其實,引發(fā)懸念固然是這兩場對話的用意之 一,更重要的是,《雷雨》開頭魯貴、四鳳的父女對話勾勒出了戲劇中主要人物 的關(guān)系,正如《群鬼》開頭以使女呂嘉納與繼父安格斯川的對話來交代劇情,其 作用更在于大容量戲劇內(nèi)容的展現(xiàn)和戲劇形式的凝練。
回溯式戲劇結(jié)構(gòu)當然不必都以不免受到刻意、冗長之譏的類似對話開頭,正如曹禺的《北京人》和易卜生的《羅斯莫莊》都呈現(xiàn)出更為圓融的結(jié)構(gòu)形式,但基本的回溯式戲劇結(jié)構(gòu)內(nèi)核卻沒有改變。《北京人》是三幕劇,第一、二幕發(fā) 生在中秋節(jié),第三幕則是一個月后的深夜。劇中曾家老少都是有故事的人,而他 們的主要故事在開場之前已經(jīng)完成。曾文清和愫方是相愛卻不能表露的表兄妹, 因為文清年少遵父母之命娶了精明霸道的思懿為妻,如今兒子曾霆都已經(jīng)結(jié)婚成 家。曾霆和妻子瑞貞也是包辦婚姻,在懵懂中成親,兩人并無愛情。愫方為照顧 姨母寄居曾家,姨母去世后就成了姨夫曾皓的護士和拐杖,被這個自私的老太爺 壓榨著青春和感情。文清的妹夫江泰是個老留學生,早年曾經(jīng)做官,后因侵吞公 款離了職,與妻子文彩也寄住在曾家,成日地酗酒發(fā)牢騷。中秋節(jié),文清兒時的 奶媽來曾家送節(jié)禮,正遇到一群討債的人來曾家堵門要賬,由此慢慢“回溯”出 這個老北京舊世家過去的故事,呈現(xiàn)出曾家現(xiàn)在逐漸敗落的跡象,以及困守在舊 家庭中兩輩人的苦惱與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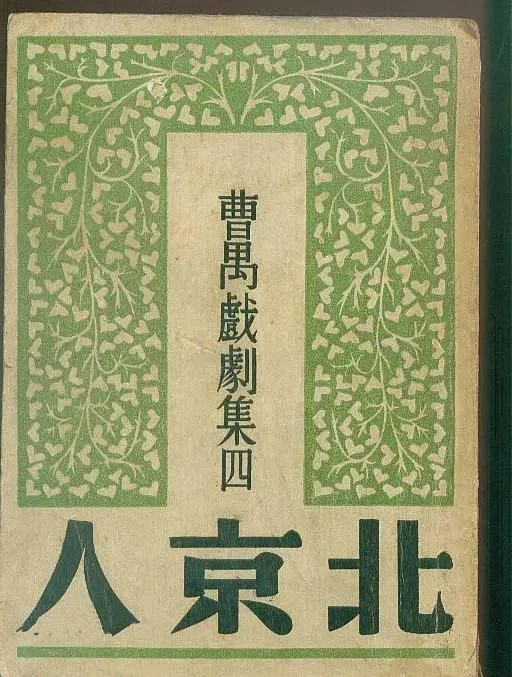
《羅斯莫莊》描繪的是古老望族羅斯莫家族的故事,主人公羅斯莫是家族 最后的繼承人,他的妻子碧愛特遵循傳統(tǒng),身體孱弱而不能生育。當碧愛特發(fā)現(xiàn)丈夫有放棄傳統(tǒng)宗教的傾向,并且愛上了激進的呂貝克小姐,她從莊園一座橋上跳進水溝自殺。戲劇開場,呂貝克就和女仆談論羅斯莫不敢從莊園那座橋上經(jīng)過 的事,由此回溯出碧愛特的自殺;接著,通過碧愛特的兄長克羅爾對羅斯莫的訪 問,回溯出羅斯莫受呂貝克的影響而放棄傳統(tǒng)宗教的往事;然后,通過急進黨人摩騰斯果的訪問,回溯出碧愛特是因為發(fā)覺羅斯莫的轉(zhuǎn)變而自殺的真相;最后,通過克羅爾對呂貝克的追問,讓呂貝克反省自己有意引誘碧愛特自殺的行為。至 此,激進的呂貝克仿佛也受到古老的羅斯莫莊的宗教與道德觀念的影響,開始自省、懺悔,不能接受羅斯莫的求婚。終于,兩個人互相吐露愛情與內(nèi)心深處的道 德拷問,相攜著一起跳進了碧愛特自殺的水溝。
余上沅對這種《羅斯莫莊》式的易卜生戲劇倒敘事有過精彩的分析:
固然不是每出戲伊卜生都像在“Rosemersholm”里那樣的倒著敘 事,可沒有一次他不是把劇中人的歷史及彼此的關(guān)系輕輕巧巧的表白 出來。......
哪一篇不是叫已經(jīng)成了死灰的過去在現(xiàn)在又變作如火如荼的生動。......
他描寫人類的內(nèi)心生活,描寫人類靈魂的臨到大節(jié),所以他從“The Wild Duck”以后的故事,全是從結(jié)局入手的。......在這些成熟的劇本里,現(xiàn)在的故事的起頭,實在是過去的故事的結(jié)局:因為有了那樣的結(jié)局,所以才引出這樣有力量、有動作的戲劇來。6
《北京人》采取了《羅斯莫莊》式的回溯式結(jié)構(gòu),描寫了“人類靈魂的臨到 大節(jié)”,不過卻選擇了不同的結(jié)局。《北京人》中曾文清和愫方固然也不能打破 道德律令,勇敢相愛、結(jié)合,但結(jié)尾他們則走了不同的道路。在愫方的鼓勵下,文清試圖離開家尋找自立的途徑,當他鎩羽而歸時,在自責與絕望中自殺了。愫方卻在與瑞貞的相互關(guān)心和鼓勵下,打算追隨瑞貞和袁任敢父女離開曾家,尋找新生之路。《北京人》的情調(diào)是哀傷的,但由愫方的轉(zhuǎn)變和袁任敢父女的生命力 指出了某種希望的前景。
《北京人》更容易被人辨識出的是與《三姊妹》的風格相似性,曹禺曾 談及自己嘆服契訶夫的戲劇藝術(shù),說《北京人》的確“受過契訶夫戲劇的影 響” 7 。《三姊妹》是契訶夫戲劇中一部完美的作品,普羅左洛夫家的三姊妹 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和對未來的夢想中,她們的孤獨、迷惘和希望讓人印象深 刻。《三姊妹》的結(jié)構(gòu)非常考究,契訶夫開創(chuàng)了自己的戲劇風格與結(jié)構(gòu),整部戲 排除了外在的戲劇性沖突和復雜的情節(jié),呈現(xiàn)的是人物對于自己生活的反思,持 續(xù)不斷地分析自己的命運,人物在社交場合的對話也具有獨白的性質(zhì)。
斯叢狄曾著重分析《三姊妹》中兄長安德烈與耳背的仆役費拉彭特的對話。安德烈是個孤獨沉默的人,他只在明知沒有人能聽懂的時候才會說話。借助于耳 聾這一設(shè)定,安德烈和費拉彭特的對話其實是兩個人各自的獨白,安德烈的孤獨 在此異常鮮明地體現(xiàn)出來。8 《北京人》中曾文清也是這樣孤獨沉默的,他只在 疼愛他卻不懂他的陳奶媽面前才會吐露心聲。第一幕,中秋節(jié)的早晨,陳奶媽帶 著孫子小柱兒從鄉(xiāng)下來看望曾家老少,文清還未起床,兩人隔著門親熱地談話,但是彼此都聽不清對方究竟說的是什么,小柱兒還嘲笑奶奶耳聾了。第二幕,當 天夜晚,陳奶媽陪文清坐在小客廳,陳奶媽絮叨著思懿要將愫方介紹給袁任敢做 續(xù)弦的事,念叨著文清和妻子思懿的不睦,文清無法直接作出什么回應。當陳奶媽提到飯席上袁先生老望著愫小姐,文清不語,等她回頭跟小柱兒說話時,讓隔壁的曾霆念出《秋聲賦》的句子:“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 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當陳奶媽提及 大奶奶思懿不肯出房間時,文清則哀傷地吟起陸游的《釵頭鳳》:“東風惡,歡 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陸游與唐婉這對表兄妹相愛卻 不能廝守,正對應著文清和表妹愫方之間無望的感情。
如果說“回溯式”主要是就戲劇結(jié)構(gòu)而言,斯叢狄所說的分析技巧、分析 戲劇,則是從內(nèi)容和形式辯證統(tǒng)一的角度總結(jié)的戲劇概念。論者嘗將《雷雨》與 《俄狄浦斯王》的命運觀相聯(lián)系,而結(jié)合戲劇結(jié)構(gòu)的分析,兩者的相似更在于其 回溯式戲劇結(jié)構(gòu),同為運用了“分析技巧”的分析戲劇。歌德和席勒曾經(jīng)通信討 論過這種分析方式,歌德認為,“如果展示部分本身就是情節(jié)發(fā)展的一個部分, 我會把這種戲劇素材稱作最佳的戲劇素材”。席勒后來回信稱《俄狄浦斯王》的 素材就是如此,這部戲可以看作最好的悲劇類型,此劇“完全是一個悲劇性的分 析”,“一切皆備,只是一層層的揭開。即便事件再復雜、再依賴于周圍的環(huán) 境,也可以在一個極其簡單的情節(jié)和很短的時間段里完成”。9
斯叢狄認為,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和易卜生戲劇在上述戲劇結(jié)構(gòu)的相 似之外,還存在著差異。《俄狄浦斯王》的真相是客觀的,這一真相“不屬于過去,不是過去,而是當下被揭示出來”。而易卜生戲劇的主題不是過去的事件,而是“過去本身成為主題”,是《博克曼》中反復提到的“漫長的歲月”和“被 摧毀和被糟蹋的一生”。在易卜生戲劇中,真相是“內(nèi)心的真相”。這種主題本質(zhì)上是長篇小說的素材,只有借助分析技巧才能登上舞臺。10 焦菊隱曾經(jīng)論及易卜生戲劇首創(chuàng)的“討論”元素,認為這“不光是戲劇中主要的興味,而且是 戲劇的中心力”11 。如果排除很多現(xiàn)代作家關(guān)注的“討論”元素中的社會問題 成分,其實這中間更多的有著追求“內(nèi)心的真相”的分析成分,這也是易卜生 不認可自己寫的是社會問題劇的原因所在,正如曹禺開始不承認《雷雨》是社 會問題劇一樣。
如果說《雷雨》中過于激烈的戲劇沖突、過于復雜的情節(jié)和過多的偶然性 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沖淡了這種“內(nèi)心的真相”的分析,《日出》《原野》《北京 人》則逐漸減少了這些外部的戲劇性成分,逐步增加了人物內(nèi)省的刻畫。比起 《北京人》來,《日出》和《原野》包含了較為顯著的戲劇沖突,對人物的行動 多有描繪,但整體來看也是回溯式的。
《日出》開場時,陳白露已經(jīng)度過了她跌宕起伏的青春歲月,她曾經(jīng)是愛華 女校的高才生,是社交明星,父親死了,她做過電影明星,當過紅舞女,而今是 寄居在高級旅館中依傍銀行經(jīng)理、受供養(yǎng)的交際花。從高才生到交際花之轉(zhuǎn)變的 “內(nèi)心的真相”,是到了第四幕才“回溯”出來的,原來白露曾經(jīng)與一位充滿理 想的詩人結(jié)婚生子、在鄉(xiāng)下快樂地生活過。但是不久兩人都對這種生活厭倦,孩 子夭折后,詩人自己去“追他的希望去了”,白露也回到都市過上了紙醉金迷的 生活。白露和《傷逝》中的子君一樣,曾經(jīng)毅然學娜拉出走,但是她沒有像子君 離開涓生一樣孤獨死去,卻像魯迅所說的,她“出走之后”果然墮落了。這里, 《日出》對于新青年追求理想而不無盲目的揭示,是魯迅《傷逝》之后最令人痛 心的文學追問。
《原野》中仇虎一家被焦閻王構(gòu)陷、迫害,父親身亡,妹妹被賣為妓女含冤 而死,仇虎也被打入大牢,家里的土地被焦閻王霸占,這些慘烈的往事也是通過 回溯的方式呈現(xiàn)的,由此塑成仇虎一心復仇的“內(nèi)心的真相”。然而,焦閻王已 死,仇虎的復仇之劍失去了明白無誤的目標,而他內(nèi)心的復仇之火卻不能停息, 當復仇的行為指向焦閻王無辜的兒子焦大星和孫子小黑子時,仇虎開始焦灼不 安,陷入了道德焦慮,被種種幻象糾纏不已。
曹禺這幾部戲劇的內(nèi)容確實都是長篇小說的素材,正因為選擇了必須運用回 溯式戲劇結(jié)構(gòu)才能容納的長篇小說的素材,曹禺才會在每部戲中都用了大量筆墨 來寫詳細的人物小傳和舞臺提示,這些筆墨帶著鮮明的小說筆法,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多次被提及。
二、“闖入式”結(jié)構(gòu)
為了將更多的內(nèi)容納入戲劇,曹禺還運用了一種可以稱之為“闖入式”的戲 劇結(jié)構(gòu)。這些闖入者,包括《雷雨》中的魯大海、《日出》中的方達生、《北京 人》中的袁任敢袁圓父女。這些人物與戲劇背景環(huán)境都有些格格不入,仿佛是誤 闖進來的。
《雷雨》中,魯大海的形象一向被認為塑造得不夠成功,帶有概念化傾向; 《日出》中,方達生作為串場人物和旁觀者,往往被認為有著作者傳聲筒之嫌; 《北京人》中,租住在曾家的袁任敢父女似乎顯得有些突兀。更重要的是,這些 人物本身不太具有戲劇性,和戲劇的主人公之間的關(guān)系是松散的,豈不是破壞了 戲劇的結(jié)構(gòu),消弱了戲劇的主題?李健吾就認為《雷雨》的故事應該圍繞蘩漪 “這樣充實的戲劇性的人物”來展開,曹禺“不把戲全給她做”,“戲的結(jié)構(gòu)不 全由于她的過失和報復”,是令人遺憾的。12
然而,魯大海這些人物在曹禺戲劇中又不可或缺,砍去這些部分的話,曹禺 戲劇頗有變了味兒之嫌。如果說魯大海的塑造就曾受到論者的批評,為何曹禺在 接下來的戲劇中又一再運用這一戲劇結(jié)構(gòu)呢?
在論者談到魯大海、方達生、袁氏父女這些人物時,往往將其視為曹禺戲劇 對社會問題的關(guān)注傾向。曹禺在《雷雨·序》中著重申明自己沒有創(chuàng)作社會問題 劇的初衷,不過,他最終還是追認了這些社會問題內(nèi)容的存在。《雷雨》中魯大 海和周樸園作為罷工工人和資本家董事長的勞資沖突,可以看到和曹禺之前改譯 并參演的高爾斯華綏的戲劇《爭強》的相似性。在發(fā)表于1934年《文學季刊》的 《雷雨》初刊本和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雷雨》初版本中,魯大海的身份 是周樸園礦上的“工頭”,正如《爭強》中罷工代表羅大為是安敦一礦上的“工 頭”一樣。直到1937年5月《雷雨》的改訂版,才將魯大海的身份改為“工人”。魯大海和周樸園的兩強對峙,也非常接近《爭強》中工頭羅大為和董事長安敦一 的互不相讓。在曹禺為《爭強》所做的序言中,他指出這是“晚近社會問題劇的 名著”:“劇內(nèi)有一對強項的人物——傲悍的董事長和頑抗的技師——全劇興趣 就系在這一雙強悍意志的爭執(zhí)上。董事長安敦一是代表廠方的,一位真有骨氣的 老先生,抱定了見解,一絲一毫也不退讓。對方技師羅大為是鐵礦罷工的領(lǐng)袖,生來一張鋒利的口舌,火一般的性格,也保持不妥協(xié)的精神。二人都是理智魄力 勝于目前一時的情感,為了自己的理想,肯拋開一切個人的計算的。”13 可以看 出,曹禺對社會問題劇的理解和當時中國的戲劇創(chuàng)作者、研究者是不太一樣的。他重視社會問題劇中對于社會經(jīng)濟問題、現(xiàn)實矛盾的揭示,當時更重視戲劇中兩 種“強悍意識的爭執(zhí)”,而不是放在個人(及其從屬的階級、階層)與社會環(huán) 境、社會制度的矛盾上。
對社會問題劇的重視是當時中國的戲劇研究者和創(chuàng)作者的普遍認識。比如胡適就認為,在西方戲劇中,“最重要的”乃是“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 的“問題劇”。14 而當時劇作家和研究者對“問題劇”的理解,與其說接近易卜 生,不如說更接近蕭伯納。蕭伯納認為:“只有在問題劇中才含有真正的戲劇, 因為戲劇不只是自然的照相:它是人的意志和他的環(huán)境間的沖突的諷喻式表現(xiàn); 簡而言之,戲劇是關(guān)于問題的。”15 勞遜曾經(jīng)指出蕭伯納對易卜生的理解影響了 現(xiàn)代劇作家,而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易卜生的分析戲劇:
現(xiàn)代劇作家從易卜生那里學來的許多東西都是通過蕭伯納。現(xiàn)代劇作 家欽佩易卜生的緊湊的技巧、社會的分析和性格化的方法。但是現(xiàn)代劇作 家跟蕭伯納一樣地把這些因素大大地變了質(zhì)......易卜生的對自覺意志的分 析不再出現(xiàn),代替它的是某些品質(zhì)的組合來構(gòu)成性格。16
如果《雷雨》是將周樸園遺棄的魯大海作為自己礦上的罷工工人這樣一個 “偶然”或“巧合”,來將社會問題納入家庭劇的話,那么《日出》中方達生對 陳白露的造訪,一個陌生人闖入腐敗墮落的上層社會的一角,則與霍普特曼的名 劇《日出之前》有結(jié)構(gòu)上的相似性。
和易卜生的戲劇不同,霍普特曼《日出之前》的副標題就標明“社會劇”。戲劇描繪了西里西亞的地主克勞塞一家,克勞塞采煤致富之后就開始酗酒度日,他的后妻和前妻小女兒海倫娜的粗俗強悍的未婚夫偷情,他的大女兒瑪爾塔嫁給 了工程師霍夫曼。瑪爾塔也是一個酗酒者,遺傳的影響不僅讓她的胎兒不保,也使生產(chǎn)過程變成了一場煉獄之旅。霍夫曼被這個家庭所同化,他只等待繼承家庭 的財產(chǎn),甚至試圖向小姨子海倫娜求愛以獲得個人的感情慰藉。戲劇是從霍夫曼 的舊日同學阿爾弗萊特·洛特的來訪開始的。這位來訪者是一位社會研究者和理想主義者,他來到此地是為了研究礦工的境遇。在這種情況下,來訪者洛特和克 勞塞家中唯一純潔無辜的小女兒海倫娜相愛了。海倫娜希望洛特能夠帶她逃離這 個家庭,然而,當洛特得知這個家庭的酗酒傳統(tǒng),得知如果自己與海倫娜結(jié)合的 話遺傳會延續(xù)到自己的后代時,他退縮了。海倫娜在絕望中選擇了自殺。
“闖入者”洛特的來訪和離去構(gòu)成了戲劇的主要情節(jié),他試圖將海倫娜帶 離泥坑一樣的家庭,最終又放棄,帶給海倫娜的是絕望和死亡。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戲劇結(jié)構(gòu)和《日出》中方達生與陳白露串起整部戲劇的結(jié)構(gòu)是相似的。和洛特一樣,方達生也試圖帶陳白露走,離開這個墮落的環(huán)境,但他沒有成功。作為 “社會劇”的《日出之前》,當然不會僅僅把筆墨放在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線上, 洛特代表著一雙觀察社會的眼睛,戲劇中通過洛特之眼,不僅看到克勞塞一家的 沉寂無望的生活狀態(tài),還看到其他農(nóng)民的愚昧麻木,目睹一位可憐的看牲畜的女 人為了家里的八個孩子而偷牛奶的場景。諸如偷牛奶的女人等人物與細節(jié),和戲 劇的主要情節(jié)沒有必然關(guān)聯(lián),顯示著霍普特曼通過戲劇展現(xiàn)社會問題的企圖。這 樣的戲劇結(jié)構(gòu)同樣出現(xiàn)在《日出》中,方達生見證小東西和翠喜的遭遇,正如洛 特見證著偷牛奶的女人和其他農(nóng)民的遭遇。有論者指出,《日出》的第三幕在戲 劇結(jié)構(gòu)中似無必要,但曹禺卻很偏愛這一幕,完全不同意刪去這一幕的建議。這 無疑說明曹禺同樣具有霍普特曼對社會問題的關(guān)注熱情。
《日出》和《日出之前》的相似性還不止于此,標題的意象及其象征意味也 是非常相像的。白露最后選擇在黎明到來之前自殺。她拿出安眠藥后,有一段對 鏡自語:“生得不算太難看吧。人不算得太老吧。可是......這——么——年—— 輕,這——么——美......”《日出之前》結(jié)尾,海倫娜在約定好一起離開的清晨 尋找洛特時,院子里傳出她父親醉酒的瘋語;遍尋不到意中人,海倫娜發(fā)現(xiàn)了洛 特留下的訣別信,她父親的瘋語仍在重復;海倫娜拿下獵刀準備自殺的時候,她 父親醉酒的聲音還在不停重復:“難道我不美麗么?難道我沒有魅力的妻子么? 難道我的兩個女孩不美麗么?”17 《日出》結(jié)尾,方達生沒有推開白露關(guān)上的 房門,他隔著門向白露道別,要去追隨外面的太陽;《日出之前》劇終,洛特因 為害怕遺傳的鐵律,只留下一封信就悄然離開。社會問題的觀察者、理想主義的 “闖入者”離開了舊世界,而年輕、美麗的白露和海倫娜都死在了日出之前。
白露感嘆鏡中的自己“這么年輕”“這么美”之后,發(fā)出這樣的感喟:“太 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論者注意到白露的感慨不無觀念性,認為這出自作者先在的主題認定,或者不是出于人物情 感、行為的自身邏輯18 ,不過這種感慨確實是中外敏感于從古典到現(xiàn)代之時代轉(zhuǎn) 型過程的劇作家所共同的體悟。斯特林堡作為易卜生戲劇的發(fā)展者和現(xiàn)代戲劇的 開創(chuàng)者之一,他在觀察自己妹妹夫婦的生活時,也敏銳地捕捉到妹夫菲利普在臨 終前喟嘆的類似表述。在《神秘日記》中,斯特林堡記下妹夫在病床上的最后一 句話:“外面已經(jīng)是夏天了,我要睡覺了。” 19
這種在日出之前死去的模式同樣出現(xiàn)在霍普特曼的象征主義名劇《沉鐘》 里,代表了理想和希望的精靈羅登德蘭在準備到人間拯救鑄鐘人海因里希時, 水妖尼格爾曼這樣警告她,如果到人類中去,將和人一樣“會受古書束縛,挨 太陽詛咒”。《沉鐘》結(jié)尾,曾經(jīng)為羅登德蘭喚起勇氣和理想的海因里希,還是難免受到“古書的約束”和“太陽的詛咒”。海因里希懷著離棄舊世界的妻 兒的愧疚和不能繼續(xù)追趕理想的痛苦死去了,他最后的話語也正是以一種神迷 的口吻喊出:“太陽的鐘聲響在高空!太陽......太陽升起來了!——黃泉的黑 夜很長很長。” 20
在曹禺的“闖入式”戲劇結(jié)構(gòu)中,舊世界和闖入者之間的勢力對比逐漸有 所變化。《雷雨》中,蘩漪、侍萍得了瘋病、困守舊宅,子輩的三個年輕人死于 舊家庭罪惡,“闖入者”魯大海不知所終,這結(jié)局讓曹禺為戲劇定下“悲劇”的 標簽。曹禺沒有給后來的戲劇定義為“悲劇”,或許是他更加注重“闖入者”所 代表的理想和希望,并且暗示了“闖入者”未來可能走的新路。《北京人》的結(jié) 尾,依舊年輕美麗的瑞貞約好愫方,準備與“闖入者”袁任敢父女、“北京人” 一起離開曾家,同時卻讓鎩羽而歸的曾文清死在了“日出之前”。“闖入者”離 開了舊世界,而舊世界的人物也分裂成了能夠繼續(xù)前行和就此止步的兩類。
三、曹禺的悲劇觀與“哀靜的詩”
回溯式戲劇能夠?qū)⑷说囊簧虚L時段的歷史納入戲劇之中,外在變化深藏 在人物的內(nèi)心深處,通過分析技巧展現(xiàn)事件的真正動機。易卜生的分析戲劇致力 于挖掘人物的內(nèi)在自我,呈現(xiàn)具有遠大理想但卻遭到挫敗的現(xiàn)代自我,戲劇沖突 在于個人和毀滅他的社會之間的矛盾,因此,雷蒙·威廉斯將易卜生戲劇當作自 由主義悲劇的典范21 。曹禺筆下的蘩漪、陳白露身上都有著這樣自由主義悲劇的元素。而當回溯式戲劇更多地展示孤獨的人,其原始欲望被他人和社會所挫敗,比如斯特林堡的《朱麗小姐》《鬼魂奏鳴曲》和奧尼爾的《榆樹下的欲望》《悲 悼》《瓊斯皇》等代表性悲劇,雷蒙·威廉斯稱之為私人悲劇。《鬼魂奏鳴曲》 和《雷雨》的故事有相像之處,劉紹銘等研究者曾指出《榆樹下的欲望》和《雷雨》的主題相似性,而《原野》從《瓊斯皇》那里頗有受益之處也是研究者屢屢 提及的,更重要的是,上述三組對照中前后兩者在戲劇結(jié)構(gòu)上是共通的,而作為 戲劇形式的結(jié)構(gòu)聯(lián)系并決定著戲劇主題,背后正是劇作家的戲劇觀。
奧尼爾對《悲悼三部曲》曾經(jīng)做過這樣的說明:“有否可能把古希臘的命 運觀念大致上改成現(xiàn)代的心理觀念,然后把它寫進劇本,使今天不信神、不信因 果報應的有知識的觀眾也能接受并為之感動呢?”22 換句話說,奧尼爾依然重視古希臘悲劇的主題與結(jié)構(gòu),只不過將命運觀替換成了現(xiàn)代心理學。這和李健吾對 《雷雨》的評論極為相似。李健吾肯定《雷雨》中的命運悲劇成分,認為曹禺一 方面運用了古希臘的命運悲劇主題與形式,另一方面運用了易卜生式“環(huán)境與遺 傳”的自然主義戲劇的主題與形式,但是他又進一步指出《雷雨》中的命運不是 “形而上的”,將其歸結(jié)為曹禺戲劇對于“人物的錯綜的社會關(guān)系和人物的錯綜 的心理作用”的表現(xiàn)方式,換言之,取消了其命運悲劇的內(nèi)涵,置換成了現(xiàn)代的 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內(nèi)容。在此意義上,肯定“這是作者的勝利處”。23
在回溯式戲劇中,長時段的個體生命歷程于回溯中展示出來,而主人公于此 對自我有了深入的認識和反省,人物的心理世界由此被呈現(xiàn)、感知,這是現(xiàn)代悲 劇中現(xiàn)代自我的覺醒,也是現(xiàn)代自我的悲劇性所在。《雷雨》中的蘩漪(甚至周 樸園)、《日出》中的陳白露、《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和愫方,都是這樣的現(xiàn)代 自我形象。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雷雨》第四幕中周樸園有所悔悟,而在序幕和尾 聲中,他也是作為一個懺悔者的形象出現(xiàn)。在此意義上,周樸園的形象與斯特林 堡《鬼魂奏鳴曲》中曾經(jīng)作惡多端的主人公何梅爾經(jīng)理有相近之處。
闖入式戲劇結(jié)構(gòu)更容易呈現(xiàn)社會問題,“闖入者”和他闖入的世界是對立 的,這樣的結(jié)構(gòu)設(shè)置是因為他所闖入世界中的人物不能夠通過自己的反省認識到 其身處的社會之問題所在,“闖入者”既是觀察者又是評判者,在某種程度上也 代表了作者的主觀聲音。《雷雨》中,魯大海宣判周樸園的罪惡。《日出》中, 方達生宣告陳白露如果不離開腐敗的旅館代表的金八所左右的世界,未來將是一 條死路。《北京人》中的人類學者袁任敢,“嘴角常在微笑,仿佛他不止是研究人類的祖先,同時也嘲笑著人類何以變得這般墮落”,他頌揚代表原始生命力的 “北京人”而批判“人吃人的文明”:
這是人類的祖先,這也是人類的希望。那時候的人要愛就愛,要恨 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們整年盡著自己的性 情,自由地活著,沒有禮教來拘束,沒有文明來捆綁,沒有虛偽,沒有欺 詐,沒有陰險,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惱;吃生肉,喝鮮血,太 陽曬著,風吹著,雨淋著,沒有現(xiàn)在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們是非常 快活的! 24
《原野》也運用了回溯式和闖入式兩種結(jié)構(gòu),不過是一種變形:仇虎既是不 斷回顧家庭的血淚歷史、對個人際遇反省的主人公,也是來到焦閻王家中實施復 仇行為的闖入者。他困于黑林子里因內(nèi)心糾葛而產(chǎn)生種種幻覺,甚至由于小黑子 因自己而死等內(nèi)在道德焦慮而終于自殺,是典型的回溯式結(jié)構(gòu)的個人悲劇。而仇 虎對于焦閻王所代表的壓迫者的仇恨,他臨別前叮囑金子去尋找他的同伴、去追 尋遍地都是黃金的理想之地,顯然帶有“闖入式”戲劇中審判舊世界的理想主義 者的色彩。
可以看出,曹禺的“闖入式”戲劇的確指向社會問題,但是和同時代批評家 理解的“社會問題劇”又不是一回事。他最初在談到《雷雨》的寫作時,特別指 出這“絕非一個社會問題劇”,而是一首敘事詩:
我寫的是一首詩,一首敘事詩,(原諒我,我絕不是套易卜生的話, 我決沒有這樣大膽的希冀,處處來仿效他。)這詩不一定是美麗的,但是 必須給讀詩的一個不斷的新的感覺。這固然有些實際的東西在內(nèi)(如罷 工......等),但絕非一個社會問題劇。——因為幾時曾有人說“我要寫一 首問題詩”?因為這是詩,我可以隨便應用我的幻想,因為同時又是劇的 形式,所以在許多幻想不能叫觀眾接受的時候,(現(xiàn)在的觀眾是非常聰明 的,有多少劇中的巧合......又如希臘劇中的運命,這都是不能使觀眾接受 的。)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把這件事推溯,推,推到非常遼遠時候,叫觀眾 如聽神話似的,聽故事似的,來看我這個劇,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 及《尾聲》...... 25
這段自白揭示了曹禺獨特的戲劇觀與悲劇觀,塑成了他的特有的戲劇結(jié)構(gòu),難怪會招致曹禺戲劇中“觀念論壓倒社會學”,其失敗在于“性格悲劇、命運悲 劇和社會悲劇的混合”等批評。
在《雷雨》誕生的時代,劇作家和戲劇批評家受近現(xiàn)代思想影響,往往將 社會科學作為理解時代、理解戲劇的根本,將社會問題劇看作現(xiàn)代戲劇的正宗,而將命運悲劇看作社會科學誕生之前的古典戲劇的主題與形式,在這個意義上,現(xiàn)代的象征主義也可以視為古典戲劇之遺留,是落后于時代的古典戲劇的變形。蕭伯納把易卜生戲劇中的現(xiàn)代自我心理探尋和象征色彩的終極追問輕輕抹去,在闡釋中將其完全“社會問題劇”化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中國的戲劇批評家也有這 樣的傾向,要求現(xiàn)代戲劇家的創(chuàng)作完全“社會問題劇化”。張庚就這樣批評《雷雨》:“說這劇作的失敗是在于把性格悲劇,命運悲劇和社會悲劇混合在一起, 粗看似乎是對的,但仔細一想,卻恰恰相反,在現(xiàn)代的悲劇構(gòu)成上,需要的正是 混合,不,有機的統(tǒng)一,而這劇的失敗,正是因為這不是統(tǒng)一而是混合,時時現(xiàn) 出了裂痕和矛盾。”26 在張庚這里,所謂的“統(tǒng)一而不是混合”,就是將命運悲 劇、性格悲劇統(tǒng)一到社會悲劇中,命運不是不可知的而是社會的,性格不是神秘 的而是被支配命運的力所支配,進而也就是社會塑成的。
呂熒對曹禺戲劇“觀念論勝于社會學”的批評可以看作這類社會學批評的集 大成者。呂熒分析了《〈雷雨〉序》中曹禺對自己悲劇觀的闡述,他認為,曹禺 的意識根底是“二元”的,即一方面是希伯來先知的“上帝”或希臘悲劇家們的 “命運”,一方面是近代的人的“自然的法則”。前者是觀念論的,后者才是社 會學的。而在《雷雨》中,“觀念的命運的一元更強于社會學的‘自然法則’的 一元”。而《日出》雖然也是“二元的觀念的產(chǎn)物”,但是社會學的一元強于觀 念論的一元,因此是進步的。《原野》中,從仇虎結(jié)尾向金子描述他的同伴可以 看到社會學的理想,但是呂熒認為這里“對社會學的未來世界的理解”只是“純 觀念的形態(tài)”,是原始的憧憬,失去了社會的階層的特性和本質(zhì)。同樣地,《北 京人》依舊是將原始的憧憬誤作社會學的憧憬而肯定了,因此并沒有真正的社會 學的見地。27
呂熒的分析不乏真知灼見,他有理有據(jù)地指出了社會問題劇之于曹禺戲劇確 實是一頂名不副實的帽子。曹禺確乎能夠從社會問題中發(fā)現(xiàn)戲劇主題,確乎創(chuàng)造性地采用了能夠展現(xiàn)社會問題的“闖入式”戲劇模式,但他顯然并不贊同蕭伯納 “只有在問題劇中才含有真正的戲劇”的戲劇觀。郭沫若曾經(jīng)注意到《雷雨》的 “古風”:
作者所強調(diào)的悲劇,是希臘式的命運悲劇,但正因為這樣,和它的形 式之新鮮相對照,它的悲劇情調(diào)卻不免有些古風。......人生已成為黑暗的 命運之主人了。作者對于這一方面的認識似乎還缺乏得一點,因此他的全 劇幾乎都蒙罩著一片濃厚的舊式道德的氛圍氣,而缺乏積極性。就是最積 極的一個人格如魯大海,入后也不免要陰沉下去。28
不過,和那些后來徑直批評曹禺戲劇失敗于觀念論的批評家不同,郭沫若進 一步指出,這種“作者的悲劇情調(diào)之古風和他的藝術(shù)手法之新味間的矛盾正應該 是目前的悲劇社會,尤其中國的社會之矛盾一般之一局部的反映”29 。也許可以 說,以社會問題劇來要求曹禺戲劇的話,他的確在展現(xiàn)問題之后似乎就止步不前 了,沒有走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剖析和現(xiàn)實主義的典型塑造。1936年魯迅向斯 諾推薦中國最優(yōu)秀的劇作家時,特別提到“近來最受歡迎”的“一位名叫曹禺的 左翼劇作家”30 ,顯然,魯迅是統(tǒng)而言之將對社會問題的關(guān)注涵蓋在了“左翼戲 劇”的文學范疇,是在普列漢諾夫的社會學批評語境中所做的判斷,而不是用的 周揚式“透過現(xiàn)象揭示本質(zhì)”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評判方式。
郭沫若所說的曹禺的“悲劇情調(diào)之古風和他的藝術(shù)手法之新味間的矛盾”, 正如斯叢狄指出的易卜生戲劇透露出的既要遵循古典悲劇的規(guī)范,又要展現(xiàn)市民世界的結(jié)構(gòu)性矛盾。雖然易卜生戲劇寫出了人物的悲劇性死亡,但是這種個人的 悲劇性并不是市民劇的悲劇,市民世界的悲劇在于生活本身。在斯叢狄看來,易卜生、霍普特曼都在延續(xù)古典悲劇規(guī)范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性地在現(xiàn)代悲劇中塑造了現(xiàn) 代自我,觸及到了社會問題,但是在他們的戲劇結(jié)構(gòu)中同時具有內(nèi)在的矛盾,體 現(xiàn)了傳統(tǒng)悲劇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中的形式危機。呂熒批評說《原野》和《北京人》走的是現(xiàn)代歐美作家走的路,郭沫若則將《雷雨》古風的悲劇情調(diào)和新味的藝術(shù)手法 之間的矛盾看作是中國現(xiàn)代的悲劇社會所決定的,兩者褒貶不同,但是所針對的 戲劇的內(nèi)在形式危機則是一致的。
可以說,易卜生戲劇盡管經(jīng)常被扣上社會問題劇的帽子,但他的回溯性戲劇更多地呈現(xiàn)為現(xiàn)代自我的個人悲劇,霍普特曼的戲劇盡管也聯(lián)系著現(xiàn)代自我的個 體認知,但他的闖入式戲劇更多地體現(xiàn)為對社會問題的探究。這是與兩位戲劇家 所身處時代與國度的核心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易卜生早于霍普特曼半個世紀,易卜生所在的挪威和霍普特曼所在的德國比起來,其現(xiàn)代性問題的發(fā)生也較晚。但 是,曹禺所接受的戲劇理念,尤其是他所處的時代和環(huán)境,卻使他想“畢其功于 一役”,將這兩種現(xiàn)代戲劇主題統(tǒng)一到同一部戲劇中。同時,他也就創(chuàng)造性地化 用了回溯式和闖入式兩種戲劇結(jié)構(gòu),這樣,戲劇中就既包含個人悲劇,也包含社 會問題劇。而這兩個問題,確實是曹禺時代的中國最重要的問題。
不過,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問題。所謂戲劇結(jié)構(gòu),應該是統(tǒng)轄整部戲劇的 結(jié)構(gòu),在易卜生和霍普特曼等劇作家那里,他們在一部戲劇中所用的核心結(jié)構(gòu)是 唯一的。曹禺同時運用兩種戲劇結(jié)構(gòu)來表現(xiàn)兩個不同的主題,這兩者之間當然會 形成矛盾和張力,甚至使戲劇看起來有點怪,有點不自然。比如《雷雨》呈現(xiàn)了蘩漪的個人悲劇和魯大海的革命悲劇兩個重要主題,但是這兩個人之間的關(guān)系非 常松散,他們之間也沒有任何戲劇沖突。同樣地,《日出》中陳白露和方達生也 分別代表了兩個戲劇主題,但是方達生來到旅館、試圖帶走(拯救)陳白露的動機,卻顯得不夠充分。
曹禺對此并非毫無自覺,他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從兩方面解決這種形式危機:一 是弱化“回溯式”和“闖入式”戲劇的外在形式,將其內(nèi)在化,形成戲劇的雙重 隱形結(jié)構(gòu);二是將戲劇的寫成“詩”,用情感的力量和象征的手法去克服命運悲 劇、回溯式戲劇和闖入模式之間結(jié)構(gòu)性矛盾。而他的戲劇詩的悲劇觀念,既有易 卜生的元素,也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的象征色彩,梅特林克的“靜的戲劇”的 成分。關(guān)于曹禺戲劇詩和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的關(guān)系,因篇幅所限這里 不再贅述,只簡單談一談其與梅特林克的“靜的戲劇”的關(guān)聯(lián)。
曹禺在談到《雷雨》的序幕和尾聲時說希望由此使觀眾恢復平靜,這和亞里 士多德所說的悲劇的凈化并不是一回事,因為凈化是由恐懼、震驚而升華,但曹 禺卻希望觀眾漸漸平靜而哀傷。亞里士多德強調(diào)的是“憐憫與恐懼”,曹禺卻不 要觀眾受“驚嚇”,只想送看戲的人們“帶著一種哀靜的心情”回家:
這劇收束應該使觀眾的感情又恢復到古井似的平靜,但這平靜是豐富 的,如秋日的靜野,不吹一絲風的草原,外面雖然寂靜,我們知道草的下面,翁翁叫著多少的爬蟲,落下多少豐富的谷種呢。31
梅特林克有一篇著名的《日常生活的悲劇性》,試圖揭橥日常生活中的悲劇因素作為現(xiàn)代戲劇的本質(zhì),而且特別用到一個靜默地坐在扶手椅上的老人的形象:
日常生活中有一種悲劇性,它比巨大的冒險事件的悲劇性遠為真實、 遠為深刻、遠為符合我們真正的存在。很容易感覺到它,但把它表現(xiàn)出來 卻并非易事,因為這種基本的悲劇性并不單純是物質(zhì)方面或心理方面的。這和人與人之間的特定斗爭、兩種愿望之間的斗爭或激情與責任之間的永 恒斗爭無關(guān)......
一個老人坐在扶手椅里,在燈下默默地等待著,不自覺地聽取籠罩著他的家 的永恒法則,雖不明白卻解釋著在門窗的寂靜和光亮的微聲中隱含的東西,感受 著他的靈魂和命運的存在,稍稍耷拉著頭,沒有感覺到人世間的一切強有力的東西悄然而至......有時我這樣想,這個默然不動的老人所經(jīng)歷的生活實際上比情人 扼死他的女友,將領(lǐng)取得一次勝利或者“丈夫為他的榮譽報仇”更為深廣、更具 有人情味、更有普遍意義。32
這個生活經(jīng)歷“更為深廣、更具有人情味、更有普遍意義”的坐在扶手椅上 的老人,不知怎的,令人想起《雷雨》尾聲中“坐在爐旁的圈椅上”“呆呆地望 著火”的周樸園。
小結(jié)
曹禺的四部重要劇作中只有《雷雨》標明是悲劇,但《日出》《原野》《北 京人》中依舊彌漫著濃厚的悲劇氛圍,并且以主人公(之一)的死亡作為結(jié)束。在曹禺的戲劇觀中,“悲劇”無疑占據(jù)了中心的位置,他也曾專門以“悲劇的精 神”為題作過演講。在他的悲劇創(chuàng)作中,回溯式的隱形結(jié)構(gòu)能夠體現(xiàn)個人歷史和 復雜心理,能夠容納現(xiàn)代的個人悲劇(蘩漪、陳白露等),闖入式的隱形結(jié)構(gòu)能 夠更多地展現(xiàn)社會問題,對于腐敗的舊世界、惡社會加以審視與批判,能夠容納 現(xiàn)代的社會悲劇(魯大海、仇虎、方達生等)。這雙重隱形戲劇結(jié)構(gòu)之間既互相補充和支撐,又充滿著矛盾和張力,曹禺力圖用“哀靜的詩”來統(tǒng)轄這兩者, 從而將個人悲劇與社會悲劇統(tǒng)一起來。同時,他在不同的戲劇中,分別運用了 整體上外在的鎖閉式結(jié)構(gòu)(《雷雨》《原野》)和開放式結(jié)構(gòu)(《日出》《北 京人》),又運用了序幕與尾聲(《雷雨》)、題記(《日出》)、象征主義 (《原野》《北京人》)、人像展覽式(《日出》《北京人》)等獨特的結(jié)構(gòu)形 式,進而將易卜生的回溯式和霍普特曼的闖入式兩種不同的戲劇結(jié)構(gòu)內(nèi)在化、隱形化,形成獨特的曹禺式戲劇。從《雷雨》到《北京人》,曹禺戲劇的結(jié)構(gòu)越來 越成熟,越來越具有個人的風格,而這雙重隱形結(jié)構(gòu)及其背后的雙重悲劇主題始 終貫穿著他的戲劇。
易卜生、斯特林堡、梅特林克和霍普特曼的戲劇代表的是西方戲劇的現(xiàn)代 危機,他們用回溯式分析戲劇和闖入式結(jié)構(gòu)來納入新的內(nèi)容,突破了古典悲劇的 結(jié)構(gòu),也改變了以沖突為戲劇本質(zhì)的古典戲劇內(nèi)涵,或者說將“沖突”的內(nèi)涵改 變了方向。作為中國現(xiàn)代悲劇的創(chuàng)造者的曹禺來說,他要同時面對西方現(xiàn)代戲劇 一百年來觸及到的不同層面的現(xiàn)代悲劇主題,這也是后發(fā)展的現(xiàn)代中國的真實現(xiàn) 狀。曹禺有雄心和勇氣,以戲劇形式把握這個時代的中國和中國人,他也的確開 創(chuàng)了屬于自己的戲劇形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的現(xiàn)代戲劇之路。
注釋:
1 [蘇]E. 霍洛道夫《戲劇結(jié)構(gòu)的兩種類型》(李明錕譯,《戲劇藝術(shù)》1980年第4期) 和周端木《戲劇結(jié)構(gòu)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0頁)都把鎖閉式和開放式 作為戲劇史上最重要的兩種結(jié)構(gòu)類型。在《戲劇結(jié)構(gòu)論》的附錄《論戲劇結(jié)構(gòu)》中, 周端木把曹禺的《雷雨》視為鎖閉式結(jié)構(gòu)的典型戲劇。2 顧仲彝:《論劇本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戲劇藝術(shù)》1978年第2期。
3 16 [美]J. H. 勞遜:《戲劇與電影的劇作理論與技巧》,邵牧君、齊宙譯,中國電影出 版社1989年版,第147、221頁。
4 11 焦菊隱:《論易卜生》,原載1928年3月20—28日北京《晨報》副刊,北京人民藝術(shù) 劇院戲劇博物館編《焦菊隱文集》第1卷,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5 劉紹銘:《〈雷雨〉所受的西方文學的影響》,《小說與戲劇》,臺北洪范書店1977 年版,第117頁。
6 余上沅:《易卜生的藝術(shù)》,原載1928年5月《新月》第1卷第3期,陳惇、劉洪濤主編 《現(xiàn)實主義批判:易卜生在中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1頁。
7 田本相、劉一軍:《曹禺訪談錄》,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頁。
8 9 10 [德]彼得·斯叢狄:《現(xiàn)代戲劇理論(1880—1950)》,王建譯,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6年版,第21~22、30~32頁。
12 23 劉西渭(李健吾):《〈雷雨〉——曹禺先生作》,天津《大公報》1935年8月31日。23 萬家寶(曹禺):《〈爭強〉序》,崔國良編《曹禺早期改譯劇本及創(chuàng)作》,遼寧大 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9頁。
14 胡適:《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56頁。
15 原文為:“...it will be seen that only in the problem play is there any real drama, because drama is no mere setting up of the camera to nature: it is the presentation in parable of thecon ict between Man’s will and his environment: in a word,of problem.”(Bernard Shaw,Preface of Mrs Warren’s Profession,Plays of Unpleasant, Penguin Book, 1981, p.197.[英] 蕭伯納:《〈華倫夫人之職業(yè)〉序》,《不愉快的戲劇》,企鵝出版社1981年版,第 197頁。
17 [德]赫卜特曼(霍普特曼):《日出之前》(五),耿濟之譯,《小說月報》1925 年第16卷第12期。
18 27 呂熒:《曹禺的道路》(上),《抗戰(zhàn)文藝》1944年第9卷第3—4期。
19 [瑞典]斯特林堡:《斯特林堡文集》第5卷,李之義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 第122頁。
20 [德]葛哈特·霍普特曼:《沉鐘》,李永熾譯,遠景出版事業(yè)公司1981年版,第 39、114頁。
21 參見[英]雷蒙·威廉斯《現(xiàn)代悲劇》第二部分第一節(jié),丁爾蘇譯,譯林出版社2007 年版。
22 [美]尤金·奧尼爾:《奧尼爾論戲劇》,劉海平譯,《奧尼爾文集》第6卷,人民文 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頁。
24 曹禺:《北京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版,第155、156頁。
25 31 曹禺:《〈雷雨〉的寫作》,《質(zhì)文》1935年第2號。
26 張庚:《悲劇的發(fā)展——評〈雷雨〉》,《光明》(上海)1936年第1卷第1期。
28 29 郭沫若:《關(guān)于曹禺的〈雷雨〉》,原載《東流》(日本東京)1936年第2卷第4期, 王興平、劉思久、陸文璧主編《曹禺研究專集》(上),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 544、545頁。
30 [美]斯諾整理《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安危譯,《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
32 [比利時]莫·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財富》,鄭克魯譯,《文藝理論研究》1981年 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