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別爾嘉耶夫的原著,重新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

二十世紀初我國開始譯介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由于我們的訴求與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訴求基本吻合,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別、車、杜對他的社會學、階級論的評價,強調(diào)他的人道主義思想與感情,把他視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階級的代言人,注重的是其創(chuàng)作的社會現(xiàn)實題材,而忽略了其表達的宗教的、哲學的思想。這一接受傾向持續(xù)了近半個世紀。對他的宗教、哲學思想的認識,在1947年耿濟之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譯者前記”中剛剛顯現(xiàn),就隨著整個國家意識形態(tài)新階段的到來而中止,“并沿社會學評價的方向越走越遠”。[1]
從五十年代開始,由于《群魔》中對革命者形象的“歪曲”而將其定為反動作家,對他的譯介與研究在中國大陸完全停止,直到八十年代才重又恢復。此后,由于文學批評思想與方法的多樣化,對他的研究日漸豐富與深入,其中也開始關注他的宗教、哲學思想,如挖掘其作品中的圣經(jīng)原型,分析他的宗教心理來源及與俄羅斯宗教文化的關系,研究其作品的宗教理念下的詩學原則,探討他的原罪說、救贖論、苦難說、末世論等等。然而,這些零星的研究似乎揭示了什么,又似乎遮蔽了什么,總顯得意猶未盡。究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學思想為何,我們似乎還沒有能力完全揭示清楚。同時,我們也發(fā)現(xiàn),即便已有的對其宗教、哲學思想的認識,也多是借鑒了國外學者的論述。其中,一批俄國宗教哲學家、文論家的著述成為我們主要的思想資源。
韋勒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評論史概述》一文中指出,俄國宗教哲學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是真正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的第一人。其實,在梅氏之前,弗·索洛維約夫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講話,稱他是“上帝的先知”,羅贊諾夫的《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傳說》認為宗教思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的核心。然而,無論是梅氏,還是索氏與羅氏,都沒能系統(tǒng)地呈現(xiàn)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世界觀的全貌,集大成者是別爾嘉耶夫,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中集中闡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我國較多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的研究成果,如趙桂蓮的《漂泊的靈魂》、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語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何懷宏的《道德·上帝與人》等,也都大量引用了別爾嘉耶夫的該著作。因此,我們有必要回到別爾嘉耶夫的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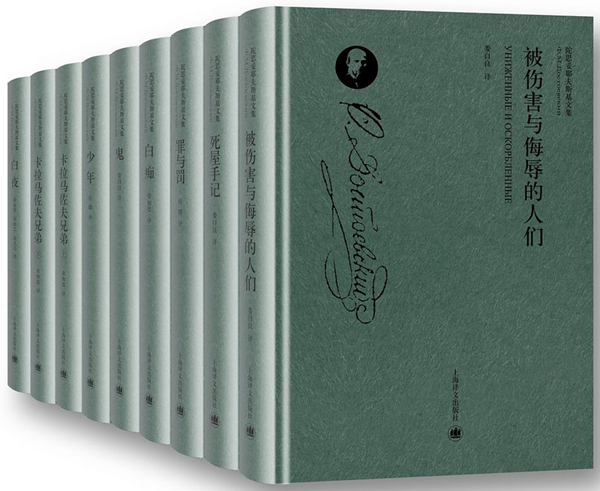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5月版
別爾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于1923年在布拉格首次出版,它凝聚了別爾嘉耶夫許多年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間斷的思考,因為在此之前,他寫有《大法官》(1907)、《斯塔夫羅金》(1914)、《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中關于人的啟示》(1918)、《俄羅斯革命的精神實質(zhì)》(1918),并于1921年至1922年間在“宗教文化民間學會”作了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系列講座,最終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結集出版。這期間正是別爾嘉耶夫的哲學觀形成、發(fā)展、成熟的重要階段。他從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發(fā),形成了自己世界觀的基本面貌。他說:“我不僅試圖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并且也融進許多我個人的世界觀。”[2]別爾嘉耶夫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的關系,正如有學者認為巴赫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的關系一樣,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造了“對話理論”與“復調(diào)小說”,而是巴赫金根據(j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詩學,應該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為《巴赫金的詩學》;也可以說,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造了“自由哲學”,而是別爾嘉耶夫根據(j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自由哲學”,表達了自己的世界觀,可以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為《別爾嘉耶夫的世界觀》(在俄羅斯學者中正有這說法)。然而,無論是“六經(jīng)注我”,還是“我注六經(jīng)”,如果說巴赫金從詩學角度成功闡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那么,別爾嘉耶夫則從宗教哲學角度成功闡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如果將這幾乎是前后問世的(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初稿1929年問世,時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問題》)研究成果結合起來看,則相得益彰,近乎完美互補,算是俄羅斯本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雙峰齊立。
我們在閱讀與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的時候,有三個背景因素應當考慮:一是社會歷史的因素。時值俄國十月革命前后的劇烈動蕩時期。這期間發(fā)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一起決定了這一時代的災難意識。二是思想、精神或曰哲學因素。這一時期,哲學的許多問題都發(fā)生了劇烈變化。面對現(xiàn)代性的各種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他的方法和原則成了這一時代的精神源泉。三是個人經(jīng)歷因素。在自己世界觀形成過程中,別爾嘉耶夫始終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自己所有哲學、歷史、倫理、美學思想的基礎。同時,在哲學批評傳統(tǒng)中,別爾嘉耶夫始終認為與自己有著血緣關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許正是因著精神上的血緣關系,這一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專著才具有了區(qū)別于別爾嘉耶夫所有其他哲學著作的顯著特征:即整個文本充滿了熱烈的火一般的激情。他還沒有哪一本哲學著作寫得如此熱烈灼人。這是一部鮮活、具體、形象的,而非呆板、玄奧、抽象的,熱烈、激情、充滿靈感的,而非冷靜、理智、遍布推論的哲學著作。盡管別爾嘉耶夫說自己的著作不是文學批評,可它們絲毫不亞于任何文學批評,甚至文學批評也沒有如此的激情四射。我們有理由稱之為形而上的文學批評。也許正是從該書的文風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別爾嘉耶夫?qū)ν铀纪滓蛩够膿磹郏杏X到他們同樣的血的沸騰,感覺到他們在狄奧尼索斯式的激烈性情上的相似。激情是這一著作的顯著特征之一:在其他所有著作中壓抑的激情,在這里綻放了。俄羅斯學者謝·阿·吉塔連科在其專著《尼·別爾嘉耶夫》[3]中指出別爾嘉耶夫的激情與哲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認為,別爾嘉耶夫遺傳了父系傳下來的可能導致病態(tài)的非理性的激情因子,這種基因有可能導致他極度興奮而不能自控激情。因此,他把理性的哲學作為與自己激情的自發(fā)力量斗爭的工具。關于斗爭的結果,別爾嘉耶夫曾寫到,在他身上“壓抑了抒情的自發(fā)力量”,而使自己的精神風景呈現(xiàn)為一片無水的荒漠中的懸崖峭壁。吉塔連科在別爾嘉耶夫的精神發(fā)展歷程中看到了這樣的變化:年輕時,激情昂揚充沛時,他更多的把自己對世界的感受納入某種思想框框,而近老年時,激情有所減退,他把對世界的感受表現(xiàn)得更具激情。吉塔連科的分析角度很有意思。但不管哲學是不是別爾嘉耶夫用來與自己的激情斗爭的工具,我們至少知道他是具有暴躁、無常、激情的基因的(這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太相似了),而且這些特點若隱若現(xiàn)地沉浮于其哲學著作中,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中,當面對他摯愛的、如此親近的、有著精神上血緣關系的他的精神之父陀思妥耶夫斯基時,這一激情終于無法抑制地爆發(fā)了,宣泄了出來。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把讀者拽進激情的旋風之中。1920年至1921年間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的時候,他已將近半百,按照吉塔連科的說法,別爾嘉耶夫也到了該抒發(fā)自己的激情的年紀了。不過,我認為,激情是否能宣泄出來,是直接與寫作對象、寫作題材有關的。
我們之所以認為該著作可以稱為“形而上的文學批評”,是因為他在書中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個創(chuàng)作的定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是“思想的藝術”。也就是說,他首先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當作“藝術作品”來看待,而不像其他哲學家那樣視之為哲學著作,而且,這個“思想”不僅是“一種有機的生命”,而且還有“自己活生生的命運”,他認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中“起著巨大的核心作用”。別爾嘉耶夫這里說的“思想”的巨大的核心作用,不是通常說的作品以某個思想為核心展開藝術創(chuàng)作,而是“思想”本身就構成情節(jié),構成悲劇的張力,構成整個藝術作品發(fā)展的動力和源泉,形而上的思想構成整個藝術的內(nèi)在魅力,它使所有人物都運動甚至瘋狂起來,追趕著整個情節(jié)跌宕起伏,形成強大的沖擊力;是思想帶來的激情,是思想的利刃把人物逼向最極端的境地,把人物推向悲劇的最高峰。別爾嘉耶夫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是藝術地解決思想主題,是思想的悲劇式運動。地下室的主人公——是思想,拉斯柯爾尼科夫——是思想,斯塔夫羅金、基里洛夫、沙托夫、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是思想,伊萬·卡拉馬佐夫——是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都專注于某種思想,沉醉于某種思想。他小說中的所有對話,都是驚人的思想的辯證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寫的一切,都是關于世界的‘該死的’問題的。這毫不意味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為了貫徹某種思想而寫一些片面的論題式小說。思想完全內(nèi)在于他的藝術,他藝術地揭示思想生命。”[4]別爾嘉耶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這一抽象的詞角色化,“思想”就仿佛一個人物那樣出場,具有鮮活的生命。他整個的藝術,就是“思想”的藝術,它的誕生,它的道路,它的毀滅。別爾嘉耶夫與當時唯美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時髦”相悖,特別強調(diào)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這似乎有點十九世紀陳舊的社會學批評之嫌,但事實上,完全不是別林斯基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道主義思想”,而是關于人的本質(zhì)、人的精神深度、人的精神命運、人與上帝的關系、人與魔鬼的關系的思想。
我們之所以稱其著作為“形而上的文學批評”,還因為它對文學史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有的定位具有顛覆意義。在別爾嘉耶夫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論述中,有一個根基性問題,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是一位現(xiàn)實主義者。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不是現(xiàn)實主義者,而是象征主義者。他認為,偉大的和真正的藝術不可能是現(xiàn)實主義的,真正的藝術都是象征的——它標明一個更為深刻的真實,它總是穿越到另一個世界。別爾嘉耶夫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真實的不是經(jīng)驗的事實、表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實、生活秩序的事實、帶著泥土味的人的事實;真實的是人的精神深度、人的精神命運、人與上帝的關系、人與魔鬼的關系……那些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最深刻的主題的人的精神分裂,并不受制于事實性的敘述”。[5]他說,伊萬和斯麥爾佳科夫之間的關系,使伊萬本人的兩個“我”得以揭示,而這并不能被稱為“現(xiàn)實主義的”。伊萬與鬼之間的關系,更不是現(xiàn)實的。別爾嘉耶夫認為,“聯(lián)系人們的不僅僅是那些在意識之光的照耀下顯而易見的關系和制約,還存在更為隱秘的關系和制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們之間所有復雜的沖突和相互關系,揭示的不是客觀對象的、“現(xiàn)實的”真實,而是人們內(nèi)在的生活和內(nèi)在的命運。在人們這些沖突和相互關系中揭開人之謎,人的道路之謎。所有這一切,鮮有與所謂“現(xiàn)實主義的”小說類似的。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可能是心理學的現(xiàn)實主義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不是心理學家;他作為一個精神現(xiàn)象,意味著一種內(nèi)在的轉折,轉向人的精神深度,轉向精神體驗,他使人穿越混沌的“唯物主義的”和“心理的”現(xiàn)實,他是“靈魂學家和象征主義者-形而上學者”。
我們知道,別林斯基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道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高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也許,從“人道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到“更高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再到別爾嘉耶夫的“形而上的象征主義”,我們是在一步步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別爾嘉耶夫的“形而上的象征主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論斷,改寫了文學史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定位。
二
如果說巴赫金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的關鍵詞是“復調(diào)”“對話”“多聲部性”“未完成性”等,那么別爾嘉耶夫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的關鍵詞是“人”“自由”“惡”“愛”“革命”“神人和人神”等,且所有這些詞都具有宗教哲學而非社會學的含義。
人 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創(chuàng)作關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除了人,別無他物”,“他為之獻出自己所有的創(chuàng)作力量”。[6]他認為,相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更多是一位“神學家”,他更關心“上帝”的問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關心的是“人”的問題,他是一位“人學家”,但這個“人”,是處于“人與上帝”關系中的“人”,他是“宗教人學家”。在已有的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還沒有誰把“人”字如此赫然地凸顯地推到我們面前。韋勒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評論史概述》[7]對一個半世紀以來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進行了分析,指出,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皮薩列夫關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義精神,民粹派的米哈伊洛夫斯基稱其是“殘酷的天才”,法國的德·沃蓋伯爵認為他的主要作品“可怕”而且“不堪卒讀”,法國青年批評家埃米爾·埃納昆看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摒棄理性、歌頌瘋狂白癡和低能,著名的喬治·勃蘭兌斯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揚賤民和奴隸道德,尼采從他那里學到的是犯罪的心理、奴隸的精神狀態(tài)、仇恨的本性,舍斯托夫只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災難和啟示錄式的幻象,高爾基抨擊他是“俄國的罪惡的天才”,喬治·盧卡奇用簡單的二分法來對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情心和思想意識,維·伊萬諾夫強調(diào)的是他作品中的神話成分,紀德看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學、多義性和非決定論等等。可以看出,唯獨“人”的主題,人、人的命運的主題沒有被明確提出來。只有在別爾嘉耶夫這里,“人”的主題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寫的主題浮現(xiàn)了出來。別爾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第一章就以“人”為題目進行了論述,指出,從《地下室手記》之后,人,人的命運就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興趣的絕對對象,而這不僅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理念,也是他創(chuàng)作的藝術原則。別爾嘉耶夫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敘述結構,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結構中有一個巨大的中心。一切人和事都奔向這個中心人物,或這個中心人物奔向所有的人和事。這個人物是一個謎,所有的人都來揭開這個秘密。”[8]《少年》中的韋爾西洛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萬都是這樣的中心,《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也是類似的人物。別爾嘉耶夫認為,在他們不同尋常的命運中,掩蓋著人一般的秘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們幾乎沒有別的‘事情’可干”,最嚴肅的、唯一嚴肅的“事情”就是揭開人的秘密,人高于一切“事情”,人就是唯一的“事情”。同時,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都是對人性的實驗,是對在自由之中的人的命運和在人之中的自由的命運的發(fā)現(xiàn)。
由此別爾嘉耶夫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自由”的思想。
自由 別爾嘉耶夫強調(diào)指出:“人及其命運的主題,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首先是自由的主題”,“自由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觀的核心”。[9]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內(nèi)心最深處的激情是自由的激情,而直到現(xiàn)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一點還沒有被充分意識到。別爾嘉耶夫指出,在《地下室手記》中揭示的是人的非理性,但這一非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非被造”的自由的本性。“地下室人”的非理性,決定了拉斯柯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伊萬·卡拉馬佐夫等人的命運,從此,人開始了在自我意志的自由之路上痛苦的徘徊、流浪,伊萬·卡拉馬佐夫是自由之路的最后一個階段,走向了自由意志和反抗上帝。
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樣看待這一自由意志和反抗上帝的。自由意志“保留了我們最主要的和最寶貴的東西,即我們的人格和我們的個性”[10]——這是地下室人的話,但同時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人的自由之路的悲劇的辯證法:這個自由意志和反抗會導致扼殺人的自由,瓦解人的個性。別爾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在自我意志中自由怎樣被消滅,在造反中人怎樣被否定,拉斯柯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基里洛夫、伊萬·卡拉馬佐夫即是證明;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深深知道人神的誘惑,他讓自己的所有人物都走過了人神之路,正是這樣,人神的謊言在無限的自由之路上被揭穿了,在這條路上,人找到的是自己的終結和死亡。在伊萬·卡拉馬佐夫之后,出現(xiàn)了佐西馬和阿廖沙的形象,并且,關于人的自由的悲劇的辯證法是以《傳說》中的基督形象結束的。這也就是說,人,經(jīng)由無限的自由,發(fā)現(xiàn)了通向基督的道路——神人之路,在這條路上,人找到的是自己的得救和對人的形象的最終肯定。只有基督拯救人,守護人的形象。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面的關于自由的宗教思想就在于此。這一關于自由的悲劇的辯證法就是關于人、人的命運的辯證法。
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的“殘酷性”都與他對自由的態(tài)度有關,他不愿意卸下人的自由之重負,不愿意用失去自由的代價來換取人免于痛苦。即便是善、真理、完美、幸福,也不應以自由為代價來換取,而應當是自由地接受;即便是對基督的信仰,也應當是人自由地接納基督。“自由地接納基督——這是基督徒全部的尊嚴,是信仰,也是自由的全部意義。”不能把自由與善、與真理、與完美、與幸福混為一談。自由有自己獨特的屬性,自由就是自由,而不是善。所有的混淆自由與善,混淆自由與完美,都是對自由的否定。強迫的善已經(jīng)不是善,它可以再生惡。自由的善,這是唯一的善,它以惡的自由為前提。自由的悲劇就在于此。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人物走過的道路展示的正是這樣一個過程,他向人提供了一條自由地接受真理的道路:人具有“非被造”的自由,但自由消解了自身,走向自己的反面,轉化為自我意志,轉化為人反抗式的自我肯定;自由成為無目的的、空洞的自由,它使人變得空虛。斯塔夫羅金和韋爾西洛夫的自由就是這樣無目的的和空洞的;自由的個性瓦解和腐化了斯維德里蓋洛夫和費奧多爾·巴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自由使拉斯柯爾尼科夫和彼得·韋爾霍文斯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基里洛夫和伊萬·卡拉馬佐夫惡魔般的自由殺死了人。這里,自由,作為自我意志,瓦解并斷送了人。人應當走自由之路,但當人在自己自由的恣意妄為中不想知道任何高于人的東西時,如果一切都是許可的,自由就轉化為奴役,自由就毀滅人。如果沒有任何高于人本身的東西,就沒有人。如果自由沒有內(nèi)容,沒有目的,沒有人的自由與神的自由的聯(lián)系——沒有對高于人本身的上帝的信仰,那么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拉斯柯爾尼科夫和斯塔夫羅金,基里洛夫和伊萬·卡拉馬佐夫的命運都證明了這一真理。但是,就是“信仰”,也應當是自由地去信仰。別爾嘉耶夫認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創(chuàng)作頂峰《宗教大法官的傳說》中的基督形象揭示的正是這一深刻思想。基督拒絕了“奇跡、神秘和權威”,這些都是對人的良心的強迫,是剝奪人精神的自由。任何人不能強迫人的良心信仰基督。各各他的宗教是自由的宗教。上帝的兒子,以“奴仆的形象”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受盡世間磨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形象中,沒有任何強制,沒有以“奇跡、神秘和權威”的強力使人信仰他。他不是統(tǒng)治這個世界的強力。別爾嘉耶夫認為,正是這里隱藏著基督教最主要的秘密,自由的秘密——基督是給予自由的人,基督教是自由的宗教,真理不是強制的真理。人精神的自由,宗教良心的自由,是基督教真理的內(nèi)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拉斯柯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基里洛夫、韋爾西洛夫、伊萬·卡拉馬佐夫都在經(jīng)歷“懷疑的大熔爐”之后,從他們精神的深處,從他們自由的良心深處響起了彼得的話:“你——基督,上帝活著的兒子。”
但是無論如何,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惡(包括犯罪)的問題,誰對惡負責的問題,必須面對伊萬的“不是不接受上帝,是不接受存在著惡、存在著嬰孩無辜的眼淚的世界”的問題。
惡 別爾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發(fā)現(xiàn)了一種獨特的、與眾不同的對待惡的態(tài)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惡的問題是這樣提出并解決的:自由之路會轉化為自我意志,自我意志會導致惡,惡會導致犯罪,犯罪內(nèi)在地不可避免地導致罰。實質(zhì)上,罪與罰的問題就是惡和對惡負責的問題。別爾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同對待惡的膚淺的、表面的態(tài)度作斗爭,反對以社會環(huán)境來膚淺表面地解釋惡和犯罪并在此基礎上否定罰。陀思妥耶夫斯基痛恨這種正面的、積極的人道主義理論,他在其中看到了對人性深度的否定,對人的精神自由以及與自由相關的責任的否定。他準備捍衛(wèi)最嚴酷的懲罰,把它作為對自由應負有責任的人的相應屬性。以人的尊嚴的名義,以人的自由的名義,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了對各種犯罪的懲罰之不可避免性。這種懲罰需要的不是外在的法律,而是來自人自由的良心的最深處。惡是人具有內(nèi)在深度的標志。由此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待惡的態(tài)度是極端悖論的。惡就是惡。惡的本性——是內(nèi)在的、形而上的,而不是外在的、社會的。人,是一個自由的存在。自由是在上帝控制之外的人的本性,它是非被造的、非理性的,因此,自由既創(chuàng)造善,也創(chuàng)造惡。惡出現(xiàn)在自由的道路上。沒有自由,惡就無法解釋,沒有自由,上帝就要對惡負責。但如果因為它可以產(chǎn)生惡,就拒絕自由,那將意味著產(chǎn)生更大的惡。人作為一個自由的存在,對惡負責。由惡而來的罪應當被罰。但是,惡還是人的道路,人悲劇的道路,是自由人的命運,是同樣可以豐富人,帶人走向更高的臺階的體驗。但是別爾嘉耶夫提醒人們,這個真理是危險的,它應當避開精神幼稚的人。任何有為了“豐富自己,需要走惡之路”想法的,都是奴隸式的和幼稚的人;認為人可以有意識地走惡之路,為的是得到更多的滿足,隨后在善中取得更大的成就——這是發(fā)瘋了。惡之中的自我滿足即死亡。
可以看出,惡的問題與罰的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同時,罰的問題,也就是贖罪的問題和復活的問題。惡的經(jīng)驗,可以豐富人,可以使意識更為敏銳,但為此需要經(jīng)歷磨難,需要經(jīng)歷地獄之火;苦難之路,可被認為是對人的惡的罰,它可以贖罪,可以焚燒罪惡。只有通過苦難人才可以上升,別爾嘉耶夫認為,這一思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學非常本質(zhì)的特征。苦難也是人的深度的標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苦難之于贖罪與復活的力量。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苦受難之宗教”的基礎,也是他對惡與苦難的肯定根源所在。由自由產(chǎn)生的惡毀滅了自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贖罪恢復人的自由,還人以自由。別爾嘉耶夫發(fā)現(xiàn),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所有小說中引領人走過的正是這個精神過程,走過自由、惡和贖罪。佐西馬長老和阿廖沙被塑造成認識了惡并走向更高境界的人。在阿廖沙身上有著卡拉馬佐夫家族的惡的元素,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構思,阿廖沙是一個經(jīng)過了自由體驗,走向了精神復活的人。
與惡的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的罪的問題還是一個宗教道德問題,是一個“是否一切都允許”的問題。別爾嘉耶夫發(fā)現(xiàn),“一切都允許嗎”這一問題一直折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問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呈現(xiàn)出不同形式:《罪與罰》寫的是這個,相當程度上《群魔》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寫的也是這個。別爾嘉耶夫認為,罪的問題,這同樣是人的自由體驗的問題。當人走上自由之路,一個問題就擺在了人面前:人的天性中有沒有道德界限?人是否敢于做任何事情?一個自命不凡的人,自認為肩負著為人類服務的使命的人,可不可以殺死最無足輕重的可憎的老太婆,可不可以殺死妨礙了“革命”的沙托夫,可不可以殺死最為罪惡的費奧多爾·卡拉馬佐夫?
在《罪與罰》中,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自由已經(jīng)轉化為自我意志,他認為自己是人類中被揀選的那部分人,肩負著使人類幸福的使命,為此,他認為,一切都是允許的。于是他去檢驗自己的力量。但是,《罪與罰》通過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精神歷程以驚人的力量表明,在越過了具有類上帝的人性所允許的界限之后,在體驗了自己的自由的極限和自己的力量的極限之后,出現(xiàn)了可怕的后果。拉斯柯爾尼科夫殺死的不是“微不足道的”和罪惡的老太婆,而是自己。“犯罪”之后——這本是一次純潔的實驗——他失去了自由,被自己的無力壓垮。他明白了,殺死一個人輕而易舉,這個實驗并不困難,但它不能給人以任何力量,反而使人失去精神力量。任何“偉大的”“非凡的”世界的意義(按照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說法)也沒有因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而產(chǎn)生。他被發(fā)生的“微不足道”的事件所擊潰。在經(jīng)歷了內(nèi)在的艱難體驗后,經(jīng)驗告訴他,不是一切都允許的,因為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具有絕對的意義。人所具有的精神性不允許以自我意志殺死哪怕最壞的、最為罪惡的人。人以自我意志消滅另一個人,他也就消滅了自己。任何“思想”,任何“崇高的”目的都不能為對待即使最為罪惡的人的那樣一種態(tài)度辯護。所有的人類生命,比未來人類的幸福,比抽象的“思想”更珍貴。這就是基督教的意識,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這一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臆斷,拉斯柯爾尼科夫自行解決能
否以自己“思想”的名義殺死哪怕最壞的人的問題。但這一問題的解決不屬于人,而屬于上帝。以自己的意志解決這一問題的人,殺死他人,同時也殺死自己。別爾嘉耶夫認為,《罪與罰》的意義就在于此。這是在上帝面前的“罪”。
在《群魔》中是自我意志轉化為無神論的個人主義思想和無神論的集體主義思想的嚴重后果。彼得·韋爾霍文斯基認為,以自己“思想”的名義,一切都是允許的。與拉斯柯爾尼科夫相比,這里,人的毀滅已經(jīng)走得更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了“思想”本身、最終目的本身的轉化和蛻變,它們最初都是多么崇高而迷人,最終卻是走向暴虐殘酷;人性中產(chǎn)生了道德上的白癡,失去了善與惡的一切標準,形成了一種駭人的氛圍,充滿了血腥和殺戮。沙托夫的被殺令人震驚。在彼得·韋爾霍文斯基身上,人的良心——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還存在的良心,已經(jīng)徹底粉碎,他已經(jīng)不會懺悔,已經(jīng)瘋狂到了極點。因此,在別爾嘉耶夫看來,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屬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那一類形象,這些人未來已經(jīng)不再有人的命運(五人小組的人不是自首就是被捕,都有結局,唯有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是消失,作者沒有任何交代,這是否就是一種象征——是沒有未來命運的)。別爾嘉耶夫發(fā)現(xiàn),斯維德里蓋洛夫、費奧多爾·巴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斯麥爾佳科夫、永遠的丈夫,都屬于這樣的人。但是,拉斯柯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基里洛夫、韋爾西洛夫、伊萬·卡拉馬佐夫還有未來,盡管從經(jīng)驗上講他們已經(jīng)死亡,但他們還有人的命運。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沉迷于虛假的思想而失去了人的形象。他從反面證明不是一切都允許的,如果允許,人就將成為人神,人的神化將消滅人性。這也是在上帝面前的“罪”。
而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萬·卡拉馬佐夫并沒有殺死父親,殺人的是斯麥爾佳科夫。但伊萬自己潛意識中希望父親死,并慫恿了斯麥爾佳科夫,鼓勵了他的犯罪意志,所以良心的痛苦使伊萬瘋了。還有米卡·卡拉馬佐夫,他同樣沒有實施弒父,但他說過“那樣的人活著干什么”,所以他認為自己是以這種方式在自己的精神深處完成了弒父。因此,他平靜地接受法律的懲罰,借此贖自己的罪。這種良心的煎熬也說明不是一切都是允許的。
如果說《罪與罰》是個人層面上面對上帝的“罪”,那么《群魔》就是社會層面上面對上帝的“罪”,《卡拉馬佐夫兄弟》則是意識層面上面對上帝的“罪”。別爾嘉耶夫?qū)訉由钊氲亟沂境鐾铀纪滓蛩够髌分刑N含的關于“罪”的深刻思想。
愛 關于愛,別爾嘉耶夫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愛情,發(fā)現(xiàn),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中愛情占據(jù)了重要的地位,但這卻不是獨立的地位;愛不具有自身的價值,不具有自身的形象,它僅僅揭示人的悲劇之路,是人的自由體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愛情的位置完全不同于普希金的塔吉雅娜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愛情的位置。這里的女性因素完全是另外一種狀況。女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中沒有獨立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學是絕對的男人的人學。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女人的關注,完全是把女人作為男人命運中的因素,作為人的道路上的因素來關注的。人的靈魂首先是男人的靈魂。女性因素只是男人精神悲劇的內(nèi)在主題、內(nèi)在誘惑。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我們塑造了什么樣的愛情?是梅什金和羅果仁對娜斯塔霞·菲里波夫娜的愛,是米卡·卡拉馬佐夫?qū)Ω耵斏昕ǖ膼郏琼f爾西洛夫?qū)θ~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的愛,是斯塔夫羅金對許多女人的愛。這里,任何地方也沒有美好的愛情形象,任何地方也沒有具有獨立意義
的女性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只有一個主題——人悲劇的命運,人自由的命運。愛情只是這一命運的一個因素而已。但命運只是拉斯柯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基里洛夫、梅什金、韋爾西洛夫以及卡拉馬佐夫家族的伊萬、德米特里和阿廖沙的命運,而不是娜斯塔霞·菲里波夫娜、阿格拉雅、麗莎、葉里扎維塔·尼古拉耶夫娜、格魯申卡和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的命運。總是男人的悲劇命運在折磨著人。女人只是男人的內(nèi)在悲劇。女人只是這一命運中碰到的難題,她只是男人命運的內(nèi)在現(xiàn)象。她只是他的命運。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男人的精神的悲劇道路,這對于他也就是人的道路。女人在這條道路上起著重要作用,但女人只是男人的誘惑和欲望。男人被對女人的欲望所束縛,但這似乎依然是男人自己的事情,是男人的欲望本性的事情;男人是自我封閉的,他沒有走出自身,走入另一個女性的存在。女人只是男人清算自己的見證,只是用來解決自己的、男人的、人的問題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男人從來不與女性結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之所以如此歇斯底里,如此狂暴,正是因為她不能與男性結合而注定毀滅。陀思妥耶夫斯基確信愛毫無出路的悲劇。
別爾嘉耶夫還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層面上關于愛的思想,即基督教的愛。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把基督教作為愛的宗教而接受的。基督首先是無限的愛的預言家。正如在男女之愛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出悲劇式的矛盾,他在人與人的愛之中也揭示出這一矛盾,如大法官對人的愛。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個卓越的發(fā)現(xiàn),即,對人和人類的愛可以是“沒有上帝”的愛。在《少年》中,韋爾西洛夫天才地預言了一個未來烏托邦:人們相互依靠,相互愛,因為上帝死了,人類只剩下了人類自己了,人類也不再有永生。先前對上帝的愛,對永生的愛,轉向?qū)ψ匀弧?/p>
世界、對人、對所有小草的愛。這不是因存在的意義,而是因存在的無意義生發(fā)的愛;不是為了肯定永恒的生命,而是為了利用短暫的生命瞬間。別爾嘉耶夫認為,這個烏托邦對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愛的思想非常重要。因為,這樣的愛在不信上帝的人類中永遠也不會出現(xiàn);在不信上帝的人類中有的將會是《群魔》中所描繪的一切,將會是大法官對人類的愛。不信上帝的人類必定會走向殘酷,走向彼此殺戮,走向把人當作簡單的工具。對人的愛只能存在于上帝之中,這個愛肯定每一個人的面容中永恒的生命。這才是真正的愛,基督的愛。基督的愛是在每一個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上帝之子,在每一個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上帝形象。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核心的思想。人首先應該愛上帝。這是第一誡。第二誡是愛每一個人。愛人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為有上帝——唯一的父存在。我們應該愛每一個人中的上帝形象。如果不存在上帝,愛人就意味著把人當作上帝來崇拜,那么,人神就會把人變?yōu)樽约旱墓ぞ摺R虼耍瑳]有對上帝的愛,愛人就是不可能的。伊萬·卡拉馬佐夫就說過,愛人是不可能的。男女之愛是這樣,其他各種人與人之間的愛也是這樣。真正的愛是對人身上的上帝形象、對永生的肯定。基督的愛正是這樣的愛,基督教是真正愛的宗教。
革命 關于革命的思考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個重要主題。別爾嘉耶夫發(fā)現(xiàn),在對革命的考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革命對個性的奴役和革命的進步學說的悖論。革命實質(zhì)上“不是被外部原因或條件所規(guī)定,它是被內(nèi)部所規(guī)定。革命意味著人對上帝、對世界、對人類根本態(tài)度的徹底轉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革命的考察,實質(zhì)上也是對人性界限、對人類生活道路的考察。別爾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個人的命運中所發(fā)現(xiàn)的東西,他在民族的命運中,在社會的命運中同樣也發(fā)現(xiàn)了。‘一切都是允許的嗎’這一問題擺在個人面前,也擺在整個社會面前。把單個的個人引向犯罪的道路會把整個社會引向革命。這是個人和社會命運中類似的經(jīng)驗、相同的時刻。像在自我意志中越過了允許的界限的人失去自己的自由一樣,在自我意志中越過了允許的界限的民族也同樣失去自己的自由。自由轉化為強權和奴役。”[11]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革命實質(zhì)的揭示,實際上揭示的是社會層面上對人的強權與奴役。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喜歡“革命”,正是因為它導致對人的奴役,導致對精神自由的否定;出于對自由的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思想上反對“革命”,揭露它必定導致奴役的本質(zhì)。
關于進步,別爾嘉耶夫指出,進步之路引導人類走向未來普遍的幸福,但進步也因此給一代又一代人帶來死亡,他們以自己的勞作和苦難為這一幸福鋪設道路。所以,他從道德和宗教的良心上不能與“進步”思想妥協(xié)。別爾嘉耶夫發(fā)現(xiàn),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贊同“地下人”和伊萬·卡拉馬佐夫的造反,反對“進步”宗教。但是,伊萬·卡拉馬佐夫說:“我不接受這個上帝的世界……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他創(chuàng)造的世界。”別爾嘉耶夫認為,伊萬·卡拉馬佐夫的這一辯證法是拒絕承認在世界生活中上帝的意義。別爾嘉耶夫認為,如果世界的意義不在上帝那里,那么人就會認為意義在未來“美好”的世界中;而且,如果沒有上帝,如果沒有贖罪者和救贖者,如果歷史進程沒有意義,那么世界就應當被摒棄,那么就應當拒絕未來,那么進步就是丑陋的思想。而無神論的伊萬正是這樣認為的,所以,伊萬必定既否定這個世界,也反對未來“美好”的世界,進而把自己進入“美好”世界的入場券還給了上帝。但是,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要遠遠高于伊萬的辯證法,他揭示了世界的上帝意義,他相信上帝,相信世界的上帝意義。但是,在伊萬的造反極限中,與某種正面的真理有某種契合。這就是為什么陀思
妥耶夫斯基有一半站在伊萬·卡拉馬佐夫一邊。
神人與人神 別爾嘉耶夫認為,《宗教大法官的傳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的頂峰,他“正面的宗教思想,他獨特的對基督教的理解,首先應該在《宗教大法官的傳說》中去尋找”。在這里有兩個形象——基督與大法官,他們代表著兩種精神,即神人與人神,基督與反基督。基督——珍視人的自由。人自由地愛勝于一切。基督不僅愛人,而且確認人的尊嚴,承認人有能力達到永恒,他想讓人得到的不僅是幸福,而且是與人相稱的、與人高貴的稟賦和絕對的使命——自由相符的幸福。別爾嘉耶夫認為,《宗教大法官的傳說》中的基督形象是一全新的形象——基督是給予自由的基督,基督——即是自由,基督教——即是自由的宗教。別爾嘉耶夫認為,“這是還未曾有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獨創(chuàng)的對基督特征的理解。像這樣把基督形象闡釋為自由精神,哪怕是個別人的點到之筆也從未有過。這一精神自由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基督拒絕奴役世界的一切權力。權力意志既剝奪強權者的自由,也剝奪受強權者所奴役的人的自由。”[12]在《宗教大法官的傳說》中,與基督的形象相對立的是大法官的形象——反基督形象,與基督的自由精神相對立的是大法官強制的幸福的學說。大法官,人神——不信仰上帝,也不信仰人。他說,人,無力承擔自由的重負。自由之路是艱難之路,是痛苦之路,是悲劇之路。人,擔當不了自由。他以人們幸福的名義拒絕自由,以人類的名義拒絕上帝。他要創(chuàng)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其中沒有罪惡,沒有苦難,沒有無辜嬰孩的眼淚。這是以熱愛善的名義反抗上帝的邏輯:上帝不能被接受,因為世界是如此糟糕,因為世界充滿了欺騙和不公正。但是,這一善、這一幸福被強制給予人們,結果是扼殺人類的自由,否定人的精神自由,把自由出賣給必然王國,走向最大的強權。別爾嘉耶夫認為,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的預見之一。這一反基督精神同樣產(chǎn)生于自我意志和反抗上帝。當自我意志和反抗上帝發(fā)生在個人身上時,毀滅的是自己,當自由意志與反抗上帝發(fā)生在社會建構時,那么,就會剝奪人類的自由。這是在社會層面上又一次揭示自由內(nèi)在的悲劇的辯證法。
別爾嘉耶夫發(fā)現(xiàn),在整篇《傳說》中,都是大法官在進行強勢的論辯與說服,而基督始終處于無語與“順從”之中,但“自由的真理非語言所能表達,易于表達的只是強權的思想”。外表的強大總是實質(zhì)的虛妄,無言的沉默隱藏著無比的力量。“基督和他的真理的隱性表達使其藝術表現(xiàn)力尤為強烈。”在《宗教大法官的傳說》中別爾嘉耶夫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個正面的宗教世界觀根本所在。他說,在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解決的只有一個主題,即人類精神自由的主題。我們也可以說,別爾嘉耶夫在這里找到了自己全部宗教哲學的根基,從此,自由基督的精神形象,自由基督教的信仰成為他整個哲學與生命激情的源泉。
耿海英
2019年8月
注釋:
1.陳建華,《中國俄蘇文學研究史論》(第三卷),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第129頁。
2.Н.А.Бердяев.МиросозерцаниеДостоевского//Смыслтворчества.Москва.2004.C.383。
3.С.А.Титаренко.Н.Бердяев.Москва-Ростов-на-Дону.2005。
4.Н.А.Бердяев.МиросозерцаниеДостоевского//Смыслтворчества.Москва.2004.C.399。
5.別爾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耿海英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頁。
6.別爾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第21頁。
7.赫爾曼·海塞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斯人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65頁。
8.別爾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第22-23頁。
9.別爾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第39頁。
10.別爾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第30頁。
11.別爾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第85頁。
12.別爾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第127頁。
本文為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俄】尼古拉·別爾嘉耶夫/著 耿海英/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版)譯者耿海英所寫的導讀,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刊發(fā),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為:別爾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