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士的故事:跟著她一起穿過病房,從出生到死亡
【編者按】英國作家克里斯蒂·沃森的第一部小說《遠方小小的太陽鳥》(Tiny Sunbirds Far Away)就獲得了科斯塔獎長篇首作獎,第二部小說《女人當國王的地方》(Where Women Are Kings)也頗受稱贊。不光寫作,克里斯蒂·沃森還曾做過20年的護士,也在通過教學與寫作來推廣護理理念。《護士的故事》是她20年護士生涯的記錄,近日推出了中文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摘錄其序言的部分內(nèi)容。

克里斯蒂·沃森
十六歲那年,我離開學校,搬去和我二十多歲的男朋友以及他的四個二十多歲的男室友一起住。那時的生活簡直混亂不堪,但我愉悅又滿足地在錄像店工作了一段時間,拿家用錄像帶從隔壁的中國外賣餐館換雞肉炒面吃。我的素食主義信念開始動搖,同時開始專心在店里放成人電影,朋友們坐滿房間。我還想成為農(nóng)民,就報名上了農(nóng)業(yè)學校,堅持了兩個星期。BTEC(Business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的縮寫,該組織在英國負責提供各類成人職教課程)的旅游課程我堅持了一周。委婉點說,我找不到方向。
我真正感到崩潰,是有一回因面試遲到,錯過了必勝客餐廳兒童游樂區(qū)演藝人員的工作機會。而且盡管我當時只有十六歲,全然懵懂無知,但戀情告吹還是讓我格外震驚。我的驕傲意味著我不能再回家了。我沒有工作,無家可歸。于是,我成了一名社區(qū)志愿服務者。那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給年滿十六歲而不是十八歲的工作人員提供住宿的工作。我被安排到一個由麻痹癥協(xié)會(現(xiàn)在叫麻協(xié)會)運營的社區(qū),每周可以賺到20鎊零用錢。我負責照料那些身體嚴重殘疾的成年人:幫助他們上廁所、吃飯、穿衣服。那是我頭一回覺得自己似乎在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我把素食主義拋到九霄云外,開始擁抱更遠大的事業(yè)。我剃了個光頭,穿著從慈善商店淘來的衣服,把零用錢統(tǒng)統(tǒng)花在蘋果酒和香煙上。我一無所有,可是過得很快活。同時,那是我頭一回跟護士一起工作。我看著那些訓練有素的護士,就像生病的孩子看著她的父母一樣。對于她們在做的事情和工作本身,我羨慕得無話可說。
“你應該去當護士,”她們中的一個說,“他們會給你一筆助學金,還有住的地方。”
我去了當?shù)氐膱D書館,發(fā)現(xiàn)整棟樓里都是像我這樣的流浪漢。我去過我們學校的圖書館,還去過斯蒂夫尼奇的圖書館,在年紀更小的時候去過很多次。但這里的圖書館不只是個借書和學習的地方,它是一個避難所。有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睡著了,管理員便由著他睡下去。一個男人幫一個坐在機械輪椅上的女人拿了本放在書架頂層的書,那男人脖子上戴著一個標記,表明他是個孤獨癥患者。還有孩子們在里面跑來跑去,一伙稍大一點的孩子擠在一起,放聲大笑。
我發(fā)現(xiàn)了瑪麗·西戈爾(Mary Seacole)。和弗洛倫絲·南丁格爾一樣,她也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照護了許多士兵。她從小玩給洋娃娃打針吃藥的游戲,然后發(fā)展到寵物,以此嘗試護理工作,再到最終真正去幫助人類。我以前從沒把護理當作一種職業(yè),但那時,我回憶起了小時候,我和哥哥那時經(jīng)常故意把洋娃娃里面的填充物弄出來,或把它們的眼睛扯下來,這樣我就能動手讓它們恢復原本的樣子。我還記得我的小學同學們會排成一隊,讓我來檢查他們有沒有貧血;我一定先向他們吹噓了自己的專業(yè)知識,而等放學后,我會讓他們排成一隊,挨個兒翻他們的眼皮,看他們是否需要多吃洋蔥和肝臟;還有數(shù)不清的嗓子疼的小伙伴們,我會用手指輕輕按在他們的脖子上,像按在單簧管上一樣,檢查他們的“淋巴結”。
那些書里沒寫太多關于護理或如何從事這份職業(yè)的內(nèi)容,所以我不確定自己能否勝任。我發(fā)現(xiàn)護理工作早在史書記載之前就已存在,在每種文化中都歷史悠久。最早談及護理工作的書面文字之一是公元前1世紀的印度醫(yī)書《阇羅迦本集》(Charaka Samhita),書中說,護士應當同情每一個人。護理工作還跟伊斯蘭教關系密切。公元7世紀初,虔誠的穆斯林會成為護士——伊斯蘭教歷史上第一位專業(yè)護士魯法伊達·賓特·薩阿德(Rufaidah bint Sa’ad),便因她的同情與共情,被描述為一位完美的護士。
同情、憐憫、共情: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造就一名好護士的品質(zhì)。我時常回憶這次去白金漢郡圖書館的經(jīng)歷,因為在我的職業(yè)生涯中,這些品質(zhì)似乎總是匱乏的——這些我們已然遺忘或不再珍視的品質(zhì)。但16歲時,我精力旺盛,心懷憧憬和理想主義。而到了17歲,我決定去追逐這一目標。我不想再變換職業(yè)選擇,任自己游來蕩去;我要成為一名護士。此外,我知道當了護士后,派對自不會少。
幾個月后,不知怎的,盡管比官方規(guī)定的準入年齡17歲半小幾個星期,我還是誤打誤撞報上一門護理課程。我搬進貝德福德的護士總部,它位于醫(yī)院后方,是一片很大的公寓區(qū),充斥著砰砰砰的關門聲以及不時傳來的尖叫和笑聲。在我這一層住的大部分是工作頭一年的新人護士,還有幾個放射專業(yè)和理療專業(yè)的學生,偶爾還會有輪班的醫(yī)生。學護理的學生幾乎都年輕又狂野,第一次離家在外。愛爾蘭女生的數(shù)量相當可觀(“我們有兩條路可選,”她們對我說,“護士,或修女。”);男生很少(在那個年代,幾乎都是基佬)。洗衣房在樓下,旁邊是通風不良的電視房,里面的扶手椅是塑料涂層的。在暖氣片二十四小時持續(xù)高熱的作用下,只要坐在里面看一會兒電視,我的大腿后部就會粘在椅面上。漫不經(jīng)心地脫口說出“我被粘在椅子上了”,我就這樣與一位精神科見習醫(yī)師相識,他后來做了我好幾年男朋友。我的房間緊挨著衛(wèi)生間,聞起來總是濕乎乎的,我有個朋友還在地毯上種過水芹。廚房很臟,冰箱里塞滿過期食品。其中一個櫥柜上貼著字條,上面用大寫字母寫著:別動別人的食物。我們知道你是誰。
帶回聲的走廊里有部電話一直在響,晝夜不停。走廊里還經(jīng)常回蕩著吵架聲、快步跺過的高跟鞋聲以及音量很大的音樂聲。我們通常抽香煙,但大麻的味道就像某種持續(xù)存在的低分貝背景噪聲,一段時間之后你就對它渾然不覺。我們自由進出彼此的房間,從不鎖門。在我房間里,床鋪的正上方貼著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心臟解剖圖,還有一個擱架,上面放著護理學教材和翻爛了的小說,床邊還有一堆哲學書。房間里有一個熱水壺、一臺沒法調(diào)小的電暖氣和一扇打不開的窗子。有一個可以洗東西的水槽(洗身體或杯子),可以撣灰,可以嘔吐,還可以在廁所堵塞的幾個星期里解決小解的問題。對于我的同齡人來說,這條件算不上優(yōu)越;但我長期在社區(qū)公用房和別人共居一室,在那之前則和男友還有他的男室友們住在一座房子里,所以這地方對我而言簡直是天堂。
不過,頭一個晚上總是最難熬的。我不知道作為一個護士,自己該做點兒什么,于是開始后悔沒有向那個鼓勵我做護士的前輩請教更多問題。我害怕失敗,害怕看到我父母在聽到我再一次改變心意之后的表情。他們已經(jīng)因為我要當護士的決定受夠了驚嚇:我爸爸竟然真的放聲大笑起來。盡管我的工作要我成為一個照顧別人的人,可他們依然覺得我是個沒法照顧別人的叛逆孩子。他們沒法想象我會全身心投入這樣一樁事關善良的職業(yè)。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沒法入睡,聽鄰屋的女孩和她男友爭吵。她男友是個身形瘦長、喜怒無常的保安,似乎正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和她住在一起。即便他們消停下來,我也沒法入睡。我腦袋里的疑惑不住翻騰。我知道自己至少要在教室里好好學習一下,才不會失手讓人送命,或不得不去做清洗老人陰莖之類的恐怖事情。但我還是滿心焦慮。我起身上廁所,廁所是整層樓共用的;看到廁所門上粘著一條用過的衛(wèi)生巾時,我開始干嘔。除了因為那玩意兒本身就很惡心,我記得我當時只要看到血就會犯暈。
第二天早上的職業(yè)健康檢查確認了我易犯惡心的體質(zhì)。我們每個人都要采集血樣。“完善你們的檔案,”采血師宣布,“以防你們有人被針刺傷,感染艾滋病病毒。我們能夠檢查出你是否已經(jīng)是HIV陽性。”那是1994年,關于艾滋病的謠言和恐懼四處彌漫。采血師給我的手臂綁上止血帶。“你是學護士,還是學醫(yī)的?”她問我。
我看著針頭,鮮血正漸漸充滿針管,房間開始變得模糊。她的聲音越來越遠。
“克里斯蒂,克里斯蒂!”醒來時,我正躺在地板上,腿還搭在椅子上,采血師出現(xiàn)在我正上方。她笑了:“你沒事了?”
我慢慢用胳膊肘撐起身子,眼神重新聚焦。“怎么回事?”
“你暈倒了,親愛的。真不幸,看來你得重新考慮一下職業(yè)規(guī)劃了。”
二十年的護士生涯,我為此付出許多,但收獲更多。我想同你分享這樁非凡事業(yè)中的悲傷與喜樂。跟我一起穿過病房,從出生到死亡;穿過兒童特護區(qū),推開雙扇門來到內(nèi)科病房;響應電鈴敲擊的嗶嗶聲,奔跑著穿過走廊,路過藥房和職工餐廳,來到急診室。我們將探索醫(yī)院本身,以及護理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剛開始時以為,護理工作涉及:化學、生物學、物理學、藥物學以及解剖學;而我現(xiàn)在知道,護理工作的真諦在于:哲學、心理學、藝術、倫理以及政治。我們在人生路上總會遇到這些人:患者、家屬和醫(yī)護人員——這些你可能早已熟識的人,因為我們都會在人生的某些時刻受到照護。我們每個人,都是護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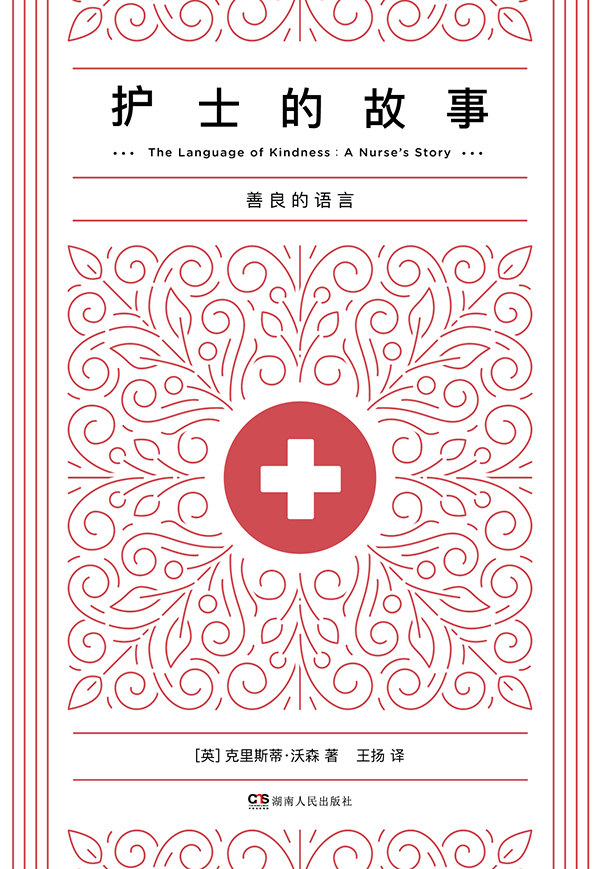
《護士的故事》,【英】克里斯蒂·沃森/著 王揚/譯,
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