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星站》:獻(xiàn)給多元文化的未來之詩
原標(biāo)題:身份、空間和血統(tǒng):獻(xiàn)給多元文化的未來之詩——拉維·提德哈《中央星站》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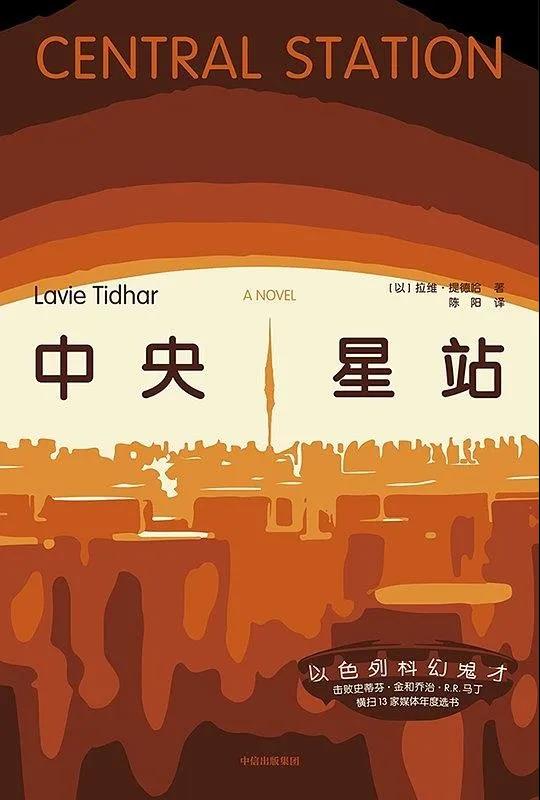
《中央星站》
作者: [以] 拉維·提德哈
譯者: 陳陽
中信出版集團(tuán)
2019年11月
“她的名字消失了,就像鑰匙和襪子消失了一樣。放錯了地方,然后,再也找不到。
慢慢地,不可逆轉(zhuǎn)地,把記憶綁在一起的紐帶,像核糖核酸一樣,開始弱化和斷裂。”
——《中央星站》
初讀《中央星站》時,我剛剛離開享有“宇宙中心”之稱的五道口。在這里,書中的景象與眼前所見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共鳴。
五道口并非連接地球和宇宙萬物的交通樞紐,卻同樣是高新技術(shù)的焦點(diǎn)之地。在這里,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當(dāng)你站在成府路和中關(guān)村東路的交匯點(diǎn)時,你會同時看到來來往往的學(xué)生、大學(xué)老師、匆忙上下班的上班族、外出散步的退休老人、違章的外賣員、協(xié)勤和交警、走走停停的清潔工、騎著三輪車搬運(yùn)廢舊共享單車的中年男子和來自數(shù)不清的國家的皮膚或白或黃或黑的外國人……路口的西北聳立著背靠清華科技園的快手大廈,東北是一座不高也不小的購物中心,西南方有藥店和中國科學(xué)院的若干研究所,而東南角則是一整條街的飯館和露天攤位,奶茶店挨著烤豬蹄鋪?zhàn)樱饷媾胖蜷L或短的食客隊伍。這種錯綜復(fù)雜的混雜感,是我對五道口的第一印象,也是我對北京很多地區(qū)的印象。

英文收藏版封面
與《中央星站》不謀而合的正是這份印象。二者之間的共鳴讓我在閱讀時幾乎將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作者對空間和文化氛圍的書寫上——事實(shí)上,在閱畢全書后,我相信,這正是拉維·提德哈這位出生在以色列的集體社區(qū)中的科幻作者所試圖描繪的,也是本書的核心價值所在。本書成功地做到了一件鮮少有科幻作品關(guān)注的事,即完成對一種生活空間所蘊(yùn)含的文化的復(fù)調(diào)描寫。如果把這種空間限制在城市里,那么,它所繼承的并非《神經(jīng)漫游者》或《道路滾滾向前》中的那種徒有其表的美學(xué)刻畫,而是如《城市與群星》《摩天樓》一般,在細(xì)膩地完成烏托邦的建構(gòu)后,帶領(lǐng)讀者深入其中,帶讀者領(lǐng)略烏托邦的方方面面。
《中央星站》的故事圍繞一座太空漫游時代的航站樓展開。航站樓坐落在特拉維夫,身為高科技的結(jié)晶,外圍卻居住著大量平民百姓。拋卻作者的語言風(fēng)格,這正是一個典型的符合“High Tech, Low Life”標(biāo)準(zhǔn)的賽博朋克空間,其中有普通人類、接上了腦機(jī)系統(tǒng)的賽博格、機(jī)器人和被稱為“他者”的意識生命。四種不同的種族帶著各自對世界的認(rèn)識,生活在相同的空間中,生活在對彼此的友善和敵視里。
但是與慣常的賽博朋克小說不同,《中央星站》的賽博世界是極為獨(dú)特的。在故事中,雖然充斥著令人頭暈?zāi)垦5奈磥砑夹g(shù),其中甚至存在著在虛擬世界制造神明的藝術(shù)家和吸取數(shù)字精神的吸血鬼。但這些技術(shù)存在的價值卻并不應(yīng)被簡單地解讀成對未來的展望或是在科幻背景下對以色列乃至中東幻想文學(xué)的美學(xué)傳承,而是擁有更加深層次的邏輯。
挖掘這一邏輯的切入點(diǎn)是“身份”,即人的出身和社會地位。在《中央星站》中,作者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描寫或強(qiáng)調(diào)人物的身份——就連節(jié)標(biāo)題也如此,諸如棄物之王、血族、機(jī)械人、書商、造神藝術(shù)家和圣人。這些身份不僅多樣而且復(fù)雜,具體體現(xiàn)在三個維度上:其一是因星際旅行而得到大幅拓展的民族多樣性(不僅是多民族、多國家,還是多星球);其二是物種多樣性(人類、機(jī)器人、賽博格和數(shù)字生命);其三則是單一個體的復(fù)雜出身(每個人身上都承載了大量的血統(tǒng),這僅從弗拉基米爾·鐘這樣的跨國名字上就能看出一二)。
僅僅是將兼具三個維度的復(fù)雜身份的人數(shù)以萬計地疊加在相同的生活空間中,我們就已經(jīng)能夠創(chuàng)造出一種多元社會的驚人圖景,因為從物種的角度入手,不同物種實(shí)際上居住在完全不同的環(huán)境中。這就形成了現(xiàn)實(shí)-虛擬現(xiàn)實(shí)疊加的二重世界(設(shè)想一下,當(dāng)你走進(jìn)一間空空如也的屋子,卻同時也走進(jìn)了虛擬世界的一整個國家的畫面)。
但提德哈卻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繼續(xù)圍繞血統(tǒng)展開了他的一篇又一篇故事。在他筆下,血統(tǒng)不僅是字面意義上的文化傳承,還是一種文化和精神的雜交,而中央星站這樣一個規(guī)模龐大的文化熔爐,正好為這種文化雜交搭建了最好的舞臺。于是,在故事中,我們雖然找不到任何一個確切的中國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俄羅斯人、美國人、東南亞人,卻能在每個人的身上找到這些民族的文化在他們身上投下的影子。與保羅·巴奇加盧皮的《發(fā)條女孩》相比,這更進(jìn)了一步,從帶有種族隔離色彩的多民族雜居上升到了打破隔墻的民族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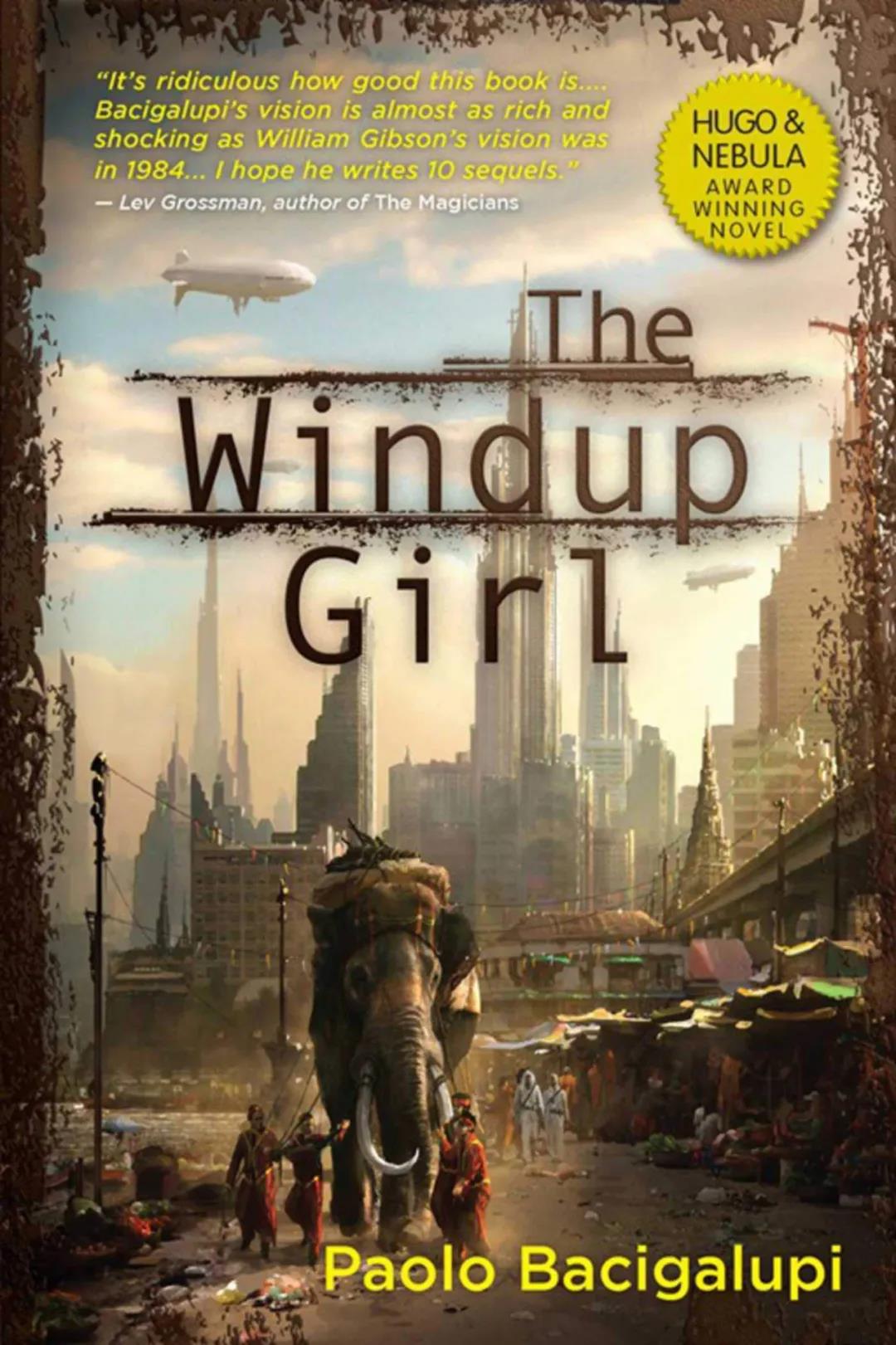
《發(fā)條女孩》
體現(xiàn)這種身份融合和血統(tǒng)傳承的最佳代表即故事的核心主角之一——鮑里斯·阿哈龍·鐘。身為一名云游浪子,他的身上集中了太多的標(biāo)簽:有本土情人的機(jī)器人技師、身兼俄羅斯血統(tǒng)、中東血統(tǒng)和東方血統(tǒng)的云游外星的浪子……這允許他同這樣一個空間里的所有人物乃至權(quán)利中心產(chǎn)生互動,讓他成為了故事中所有矛盾的焦點(diǎn),也成為故事精神內(nèi)核的化身。
在此,我們暫且跳過中間草蛇灰線的復(fù)雜糾葛和所有其他人物弧光,僅以鮑里斯為例,觀察故事的開端和結(jié)尾。在開頭,鮑里斯帶著一種思鄉(xiāng)般的沖動返回了地球,回到了他出生、長大的故土,希望在這里找到縈繞在他心中的困惑的答案。而在故事行將結(jié)束之時,我們知道了這份困惑究竟是什么——它是對自我身份的困惑,是對自我存在意義的困惑。
鮑里斯的困惑因中央星站的多元文化而獲得了別樣的意義:在如此豐富多彩的一個宇宙中,它不僅是鮑里斯一個人的問題,也是所有誕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人的共同困擾,即“出生在這樣一個世界里,背負(fù)著代代傳承的遺產(chǎn),面對著紛繁多樣的選擇時,我究竟是誰?我要選擇什么樣的人生?”對生活在中央星站的人們來說,回答這個問題,意味著自己要同時同過去和未來作戰(zhàn),以爭得屬于自己的人生軌跡。
《中央星站》把回答這一問題視作作品的核心,以單元劇的形式闡述了不同身份的人的選擇。這意味著作者徹底摒棄了烏托邦小說慣常的革命敘事,把同世界的對抗轉(zhuǎn)換為同自己的對抗。提德哈所關(guān)注的顯然不是為什么未接入腦機(jī)接口的人會被視作殘廢,也不關(guān)心新時代的癮君子(即吸血鬼卡梅爾)要得到怎樣的處置。他關(guān)注的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如何生活,如何作為一個個獨(dú)特而鮮活的生命勇敢地活下去。
這種視角看似充滿避世色彩,卻不僅符合多災(zāi)多難的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傳統(tǒng),也符合多元文化世界的社會特征。在這樣的世界里,我們將很難找到一種通用的壓迫-反抗模型來構(gòu)建相應(yīng)的革命敘事,迎接我們的將會是百家爭鳴,將會是成千上萬的互不相同的聲音的喧囂、爭鳴和交融。在這樣的世界里,如故事結(jié)尾的鮑里斯那樣離開大城,駛向荒野,用行動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或許正是所有平凡之人向世界發(fā)起的勇敢反抗。
至此,《中央星站》的觸動人心之處便昭然若揭了。它通過身份的多樣性來構(gòu)建空間基底,借血統(tǒng)的交錯和傳承構(gòu)筑了一座令人眼花繚亂的多元化城市,并敏銳地捕捉到了在這樣一個多元世界里,人們內(nèi)心最大的不安。這超越了美國科幻從古至今浸染著殖民主義色彩的高高在上的使命感,也跳出了新浪潮vs.黃金時代、內(nèi)心宇宙pk外在宇宙的慣常科幻討論,同時也不似《他方世界》那般賣弄文字游戲,而是用詩意的語言傳達(dá)出濃厚的生活氣息,欣然邀請讀者進(jìn)入作者筆下的“小世界”和“大世界”。
相比已經(jīng)逐漸演化成平行宇宙的美式賽博朋克作品,《中央星站》中的世界要更加貼近現(xiàn)實(shí)。從以色列多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拉維孕育出了一部關(guān)于未來的預(yù)言和寓言。這之中的未來,不僅是以色列的未來,不僅是作者所提到的義烏的未來,抑或五道口的未來、或四惠東地鐵站之外的高樓大廈之下的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的未來,也是在這個信息爆炸、科技飛躍式發(fā)展的時代里,我們所有人都將要面對的未來。
作者簡介
HeavenDuke,純粹幻想系作者,《科幻百科》公號創(chuàng)始人,夢想做一只網(wǎng)絡(luò)爬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