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公共事件的韓國文學:我來了,我看見,我銘記
2019年,借由引進《82年生的金智英》,我才真正開始接觸韓國文學,此前,和很多人一樣,我對韓國影視如數(shù)家珍,對韓國文學的印象卻還停留在“韓國還有文學?”而真正進入這個領域,才明白自己的無知和傲慢。
其實從2007年,中韓建交十五周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已經(jīng)引進了一批優(yōu)秀的韓國文學作品,大多由翻譯家薛舟、徐麗紅伉儷翻譯。其中包括被稱為“90年代韓國文學神話”、代表作《尋找母親》在韓國創(chuàng)出200萬冊銷售奇跡的申京淑;被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勒克萊齊奧贊譽“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女作家”的八〇后天才作家金愛爛;拿遍韓國各大文學獎,又因參加一檔綜藝節(jié)目《懂也沒用的神秘雜學詞典》,以其博學、儒雅形象圈粉無數(shù)的金英夏;以及李文烈、具景美等在韓國非常著名、受歡迎的當代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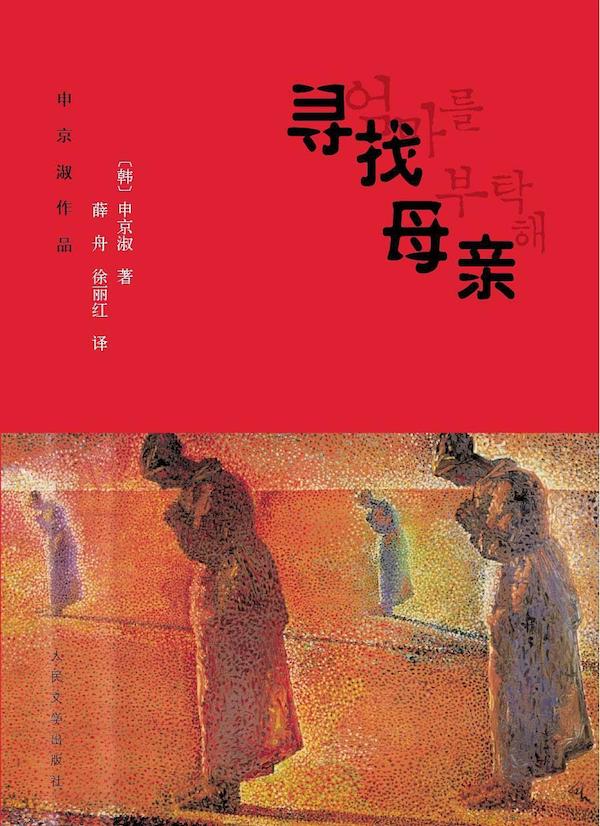
申京淑《尋找母親》
引進《82年生的金智英》是我在讀完全書后兩小時內就做出的決定。這本2016年在韓國引起軒然大波的女性小說,以近似社會學報告的寫實風格,描寫了一位八〇后普通女性,從童年到成為母親的人生中,在日常生活中所經(jīng)受的潛移默化的性別歧視。這本書經(jīng)由正義黨黨鞭魯會燦公開送給文在寅總統(tǒng),逐步擴大影響力,一些女明星在推薦本書后,甚至遭到網(wǎng)絡暴力,在爭議中成為銷售150萬冊的暢銷書,并最終拍攝為電影,由孔劉、鄭裕美主演,在韓國上映后獲得極高的口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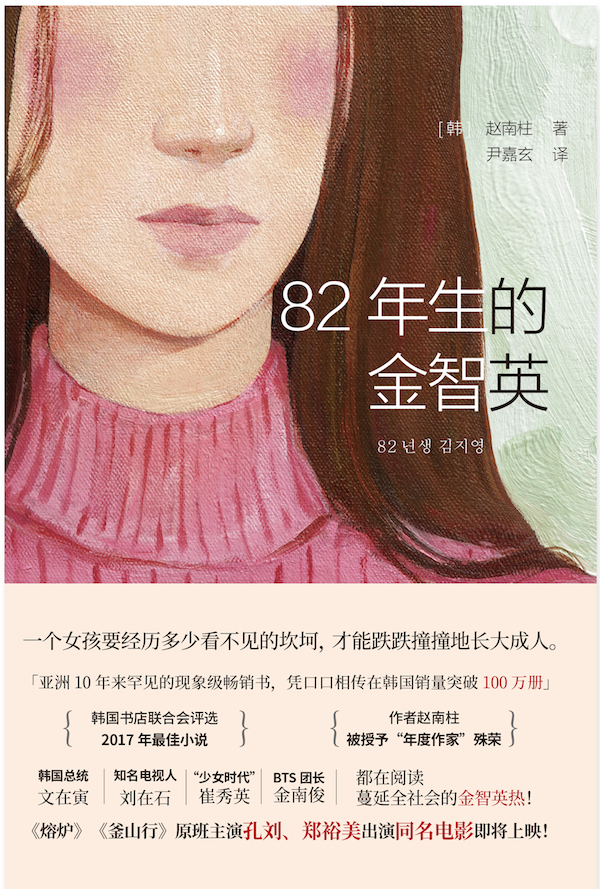
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
在制作和推廣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們與韓國文學翻譯院、駐華韓國文化院建立起合作關系,見識到韓國政府對文化輸出的重視,以及他們的文化輸出機構務實、細致的工作風格。文化院,在我們決定邀請作者來華后,提供專業(yè)場地給我們做線下活動、媒體專訪,并包攬了招募觀眾、設計宣傳物料的工作。院長本人中文很好,風趣、謙和,在活動前專門宴請作者和出版方。活動結束幾個月后,還特地邀請我們去參加送年會,維系感情。韓國文學翻譯院,在我們邀請作者來華時提供翻譯、交通、住宿資助,流程簡潔,批復很快。這兩家機構給我和營銷同事留下極好的印象,他們做事非常積極主動,不打官腔,不許空頭支票,溝通效率高,每一件小事都落在實處。
翻譯院與我們對接的負責人是一位中文很好的韓國人柳小姐,在活動結束一個月后,她來信介紹翻譯院引介韓國文學的長期項目。翻譯院會招募譯者,由他們自主選擇自己心儀的韓國文學書籍,撰寫中文的審讀報告。這些報告每個季度會匯總一次,請專業(yè)的評審員評審。第一批評審員是中國的出版社編輯,評估角度是試譯稿的翻譯質量、圖書內容本身的文本價值,以及中國出版方、中國市場的接受程度。第一批評審通過的試譯稿(得分在合格線上),會由第二批評審員評估翻譯準確性、涉及韓國文化相關細節(jié)的準確性。這批審讀者多為韓國的大學老師。兩次評審都通過的譯者,翻譯院會提供資助,請他們翻譯全書,同時向中國的出版方推薦。在翻譯院的網(wǎng)站上可看到很多韓國文學新書的資訊,包括圖書的基本信息、內容介紹、作者介紹等,推薦的作家很多是文壇新人。
我曾有幸參與一些評審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了解到許多初次聽說的優(yōu)秀作家。這批作品作者大多是七〇后和八〇后的年輕作家,寫作風格各異,但讓我印象極深的是,他們的作品中幾乎不見作者本人現(xiàn)身,對“他人”的關注遠大于“我”。他們似乎不約而同地關注歷史、社會、邊緣群體,尤其是對社會變革關鍵事件的記錄。他們記錄的方式、角度各不相同,形式多元,但都很有分量,很有創(chuàng)造力,而且沒有失掉文學性。
有人在世態(tài)小說中融入超現(xiàn)實的細節(jié)。一位叫金勁旭的作家,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少年不老》:三位具有超能力、生活落魄的底層老人,十幾年前曾是同事,屬于同一個組織。其中一位的能力是可以看到發(fā)生在不同時空的事件的場景。有一天,他夢見自己曾經(jīng)的上司赤身裸體站在吊索之后,感覺在向他求助,于是決定聯(lián)絡兩位前同事,一起去救上司。三位老人踏上尋找上司的公路旅行,而由于衰老,他們的能力也隨之衰退,力不從心。他們運用各自殘存的能力,勉勉強強最終趕到上司生活過的地方時,發(fā)現(xiàn)那只是一個廢棄的集裝箱,上司已經(jīng)不見蹤影,只有一條瘸腿的黃狗。全文中沒有直接揭示三人的身份,只通過他們的對話、行為等細節(jié)做出暗示——原來這三人曾是參與“光州事件”軍警,上司則是他們心狠手辣的長官。他們始終相信,上司和國家會記住他們的忠誠。但當他們終于找到上司時,發(fā)現(xiàn)他正蜷縮在高高的煙囪上,而煙囪上掛著抗議的橫幅——“我們還能繼續(xù)工作,單方面解雇等于殺人”。曾經(jīng)擁有絕對權力者,在十幾年后,成為貧窮、衰弱的底層人民,變成了自己曾經(jīng)逮捕的“國家的敵人”,體驗了他們的處境,甚至最高領導自己成為了爬上高臺的示威者。整個故事形成一個完美的閉環(huán),非常高級的黑色幽默。

金勁旭《少年不老》
有人選擇的角度是黑暗時代普通人的善意引發(fā)的蝴蝶效應。一位叫趙海珍的作家,寫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光之護衛(wèi)》,每個故事發(fā)生的時代背景不同,主人公身份差異也極大。但主題都有相似之處——普通人微小的善,如何對其他人的命運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其中有個故事《東柏林》,主人公是德國人。她的祖母去世了,年輕時曾有個很要好的韓國留學生朋友。主人公因此和一位在作家交流活動上認識的韓國詩人寫信,拜托他找到那位朋友。在一來一往的書信中,還原了20世紀60年代韓國政府秘密綁架韓國留學生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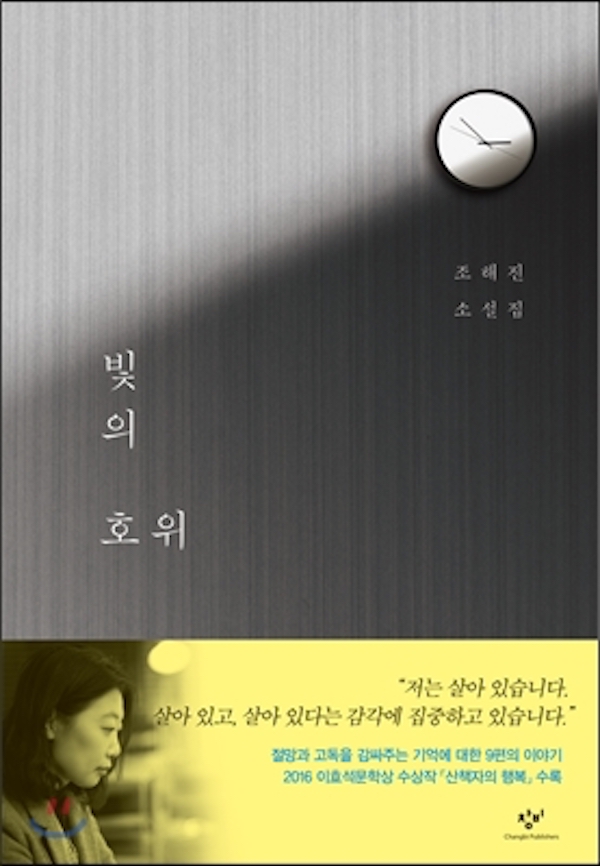
趙海珍《光之護衛(wèi)》
有人選擇類型小說。一位主職是電臺節(jié)目主編的叫LEE jaeik 的作家,以一樁真實的駐韓美國士兵虐殺妓女的案件為題材,寫了一部情節(jié)戲劇性很強的浪漫驚險小說。其中涉及美韓關系、基地村(駐韓美軍紅燈區(qū))引發(fā)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Lee JaeIk 艾琳
考慮到這些作品并非翻譯院特意挑選,而是由譯者根據(jù)自己的興趣主動申報,可見韓國當代的年輕作家群體對社會的關注程度。
也有老一輩作家的作品。一位出生于1937年,名叫權正生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是一本名為《夢實姐姐》的兒童文學作品。根據(jù)資料,這本書1984年初版后,每隔幾年就會再版,直到今天,總印次超過150次,是名副其實的經(jīng)典。但這本兒童文學卻是頗沉重的歷史題材,主角夢實是一位身世坎坷的十歲小女孩,在韓國解放后,她跟隨逃難到日本的父母回到韓國,在戰(zhàn)后滿目瘡痍、物資極其匱乏的環(huán)境下,以頑強的意志自救及救人,努力生活。一位小學教師評價道:“對于那些沒有時間去感受歷史,只忙于背誦的孩子們來說,該作品最能讓他們如饑似渴地去了解。”從這部作品中,我依稀看到一種不同代際作家之間的傳承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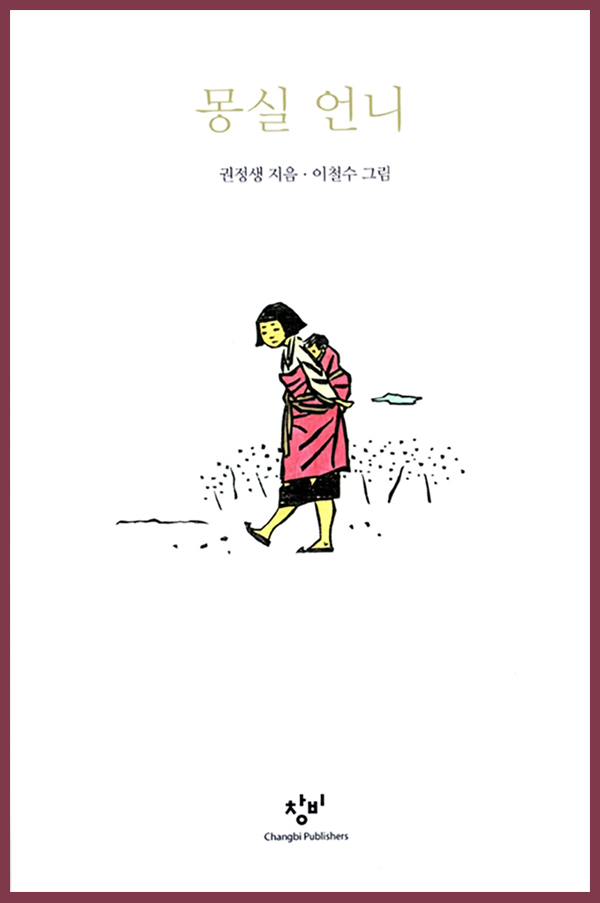
權正生《夢實姐姐》
那幾天我正好也在讀金愛爛的小說,她的作品讓我發(fā)自內心地驚嘆。她是一九八〇年生,但筆力之老道,對社會眾生相的描摹之精確、冷靜,從中體現(xiàn)的閱歷之豐富,心智之成熟,完全不像年輕作家。在她的作品中,也隱藏著歷史片段的閃回,《水中的歌利亞》中女主人公的父親也曾爬上高塔抗議,和《少年不老》結尾的意象如出一轍。雖然不熟悉韓國現(xiàn)代史,我猜想這一定是某個社會事件中一個象征性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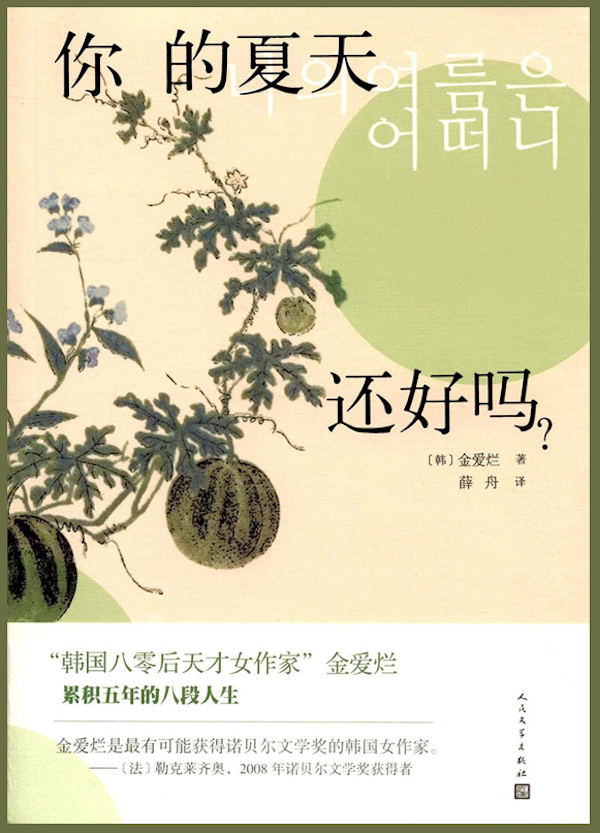
金愛爛《你的夏天還好嗎》
2014年,曾以《素食主義者》斬獲國際曼布克獎的著名中生代作家韓江,創(chuàng)作了以“光州事件”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少年來了》。她寫道:“有些記憶是時間治愈不了的傷痛,不會因事隔多年而變得模糊或者遺忘,吊詭的是,時間越久反而只會剩下那些痛苦記憶,對其他回憶則逐漸麻木。”

韓江《少年來了》
也是同一年,發(fā)生了世越號沉船事件,給全社會造成深重創(chuàng)傷之余,也激起了民間對政府的憤怒問責。韓國影視界迅速反應,推出了一系列該事件的紀錄片、劇情片,從各個角度剖析這一事件。但中國讀者不了解的是,其實在韓國文學界也產(chǎn)生了反思的作品。一位叫金琸桓的作家,受此事件觸動,在遍訪受害者之后,寫下了兩本小說《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 《那些美好的人啊:永志不忘,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這兩部作品被評論家認為是“世越號文學”的開端。金琸桓說:“我一直堅信文學應該站在窮苦、弱勢和受傷害的人這邊。不僅文學,社會共同體也是如此,屬于共同體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
他一直關注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受害者。2018年,在經(jīng)過扎實的資料搜集和采訪后,他寫下了以韓國MERS患者經(jīng)歷為主題的紀實文學作品《我要活下去》。他在后記中提到,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的起心動念,是注意到媒體對受害者的報道遠遠不夠充分,很多時候他們淪為新聞中的一個數(shù)字,而非一個完整的“人”。“在說出不會遺忘、會永遠記住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應該記住什么,必須找回‘人’,而非‘數(shù)字’”。這部作品以三位MERS患者的個人經(jīng)歷為主線,還原出他們平凡人生被打斷的過程。他們不只有“患者”這個身份,也是熱愛書籍的倉庫管理員,患淋巴癌卻總是笑對人生的年輕牙醫(yī),懷揣理想主義的實習記者,卻因為政府失能、疾控機構反應滯后和名為“無知”和“恐懼”的病毒,成為被社會排斥、忽視的邊緣人。災難之中,沒有勝者也沒有敗者,唯有受害者和幸存者,作者帶領幸存者,去凝視受害者的命運,看到生命的尊嚴,也看到“如果我們只安于這種卑怯的幸運,總有一天我們也會孤單地面對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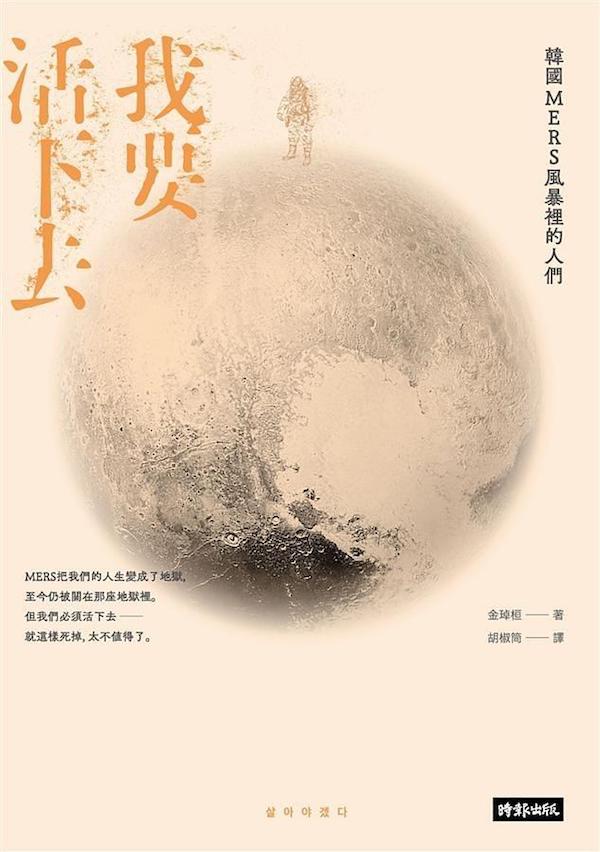
金琸桓《我要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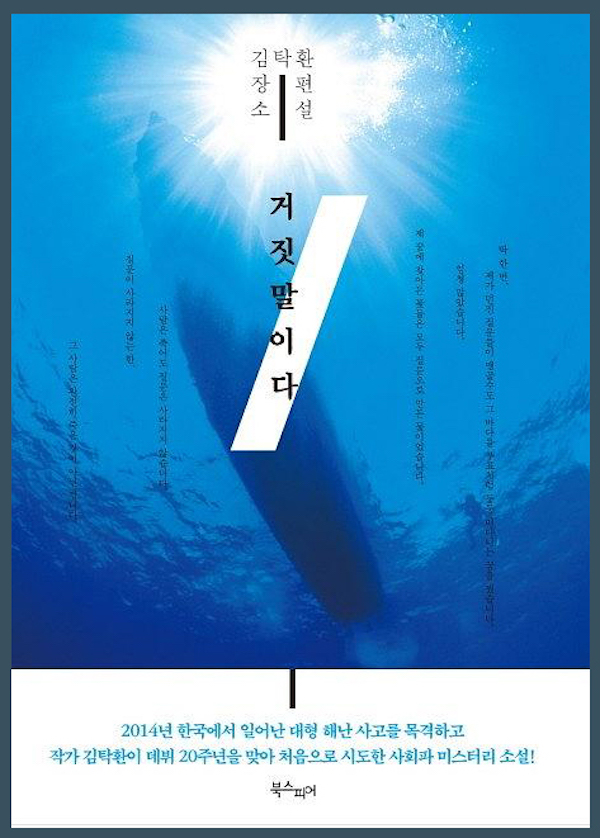
《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
西江大學文學系教授禹燦濟曾評價:“韓國文學就是痛苦的文學啊。”這種對痛苦的正視,這種如此普遍、大規(guī)模、自發(fā)性的記錄,令人嘆為觀止。
所以不只是韓國的影視界有這樣的傳統(tǒng),韓國的文學界亦然。韓國文學直接改變現(xiàn)實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大家熟知的《熔爐》促成“熔爐法”,還有《82年生的金智英》使得首爾市宣傳性別平等相關公共政策時采用“XX年生的XXX”的格式,甚至有少數(shù)黨領導人建議將性別平等法案直接命名為“金智英法”。

《熔爐》
英國作家珍妮特·溫特森說:“這就是文學所給與的——一種語言,強大到足以說出生活如何艱難。這不是藏身之處。這是安身之所。”我所見的這些韓國當代文學,就如同一座座佇立的紀念碑,供本國的民眾吊唁、紀念、反思之外,也讓我這個千里之外,此前對韓國歷史完全不了解的外國人,聽到了他們海浪般的吶喊。
我來了,我看見,我銘記。也給今天的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