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的緬甸與彼得斯的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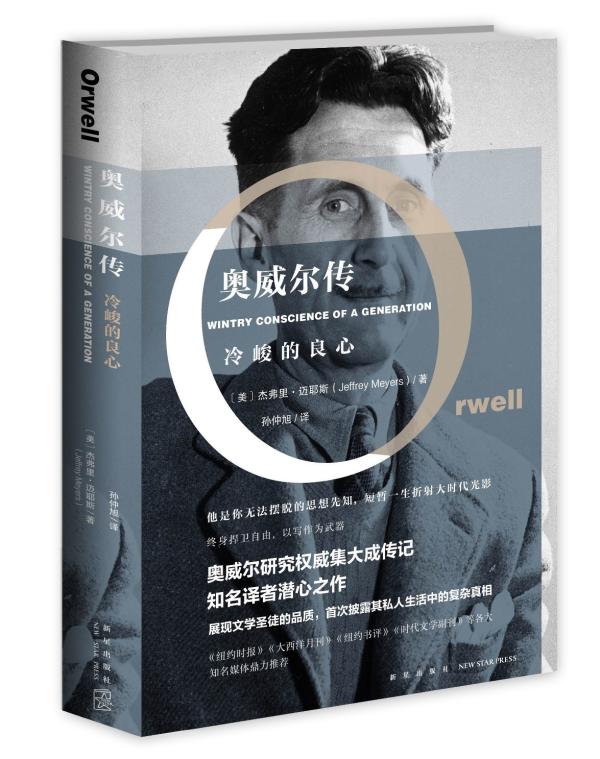
《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美]杰弗里·邁耶斯著,孫仲旭譯,新星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472頁,56.00元
香港“反修例事件”使香港警隊站到了風(fēng)口浪尖,這支曾以“皇家警察”命名的老牌警隊的歷史也備受關(guān)注。一般人并不了解,這支“世界最專業(yè)警隊”是以倫敦大都市警察局為樣板建立的,轉(zhuǎn)頭又成為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乃至整個上海警察系統(tǒng)的樣板,最初的上海巡捕即來自于從香港警察中招募的小隊英國人,“巡捕”也不過是對“police”的中式稱呼。“殖民地警察”與“租界巡捕”一體兩面,乃是“日不落帝國”在海外不可或缺的支柱。
說到“殖民地警察”,不可不提的是喬治·奧威爾,他在緬甸的五年(1922-1927)警察生涯到底與《1984》中令人聞風(fēng)喪膽的“秘密警察”角色塑造有何關(guān)聯(lián),一直是研究者關(guān)心的問題。這方面的力作當(dāng)屬杰弗里·邁耶斯的《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利用豐富的文獻(xiàn)資料還原了奧威爾不為人熟知的“緬甸歲月”。而在同時代的“租界巡捕”中,也有若干人物留下了自己的聲音,典型者如E.W.彼得斯和阿爾弗雷德·廷克勒,前者于1929年至1935年擔(dān)任上海租界巡捕,因被控酒后值勤時將乞丐拋入黃浦江的“毛德彪案”而知名,留下了類似“口述歷史”的《英國巡捕眼中的上海灘》;后者則是1919年至1930年間的上海巡捕,作為英國歷史學(xué)家羅伯特·畢可思研究的主角,在其著作《帝國造就了我:一個英國人在舊上海的往事》中“重生”。將這幾位“帝國警察”的歷史留聲略作比較,當(dāng)可見出“日不落帝國”在日落之際的光怪陸離。
“普通人”
1921年冬,原名埃里克·布萊爾的奧威爾從著名的伊頓公學(xué)畢業(yè),沒有選擇尋常的上大學(xué)或從軍、經(jīng)商之路,而是決定報考緬甸警察。他父親是兩年前才從印度殖民地的公務(wù)員崗位上退休回國的,這使得奧威爾“生下來就擔(dān)負(fù)上了殖民主義之罪”。他還有個外婆在緬甸,但“對埃里克有很強(qiáng)吸引力的是制服、金錢、冒險、危險、權(quán)威和半軍事性警察機(jī)關(guān),那讓他得以負(fù)責(zé)帝國的一小塊地方”。知情者稱,“在當(dāng)時,緬甸警察是個不錯的工作,工資相當(dāng)高”。他的年薪為四百四十四鎊加獎金,比他父親一年的養(yǎng)老金要高。
同樣不同尋常的是,奧威爾還得參加警察考試,他為此準(zhǔn)備了半年時間,參加了為期八天的考試,“科目包括拉丁語、希臘語、英語、法語、歷史、地理、數(shù)學(xué)和繪圖”。他的拉丁語得分最高,歷史和地理得分最低,最終成績在二十九人中排第七,在三個被派往緬甸的人中排第一(其他人報考的還有印度和孟加拉國)。其后又經(jīng)過了體檢和“勉強(qiáng)通過”的騎馬考試,他被任命為緬甸警察見習(xí)警官。
應(yīng)該是殖民地與租界要求不同的緣故,招募上海巡捕不需要考試的環(huán)節(jié)。作為退役士兵的廷克勒和彼得斯都只經(jīng)歷了“簡單”的面試和“嚴(yán)格”的體檢。羅伯特·畢可思在《帝國造就了我》中引用了上海工部局倫敦辦事處1919年刊登在《人民報》上的招聘巡捕的廣告,要求“應(yīng)征者必須未婚,身體健康,牙齒好。年齡約20-25歲,身高不低于5英尺10英寸(約178厘米),胸部完全擴(kuò)張約38英寸,能夠提供良好的品行推薦書”。待遇則是“初始薪水每月85塊銀元(約13英鎊)……配有慷慨的養(yǎng)老金計劃和2英鎊的津貼”。
畢可思對當(dāng)年招募的七十四名上海巡捕進(jìn)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他們中有勞工、農(nóng)場工人、礦工、管工助手、銀行職員、皇家海軍士兵,還有職業(yè)士兵,大約四分之一的人來自倫敦,少量來自蘇格蘭,其余的人多半來自英格蘭農(nóng)村。他們大多來自工人階級和底層,這種社會階層的情況也符合當(dāng)時英國國內(nèi)的警察狀況。畢可思的結(jié)論是,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招募的是“普通人”,“這證明了廣泛宣傳的關(guān)于這些人和帝國的浪漫主義想法的虛假”,他們不是上升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的年輕兒子,也不是在“更自由的”殖民地世界中尋求刺激。“研究中國歷史和殖民地歷史的學(xué)者長期以來假定上海工部局巡捕房由浪漫的冒險家組成,或者由暴力的黑人和黃種人組成。對殖民主義主觀上的敵對或者對它的懷舊的同情,歪曲了對殖民現(xiàn)實的正常事物的理解。”
對這些“普通人”,作為現(xiàn)代職業(yè)警察制度誕生地的英國自有一套體系性的訓(xùn)練方法。1919年的廷克勒到達(dá)上海后經(jīng)歷了“六個星期的艱苦訓(xùn)練”,包括每天一個小時的上海話,分配到各捕房之后還要用業(yè)余時間每天學(xué)習(xí)一個小時上海話,每月額外獲得一天假期作為補(bǔ)償。培訓(xùn)伴隨著考試,鑒于上海復(fù)雜的司法環(huán)境,《警察知識》是“非常困難的科目”,如“1925年的測試卷有這樣的問答題,以下國籍的外國人應(yīng)當(dāng)在什么法庭受審?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日本人?無國籍人?這種問題是這種特殊的工作環(huán)境中的核心問題”。1929年的彼得斯參加了三個月的培訓(xùn),“每天早上六點(diǎn)起來早操,內(nèi)容包括三英里的長跑和一些瑞典式鍛煉。每周有兩天可以不跑步,但是別的訓(xùn)練還要照常進(jìn)行。訓(xùn)練之后我們沖回宿舍,洗澡、吃飯,然后在九點(diǎn)鐘準(zhǔn)時開始理論培訓(xùn)。我們要上的課程包括警察法、初等數(shù)學(xué)、地理和常識知識”。他對實戰(zhàn)訓(xùn)練頗有微辭,“由于上海的搶劫和綁架非常猖狂,所以上海的巡捕不得不加練一些模擬這些情況發(fā)生時如何應(yīng)對的項目。我相信這些訓(xùn)練項目都是上海的巡捕房獨(dú)創(chuàng)的,世界其他任何國家的警察都不會需要這些訓(xùn)練”。
培訓(xùn)要求更高的是“殖民地警察”。奧威爾在緬甸曼德勒的警察訓(xùn)練學(xué)校足足待了十四個月,為“兩年實習(xí)期”必須通過的考試做準(zhǔn)備,科目有刑法、程序法、省警察法令和規(guī)定,以及兩門東方語言,其中一門除能說外,還要達(dá)到能讀能寫的較高標(biāo)準(zhǔn)。奧威爾憑借語言天賦輕松過關(guān),還獲得了不少獎金,這期間,他居然“從未去過一間警察局”。而在上海,“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語言始終是一個障礙……在指控室里很容易就依賴翻譯,依賴洋涇浜英語和下級以及公眾交流,掌握基本詞匯就可以勉強(qiáng)過活”。
“我們的麻煩在于,我們根本躲不開墮落”
引進(jìn)、擴(kuò)編和強(qiáng)化訓(xùn)練警察力量的現(xiàn)實需要來自而且不限于治安問題。上海實行的是復(fù)雜的“一城三治”(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模式,警察在追緝罪犯時不得不在“邊界”處止步,眼睜睜地看著罪犯逍遙法外。上海從二十世紀(jì)二十年代初開始犯罪率激增,到了1928年已經(jīng)被《字林西報》稱為“東方的犯罪中心”,“充斥著武裝搶劫、綁架、謀殺和毒品交易”,尤以法租界為甚。同時,“政治問題”也是一個焦點(diǎn)。“1919年后,新的公共行動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的政治情況徹底改變了上海的景象。”工部局認(rèn)為,勞工暴動、反日抵制、“布爾什維克思想”的蔓延、俄國難民將要大量涌入的可能性以及中國人政治活動的普遍增加造成了大量不可預(yù)知的威脅。“革命、政治運(yùn)動都被視為城市犯罪的一種形式。”(魏斐德《上海警察》)
在此背景下,招募巡捕包括華捕、印捕甚至日捕、俄捕成了必須。公共租界巡捕人數(shù)最多時達(dá)五千余人,法租界也達(dá)四千余人。但對這些人的素質(zhì),領(lǐng)導(dǎo)層并不放心。華捕收入極其微薄,是英捕的十分之一、日捕的七分之一,大量青幫混跡其中包娼庇賭、混水摸魚。黃金榮從法租界的探長成長為一代“大亨”,即為典型。1929年警務(wù)處長巴雷特提醒上海工部局說,“中國巡捕幾乎都不能靠薪水生存,尤其是生活在營房外的已婚男人”。印度巡捕被蔑稱為“紅頭阿三”,被指“怯懦、幼稚和野蠻”。彼得斯對白俄巡捕同行的評價則是“他們?nèi)藬?shù)不多,工作能力也很差,但是卻比其他人都能惹麻煩”。英國同胞似乎也靠不住,廷克勒的記錄表明他“在過去的18個月中,不止一次嚴(yán)重違紀(jì)”,最后因被降級而辭職,他在家信中宣稱“巡捕房里清白的人不超過6個”;對彼得斯等的一份官方報告稱“他們不擅長漢語,喜歡狂喝啤酒,退役士兵類型通常不太可靠,不過在管理下也不太壞”。
在“普通人”之外,畢可思也不忘指出這些人的“邊緣人”身份:“可想而知,任何地方的警察都尊貴不到哪里去”,盡管他們一個個身材高大制服整齊威風(fēng)凜凜,在上海灘街頭處處體現(xiàn)著殖民者的種族威權(quán),但在帝國體系中,他們本就出身于底層,即使成為巡警也走不出“大廈的底端”,始終被排除在精英之外,在現(xiàn)實中“知道了自己是邊緣人,他們?yōu)樵谏虾5耐鈬硕嬖凇薄5D(zhuǎn)過臉去,這些“帝國的仆人”也很快學(xué)會了支撐帝國的種族觀念,享受著比華捕高十倍有余的薪水,甚至回家也有仆人侍候,廷克勒的一名同事說“我們很快就適應(yīng)了,知道在需要東西的時候按鈴了”。在緬甸的奧威爾也有仆人,在訓(xùn)練仆人為自己脫衣穿衣的同時,他“把衣服和煙蒂都往地板上丟,讓仆役撿”。
警察職業(yè)不可避免地要與種種社會悲劇打交道,而這有時會成為難得的寫作素材。彼得斯在《英國巡捕眼中的上海灘》中細(xì)致描述了他經(jīng)歷過的死刑場景。 “幾個看起來陰沉狡詐的中國獄卒打開了監(jiān)獄的大門。從這些人身上一點(diǎn)看不到人性的存在,讓我覺得像是等待撲向獵物的禿鷲,我最不情愿的莫過于和這些人共處一室”,三個死刑犯“似乎已經(jīng)完全拋棄了對死亡的恐懼,還互相開著玩笑,內(nèi)容仍然是詛咒把自己抓住的偵探,以及自己早晚會回來找他們報仇之類”,行刑后“一些中國的婦女和孩子沖到刑場上,把一些銅錢浸到死者的鮮血中,甚至有一個女孩拿了好多糕點(diǎn)泡在血里,而她們這么做的原因是據(jù)說可以保佑自己的家庭不受惡靈騷擾”。
奧威爾的小說《緬甸歲月》,被董樂山稱為“平庸之作”,沒有太多描述英國警察的角色,但另外兩篇涉及他警察生涯的散文《射象》和《絞刑》,無疑是他的早期文章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后者更被視為他的“第一篇出色作品”。他細(xì)致描寫了自己親身經(jīng)歷過的一次絞刑,一個聽到上訴被駁回時尿到地上的死囚在前往行刑的路上,下意識地往旁邊跨開一步,以避過路上的一個水坑——似乎害怕被處決時著涼。奧威爾寫道:“那一刻之前,我未曾意識到那意味著摧毀一個健康、有意識的人。看到那個死囚邁向旁邊以避開水坑時,我認(rèn)識到將一個生命正當(dāng)盛年時令其中斷一事的不可理解及錯得可怕之處。” 他在筆記本中甚至更進(jìn)一步點(diǎn)明這篇文章的內(nèi)在主題:“當(dāng)一個殺人犯被絞死時,在此儀式上只有一人未犯殺人罪。”研究者指出,“這是他首次本能地表現(xiàn)出了人道主義,并成了他所有作品的特點(diǎn)”。邁耶斯認(rèn)為,這是奧威爾唯一一次經(jīng)歷絞刑,盡管如此,他敏感的筆觸卻能從獵奇的敘述上升到文學(xué)和人道的層面,這也是奧威爾之所以成為奧威爾的原因。
“帝國總是一樁虛張聲勢的事業(yè)”
大英帝國是十九世紀(jì)全球政治的象征。英國人用了六十來年的時間,通過三次戰(zhàn)爭,于1886年將緬甸并入了英屬印度,實現(xiàn)了完全控制,由英籍軍官指揮的一萬兩千名武裝印度兵足以彈壓緬甸一千四百萬人口。英國人相信他們的工作是把“法律和秩序帶到野蠻之地”。然而,正如一位緬甸歷史學(xué)家所言:“1919年前,英國人和緬甸人是朋友;1930年后,他們只是政治上的對手;但在1919至1930年之間的黑暗時期,他們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互相鄙視。”奧威爾一開始也未能免俗,在《緬甸歲月》中,他以明顯種族主義的口吻稱曼德勒是“一個非常令人討厭的城市——多塵,炎熱得難以忍受,據(jù)說它有五種以P開頭的主要出產(chǎn),即佛塔、賤民、豬、牧師和妓女”。就其本人而言,他在緬甸沒有交到一個本地朋友,甚至在警察同事之間,他還把唯一一個緬甸籍同事的名字用來命名自己小說中的一個大惡棍。盡管奧威爾有“巨細(xì)無遺地處理案件時對絕對公平的追求”,但“他當(dāng)?shù)蹏飚?dāng)?shù)猛纯啵忉屵^不懲罰、不打人的理論在(伊頓)公學(xué)非常管用,但在緬甸人身上行不通”。最令他心煩意亂的可能是在拒買英國貨運(yùn)動中普遍參與政治運(yùn)動的僧侶學(xué)生們,“他們手持短棍到處走動并擊打那些被發(fā)現(xiàn)使用英國貨的人”,還在街頭或足球場譏笑外國人(畢可思也認(rèn)為,被中國人取笑是在上海的英國人最不能容忍的,這個理由還可以在法庭供述和書面報告中當(dāng)作能使輕微暴力行為合法化的理由)。當(dāng)奧威爾正式成為作家之后,他在一篇隨筆中寫道:“當(dāng)時我根本不知道大英帝國已日暮途窮,更不知道和即將替代它的那些歷史短一些的帝國比起來,它還是要好得多。我只知道自己夾在兩種感情中間,一是憎恨我為之服務(wù)的帝國,一是對那些盡力讓我無法工作的心地陰險的小畜生們感到憤怒。我一方面認(rèn)為英國對印度的統(tǒng)治是難以動搖的暴政……違背了被征服人民的意愿;另一方面我認(rèn)為世界上最開心之事,莫過于把刺刀捅進(jìn)一個和尚的肚子。”
上海的情況顯然比緬甸更為復(fù)雜,畢竟英國人在緬甸只需要九十名英籍警官,在上海則需要近五百名。1922年,上海公共租界警務(wù)處的一名副處長警告稱“中國大眾‘溫順和服從’的日子已經(jīng)一去不復(fù)返了”。但上海巡捕一貫敢于“在人群擁擠的街道開火”,特別是當(dāng)這群人不過是中國人的時候。1925年,英國巡捕針對在租界內(nèi)散發(fā)傳單的游行學(xué)生開槍轟擊,釀成十三人死亡的五卅慘案,中國政府外交部指其既未事先鳴槍警告,又“據(jù)報告所有傷斃之人,槍彈多從背入,巡捕無一死傷,顯系任意轟擊,毫無理由”,事后僅對兩人免職退休了事。廷克勒便是參與鎮(zhèn)壓的巡捕之一,意識到了危機(jī)的他并未體現(xiàn)出反省意識,反而狂妄地聲稱“只有戰(zhàn)爭才能讓白人還有可能在中國居住”。在國民黨北伐期間,已經(jīng)調(diào)往情報室工作的廷克勒不無先見之明地斷言,如果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沒有被重新收回,“帝國在幾年之后將衰退到十分之一的實力(它已經(jīng)是一個二流國家了)”。面對新的國民政府雄心勃勃的“大上海”建設(shè)計劃對租界主權(quán)的爭奪,公共租界放低了姿態(tài),一面積極協(xié)助國民黨鎮(zhèn)壓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一面勉力維持自己對租界的統(tǒng)治,警務(wù)處長巴雷特向工部局“實誠”地報告,“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希望有一支龐大警力以供調(diào)度支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讓這一組織更加完善,以盡可能地阻止華人團(tuán)體奪回租界控制權(quán)”。
想奪得租界控制權(quán)的并不止于“華人團(tuán)體”,還有想建立新的殖民體系的日本帝國,對此強(qiáng)敵,大英帝國頗有色厲內(nèi)荏之嫌。這一點(diǎn)在彼得斯的書中多有體現(xiàn)。1930年加入上海巡捕的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日本巡捕“實際上由他們自己的官員負(fù)責(zé)監(jiān)督,雖然我們名義上也管理他們,但是其實我們已經(jīng)被上級告知要少管閑事”,“事實上任何日本國民或者日本的附屬國的國民,與巡捕發(fā)生任何沖突,日本領(lǐng)事都要進(jìn)行調(diào)查,而且最后結(jié)果一定是他們的國民沒錯,然后他們就會要求巡捕房道歉,而奇怪的是巡捕房總是會答應(yīng)道歉,以日本在上海的權(quán)利和影響力,他們總能得到他們想要的”。特別是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后,“日本人在上海的勢力和特權(quán)明顯升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們現(xiàn)在甚至可以做許多別國人不敢做的事,而且完全不用承擔(dān)任何責(zé)任”,“事實證明,現(xiàn)在日本人才是在上海最有特權(quán)的人,一次我在值班室執(zhí)勤的時候,警務(wù)處處長親自過來前來視察,臨走還不忘告訴我們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對日本人更加有禮”,“直到今天,我們英國人還是上海公共租界里最有影響力的人,而我要說我們巡捕房是維護(hù)英國國家聲望的重要工具,但是如果英國巡捕都要對日本人唯命是從,甚至對他們的不法行為坐視不管的話,每個自尊自愛的英國人離開上海的時候也就到了”。并不意外,在“孤島時期”,公共租界巡捕房只能乖乖地將抓獲的國民黨特工作為“恐怖分子”移交給日本憲兵隊,并委任一名日本人作為警務(wù)處特別副處長,充當(dāng)自己的“太上皇”。對前巡捕廷克勒在一場沖突中被日本軍人毆打致死的命運(yùn),他們也漠然接受。但這些都未改變他們最后被完全剝奪租界權(quán)力的命運(yùn),工部局巡捕房有一段時間成了沒有英國人的巡捕房,然后被日本人交給了汪偽政權(quán)的警察局。而在香港,英國人也迅速潰敗投降,二戰(zhàn)后才卷土重來,又統(tǒng)治了半個世紀(jì)。從縮水的大英帝國殖民地返回的警察,不少成了秘密情報組織的成員,后來成為著名間諜小說家的原軍情五處職員勒卡雷在自傳《鴿子隧道》中評論道,“面對那些拼命想把自己國家搶回來,甚至不惜采取莽撞行動的當(dāng)?shù)厝耍麄兓蛟S有著豐富的鎮(zhèn)壓經(jīng)驗。但是,面對他們自己幾乎都不怎么理解的祖國,情況就顯得有些令人不安了”。與帶有文明抱負(fù)的羅馬帝國相比,大英帝國滿足于政治算計和斤斤計較,其在“非殖民地化時期”的“精心撤退制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自相殘殺”,包括印巴分治、巴勒斯坦問題、土耳其的問題、中東領(lǐng)土糾紛、南非種族問題、新馬問題以及香港問題等等,被強(qiáng)世功稱之為“歷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國”。
奧威爾于1927年9月離開緬甸,他后來寫道:“我之所以辭了那份工作,部分是因為那里的氣候已經(jīng)毀了我的健康,部分是因為我已經(jīng)有了寫書的模糊念頭,但主要是因為我無法再為帝國主義服務(wù),當(dāng)時,在很大程度上我已將其視作一場騙局。”“當(dāng)一個被統(tǒng)治民族奮起反抗時,你必須鎮(zhèn)壓,這樣做時,你不得已采取的鎮(zhèn)壓手段讓所謂西方文明更為優(yōu)越的斷言不攻自破。為了統(tǒng)治野蠻人,你只能自己也變成一個野蠻人。”研究者稱奧威爾的寫作是“復(fù)原及清除自己內(nèi)在野蠻人一面的漫長過程”。在更加暴力化的上海,廷克勒和彼得斯都沒能和奧威爾一樣自覺停止“野蠻化”的進(jìn)程,被畢可思疑惑著“為什么對這個世界如此惱怒”的廷克勒在上海迎來了自己暴力化的死亡,而彼得斯卻冷酷無情地隨意制造了他人暴力化的死亡,也因此幾乎毀掉了自己。
假設(shè)奧威爾當(dāng)初選擇了上海或許是件有趣的事。無疑他將經(jīng)歷更多的槍戰(zhàn)和絞刑,更將經(jīng)歷一系列歷史性的事件,包括五卅慘案和“四一二”,也可能會成為另一個以描述中國革命而成名的馬爾羅,無論如何,他終將明了少年時一直“被教導(dǎo)相信”的帝國主義的特性,認(rèn)識到英國人所言“沒有永遠(yuǎn)的朋友,也沒有永遠(yuǎn)的敵人,只有永遠(yuǎn)的利益”的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