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學星評《俄羅斯文學》 “迷宮”內(nèi)外的普希金與俄國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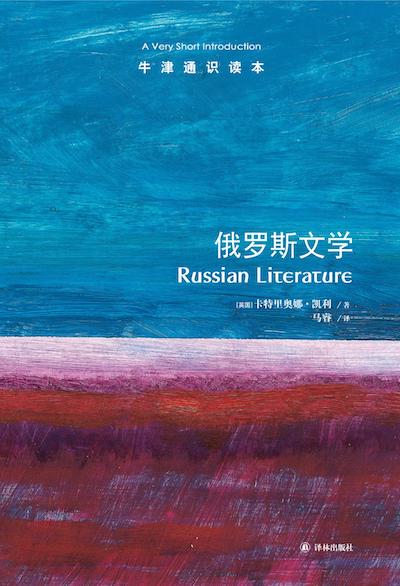
《俄羅斯文學》,[英]卡特里奧娜·凱利著,馬睿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72頁,39.00元
譯林出版社引進了牛津通識讀本叢書,其中包括卡特里奧娜·凱利所著的《俄羅斯文學》。該書已由馬睿譯出,并于2019年12月正式出版。作者凱利是牛津大學的教授,她在“前言”中已明確,不希望把這個讀本寫成一部“循規(guī)蹈矩的文學史”。那么,究竟要怎樣寫,會寫成什么樣?初讀下來,發(fā)現(xiàn)這本書的寫作確實與眾不同,既不是作家生平與作品的羅列,也不是對文學運動的概述或文學鑒賞。凱利的做法頗為獨特,她將普希金的《“紀念碑”》一詩拆解開來,從中挑出七句詩來表征作家崇拜等俄國文學傳統(tǒng),并將這些傳統(tǒng)一一揭示出來。在完成拆解“紀念碑”這一步驟后,凱利開始“拆解”七句詩所表征的俄國文學傳統(tǒng)。借助這些 “路標”,凱利開啟了對俄羅斯文學這座“迷宮”的“發(fā)現(xiàn)之旅”,并使之呈現(xiàn)出立體性、動態(tài)性和開放性。
1836年,普希金創(chuàng)作了被當作“文學遺囑”的一首詩,名為《“我為自己豎起來一座非手造的紀念碑”》,全詩分五個小節(jié),共計二十行。凱利在撰寫《俄羅斯文學》一書時,將普希金的這首詩作為抓手。在該書的“前言”和第一章中,作者對該書的寫作方法,尤其對選擇“紀念碑”作為抓手的原因作了說明:“不光有助于了解這首詩本身的意義,至少同樣有助于了解俄羅斯文化價值觀的演變”,還在于“在短短的五小節(jié)二十行詩中,它提出了七個主題,它們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俄羅斯文化中引起了廣泛共鳴”。

普希金
第一章以詩句“我為自己豎起來一座紀念碑”為標題,主要探討作家紀念物和作家崇拜現(xiàn)象,揭示了各種形式的紀念碑被賦予的意義。第二章選用詩句“我的名字將傳遍偉大的俄羅斯”,認為普希金更希望讓作品成為自己的“紀念碑”,討論了文學作品的傳播問題,涉及十八世紀末開始的圖書審查制度、文學“進步性”、審美保守主義等文學和文化現(xiàn)象。第三章以《“紀念碑”》第二小節(jié)中的詩句為標題“我的名字會遠揚,哪怕僅僅有一個詩人流傳”,既展示了普希金對后世作家的影響,譬如《青銅騎士》在安德烈·別雷的現(xiàn)代主義小說《彼得堡》中的回響等,也指出普希金在文學語言、體裁創(chuàng)新等方面發(fā)揮的作用有被夸大之嫌,譬如他“沒有為鴻篇巨制的心理小說提供典范”,托爾斯泰、契訶夫、布羅茨基、西尼亞夫斯基等不同時代的作家都有“反普希金”的表現(xiàn)。第五章題為“我的詩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討論在俄羅斯習慣于將作家看作“思想大師”這一傳統(tǒng)和現(xiàn)象:別林斯基希望普希金創(chuàng)作“有著無懈可擊的嚴肅性和對全民族的重要意義”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強調(diào)其社會責任”,托爾斯泰主張藝術(shù)要“致力于善的傳播”等,話題涉及到權(quán)力、意識形態(tài)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談到了作家們的“道德妥協(xié)”現(xiàn)象,并指出西方讀者對俄羅斯文學的期待:“許多西方讀者希望俄羅斯作家為他們提供直接無反諷的倫理問題討論,全然不顧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這些在西方早已過時。”第六章以詩句“和愚蠢的人們又何必較量”為題,探討女性寫作問題。第七章“她的各族的語言都將把我呼喚”,主要討論了普希金、萊蒙托夫等人所代表的俄羅斯文學傳統(tǒng)中的“中心意識”,指出:“19世紀和20世紀的俄羅斯作家都棲居在一種帝國意識之上,他們往往將非俄羅斯人看成多彩的民族學展品,看成或古怪或有趣的他者。”第八章“哦,詩神,繼續(xù)聽從上帝的意旨吧”,探討俄羅斯文學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guān)系,認為俄羅斯文學的獨特性“恰恰在于它能夠擁抱精神和物質(zhì)兩個世界”。在全書的最后,作者提醒讀者不要誤以為“已經(jīng)抵達了迷宮的中心”:“相反,這樣的中心并不存在: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條回到起點的小徑入口。”
凱利在讀本最后所說的“回到起點”,既表明她對俄羅斯文學的介紹已告一段落,也是一種提示,希望讀者意識到這本書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史,它對任何作家、作品或文學現(xiàn)象都未做出“定論”。顯然,這不是人們通常見到的那種文學史,而是從社會文化視角中呈現(xiàn)出來的一種文學歷程,是一部鮮活的文學史,其首要的一個特征即為立體性。
我們知道,在平面造型藝術(shù)中,要獲得立體性的效果,需要借助明暗、透視、色彩等藝術(shù)造型手段。在這部《俄羅斯文學》中,突出明暗關(guān)系成為體現(xiàn)人物或創(chuàng)作之立體性的方法之一。時至今日,歷經(jīng)二百多年,俄羅斯歷史上早就形成了“普希金神話”,普希金被譽為“俄羅斯文學之父”,被稱作“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如果采用視覺感受形成的明暗關(guān)系去判斷,對普希金的這些稱頌顯然屬于“明”的一面。要體現(xiàn)普希金這個人物的立體性,自然需要補全其“暗”的一面。為了獲得真切的視覺印象,明與暗缺一不可。普希金有時讓人覺得陌生,蓋源于此:“對普希金感覺陌生的不光是外國人,俄羅斯評論家也談到過這一點。親西方的評論家認為,這表明普希金是真正的文明人,是可恥的落后社會中的一枝獨秀;而在民族主義者看來,這是個重大的悲劇,象征著知識分子與‘俄國人民’的疏離。”
在意識到普希金身上存在明暗關(guān)系不合理這一缺陷后,作者凱利在撰寫《俄羅斯文學》這本書時采取了多種手段,她要為光彩照人的普希金形象補上“暗影”,以使之獲得立體效果。譬如,在提到1880年開始矗立在莫斯科普希金廣場上的雕像時,除了談到這座普希金雕像巧妙地表現(xiàn)出詩人靈感乍現(xiàn)的瞬間外,還談到雕像留給列夫·托爾斯泰的印象:像一個男仆在向主人宣布“上菜了”。更為可笑的是,在雕像的底座上,竟然鐫刻著《“紀念碑”》這首詩,而這首詩的“主題恰恰是將詩歌的活的豐碑與死沉的金石截然對立”。此外,書中還談到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賭,酷愛醋栗果醬,而托爾斯泰對上述四樣中的至少三樣同樣偏愛有加”。在論及普希金的創(chuàng)作時,認為普希金的代表作《葉甫蓋尼·奧涅金》并非別林斯基所謂的“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而是“偷聽八卦的有趣篇章和‘操縱情節(jié)’的實例”。在介紹普希金有“民族詩人”稱號的同時,也沒有回避披薩列夫的評論,后者曾稱《一八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一詩為“通篇押韻的胡言亂語”。在提及普希金的《青銅騎士》《黑桃皇后》等作品時,也不忘關(guān)注他的秘密作品如《加百列頌》等。當然,在介紹其他作家或作品時,同樣未曾忘記這種明暗關(guān)系,譬如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普遍人類自由的預(yù)言家”之時,不忘指出他在《作家日記》(1876-1881)中顯而易見的泛斯拉夫彌賽亞主義和反猶主義。簡言之,凡書中論及的作家或作品都沒有被簡單地蓋棺定論,圍繞著他(它)們的爭論仍在繼續(xù):對作家形象的塑造體現(xiàn)著明與暗的依存關(guān)系,對作品的解讀和評價保持著褒與貶的對立狀態(tài)。所有這些努力都在回避“定論”,而是指向作者凱利所說的目標——“回到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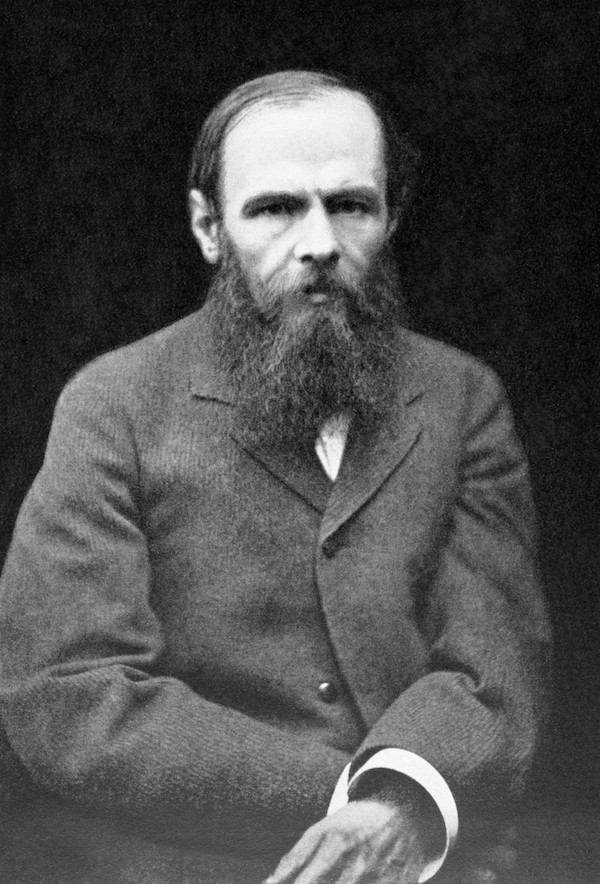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
動態(tài)性可視作《俄羅斯文學》寫作策略的第二個特點。在介紹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時,將其在不同評論家、不同思潮、不同時代語境下所獲得的“狀態(tài)”呈現(xiàn)出來,即是我們所說的動態(tài)性。動態(tài)是相對于靜態(tài)而言的,在文學史寫作中留心并體現(xiàn)動態(tài)變化,自然有助于擺脫刻板而僵化的寫作范式,避免將文學史變成簡單的資料羅列。這種動態(tài)性體現(xiàn)在全書的每一部分,限于篇幅,在此僅以第三章為例加以說明。第三章談?wù)摰闹黝}是“普希金與俄羅斯文學正典”,討論了普希金及其作品在歷史長河中經(jīng)歷的跌宕起伏,人們對詩人的態(tài)度多有變化,呈現(xiàn)出一種動態(tài)過程。
在十八世紀末,作家的作者身份得到強調(diào),開始實行圖書審查制度,旨在讓作者對自己所寫的東西負責,不再提倡匿名出版。此時,“俄羅斯需要能和法國、德國或英國文學分庭抗禮的文學”,這種局面讓普希金有了使命感,意識到自己有可能成為“民族詩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評論家皮薩列夫評價普希金的一首詩為“通篇押韻的胡言亂語”。1880年在莫斯科豎立普希金紀念碑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講話和屠格涅夫的致辭都充滿了溢美之詞。1898年托爾斯泰在《藝術(shù)論》中,“譏諷人們居然把普希金這么一個花花公子和好色之徒塑造成民族圣賢”。1899年,普希金誕辰一百周年,人們對“民族詩人普希金”的崇拜有增無減。二十世紀初,相對于契訶夫、果戈理、拉季舍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高爾基和托爾斯泰,普希金并不受歡迎。在將進步性作為衡量尺牘的年代,詩人普希金要讓步于羅蒙諾索夫、涅克拉索夫等人。1920年代,“普希金被認為是藝術(shù)天分極高但觀點可疑的人”。1949年普希金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被譽為“天才中的天才”。后來,由于審美保守主義泛濫,人們能讀到的普希金作品僅有兩部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和《上尉的女兒》。這一章從圖書審查制度談起,考察了普希金的形象建構(gòu)及其作品在解讀或評價上的動態(tài)性變化,讓讀者置身于社會歷史文化的“斗轉(zhuǎn)星移”之中,參悟與思考俄羅斯文學的現(xiàn)象與特質(zh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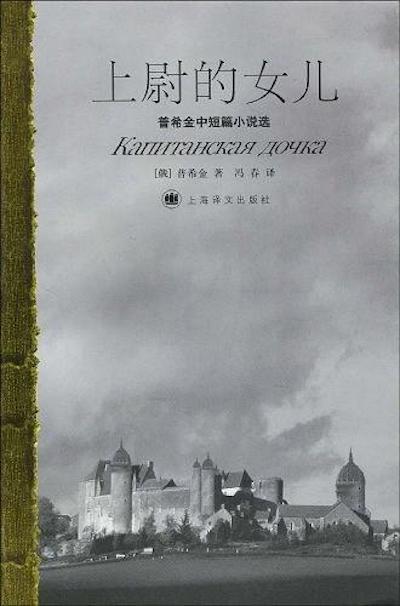
《上尉的女兒》
開放性可算作《俄羅斯文學》寫作策略的第三個特點,表現(xiàn)為敘述角度的對話潛質(zhì)、問題討論的未完成性等多個方面。開放性與前面提到的兩個特點(立體性、動態(tài)性)相輔相成,共同展示作者凱利的一種姿態(tài),即她歡迎廣大同行與讀者參與討論。
首先,《俄羅斯文學》一書的敘述角度具有對話潛質(zhì)。正如該書的序言作者劉文飛教授所言,西方作者“似乎更愿意從文化史、思想史、民族精神發(fā)展史的角度來打量俄羅斯文學”,這明顯有別于采用進步性、人民性等概念去考察俄羅斯文學的習慣做法。本書作者凱利作為西方學者,她在介紹俄羅斯文學時,所采取的敘述角度更具西方特色。相對于羅列作品清單等文學史寫作“套路”,凱利的做法簡直屬于離經(jīng)叛道。除了凱利挑中的《“紀念碑”》的七句詩,其余十三句詩為何沒被選中?它們是否也能發(fā)揮“路標”的作用呢?《俄羅斯文學》一書在章節(jié)和主題設(shè)計等方面不走尋常路,由此帶來的“發(fā)現(xiàn)”也不會尋常,這必然導(dǎo)致該書與傳統(tǒng)文學史之間的對話。
此外,開放性還表現(xiàn)為問題討論的未完成性。就拿對普希金的評價來說,我們在“前言”中讀到的話是這樣的:“普希金與但丁、莎士比亞或歌德一樣,天賦異稟,思想深邃;閱讀他的作品回報頗豐。”而書中另一處則提到,“普希金崇拜的浮夸風氣惹得人們把他理解為小丑、游戲者、可與之‘散漫溜達’的討喜熟人”。作者之所以同時提供性質(zhì)絕然不同的信息,是想讓讀者們更真切地感受到問題討論正處于“進行時”。作者忙于張羅一場超越時空的圓桌會議,邀請普希金的不少同行參加討論,發(fā)言者立場各有不同,甚至針鋒相對:別林斯基宣稱:“每一位受過教育的俄國人都應(yīng)當擁有一部普希金全集,否則他就沒有資格聲稱自己受過教育或聲稱自己是俄國人。”托爾斯泰則稱普希金是“花花公子和好色之徒”,布羅茨基在《獻給瑪麗婭·斯圖亞特的二十首十四行詩》中,不無嘲諷地戲仿普希金的《“我愛過您”》……
我們知道,開放性是相對于封閉性而言的。作者在書中并置各種“他者”的聲音,無形中讓作家或作品保持著“熱度”,表現(xiàn)出活力,從而脫離封閉狀態(tài)。《俄羅斯文學》的寫作策略具有開放性,還在于它重視考察俄羅斯作家與西方作家之間的影響關(guān)系。譬如,談到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與簡·奧斯汀的《勸導(dǎo)》、維克拉姆塞斯的《金門》之間的相似性,談到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寧娜》與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之間的關(guān)系,狄更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阿赫瑪托娃對T. S. 艾略特和詹姆斯·喬伊斯的崇拜,茨維塔耶娃對賽珍珠的癡迷等。

列夫·托爾斯泰
《俄羅斯文學》一書的作者以超人的學術(shù)勇氣、開闊的視野和深厚的學養(yǎng),拋開羅列作家或作品清單的文學史慣常做法,而是聚焦俄羅斯文學的熱點問題,追根溯源,旁征博引,將俄羅斯文學生態(tài)的立體畫面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確,《俄羅斯文學》不是一本“循規(guī)蹈矩的文學史”,沒有流于固化知識的陳述,而是如該書作者所希望的那樣,旨在“激發(fā)思考,激起爭論”。總之,這是一本不落俗套的書,無論是書的寫法,還是書的內(nèi)容,當然還有譯文的精準,都能激起閱讀的興趣,給我們的認知帶來一份新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