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普克納談世界文學、宣言與戲劇
哈佛大學戲劇、英語文學與比較文學“拜倫和安妮塔·維恩”講席教授馬丁·普克納(Martin Puchner)最新被翻譯為中文的著作《文字的力量》(The Written World: The Power of Stories to Shape People, History, Civilization)是一部文學的全球史。去年,《上海書評》在清華大學專訪了普克納教授,請他談談世界文學,以及他關于宣言(manifesto)這一文類的研究,和他在哈佛的戲劇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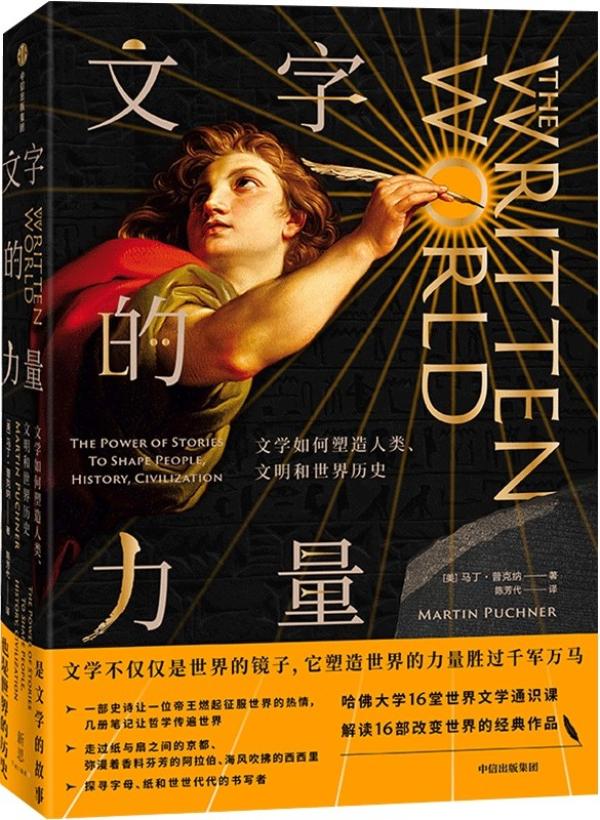
《文字的力量:文學如何塑造人類、文明和世界歷史》,[美]馬丁·普克納著,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7月出版,448頁,58.00元
一個真正的全球故事
您是第三、第四版《諾頓世界文學選集》的主編,也在哈佛大學教世界文學課,能先從教學(pedagogical)角度談談世界文學嗎?從學術角度看,目前世界文學研究有頗多路線,比如莫雷蒂(Franco Moretti)和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的做法,主要取徑于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分析,而您的同事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則在精神上更接近歌德的世界主義,保留了“世界文學杰作”正典的觀念。換言之,今天隱隱存在著體系論者(systematizers)和文本細讀者(close-readers)之爭。在這個學術語境里,您如何定位《文字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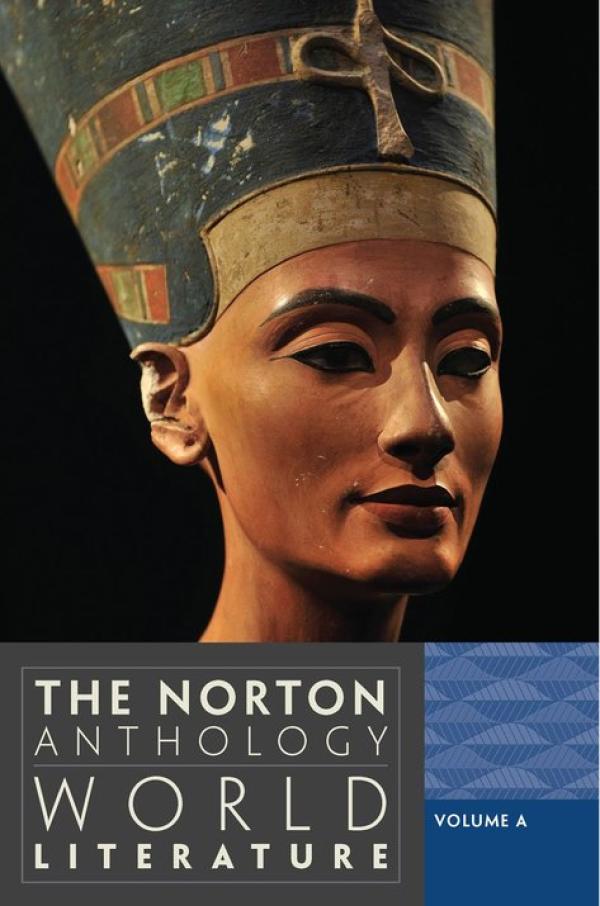
普克納主編《諾頓世界文學選集》,W. W. 諾頓出版社,2012年第三版,2018年第四版
普克納:我最初和世界文學結緣就和教學法、教學工作相關。如你所知,我最早的兩本書主要聚焦于現(xiàn)代主義,后來,通過編輯《諾頓世界文學選集》,我開始涉足世界文學。這部選集雖然是由一個學者團隊編纂的,但卻是教學用書,在美國的一千多所學校,主要是本科院校——也有一些高中和研究生院——使用。我們將不同地域的文本納入一個宏觀圖景,突出各國文學在歷史上的交往和歷史性關聯(lián),以及一些重要母題在不同作家那里的變奏。我也拜訪了很多開設大型導論課的本科院校,和授課老師交流。在這個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對世界文學的向往往往來自偏遠地區(qū),越是地方偏僻、排名不高的學校,對世界文學導論課程的需求就越強。世界文學給那些不太有機會去海外旅行的學生提供了一個認識世界的機會。我當然也會從更學術的角度更理論地來思考世界文學,但對我而言,我總會回到教學問題,部分是因為,我覺得眼下從事人文學科的人努力去激發(fā)學生,去向更大范圍的公眾發(fā)聲,是很要緊的,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技術驅動的世界里。我想很多學者過于與世隔絕了,他們只對自己狹隘的專業(yè)領域感興趣。而對于我,這個教學的觀念,激起學生和一般讀者對于文學的興趣的觀念,變得越來越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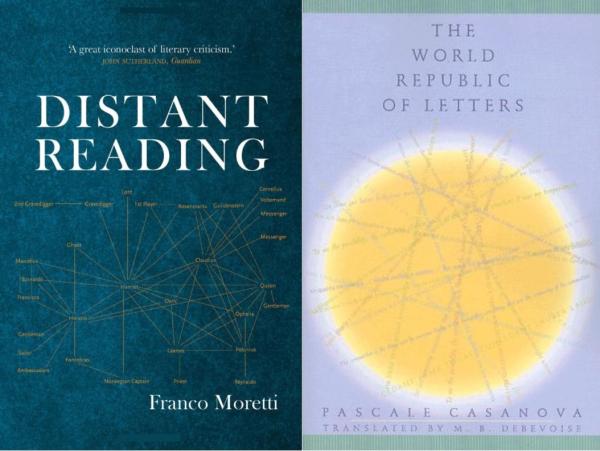
莫雷蒂著《遠讀》和卡薩諾瓦著《文學世界共和國》
應該說,我是弗朗哥·莫雷蒂和他的數(shù)字人文方法的崇拜者。我想在所有做數(shù)字人文的人里,他是概念上最有意思的。我非常欣賞他的“遠讀”(distant reading)概念,以及他看待文類發(fā)展、做量化分析的方式。我希望更多人文領域的學者適應它。我自己,如你所知,并沒有走這條路。當然,我同樣試圖著眼于大局,這點是我和莫雷蒂共享的,但我也設法把這種大局觀和某種程度的細讀結合起來。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另一件事對我很重要:成文(written)故事的歷史。我想,我既然關于講故事寫了那么多,也應該想想自己要寫怎樣的故事。于是,我努力把各種理論觀念鑲嵌在故事和人物中,這么做或許可以讓這本書抵達更多的公眾。無疑,在它背后是有理論觀念的,但我試圖把它們嵌在各種場景里,而非發(fā)展出一個純粹的理論框架。這是我的方法,但我從莫雷蒂和帕斯卡爾·卡薩諾瓦那里學到很多。后者更側重于更晚近的文學,以及出版機制、翻譯者、中介這些。我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方法,也許,她過于強調巴黎了,當然這也沒關系,但是在我看來,對于一段漫長的歷史,比如我講述的四千年的歷史,這不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我甚至覺得按這么寫是不可能的,它更適合處理過去幾百年的歷史。
我注意到,《文字的力量》每章第一條注釋幾乎都是致謝。您感謝某位朋友對本章內容的幫助,而這位朋友通常是該章所涉領域的專業(yè)學者。您如何看待作為綜合學問(synthetic scholarship)的世界文學寫作,以及在這個意義上,您本人所扮演的匯集者(assembler)的角色?世界文學研究與某一領域——比如一部經典、一個文類、一國之文學的研究之間是什么關系?
普克納:顯然,沒有人可以精通所有這些文學,所以要寫這樣一本書,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許多其他學者的工作。如果不是和那么多人一起編輯諾頓選集,我肯定不會寫目前這本書。某種意義上,你可以說它的起源就是合作性的。當我們一群人聚在一起,考慮如何安置這些文學,我從編委會的其他成員那里受益匪淺。后來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就利用了這個網絡,我請他們閱讀這些章節(jié),以確保我不犯錯誤。存在綜合性的一面是毋庸置疑的,某種勞動分工也是必要的,我確實要依靠很多其他人的成果。
與此同時,有意思的是,通過合而觀之,通過拉遠鏡頭,我突然看到了在這些專門領域里耕耘的學者未必能發(fā)現(xiàn)的關聯(lián)和線索。我看到了很多模式(patterns),并且我所謂的模式和莫雷蒂意義上的模式并不是一回事:比如,神圣文本總是新書寫技術的早期采用者,因為它們通常處于書寫(writing)文化的中心,因而也處于從新技術獲益的最佳位置;又比如,文學生產成本的降低總會造成通俗故事一定程度上的激增,《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世界和歐洲傳播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因為新技術使進入書文(written)世界的門檻變低。諸如此類的模式只有當你把各種分散的東西放在一起看的時候才能顯現(xiàn)。所以我會說,誠然,這是基于大量他人研究的綜合學問,但在你勾畫的這幅大圖畫里,仍然有原創(chuàng)性的成分。
總的來說,寫這本書使我不僅對在每一章幫助過我的學者心存感激,也對所有其他區(qū)域研究的學者滿懷敬意。我不反對專業(yè)化,不是所有人都應該寫《文字的力量》這樣的書,但是總該有人寫,并且應該有更多這樣的書。我想一些人已經漸漸開始做這樣的研究了,開始把專門學問結合起來了。我有時候認為,作為一門學科,文學研究幾乎讓人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非常狹隘的領域,極少有人把鏡頭拉遠:為了一門學科健康發(fā)展,我們兩方面都要。
《文字的力量》的故事線是沿著上層建筑(superstructure)和下層結構(infrastructure)的此呼彼應展開的:文學的民主化——處于支配地位的講故事的人,從一小群抄寫員,到超凡魅力型教師,再向個體作者、大眾逐漸遷移——與書寫技術發(fā)明的演變聯(lián)結在了一起。尤其,書中一些人物和作品會被選中討論,是取決于下層結構的標準。您為什么要講述這么一個“唯物主義”的故事?
普克納:一定意義上,確實如你所說。最終,我想,這本書關注的焦點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自身的經驗所決定的: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史上罕見的下層結構發(fā)生變化的時刻——如果用你的說法的話。某種程度上,我試圖做的是,回望文學史的深處,看看更早的那些因技術變革而使文學的內容或性質發(fā)生變化的時刻。所以我認為,我的焦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當下的焦點。這里部分的原因是,有人說現(xiàn)在這個時代,學生不再閱讀了,再沒有好的文學寫出來了,我認為這種說法都是非歷史的。我試圖把一個歷史的維度帶入我們當前的辯論。我覺得這是歷史學家和人文學者可以貢獻的。我一直在提諾頓選集,因為確實有很多東西是因為編選集而來的。當我們浸淫在所有這些文學里,比較不同的文化,我被這些下層結構的問題,比如書寫系統(tǒng)、書寫界面、發(fā)行系統(tǒng),所深深觸動。對我而言,這是一條實實在在的線索。
另外,我還很喜歡的一點是:這是一個全球的故事。不同于相對狹窄的文類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莫雷蒂成了某種播散論者(diffusionist),比如按照他的模型,現(xiàn)代戲劇在歐洲被發(fā)明,然后輸入到了中國——我講述的下層結構的故事則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故事。
前路恰在身后:口傳、書傳、原教旨主義
《文字的力量》所呈現(xiàn)的還是一部關于口述(orality)和書文(the written)的張力的歷史。蘇格拉底對于書寫的批評是一個您經常提到的話題。借用德布雷(Régis Debray)對于不同介質——語詞(logosphere)、印刷(graphosphere)、屏幕(videosphere)主導的時代的分期,在我們這個屏幕主導的時代里,仿佛出現(xiàn)了口述的復歸。您似乎也暗示,前路可能恰在身后。這方面您能談談嗎?
普克納:我在準備寫這本關于世界文學的書的時候,我想象的是,口述和書寫(writing)的關系可能會在書的開頭非常重要,比如當?shù)谝粋€書寫系統(tǒng)被引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比如對于荷馬這樣的人,這一關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很快我就吃驚地發(fā)現(xiàn):書寫和口述的關系其實對于我要寫的整段歷史都是至關緊要的。所以我開始想的是錯的。我的最初設想是,起先只有口述,然后有一點書寫,接著書寫越來越多,最終代替了口述。但后來我認為,這是一幅錯誤的圖景,與之相反,口述與書寫是某種互聯(lián)的系統(tǒng),每個新興的書寫技術都以某種方式塑造了這一系統(tǒng),所以是不能分而待之的。
這便是為什么我納入了關于西非史詩的那一章。《桑介塔史詩》(Epic of Sunjata)入選了諾頓選集,但它還不算是世界文學正典的一部分。盡管如此,它依然是偉大的文本,幾百年來口耳相傳,有許多地方變體。受過訓練的講故事的人,從他們記憶中的情節(jié)庫里,選取與特定時間、特定觀眾最相關的內容現(xiàn)場表演,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這部史詩才被記錄下來。我和一位轉錄它的學者一起工作過,后者是在一位游吟詩人的協(xié)作下把它記錄下來的。這是個很好的例子,證明口述故事與書寫并存,并且持續(xù)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這成了我的主要觀點。如你所說,這一共存也是這個時代的我們親眼所見,正在發(fā)生的:分享語音和視頻在今天變得相當容易。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西非的史詩吟唱者開始和磁帶、光盤競爭,磁帶使口述表演文化觸及遠方的聽眾,于是,講故事的人由面向特定場所的觀眾,轉而開始跨區(qū)域地相互角逐,他們更強烈地將個性加諸故事素材,以區(qū)別于對手。另一方面,在《桑介塔史詩》與不同的書寫文化共存的幾個世紀里,歷代的吟唱者都把各種書面故事,以及書寫本身,吸收進他們的敘述。所以,我認為口傳和書寫確實是互聯(lián)互動的,我們并沒有拋棄一方轉投另一方。但你也能看到,每次新技術都稍稍改變了二者的關系,而鑒于我們時代的技術變革如此深刻,我認為,這一關系正在發(fā)生顯著地變化。
我發(fā)現(xiàn)《文字的力量》里有兩個重復出現(xiàn)且彼此相關的話題:文本原教旨主義(textual fundamentalism)和焚書。您說,文學的歷史也是焚書的歷史。為什么這么強調它們?
普克納:一旦你從四千年的角度來看文學,你一定會對這一事實感到震驚:有如此多的東西幸存了下來,但無疑,也有如此多的東西散佚了,這二者同樣令人驚嘆。我書里討論的有些文本之所以能幸存,差不多僅僅是個意外,因為我們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它們,比如《吉爾伽美什史詩》,比如瑪雅的《波波爾·烏》(Popol Vuh)史詩。這讓我切實地意識到偶然性的問題,意識到物的消逝是如此地迅速和輕易。所以我開始對文本的幸存機制產生了興趣。
焚書某種程度上是最極端的毀滅形式。一些情況下,它可能是個意外,但不少時候,它是不同欲念驅使的、蓄意的文化毀滅或破壞行為,其中的推動力包括文化間的對抗、一方對另一方的占領、對意見多樣性的恐懼。這里尤其惹人注目的是,印刷術發(fā)明后,在大眾掌握讀寫能力的時代,焚書行為反而變本加厲了,因為在這一時代,審查變得更加極端。然而,焚書的效果也降低了。它一度非常有效:西班牙的基督教征服者發(fā)現(xiàn)了美洲,幾乎成功將瑪雅文化斬草除根,只有極少,實際上只有兩部原版手抄古籍幸存了下來,一些文本則通過敵人的武器——西班牙人的紙和拉丁字母被轉錄了下來,比如《波波爾·烏》。有趣的是,甚至在這里,焚書仍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即便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經歷了一場近乎整體性的文化滅絕。但在文學的大眾生產時代,焚書變得愈發(fā)無效了。如今我們印刷,以及在互聯(lián)網上發(fā)表的速度,都比我們可以“焚燒”的速度快。但是,我又一次認為,每個與特定下層結構相關聯(lián)的書寫紀元,都會給表達造成新的挑戰(zhàn),也都會試圖控制擁有生產資料的人。下層結構變得越復雜,它就越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下。印刷時代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你一下子要面對大公司、國家或出版商所行使的種種管制。在我們的互聯(lián)網革命中,尤其在美國,這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也有很多逃避控制的機制。換句話說,我會把焚書置于對于發(fā)行機制所有權的控制的歷史中來討論。
在寫這段關于書文世界,或者說書寫權力的歷史的時候,我越來越覺得我本質上寫的是關于工具或技術的歷史。每樣工具都會使一些事情變得可能,但也都會產生一定的結果。尤其隨著神圣文本,以及利用神圣文本來塑造社會的傳統(tǒng)的出現(xiàn),我們清楚地看到,書文世界的力量可以變得破壞性十足和消極,特別當有人堅持要字面地、非歷史地理解這些文本。這就是為什么我把它稱為文本原教旨主義。它不會出現(xiàn)在口傳文化,因為在那樣的文化中,故事自動會被改編以適應每個具體時刻的需要。而一旦書寫被固定,就會出現(xiàn)這個趨向。它是某種“把你固定在某個版本的社會”的副產品。除了宗教文本,像美國憲法、《共產黨宣言》都有其原教旨主義解讀者。表明我們面對的是神圣文本的重要標志之一,是存在一個排他性的讀者群體負責闡釋它:從宗教權威,到美國最高法院,甚至是文學研究者。可以說,文本原教旨主義基于兩個矛盾的預設:其一,文本是固定不變的;其二,承認文本需要解讀,但解讀的權威須限制在一個排他的群體中。
現(xiàn)在,我們不再完全仰賴此類固定的文本了,因為我們知道,閱讀、闡釋、理解文本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動態(tài)的過程。在閱讀文本時,我們一定程度上幾乎是自動地把它們與我們的生活聯(lián)系起來。詞語的意義會改變。在我看來,似乎原教旨主義者想要做的,是抹除這個動態(tài)過程,固著在某種他們認為不變的東西上。我想對于我,結論就是,在理解這些本源性、基礎性的文本時,我們需要留給自己一定的彈性,即使我們尊重古代,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它們來指引我們。神圣文本是令人敬畏的文化紀念碑,是我們共有的人類遺產,但正因如此,我們應該允許每一代讀者將這些文本變成他們自己的。
閱讀所有的文本都像在和幽靈交談
一方面,《文字的力量》的章節(jié)在古人(the Ancients)和今人(the Moderns)之間等分,但另一方面,古今的區(qū)分,或者說前現(xiàn)代和現(xiàn)代的斷裂似乎在您書里被淡化了,至少沒有被強調。顯然,像前民族國家的俗語白話(vernaculars)在許多方面就不同于民族國家文學,您在書寫世界文學時,是如何解釋“古今之爭”的?
普克納:我想這是個公允的批評。我會說我是通過不同書寫系統(tǒng)的鏡頭來看這段歷史的,所以,對我而言,或許這就是區(qū)分古代人和現(xiàn)代人的標準。至于理解古今之分,我想最根本的是,現(xiàn)代人試圖與過去決裂,大步向前邁進。在十六、十七世紀,辯論的就是這個。當然,在我學術生涯的大多數(shù)時候,我都在關注現(xiàn)代人。我關于宣言的那本書,某種程度上就是現(xiàn)代人的寫照。我們確立一個無路可退的點(point of no return),重新開始,過去僅僅是現(xiàn)代的序言。而這,在我看來,并不是《文字的力量》這本書背后的激發(fā)性精神。
不過我也認為,古人和現(xiàn)代人的動態(tài)關系一直在不斷發(fā)生。我寫這本書最初幾章的時候,對亞述國王亞述巴尼帕(Ashurbanipal)特別著迷,他面對記錄了《吉爾伽美什史詩》的泥板感嘆:這是古代的,我是現(xiàn)代的,這些文字使我與遙遠的過去聯(lián)通,美妙極了。亞述巴尼帕必須學習他母語的古代版本——古巴比倫阿卡德語,以及更古老的書寫系統(tǒng)——楔形文字,來解讀這些他想象是“來自大洪水前”的文字。我想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與過去聯(lián)通的時間感(temporality)是書寫的效果,因為后者如此經久不朽。在你閱讀的時候,幾乎是自然而然地,會發(fā)現(xiàn)自己處在這種同過去的動態(tài)關系中,以至于你不得不去協(xié)調它。我的同事兼朋友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說,閱讀所有的文本都像在和幽靈交談,有某種東西從遙遠的過去幸存了下來。我覺得這是個非常有力的描述,我感同身受。所以,這便是反反復復發(fā)生的古今互動。而在這么說的同時,我又確實認為,在歷史的長河中存在變化。我這本書很大程度上就是關于變化的。現(xiàn)代世界,大眾掌握了讀寫技能,情況完全不同了。
旅行對您很重要。您看重歌德的西西里島之旅和易卜生的“文化”放逐,您還前往許多文學作品的誕生地,追蹤它們的死后之生,《文字的力量》的好幾個章節(jié)都以關于您旅途的心理-地理(psycho-geographical)描寫作結(您甚至還描述了您的夢,后者也可以被視為某種旅行)。為什么要在書里加入這些您個人旅行的內容?旅行之于世界文學的意義是什么?
普克納:我想部分是因為我坐在書桌前,寫著世界上各種文學間的關系、影響,它們塑造世界的力量,我覺得如果我把這當真的話,就應該去走走看看。這段時間里我經常去旅行,旅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當然你可以說,通過衛(wèi)星畫面來一場虛擬旅行很容易,不是一樣嗎?但奇怪的是,就是有一些東西,非要在旅行的時候才會注意到。比如特洛伊城的大小。我不是第一個觀察到它有多么的小——相較于我們閱讀荷馬時對它的想象。而當我追隨亞歷山大大帝的足跡旅行,一路上尤其令我詫異的是,那個時代的一切幾乎都煙消云散了,但與文學相關的劇場和圖書館的遺跡往往保留了下來:前者是保存文學的地方,也是圖書管理員抄寫重要文本并為之作注的地方,后者則致力于將荷馬的世界帶給那時的觀眾。這些東西可能聰明的學者都能在他們的研究中弄明白,但我覺得親身去那里走一走,會看得特別清楚。
最后想舉的例子,是我去圣盧西亞見德里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無疑,能在他過世前幾年與他交談是非常幸運的。我覺得如果沒有去這些加勒比小島旅行,我根本不會知道,他在那里竟無人不曉,廣場上豎立著他的雕像,足見他在當?shù)厝说男哪恐信e足輕重。凡此種種只有在和那里的人們交流后才變得清晰起來。反過來說,我也十分驚訝地意識到,地理對于他的作品是如此重要。因為如果你對一個地方一無所知,如果你不親身走過這段距離,地名就只是紙面上的詞語而已,你不知道它們意味著什么。了解這些島嶼的地理空間,親見這些地方是如何彼此聯(lián)系的,使得文學的地理維度變得分外鮮活,盡管這些都可以用別的方式來復現(xiàn)。但這是一個你閱讀時關注什么的問題。當你熟悉了這些地方,當你和那里的人們交談過,這個地理的維度自然浮出地表,變得非同小可。
宣言:起源與終結
《文字的力量》里有一章討論了《共產黨宣言》,或者說一般意義上的“宣言”(manifesto)這一文類。這直接讓我想到了您之前的著作——《革命之詩》,一部關于政治宣言與藝術宣言的雙重歷史書寫。為什么您認為宣言的政治傾向內在地就是左翼的?實際上,在《共產黨宣言》誕生之后(或之前),都有形形色色不那么左,甚至右翼的宣言。而既然您認為宣言處在藝術和政治的交叉口,為什么《革命之詩》在寫到1918年后,焦點就基本轉向了藝術呢?
普克納:我想這本書的源頭主要不是政治宣言而是藝術宣言,因為我那時正在研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段時間的藝術。我覺得當時出現(xiàn)的大量藝術宣言讀起來很有意思,我喜歡它們的口吻,喜歡那種渾身是膽的勁頭。同時我在教學中也經常用到它們,它們簡潔、精煉,很多思想、理論都濃縮其中,是很好的教學材料。我多少有點把它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我想,好吧,藝術家是寫宣言的,他們想解釋自己要做什么。但后來某一天,我非常意外地獲悉,其實這是藝術宣言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xiàn)。于是我就想追問它們是從哪來的,我很快意識到,它們的政治瘋癲其實來源于政治宣言,而這個文類就是由政治宣言所創(chuàng)造的。我要講述的就是這段復雜的前史,而那個真正塑造了宣言,把它鞏固為一個可辨識的文類的壓倒性文本正是《共產黨宣言》。我追溯了它的出版史,可能有點類似卡薩諾瓦的做法。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從某種世界文學的角度對翻譯感興趣。
理論上,你可以說宣言可以為任何人所用,也確實有各種各樣的人在寫宣言,但如果你考察一下其中占壓倒性多數(shù)的那群人,就不難發(fā)現(xiàn),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某種意義上定義了這個文類的宣言是《共產黨宣言》這個事實,把這個文類往左邊推了一把,所以如果你想寫一篇宣言而不和這個傳統(tǒng)發(fā)生聯(lián)系,那估計要費老大勁了。還有一個原因是和這個文類本身的深層結構有關:即革命的結構。即便一些古早的、前《共產黨宣言》的文本把自己稱為“宣言”,它們通常是當權者,比如國王或教皇所發(fā)布的,基本就等于發(fā)表權威的觀點或當局的法律。但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平等派(Levellers)那里,在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當中,事情正在起變化:宣言(或者說它的前身)開始從有權勢一方的表達,轉向無權勢一方的愿景。我想這便是左翼種子萌芽的時候,再后來就長出了《共產黨宣言》。弱者的聲音、革命的抱負、集體的遠景:所有這些左翼傳統(tǒng)中的宣言傾向都意味著,這一文類的歷史確實是由該傳統(tǒng)所推動的。雖然,如你所說,文類會遷移,可以被借用、改造,而宣言無疑也沒有免于這樣的命運。
恩格斯對他的合作者寫道:“我想,我們最好拋棄那種教義問答(catechism)形式,把這個東西叫作‘共產主義宣言’。”上圖為1848年2月初版于倫敦的《共產黨宣言》。
我寫《革命之詩》主要想回答的是藝術宣言來自哪里。我提到了一些二十世紀的政治宣言,所以我說,在二十世紀,它變成了一種雙重歷史。但原則上講,你是對的。我的確改變了重心,因為我的主要目標是追問,宣言這種文類如何改變了藝術世界。我意識到,從二十世紀初開始,藝術界就是一個激進革新的藝術界,一個試圖把自己和敵人區(qū)分開來的藝術界,一個贊美原創(chuàng)性的藝術界。我認為宣言也是其中的動力機制之一。這就成了我真正的焦點所在。當然有人可以寫一本研究二十世紀政治宣言的書,當中偶爾瞥幾眼藝術,這也會是一本合情合理的書。
您怎么看宣言在今天的式微,以及先鋒派的現(xiàn)狀?
普克納:式微是個大問題。我想在八九十年代,尤其在西方,以及某種程度上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大多數(shù)時候,宣言這種文類式微的一個原因是現(xiàn)實革命視野的消逝、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在西方的衰落——它不再能吸引年輕人和藝術家了。而宣言是受左翼、共產主義傳統(tǒng)滋養(yǎng)和影響的,也許這就是為什么它消失了。但我現(xiàn)在認為,一個更大的原因是和宣言中的集體(the collective),那個“我們”有關。我不知道中國多大程度上也是這樣,但美國是最極端的,歐洲稍好一些,當然主要是在年輕人當中:就是對個人身份,對你能選擇你的身份這樣的觀念,強調得幾近過分。與此同時,你能為別人說話代言這樣的觀念則變得十分可疑。比如有些作家想借一個不同種族的人物來寫一部小說,就會看起來問題重重。他們會被從頭到腳審視一番。如今,你為你自己、你的經驗,也許還有你的不論如何理解的身份群體說話,是有意義(sense)的,反之,人們覺得為一個集體說話已經不可能了,他們覺得尷尬,他們想對集體敬而遠之。
這一點我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后來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里看得尤其清楚。當時參與運動的一些人想過要寫個宣言,但他們恰恰覺得沒有人可以被授權來寫(authorized)這宣言。沒有領袖,這是一場草根運動。誰能代表我們寫?我們怎么能達成共識?后來有出版商弄了些各種觀點的集刊。總之有這么一種需求占領華爾街運動沒能完全滿足。現(xiàn)在雖然一些觀念在民主黨內的左翼里得到了非常強烈的共鳴,但作為一場運動,占領華爾街夭折了。人們期待一個組織、一篇宣言,但與此同時,又很清楚,這是不可能的。
我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宣言來看先鋒派的。對于我,宣言幾乎成了先鋒派的核心,這部分是因為它們成了早期先鋒派,尤其是未來主義的主要載體和表達形式。我想或許宣言的式微某種程度上也表明了先鋒派的式微。我們似乎正處在藝術史上的這樣一個階段:各種不同的形式可以并存共處。再也沒有那種清楚的跡象,一種風格繼另一種風格之后而興起。你也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初,風格多元得不可思議,但那時還有一個觀念即某一種風格應該占優(yōu)勢,它應該是那個獨一無二的新事物(the new)。所以那時的人們用了“先鋒”(avant-garde)這樣一個軍事術語來自我命名。我認為現(xiàn)在情況不是這樣了。用某種近乎后現(xiàn)代主義的表達來描述這種區(qū)別的話,可以說先鋒派仍舊是被某種革命的觀念驅動的。在如今的藝術界,政治革命的邏輯某種程度上已經被市場邏輯所取代。
戲劇和反戲劇,或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
您一貫對文學、哲學與表演的關系抱有興趣。在您關于現(xiàn)代主義書齋劇(closet dramas)的第一本著作和關于思想劇(drama of ideas),或者說戲劇柏拉圖主義(dramatic Platonism)的第三本著作之間,可以看出明顯的連續(xù)性。該如何理解您所謂的“反戲劇性”(antitheatricality)?
普克納:我對戲劇的興趣可以追溯到高中和大學時代,我參加過一些戲劇表演,盡管那時幾乎沒有研究過它。我最早拿的是哲學學位,然后轉到了文學。當時的研究對象成了我第一本書的主題:詹姆斯·喬伊斯、斯特芳·馬拉美這些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xiàn)代主義作家,他們故意要創(chuàng)作錯綜復雜、佶屈聱牙的文本。而我注意到的是,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和戲劇之間,存在某種艱難的、緊張的,有時是敵對的關系。所以這就成了我用來觀察這一時期的視角。有時候,這種關系意味著在創(chuàng)作小說時,利用、書寫戲劇,把戲劇收編進小說,比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有時候,它意味著寫一些他們不想其上演的戲劇;還有時候,比如在貝克特那里,它意味著即便是為舞臺創(chuàng)作,也要試圖取消、削減很多戲劇的元素。所以我就發(fā)展出了這個假說。后來我發(fā)現(xiàn),這里很多人,事實上也包括貝克特和一些戲劇導演,盡管在劇場工作,但在談論戲劇時卻帶有極大的敵意。我覺得這種敵意主要和創(chuàng)造一種與戲劇不同的純文學的企圖有關。另外還因為戲劇被看作一種中等品位的大眾藝術形式,它迎合觀眾,挑動觀眾,向觀眾發(fā)話,而這些現(xiàn)代主義者則對觀眾態(tài)度曖昧,愛恨交織。他們想抽身而退。以上大體就是我怎么發(fā)展出這個現(xiàn)代主義者和戲劇的緊張關系的視角的過程。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還有未竟之業(yè)。早期的哲學訓練總在我腦后徘徊。而那段時間我正好主要在負責一個戲劇項目,教了很多關于戲劇的課,我試著考慮我閱讀哲學的興趣怎么能幫我理解戲劇,以及反過來,對戲劇的興趣是不是有助于理解哲學。于是我真正開始思考戲劇和哲學的聯(lián)姻了。第一個發(fā)現(xiàn)是,當時鮮有跨兩個領域的學者,而放眼歷史,戲劇和哲學都對彼此懷有敵意。這是和我第一本書在概念上類似的地方。但隨后當我試圖透過表面往內里看,我發(fā)現(xiàn)二者實際上是有重疊的。于是我便對哲學對話的歷史產生了興趣,開始把柏拉圖置于戲劇的語境中考察,開始關注那些相對罕見的哲學家談論戲劇的時刻。他們想從戲劇那里得到什么?他們?yōu)槭裁匆V諸戲劇?有時候為了把自己和它區(qū)別開來,有時候則想借它來證明什么,比如他們中的一些人覺得,一部希臘悲劇往往能比他們自己更有效地表達某個哲學觀念,或者說是一種表達哲學的替代性方式。然后也有一些劇作家對哲學表現(xiàn)出明確的興趣,甚至有人專門創(chuàng)造了哲學角色,盡管那可能是個喜劇人物,令哲學家成了被嚴肅嘲諷的對象。最終就有了這么一段關于戲劇和哲學的交叉歷史。它很大程度上脫胎于我的第一本書。
如果說宣言那本書在《文字的力量》占有一章的位置,我覺得后者關于大宗師(master teachers,采訪者注:指佛陀、孔子、蘇格拉底、耶穌)的部分則和思想劇這本書有關——這些超凡魅力型教師拒絕寫作,堅持真人表演(live performance)。如果沒有思考過戲劇和哲學的關系,我可能不會意識到這點。我們前面談到的口述和書寫的關系也可以聯(lián)系到這個問題。戲劇研究里的一大爭論就是文本和表演的關系,換言之,就是書寫和口述的關系。
您是哈佛大學梅隆戲劇與表演研究學院的創(chuàng)院院長,能介紹一下您在哈佛讓戲劇擁抱理論(theater-theory embrace)的實踐嗎?為什么戲劇人應該擁抱反戲劇的一方?按理說,后者不是前者的敵人嗎?
普克納:當我在思考戲劇和哲學的關系,以及它們彼此間的敵意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我正好處在如是境地:我要在這樣一種關系里啟動一個戲劇項目。其實這件事最初和我的學術工作沒什么關系。我之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那里是有戲劇項目的,有一個很大的戲劇系,也招博士。而在哈佛,我感覺我仿佛處在一個由反戲劇偏見塑造的機構里。某種程度上,這在情理之中,因為哈佛是由新教原教旨主義者創(chuàng)立的。而他們之原教旨主義的含義之一,是對于閱讀和寫作的高度重視。你可以說他們對《圣經》的使用在很多方面是壓制性的,但這也造就了其時地球上識字率最高的社會。尤其不同尋常的是,他們堅持向婦女和兒童教授讀寫的技能,使這一能力不為上層階級壟斷,在實質上為所有人擁有。所以不得不承認,即使文本原教旨主義也可能有積極的一面。
但在清教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點是對于展示和戲劇的不信任。他們對書寫和讀寫能力的傾心投入是他們創(chuàng)建哈佛大學的初衷,這聽起來多少有點不可思議:這些清教徒剛到新世界不久,每年過冬都十分艱難,但在勉強度日了十余年后,他們竟辦了一所大學。無論如何這都是不尋常之舉。只不過這是一所極為反戲劇的大學,即便后來哈佛的宗教環(huán)境改變了,并且在一段時間內,它是由一位論派(Unitarians)主導的,該派以愛默生和梭羅為代表,要達觀(philosophical)、開明得多,但是無論如何,反戲劇的遺產多多少少還是在的。不過漸漸有人覺得,哈佛真的應該像每個正常大學一樣,有個戲劇項目。哈佛總瞄著耶魯,耶魯有一個非常大的戲劇項目,我們也得啟動一個。而我覺得,策略上最有效的方式是,我們實質不光做戲劇,我們也做哲學和理論。這是理由之一。
還有一個結合二者的理由是,既有的一些職業(yè)戲劇教育可能是相當反智的。比如一個戲劇項目,幾乎把重心都放在實踐上,放在表演、導演、舞臺布景設計上,外加一點戲劇文學選讀。在中國的語境里,這有點像戲劇學院加文學系。所以也不光是策略,而是我相信,真正設計出把戲劇和理論結合在一起的課程,而不僅僅讓學生去上一些隸屬于不同系科的課,是一件有趣且有意義的事情。某種意義上,這一關聯(lián)并非是任意的。有個出色的斯坦福學者安德里亞·威爾遜·奈廷格爾(Andrea Wilson Nightingale)追溯了“理論”(theory)這個詞的歷史,發(fā)現(xiàn)它和“戲劇”(theater)一詞共享同一個詞根thea,即“看”(seeing)。“劇場”(theater)是看的地方,“理論”(theory)的詞源之一是節(jié)日朝圣的別名,二者都能追根溯源到“看”(thea)。
我想,戲劇界的人對反戲劇的偏見表達不快,是無可厚非的反應。但我覺得戲劇人也可以從他們的敵人那里學到很多,部分是因為哲學家們,尤其是那些反對戲劇的哲學家很尖銳,事實上他們看到了戲劇的一些要害。對于我,最好的例子是柏拉圖,他對戲劇滿懷敵意,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想把哲學作為某種替代品,但他關于再現(xiàn)和表演的說法,從摹仿(mimesis)、講敘(diegesis)到演出(acting),都是值得思考的,甚者,主要的戲劇類型——悲劇和喜劇都在柏拉圖對話中出現(xiàn)過,后者仿佛前二者結合而成的第三類型。我也傾向于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對比中來考慮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同時思考,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話可以說,是第一個以正面、肯定的姿態(tài)思考戲劇的西方哲學家。他試圖理解戲劇,盡管他也對戲劇的視覺方面多少持反對態(tài)度,但他在《詩學》中討論了戲劇空間里的表演。在西方,所有的戲劇理論課都從《詩學》講起,如果說整個西方哲學史都是柏拉圖的注腳,那不妨說,整個西方戲劇理論史都是亞里士多德——作為《詩學》作者的戲劇批評家亞里士多德的注腳。但是,我覺得柏拉圖這位更早的、對戲劇更有敵意的哲學家也說了很多有意思的東西。我的學生對他很有興趣,他們一度把《會飲》搬了上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