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描淡寫”:扎加耶夫斯基論藝術(shù)與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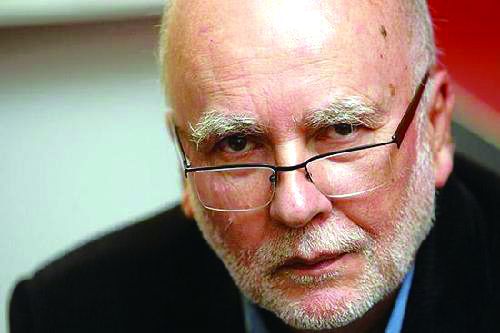
“1990年代后期,每年春天我都會(huì)在休斯頓待上一陣子,像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樣——他在克拉科夫和加利福利亞之間往返奔波,然后回到位于伯克利的一所小房子。每隔一段時(shí)間,我和米沃什會(huì)通過電話交談。有一天,米沃什給我打電話,聲音低沉而憂傷。交談不久我便意識(shí)到他的情緒極度沮喪,需要我的幫助。最后他問我,亞當(dāng)(這是他一向?qū)ξ沂褂玫恼椒Q謂),請(qǐng)老實(shí)告訴我,我這輩子有沒有寫過哪怕一首好詩(shī)?”
這是波蘭大詩(shī)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米沃什的疑問,也是《輕描淡寫》一書作者扎加耶夫斯基的疑問——而問題的答案,或許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便不難發(fā)現(xiàn)。
隨筆集《輕描淡寫》的作者亞當(dāng)·扎加耶夫斯基(1945-)是波蘭當(dāng)代著名詩(shī)人、小說家和散文家,出生于波蘭的利沃夫(今屬烏克蘭)。1945年雅爾塔會(huì)議后,利沃夫割讓給前蘇聯(lián),出世剛滿4個(gè)月的扎加耶夫斯基隨全家遷居西里西亞的格利維采,在那里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shí)期。中學(xué)畢業(yè)后,扎加耶夫斯基進(jìn)入波蘭舊都克拉科夫首屈一指的雅蓋沃大學(xué)學(xué)習(xí)哲學(xué)和心理學(xué),獲得哲學(xué)碩士學(xué)位。此后他先是在一個(gè)冶金學(xué)院任教,后到一家文學(xué)刊物做編輯,直到因參與政治抗議活動(dòng)被除名。1982年,因團(tuán)結(jié)工會(huì)爭(zhēng)取民眾權(quán)利引發(fā)的“工潮”,波蘭當(dāng)局發(fā)布戒嚴(yán)令,作為“持不同政見者”的扎加耶夫斯基雖未受到監(jiān)禁,但仍因“個(gè)人原因”,被迫離開“營(yíng)房般陰沉”的波蘭,移居巴黎。在法國(guó),他迅速加入到波蘭移民知識(shí)分子小團(tuán)體,參與文化刊物的編輯工作。1983年起,扎加耶夫斯基便往來于法國(guó)和美國(guó)之間,在多所大學(xué)教授詩(shī)歌和創(chuàng)意寫作課程。扎加耶夫斯基現(xiàn)居克拉科夫,至今已出版詩(shī)集18種,散文、隨筆11種,被公認(rèn)為當(dāng)代波蘭最具國(guó)際影響力的詩(shī)人之一。
眾所周知,波蘭昔日的首都克拉科夫是歐洲文學(xué)名城,更是詩(shī)歌的中心——因?yàn)槊孜质玻驗(yàn)樵右蛩够惨驗(yàn)楸蛔u(yù)為“詩(shī)界莫扎特”的1996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辛波斯卡。德國(guó)哲學(xué)家西奧多·阿多諾曾說:“奧斯維辛之后,寫詩(shī)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波蘭詩(shī)人們似乎并不認(rèn)同這一觀點(diǎn),上述詩(shī)人都以各自不同的風(fēng)格書寫波蘭(以及歐洲的)歷史與更為深廣的人性。對(duì)他們而言,幸或不幸,作為一名波蘭詩(shī)人,“二戰(zhàn)”前的德國(guó)占領(lǐng)和戰(zhàn)后的蘇聯(lián)瓜分(本書中使用“重置”一詞)都是無法言說的痛楚,也是無法擦除的記憶。他們或許沒有直接書寫現(xiàn)實(shí)政治,但絕非對(duì)政治漠不關(guān)心。他們所做的,是“通過對(duì)日常生活的描繪來反抗意識(shí)形態(tài)的侵襲”。在這一方面,扎加耶夫斯基與他的前輩切斯瓦夫·米沃什(以及茲別格涅夫·赫貝特)相比,可謂青出于藍(lán)而勝于藍(lán)。
早在大學(xué)畢業(yè)前后,扎加耶夫斯基便開始了小說和詩(shī)歌創(chuàng)作。在克拉科夫,扎加耶夫斯基所投身的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后來被文學(xué)史整體命名為“新浪潮”。其實(shí),在波蘭“新浪潮”這一名號(hào)之下各地存在若干派別,如華沙的雜交“方針”詩(shī)社,弗羅茨瓦夫的“阿果拉”詩(shī)社和“六六”詩(shī)社,波茲南的“考驗(yàn)”詩(shī)社,科托維茨的“上下文”詩(shī)社,等等。扎加耶夫斯基組織和參與的克拉科夫詩(shī)歌派別名為“現(xiàn)在派”,該派受到美國(guó)“垮掉派”詩(shī)歌、法國(guó)“新新小說”以及英國(guó)“憤怒的青年”等西方文學(xué)思潮影響。在內(nèi)容題材方面,該派指責(zé)當(dāng)代詩(shī)歌和小說逃避現(xiàn)實(shí)、缺乏探索當(dāng)代問題的熱情和追求真理的勇氣,主張恢復(fù)詩(shī)歌講真話的權(quán)利,重提詩(shī)人獨(dú)立思想的天職。在詩(shī)歌形式方面,扎加耶夫斯基等人則主張?jiān)姼璨粦?yīng)講究韻律,其形式應(yīng)更接近散文。由此,扎加耶夫斯基“以一種詩(shī)學(xué)的反叛姿態(tài)登上詩(shī)歌歷史舞臺(tái)”,開始在波蘭戰(zhàn)后文人團(tuán)體中嶄露頭角。
1980年代以后,由于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扎加耶夫斯基的詩(shī)風(fēng)也為之一變:原本富于進(jìn)攻性的“干預(yù)政治和社會(huì)生活的抒情詩(shī),逐步演變成對(duì)政治和社會(huì)斗爭(zhēng)保持一定情感距離的、諷刺的、觀察世界的和具有形而上學(xué)色彩的抒情詩(shī)”——詩(shī)歌是文學(xué)而不是政治。阿多諾所謂奧斯維辛悲劇之后不應(yīng)再寫詩(shī)的觀點(diǎn),在扎加耶夫斯基看來過于片面——在面對(duì)世界的苦難和殘酷時(shí),詩(shī)歌自有其無可替代的功能。一方面,奧斯維辛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之中,成為民族文化遺產(chǎn)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詩(shī)歌同時(shí)也有愉悅和游戲的成分,沒有哪個(gè)奧斯維辛可以將它完全清除。因此,作為詩(shī)人,不僅應(yīng)該銘記奧斯維辛的殘酷,也不應(yīng)忘卻詩(shī)歌的游戲功能和歡樂時(shí)刻,并應(yīng)當(dāng)與讀者分享這種詩(shī)歌的體驗(yàn)。扎加耶夫斯基承認(rèn),當(dāng)下許多詩(shī)歌——包括他本人的詩(shī)作——并“沒有致力于尋求人類和世界的真理,而是局限于追尋自由,在世界的海灘上收集一些漂亮的小玩意、鵝卵石的貝殼”。然而,在他看來,這并不意味著詩(shī)歌的衰落。詩(shī)歌可以描寫平凡的事物,但詩(shī)歌的情感卻不能平凡,它能讓讀者看到隱藏在遠(yuǎn)處的戰(zhàn)栗和狂喜。這種追求精神崇高而又不忽略生活日常性的存在,被扎加耶夫斯基恰當(dāng)?shù)孛枋鰹樘K格拉底“理性的狂迷”說。這也是扎加耶夫斯基對(duì)米沃什滿心崇拜的根本原因。照他的說法,米沃什改寫了安泰的神話:一個(gè)人同時(shí)接觸大地和天空才會(huì)恢復(fù)力量。換言之,唯有理智與情感的完美結(jié)合,才能造就不朽的詩(shī)歌。
縱觀扎加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一條主線貫穿始終,那就是:以對(duì)不合理社會(huì)制度與秩序的反抗始,到與世界和上帝的和解終。事實(shí)上,這一條主線也體現(xiàn)了歷史悠久、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波蘭詩(shī)歌文化傳統(tǒng)。歷史地看,無論是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科哈諾夫斯基和巴洛克時(shí)期的薩爾別夫斯基,還是啟蒙時(shí)期的克拉西茨基和浪漫主義時(shí)期的“一出娘胎就受著奴隸的煎熬,在襁褓中就被人釘上了鎖鏈”一代人的代表密茨凱維奇,波蘭詩(shī)人在歐洲文學(xué)史上皆深具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們的反抗意識(shí)。20世紀(jì)波蘭著名文藝?yán)碚摷揖S托爾德·貢布羅維奇在《反對(duì)詩(shī)歌》中批評(píng)詩(shī)歌的“甜蜜性”,稱詩(shī)歌是過度的文字、過度的隱喻、過度的崇高和過度的提純,很顯然,他反對(duì)的是脫離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所謂“純?cè)姟薄T谶@一點(diǎn)上,扎加耶夫斯基與貢布羅維奇的看法高度一致。
不僅如此,除了繼承古典的波蘭詩(shī)學(xué)傳統(tǒng),扎加耶夫斯基還從當(dāng)代兩位大師——米沃什和赫貝特那里汲取了養(yǎng)分。從赫貝特那里,他學(xué)到“反諷”——一種對(duì)于世界審慎質(zhì)疑而富于幽默的態(tài)度;從米沃什身上,他繼承“希望”——后者倡導(dǎo)一種“希望的詩(shī)學(xué)”,一種對(duì)于歷史和存在的信心,它們來源于擔(dān)當(dāng)?shù)挠職猓瑏碓从趯?duì)客觀真相的探索。作為詩(shī)人,扎加耶夫斯基既擁抱了米沃什的詩(shī)歌之火,又延續(xù)了赫貝特獨(dú)具特質(zhì)的“反諷”精神。這兩種特質(zhì)融匯在他晚期記述個(gè)人游歷或懷舊的作品(如《輕描淡寫》)之中,形成鮮明的創(chuàng)作特色,或可稱為“個(gè)人歷史化”的抒情。
《輕描淡寫》開頭第一句“我不會(huì)和盤托出。事實(shí)上也沒什么大不了”便從側(cè)面揭示出本書所體現(xiàn)的自傳體本質(zhì),既有所流露亦有所保留。從創(chuàng)作的角度看,這或許有過度解讀之嫌,可扎加耶夫斯基本人的確一向長(zhǎng)于自我反思。讀者倘若閱讀過其早期散文集,特別是《兩個(gè)城市》《另一種美》和《捍衛(wèi)熱情》等作品,再來讀《輕描淡寫》(本書波蘭語(yǔ)版原著于2011年出版),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其中有一些似曾相識(shí)的話題,也會(huì)明白這就是扎加耶夫斯基作品恒久不變的主題,比如文化多樣性、科學(xué)與人文、藝術(shù)與人生,等等。作者復(fù)雜的思想時(shí)刻處于“自我反省”和“自我糾纏”的狀態(tài),在幾番斟酌審視之后——他往往信手拈取某一話題,稍加推演,隨即任其發(fā)展,不久又將其重新?lián)焓凹右詫徱暋渌枷胗^點(diǎn)由此便得以進(jìn)一步升華提高,同時(shí)亦能給讀者帶來莫大的精神享受。
以本書中作者對(duì)故鄉(xiāng)利沃夫愛恨交織的復(fù)雜感情為例。作為長(zhǎng)期流亡海外的作家,扎加耶夫斯基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就是自己與故土家園的情感聯(lián)系。讀者不難從書中讀出作者對(duì)故鄉(xiāng)利沃夫永久的眷戀。家園喪失是扎加耶夫斯基一家人心中沉重的傷痛,而扎加耶夫斯基作品中最廣為流傳的詩(shī)集《去利沃夫》便受到家人有關(guān)故鄉(xiāng)種種傳說的啟發(fā)。因此,出于對(duì)故土的深切思念,作者在書中以大量的筆墨描繪了各種類型的遷徙,包括地域、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化等多個(gè)層面,以此來為自己所經(jīng)歷的背井離鄉(xiāng)找到合理定位,同時(shí)也有助于在讀者群中引發(fā)更為廣泛的共鳴。
如此一來,將扎加耶夫斯基稱為背井離鄉(xiāng)之人或許會(huì)稍顯夸張。作者不憚將確切的歷史事實(shí)(如德奧占領(lǐng)、納粹集中營(yíng)等)與難以名狀的內(nèi)心感受分隔開來,這種勇氣與理性精神,無疑令人欽佩。但與此同時(shí),正如扎加耶夫斯基在書中坦承的那樣,他本人在流亡遷徙或“重置”過程中所承受的苦痛遠(yuǎn)不及他人。事實(shí)上,他往返于兩城之間的生活模式頗為令人羨慕。不少作家(例如謝默斯·希尼)都認(rèn)為人若于兩座迥然不同的城市之間往返,其生活將極為充實(shí)而豐富。不過,扎加耶夫斯基的大部分想象仍以離棄的波蘭故鄉(xiāng)為背景,其原因或許可從作者稍顯浪漫色彩的論斷中見出端倪——“生活的悖論在于,人唯有失去后才能明白其意義”——對(duì)扎加耶夫斯基而言,可謂此心歸處,永是吾鄉(xiāng)。
“在格利維采,父母時(shí)不時(shí)地談?wù)摴枢l(xiāng)利沃夫,他們,以及和他們經(jīng)歷相似的受迫的移民,用綿長(zhǎng)的回憶織造出一個(gè)失樂園一般的故鄉(xiāng)神話。”扎加耶夫斯基曾以一種標(biāo)準(zhǔn)的詩(shī)人的敏感刻畫那些利沃夫的老居民,他們將對(duì)鄉(xiāng)土的眷念視為一種忠誠(chéng),并愿意與這一種忠誠(chéng)相依相伴,直到將其帶進(jìn)墳?zāi)梗骸敖?jīng)過戰(zhàn)爭(zhēng)和放逐后,他們緊緊抓住了老家剩下來的一切”;他們視自己為利沃夫記憶的捍衛(wèi)者,能活多久,就捍衛(wèi)它多久,捍衛(wèi)關(guān)于這座城市的記憶,捍衛(wèi)以它為背景的每一個(gè)故事。
然而扎加耶夫斯基本人卻志不在此。他對(duì)利沃夫并無深切記憶,也不愿人云亦云地加入父輩的鄉(xiāng)愁大合唱。只不過,由于父輩傾心描繪故鄉(xiāng)的美麗,他不由自主地對(duì)自己所居的城市格利維采產(chǎn)生強(qiáng)烈而持久的鄙視和輕蔑。他把自己看作“中間者”(即“第三類人”),或無家可歸者;他游離于現(xiàn)實(shí)之外,不無憤激地說:“從現(xiàn)實(shí)里,我只不過獲取一些生活的必需品而已”,同時(shí)也從不承認(rèn)利沃夫是他真正的故鄉(xiāng),因?yàn)槟莻€(gè)被父輩神化的地方,已在波蘭進(jìn)入紅色時(shí)代之后徹底變樣。像前輩詩(shī)人米沃什或赫貝特,扎加耶夫斯基反躬自問:為什么我能寫詩(shī),我能在克拉科夫找到“此心安處”?——那是因?yàn)椋覜]有真正體驗(yàn)過背井離鄉(xiāng)的痛苦啊!而那些利沃夫的“遷居客”,他們根本無法“看向高處”,無法抽離地、藝術(shù)化地書寫,將刻骨的思鄉(xiāng)之情平靜地融匯于筆端。他們無力書寫對(duì)于故鄉(xiāng)的記憶,因?yàn)閷?duì)他們來說,記憶是需要用一生去捍衛(wèi)的東西,這樣悲壯的事業(yè)容不下詩(shī)的輕盈。這也是扎加耶夫斯基始終如一的信念:藝術(shù)高于生活,但與此同時(shí)藝術(shù)也會(huì)“扭曲”現(xiàn)實(shí)。
與扎加耶夫斯基同在休斯頓大學(xué)講授創(chuàng)意寫作的作家但·萊芬伯格曾說過,扎加耶夫斯基相信自然的事實(shí)甚于觀念,他總是“像談?wù)撋衩刂锬菢诱務(wù)撔孪吹膩喡椴蓟蛐迈r的草莓”。評(píng)論家桑塔格則盛贊扎加耶夫斯基的詩(shī)歌,是“對(duì)平靜、同情、忍耐,對(duì)日常生活之寧?kù)o與勇氣的贊美”。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扎加耶夫斯基就如米沃什贊嘆的那樣,寫下了“對(duì)時(shí)間之流的沉思”。他“回憶”歷史的疼痛,試著從中找到某種人性的東西,并將歷史轉(zhuǎn)化為抒情,轉(zhuǎn)化為一種悲劇性的愉悅時(shí)刻。
除了對(duì)故鄉(xiāng)的眷戀之情,書中還有更多關(guān)于自我與他者、青年與老年、歷史與現(xiàn)狀等鮮明對(duì)比的思考。作者對(duì)于自己那些長(zhǎng)輩——思想執(zhí)拗的親戚和性情古怪的教授——的回憶,刻畫得尤其哀婉動(dòng)人,不僅描摹出作者本人年輕時(shí)代意氣風(fēng)發(fā)的形象,更體現(xiàn)出他對(duì)于那些長(zhǎng)者充滿溫情的敬意和懷念。書中關(guān)于作者在學(xué)生時(shí)代參與文學(xué)和政治活動(dòng)的生動(dòng)回憶,既有熱情洋溢的謳歌,又不乏客觀冷靜的思考,使得本書與時(shí)下出于自戀目的、內(nèi)容上難掩輕率的多數(shù)自傳寫作相去甚遠(yuǎn)。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選取素材的角度也頗為獨(dú)特:看似漫不經(jīng)心的講述,其實(shí)飽含作者的良苦用心。他選擇“只講述那些富于洞察力或啟示的故事”,猶如驚鴻之一瞥,使得敘事本身兼具密度和粒度(granularity)。“粒度”一詞,是扎加耶夫斯基評(píng)判文學(xué)作品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令人印象深刻。當(dāng)然,這種敘事方式本身也具有道德啟示的意義:一個(gè)人談?wù)撟约簳r(shí),應(yīng)該如何避免自鳴得意。正如扎加耶夫斯基在書中反復(fù)申述的:生活,不應(yīng)該是一所教人冷酷無情的學(xué)校,而應(yīng)當(dāng)是實(shí)施“同情教育”的場(chǎng)所。
扎加耶夫斯基推崇的哲學(xué)家西蒙娜·薇依在名作《重負(fù)與神恩》中曾經(jīng)斷言:藝術(shù)不能,也從來不該脫離重力和引力,脫離世間的一切的痛苦和丑惡——藝術(shù)家必須明白,只有意識(shí)到自身的束縛和局限,才能真正追求明晰而完美的表達(dá)——這也可作為狂喜的另一個(gè)定義:狂喜意味著擺脫一切痛苦、丑惡與苦難,而專注于美。對(duì)扎加耶夫斯基而言,正如他再三宣稱的:純粹狂喜的藝術(shù)品卻只能令人不快,或漠然置之,因?yàn)椤皽?zhǔn)確地來說,輕重明暗,痛苦與狂喜無盡的爭(zhēng)斗,乃是藝術(shù)的根本”。這是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念茲在茲的“藝術(shù)拯救人生”的學(xué)說,但也許的確反映了生活與藝術(shù)二者關(guān)系的本質(zhì)。正如扎加耶夫斯基在本書結(jié)尾處所言:
“輕描淡寫——真的是詩(shī)歌的上佳定義。在晨霧彌漫的日子,在清澈寒冷的早晨,詩(shī)歌的這一精彩定義錯(cuò)誤地預(yù)示著和煦的艷陽(yáng)。這是輕描淡寫,除非我們能領(lǐng)會(huì)其中的深意——那時(shí)它才表達(dá)出真理;但當(dāng)我們?cè)俅坞x開它——因?yàn)樵?shī)歌不可能成為永久的家園——它又變回為輕描淡寫。”
總體而言,無論從思想性或是藝術(shù)性方面看,《輕描淡寫》一書皆達(dá)到很高的水準(zhǔn)。用《哈佛評(píng)論》書評(píng)家萊昂納多·克雷斯的話說,通過對(duì)日常生活與文學(xué)藝術(shù)關(guān)系的思考,本書“致力于描繪一種非理性卻飽含情感與人性的思維方式,這一方式會(huì)欣然接納那些需經(jīng)內(nèi)心共鳴而非理性思辨才能觸摸到的情感。它的存在,既暴露出理性思辨的局限性,也證明了人類情感糾纏可能達(dá)到的深度”。可見,本書的確無愧于扎加耶夫斯基作為“歐洲一流思想家”的美譽(y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