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加繆《鼠疫》:重負(fù)與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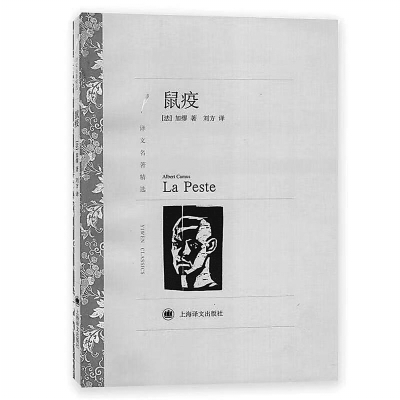
阿爾貝·加繆文字的穿透力,讓人聯(lián)想到他筆下地中海沿岸蒂巴薩夏日耀眼的陽光。那是一個用他畢生的寫作不斷對現(xiàn)實(shí)世界做出修正的大師。有誰敢像他一樣說:小說的本質(zhì)就在于永遠(yuǎn)糾正現(xiàn)實(shí)世界?
當(dāng)鼠疫蓄足全力撲向奧蘭城,人們?yōu)檎一厥サ男腋#瑨暝钟烈叩呐郏?00多頁的《鼠疫》正好行進(jìn)到三分之一,阿爾貝·加繆式的哲學(xué)像一支交響樂的主聲部,開始通過敘述人呈現(xiàn)。這種顯然已經(jīng)糅合了個人生存經(jīng)驗(yàn)的哲學(xué),用一句話即可以陳述:存在就是反抗。加繆在1957年的受獎演說中,把這種反抗視作作家這一職業(yè)的偉大責(zé)任:不能遷就謊言和奴役,要為真相的呈現(xiàn)、為自由服務(wù)。做出這樣的承諾是艱難的,因?yàn)槿吮旧硭哂械娜毕菔顾茈y履行這樣的承諾——拒絕對眾所周知的事情撒謊。

小說中的主角之一朗貝爾,一直在做著個人化的斗爭和反抗,他明言,這種斗爭和反抗是為了個體的幸福。朗貝爾是一個記者,因?yàn)橐淮闻既槐焕г诹藠W蘭,被迫和戀人分離。他一直有一種錯覺,或者說心存幻想,以為在鼠疫面前自己仍是自由的,可以自行做出抉擇,事實(shí)上他忽略了,當(dāng)災(zāi)難的陰影籠罩住了一切,已不存在個人的命運(yùn),有的只是集體的遭遇。
為了不讓鼠疫的魔爪捉住,朗貝爾想盡了種種辦法出城,當(dāng)事實(shí)證明通過合法手段出城無望時他就另找出路。他甚至找到了一個秘密偷渡的地下組織。但一心想著要出城的朗貝爾在這里好像走入了一個迷宮,他像卡夫卡小說中的灰色人物一樣永遠(yuǎn)接近不了目標(biāo)。在和里厄醫(yī)生的一次談話中,他坦言自己不是個怕冒生命危險的人,“我沒有和你們一起工作,是有我的理由”。朗貝爾在這里說的理由就是愛情,就是他的幸福。他把里厄他們的行動稱作“為理想而死”的英雄主義行徑,而他感興趣的只是“為愛而生,為愛而死”。他和醫(yī)生有一次關(guān)于人是不是一種概念的爭論,他面紅耳赤地反駁醫(yī)生——“人是一種概念,不過,一旦脫離了愛情,人就成為一種為時很短的概念,而現(xiàn)在正好我們不能再愛了,那么醫(yī)生,讓我們安心地忍耐吧,讓我們等著能愛的時刻到來,如果真的沒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時候,不必去裝什么英雄。”
這是朗貝爾的思想支撐,或者說是他的信仰。這也是朗貝爾式的反抗,它是內(nèi)在的,個體化的,由一己推及萬有的。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里厄式的反抗,實(shí)事求是,“同鼠疫做斗爭的惟一辦法就是實(shí)事求是”——當(dāng)朗貝爾問及這個詞的意思時,里厄醫(yī)生說:“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義,但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做好我的本職工作。”
里厄相信(作為小說的敘述者,在某種程度上他傳達(dá)了加繆自己的聲音),夢幻隨人而異,而共處的現(xiàn)實(shí)則是把大家團(tuán)結(jié)起來的東西,這個共處的現(xiàn)實(shí)就是災(zāi)難和惡的降臨。在他的身上,加繆呈現(xiàn)了人類通過反抗實(shí)現(xiàn)自我拯救的可能。
當(dāng)小說中人物面臨選擇時,加繆內(nèi)心隱性的圖像也一點(diǎn)點(diǎn)顯露了。在《鼠疫》里,他讓朗貝爾在追求個人幸福和承擔(dān)他人不幸之間選擇,這也是加繆自己內(nèi)心信念的一次考驗(yàn)。里厄醫(yī)生沒有阻止朗貝爾用非常手段離開奧蘭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坦白承認(rèn),在這件事情上他沒有能力去判斷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這正是加繆一以貫之的人道主義的立場:承擔(dān)是一種職責(zé),追求個人的幸福同樣無可非議。
作為一個一直在尋求象征的大師,大海出現(xiàn)在加繆筆下預(yù)示著一條救贖的道路,通向希望和陽光的那一條道路。在《局外人》里,默爾索和瑪麗·卡多納(她是小說中惟一的一個女性,是表明默爾索對外界態(tài)度的重要人物之一)之間的關(guān)系始于一個海濱浴場,在《鼠疫》中,也是一次海水浴使里厄醫(yī)生和達(dá)魯(小說中的另一個主要人物)之間心心相印,建立起了信任和友誼。
這是這部沉悶的小說中最為動人的章節(jié)之一。一個秋天的晚上,里厄和達(dá)魯在一次長談后穿過堆滿了木桶和散發(fā)著魚腥味的場地向防波堤走去,大海在他們前面不遠(yuǎn)處的巨大石基下輕聲吼鳴,它像絲絨那樣厚實(shí),又像獸毛一樣光滑,他們一動不動地浮在水上,面對著懸掛著月亮和布滿星星的天空深深地呼吸。就在他們面對這幅漫無邊際的夜景時,一種奇異的幸福感充滿了全身,雖然這種幸福感讓他們忘卻周圍的事物,也不能忘卻世上的殺戮,但畢竟讓這對朋友暫時地?cái)[脫了這座鼠疫中的城市。當(dāng)他們重新穿上衣服走上歸途時,小說家這樣描繪他們——“他們已成為一對同心同德的朋友,這天夜晚給他們留下了親切的回憶”,接下來的一切,“又將重新開始了”。這是密不透風(fēng)的敘述中少有的一處空白,笨重而又有力的敘事節(jié)奏中加進(jìn)了小提琴般抒情的樂音。這小小的變奏使小說擺脫了敘事的沉悶,也豐富了小說本身,因?yàn)樽非笮腋Ec分擔(dān)苦難之間的兩難,一直是困擾加繆式主人公的一個倫理命題,加繆在這場海水浴中讓這兩難在一對朋友身上和諧起來,就像達(dá)魯說的:“一個真正的人應(yīng)該為受害者做斗爭,不過,要是他因此就不再愛任何別的東西了,那么他進(jìn)行斗爭又是為了什么?”
小說進(jìn)行到這里變成了一篇冗長的哲學(xué)討論,朗貝爾的聲音、里厄醫(yī)生的聲音和達(dá)魯?shù)穆曇艚浑s在一起,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各自所取的方向。這場兩個頁碼的爭論在快要結(jié)束時多個聲部趨向一致,朗貝爾把自己放進(jìn)了他所置身的人群里,在這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個外地人,跟這座城里的人們跟這場突如其來降臨的災(zāi)難毫無關(guān)系。“但是現(xiàn)在我見到了我所見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這城里的人了,這件事跟我們大家都有關(guān)系。”
他留了下來,分擔(dān)他人的不幸使他最終放棄了個體的幸福。他走進(jìn)了他以前一直小心翼翼保持著距離的圣徒和英雄的行列。圣徒朗貝爾此后的工作是主管一個隔離病房的臨時負(fù)責(zé)人。按理說里厄醫(yī)生這時應(yīng)該高興才對,但朗貝爾的詰問——“你們自己不也做出了選擇?你們不也放棄了幸福?”——卻讓他深深沉默了。他明白,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們?yōu)橹釛壸约旱乃鶒鄣摹5约阂膊恢溃鞘裁丛蜃屗釛壛怂鶒郏?dāng)他投入救災(zāi)工作時,已很少想到在外地療養(yǎng)的妻子。
追求個體的幸福,理所當(dāng)然是道德的,分擔(dān)他人的不幸更是高尚的行為,問題是,后者要以前者的犧牲為條件,那么兩者之間擇誰而事,才是真正的道德?人道主義者加繆在這本薄薄的小說里,把這個沉重的命題推到了我們這些當(dāng)代讀者面前。
而他一生的行動和寫作,都是在回答這個問題。在小說和其他敘事性作品中,加繆流露的個人的意愿,是努力成為一個現(xiàn)實(shí)主義者。他鄙薄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在他看來這是在推開現(xiàn)實(shí)的同時假裝不知道這個世界還有災(zāi)難和惡,而成為一個現(xiàn)實(shí)主義者,就要有勇氣承認(rèn)人之不幸并勇于去承擔(dān)。
阿爾貝·加繆不同于19世紀(jì)文學(xué)養(yǎng)育的其他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堅(jiān)持的是一條更加廣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道路。他走在這條道路上,還加進(jìn)了自己的選擇原則。他選擇了大海、雨、陽光、欲望與死亡的斗爭,因?yàn)槟鞘前盐覀兇蠹覉F(tuán)結(jié)起來的東西。在他創(chuàng)造的《局外人》《鼠疫》這些虛構(gòu)世界里,他本可以讓默爾索輕易地撒謊,讓朗貝爾離開這座奧蘭城去和妻子團(tuán)聚,但他沒有這樣做。他讓他們?nèi)コ姓J(rèn),去擔(dān)當(dāng),甚至付出代價。他是通過默爾索、里厄和朗貝爾的選擇傳達(dá)出一個當(dāng)代知識分子在災(zāi)禍面前的選擇。
用照片呈現(xiàn)一個人的一生是困難的,因?yàn)椤耙粋€生命是變化,懷疑,矛盾”。但加繆是真實(shí)的,他在“眾人”之中,與“人數(shù)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他向我們呈現(xiàn)的神話……揭示了人類條件的深刻的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孤獨(dú)和他們對生命的熱愛”。本書收錄了加繆的女兒卡特琳娜·加繆珍藏的家庭照片、報(bào)紙影像、手稿等資料,記錄了加繆從阿爾及利亞的貧窮少年,一步一步走上諾貝爾文學(xué)獎獎臺,并最終以荒誕的方式告別人世的傳奇一生;展現(xiàn)了阿爾貝·加繆作為小說家、劇作家、哲學(xué)家、記者,乃至丈夫和父親的不同側(cè)面。翻開影像集,我們能看到一個充滿魅力的偉大人物,同時,我們也感受到他那些與我們別無二致的譏誚、狡黠、迷戀、驚喜、掙扎、憤怒……影像文字大都節(jié)選自加繆的作品,充滿魅力的形象與閃耀思想之光的文字相互映襯,讓讀者能夠更加直觀地理解加繆其人其作。
“在隆冬,我終于發(fā)現(xiàn),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zhàn)勝的夏天。”在當(dāng)下、在他逝世60周年之際,我們閱讀加繆,并從他的文字中感受這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