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jì)念 | 喬治·斯坦納:一位偉大的歐洲知識(shí)分子
當(dāng)?shù)貢r(shí)間2月3日,著名文學(xué)評(píng)論家喬治· 斯坦納(George Steiner)在英國(guó)劍橋逝世,享年90歲。

喬治· 斯坦納
喬治·斯坦納是一名博學(xué)多才的文學(xué)大師,一名散文家、小說家、教師、學(xué)者和文學(xué)評(píng)論家。他在一系列極具影響力的著作中探討了語(yǔ)言和文化的力量和局限性。喬治·斯坦納1929年出生于巴黎,父母是維也納人。1940年,就在納粹即將占領(lǐng)巴黎前不久,他們一家前往紐約居住。在他就讀的法國(guó)學(xué)校里,只有兩名猶太學(xué)生在大屠殺中幸存下來,他正是其中之一。這深刻地影響了他后來的著作。“我的整個(gè)人生都與死亡、回憶和大屠殺有關(guān)。”斯坦納成了一個(gè)“感恩的流浪者”,他說:“樹有樹根,我有腿; 我的一生都是為了這個(gè)。”他在曼哈頓的紐約法語(yǔ)學(xué)校完成余下學(xué)業(yè),并于1944年成為美國(guó)公民。
斯坦納在他劍橋的家中去世。自1969年以來,他一直是劍橋大學(xué)丘吉爾學(xué)院的杰出學(xué)者。斯坦納會(huì)說四種語(yǔ)言,并以其對(duì)歐洲文學(xué)的廣泛了解而聞名。他出版了20多本文學(xué)著作,除了文學(xué)評(píng)論,還有散文集、中篇小說和三部短篇小說集。同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一道,他維護(hù)西方正統(tǒng)藝術(shù),反對(duì)上世紀(jì)50年代的新批評(píng)主義、60年代的后結(jié)構(gòu)主義和解構(gòu)主義運(yùn)動(dòng),他在早期的文章中預(yù)見到,這一系列運(yùn)動(dòng)意味著“話語(yǔ)的后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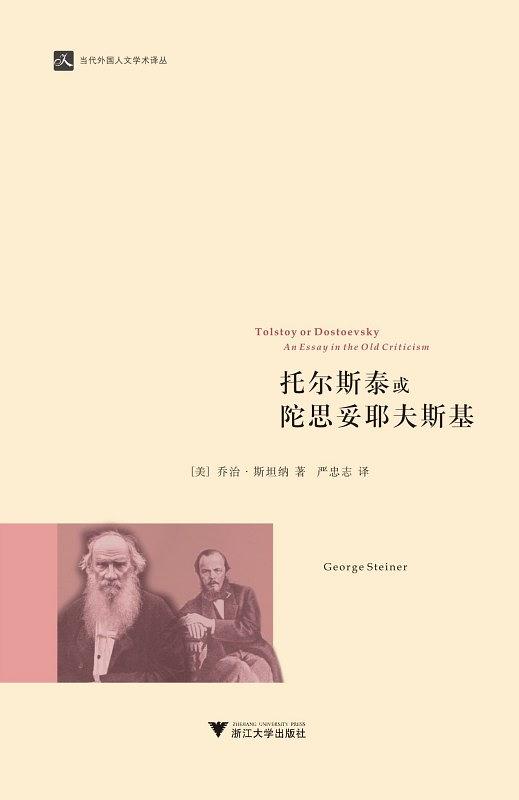
《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為他的英語(yǔ)讀者介紹了很多歐洲大陸作家。在《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1960)中,他分析了這兩位俄羅斯文學(xué)大師;在《語(yǔ)言與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1967)中,他探討了語(yǔ)言在暴行面前的局限性;在《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 ,1975)中,他分析了語(yǔ)言和翻譯。

《語(yǔ)言與沉默》
“喬治·斯坦納為我們理解文學(xué)與社會(huì)之間的關(guān)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魏登菲爾德和尼科爾森(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的艾倫·薩姆森(Alan Samson)說,“他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師和作家,我對(duì)他的死訊深感悲痛。幸好,我們依然擁有他極具開創(chuàng)性的、真正國(guó)際化的、令人贊嘆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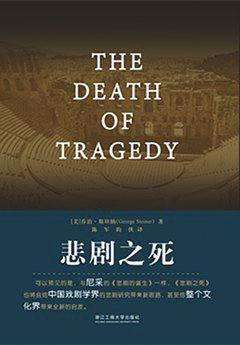
《悲劇之死》
1981年,他在中篇小說《從波蒂奇到圣克里斯托瓦爾》(The Portage to San Cristobal of AH)中想象希特勒在二戰(zhàn)中幸存下來,生活在亞馬遜河的深處。在《語(yǔ)言與沉默》里,斯坦納探索了語(yǔ)言的力量,提出了文化與道德之間關(guān)系的問題。在《創(chuàng)造的語(yǔ)法》(Grammars of Creation)一書中,他寫道:“令我驚訝的是,正如人們所見的那般天真,你可以用人類的語(yǔ)言去愛、去建設(shè)、去原諒,也可以用它去折磨、去恨、去摧毀和消滅。”
“我們現(xiàn)在知道了,一個(gè)人可以在晚上閱讀歌德或里爾克,演奏巴赫和舒伯特,卻在早上去奧斯維辛工作,”他在《語(yǔ)言與沉默》中寫道,“說他不理解他讀的東西,或者說他的耳朵很粗鄙,都是不可能的。從柏拉圖時(shí)代到馬修·阿諾德時(shí)代,知識(shí)一直以一種方式為文學(xué)和社會(huì)提供希望,而這種希望是不言而喻的,即文化是一種人性化的力量,而這種精神的能量又是如何轉(zhuǎn)移到行為上的?”
斯坦納對(duì)于文學(xué)的準(zhǔn)宗教觀點(diǎn)為他的第一本書《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素材,這本書的副標(biāo)題是“一篇舊批評(píng)文章”(An Essay in the Old Criticism)。
他在第一章中寫道:“舊的批評(píng)是由贊美產(chǎn)生的。它有時(shí)會(huì)從文本中退一步,以審視其道德目的。它不將文學(xué)作為孤立的存在,而是歷史政治能量的核心。最重要的是,舊的批評(píng)是哲學(xué)的范圍和脾氣。”
羅伯特·麥克拉姆(Robert McCrum)聘請(qǐng)斯坦納為《觀察家報(bào)》首席評(píng)論家,他也是費(fèi)伯(Faber & Faber)出版社編輯,負(fù)責(zé)斯坦納的作品。他說:“斯坦納是偉大歐洲知識(shí)分子這一正在消亡的物種的一員。他一直同時(shí)扮演著當(dāng)局者和局外人的角色,既在文化之中,也在文化之外。”
1944年,成為美國(guó)公民之后,斯坦納先后在索邦大學(xué)、芝加哥大學(xué)、哈佛大學(xué)和牛津大學(xué)學(xué)習(xí),之后成為《經(jīng)濟(jì)學(xué)人》的主要撰稿人。當(dāng)他被前往普林斯頓高級(jí)研究院面試時(shí),接受了那里的一份工作,呆了兩年,然后去了劍橋的丘吉爾學(xué)院。斯坦納在1974-1994年期間在日內(nèi)瓦大學(xué)擔(dān)任英語(yǔ)和比較文學(xué)教授,并于1994年成為牛津大學(xué)第一位韋登菲爾德勛爵比較文學(xué)教授。
“他是一個(gè)非凡的人物。他是柯勒律治意義上的評(píng)論家,而不是約翰遜意義上的。而且他還是一個(gè)出色的演說家,”麥克拉姆說,“我過去常去他在劍橋的演講,演講結(jié)束時(shí)掌聲雷動(dòng)。我們都完全被他迷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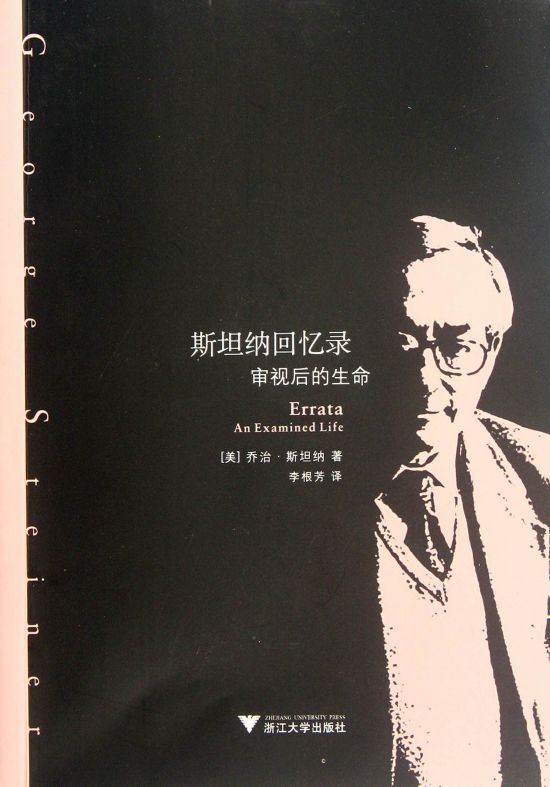
《斯坦納回憶錄》
在《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斯坦納寫道:“偉大的藝術(shù)作品像暴風(fēng)雨一樣從我們身邊掠過,推開感知的大門,以其轉(zhuǎn)化的力量壓迫著我們信仰的建筑……我們?cè)噲D記錄它們的影響,讓我們搖搖欲墜的房屋重新恢復(fù)秩序。通過一些交流的本能,我們?cè)噲D向他人傳達(dá)我們經(jīng)驗(yàn)的品質(zhì)和力量。我們要說服他們敞開心扉。在這種說服的嘗試中,產(chǎn)生了批評(píng)所能提供的最真實(shí)的洞見。”
斯坦納有時(shí)也是個(gè)爭(zhēng)議人物,一些人認(rèn)為他是個(gè)精英主義者,另一些人則認(rèn)為他夸夸其談、自命不凡,而且常常失實(shí)。
文學(xué)評(píng)論家李·西格爾(Lee Siegel)2009年為《紐約時(shí)報(bào)書評(píng)》撰寫了一篇名為《我們的斯坦納問題——我的問題》(Our Steiner Problem - and Mine)的文章。他在其中寫道:“他令人振奮的美德在于,他能夠在一段話里,從畢達(dá)哥拉斯、亞里士多德和但丁,談到尼采和托爾斯泰。而他令人惱火的缺點(diǎn)是,他可以在一段話里,從畢達(dá)哥拉斯,說到亞里士多德和但丁,再到尼采和托爾斯泰。”
用斯坦納自己的話來說,他曾被批評(píng)為“在一個(gè)人人專精于特定領(lǐng)域的時(shí)代,在一個(gè)不再有通才的時(shí)代做一個(gè)通才”。
對(duì)于精英主義的指控,斯坦納通常不予理睬。2001年接受《衛(wèi)報(bào)》采訪時(shí),他表示:“成為精英意味著充滿熱情地去愛,而不是在妥協(xié)中舍棄熱情。如果那就是精英主義,我承認(rèn)我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