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dú)角獸》:科幻、秘符與哲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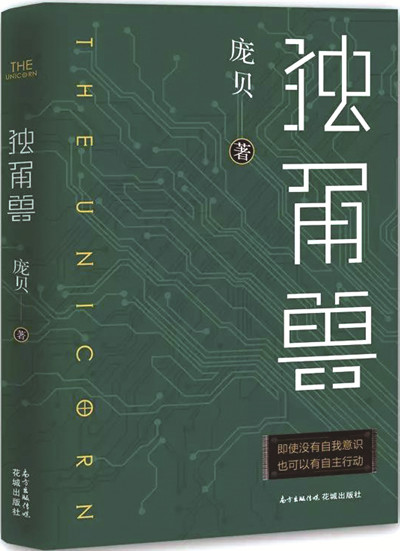
龐貝的《獨(dú)角獸》是一個(gè)風(fēng)格獨(dú)特的既好看又耐看的小說(shuō)文本,現(xiàn)實(shí)與科幻交織,現(xiàn)實(shí)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兼容,小長(zhǎng)篇卻有著大容量。這種藝術(shù)效果的實(shí)現(xiàn),既得益于作者的奇妙構(gòu)思和敘事策略,也有賴于作者的深度思考和隱喻呈現(xiàn)。
與時(shí)下標(biāo)準(zhǔn)的“軟科幻”和“硬科幻”小說(shuō)都不一樣,《獨(dú)角獸》不是天馬行空的浪漫科幻,而是直面現(xiàn)實(shí)課題,基于當(dāng)今人工智能領(lǐng)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是對(duì)看得見(jiàn)的未來(lái)的適度預(yù)測(cè)。特別的技術(shù)含量使這部作品擁有了特別的前沿性。
龐貝曾以歷史題材長(zhǎng)篇小說(shuō)《無(wú)盡藏》令文壇驚艷,《獨(dú)角獸》也延續(xù)了《無(wú)盡藏》的“知識(shí)懸疑小說(shuō)”風(fēng)格。《無(wú)盡藏》的“知識(shí)”是歷史,而《獨(dú)角獸》的“知識(shí)”是科技。與《無(wú)盡藏》的歷史性沉思不同,《獨(dú)角獸》雖依然有《無(wú)盡藏》的懸疑敘事形式,而在表層這種文筆優(yōu)雅的懸疑敘事之下,作品向讀者展現(xiàn)了更有深度的哲學(xué)性探索。這種思索是以隱喻的形式呈現(xiàn)的,而隱喻的具象載體是秘符,是文字。在《獨(dú)角獸》的這個(gè)隱喻設(shè)置中,最重要的是這四個(gè)字:“謊”和“仿”,“真”和“詩(shī)”。
“謊”是測(cè)謊儀,“仿”是仿生人;“真”是這個(gè)故事的真相,“詩(shī)”是人生的某種詩(shī)意境界,也是里爾克描寫?yīng)毥谦F的詩(shī)句。“謊”和“仿”,“真”和“詩(shī)”,這四個(gè)字背后掩藏著非常重要的信息,不僅是字詞,甚至是某種哲學(xué)符號(hào)。
在“謊”和“仿”的范疇里,我們看到小說(shuō)里有測(cè)謊這個(gè)重要情節(jié)。測(cè)謊本身也是一種證偽,而蒙冤入獄的男主艾軻竟是因改進(jìn)國(guó)產(chǎn)測(cè)謊儀技術(shù)而提前獲釋。作為頂級(jí)芯片專家,艾軻的機(jī)器人實(shí)驗(yàn)也是源自測(cè)謊儀的某些技術(shù)性啟發(fā)。科技的發(fā)達(dá)可以帶來(lái)財(cái)富,也會(huì)導(dǎo)致人性的異化。這是技術(shù)的悲哀,也是人的悲哀。《獨(dú)角獸》里也出現(xiàn)了仿生人,這既是人的進(jìn)化,也是人的退化。人們懷疑“真”的存在,在謊言的漩渦里翻滾,最后難免跌入深淵。
在《獨(dú)角獸》的末章,仿生人的出現(xiàn)已然是現(xiàn)實(shí),謊言的存在給人類帶來(lái)更大的恐懼。面對(duì)這樣的現(xiàn)實(shí),作為“原人”的人類必然會(huì)有某種恐懼感,甚至有更多基于恐懼的想象。安·蘭德有一個(gè)著名的論斷,叫作“基于恐懼的論證”。人類生活是基于恐懼,但要止于理性。在這個(gè)歷程中,我們觀察、思慮、想象,甚至把這種恐懼記敘下來(lái),是為重建一種信心。《獨(dú)角獸》直面這種恐懼,對(duì)高科技時(shí)代的人類之境況有深切憂思,也以理性的方式給出重建的信心和拯救的希望,這也是這部小說(shuō)力量感之所在。
《獨(dú)角獸》的另一個(gè)范疇是“真”和“詩(shī)”。“真”和“詩(shī)”在這部小說(shuō)里是以某種變奏的方式交替出現(xiàn)的。對(duì)于“真”的尋找,始自那場(chǎng)令艾軻蒙冤的官司。在這個(gè)探求真相的過(guò)程中,巨大的阻力來(lái)自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謊”和“仿”。在這個(gè)源于真實(shí)的《悲慘世界》式情節(jié)中,當(dāng)艾軻最終在警報(bào)聲中獲知真相時(shí),當(dāng)那位保安員意外地?fù)舻钩謽尩暮芜m時(shí),這個(gè)“真”的意義便有了精彩的彰顯。
“真”和“詩(shī)”是屬于人生某種理想狀態(tài)的寫照,而“謊”和“仿”既是來(lái)自人性本身的弱點(diǎn)和缺陷,也是由于高科技對(duì)人的異化和控制。“謊”是人類與生俱來(lái)的一種存在,在人類漫長(zhǎng)的歷史中,“謊”有時(shí)也演變?yōu)椤爸{”,成為改變歷史進(jìn)程的某種力量。而在今天這樣一個(gè)后現(xiàn)代語(yǔ)境中,“謊”和“仿”正在合力摧毀人類的“真”和“詩(shī)”。小說(shuō)展示的正是這樣一種深刻性。
《獨(dú)角獸》的人物設(shè)置亦可謂是匠心獨(dú)運(yùn)。除了主人公艾軻,“假面人”何適和“破譯者”顧濛二人之間有很多沖突。在大量的人物對(duì)話中,有他們對(duì)于歷史和文化的理解,有對(duì)央視“朗讀者”節(jié)目的理解,還有對(duì)米勒名畫《拾穗者》的經(jīng)濟(jì)學(xué)闡發(fā),由此呈現(xiàn)的沖突代表了人類的兩種價(jià)值取向:一種是基于不允許別人有幸福感的心態(tài)和思想,一種是像顧濛這樣內(nèi)心有詩(shī)情,且堅(jiān)守人之所以為人的真純的東西。這也是人類的現(xiàn)狀。
若說(shuō)顧濛與何適之間是文化觀的沖突,黑客阿桑和賈科長(zhǎng)這一對(duì)人物之間便是生存觀的分歧。顧濛與何適的不同,阿桑與賈科長(zhǎng)的不同,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不同。
《獨(dú)角獸》旨在探討人工智能的科技倫理,這部小說(shuō)是用科技、創(chuàng)富、知識(shí)、人性這些元素作為考題,且是把人性作為一個(gè)最大的考題,將其放置在跨過(guò)商戰(zhàn)的大背景之下,由此觸及人類現(xiàn)在和未來(lái)的難題。作者是用這種方式結(jié)構(gòu)這部小說(shuō),由當(dāng)下無(wú)限伸展到未來(lái)。
這部作品探討人工智能的技術(shù)倫理和未來(lái)圖景,其實(shí)也是在探討人的底線問(wèn)題,作者是在嚴(yán)肅地拷問(wèn):人的私欲究竟可以膨脹到一種什么程度?那條警示性的堅(jiān)硬的底線究竟在哪里?《獨(dú)角獸》中的主人公艾軻并不認(rèn)同時(shí)下流行的所謂“狼哲學(xué)”,因?yàn)樗陨頁(yè)碛械氖仟?dú)角獸氣質(zhì)。獨(dú)角獸不是狼(其實(shí)作為生物的狼是被人類丑化了,人類倒是應(yīng)對(duì)此反省),他最終選擇在郊外隱居(但并未放棄科研工作),他功成身退寧愿讓那個(gè)阿爾法程序代替自己擔(dān)任公司董事,這無(wú)疑是一種頗有深意的選擇。
類似這種基于現(xiàn)實(shí)科技成果的有一定科幻色彩的小說(shuō),是與那些“軟科幻”和“硬科幻”小說(shuō)都不一樣的新類型,有人名之為“科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這類小說(shuō)近來(lái)頻繁出現(xiàn),而《獨(dú)角獸》無(wú)疑最有深度也是最好看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