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利斯當(dāng)與伊瑟》:搖曳的愛之禮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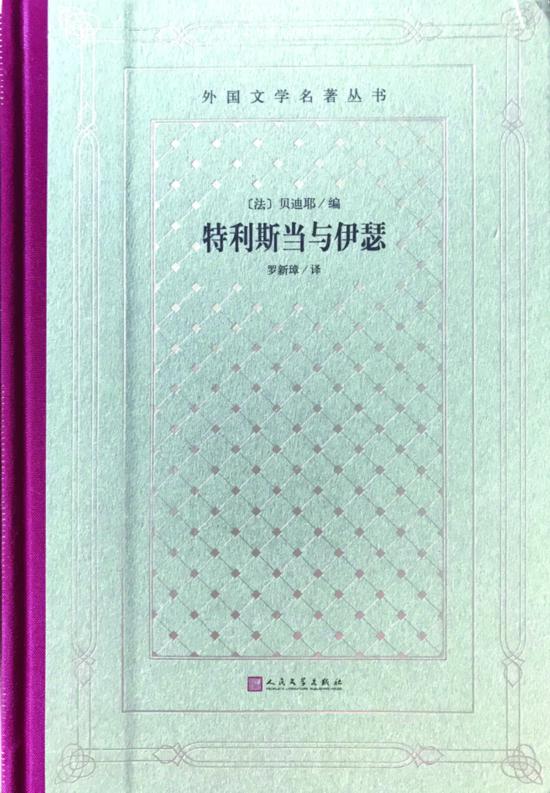
施康強(qiáng)
翻譯家、散文家施康強(qiáng)先生于2019年10月27日不幸逝世。施先生曾為羅新璋譯著《特利斯當(dāng)與伊瑟》作跋,本報(bào)特刊此文,以表緬懷之情。 ——編 者
“諸位大臣,孤家叨天之福,復(fù)承諸卿之力,得以收復(fù)國土,昭雪世仇,對先父業(yè)已盡到人子之責(zé)。但把孤兒孽子撫育成人的,是駱豪德與康沃爾的馬克王:這兩位長者,實(shí)我重生父母。受恩不忘,敢不竭誠圖報(bào)!……”
如果不是“康沃爾的馬克王”提醒這里講的是個(gè)外國故事,讀者會(huì)以為自己是在讀一篇明清擬話本小說。正是這一文體上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形成羅新璋譯《特利斯當(dāng)與伊瑟》的最大特色。特利斯當(dāng)與伊瑟的故事起源于古代凱爾特族的傳說,在中世紀(jì)被吟唱詩人寫成文字時(shí)染上騎士文學(xué)的色彩,今天通行的是法國學(xué)者貝迪耶的近代法語改寫本(1900)。說是近代法語,遣字造句多見古意,不同于近代作家寫小說。翻譯這本書,相應(yīng)要求譯者使用一種與現(xiàn)代漢語有別的白話,讓讀者產(chǎn)生一種時(shí)間上的距離感。譯者這一努力是成功的。
如譯者在《譯本序》中所說,朱光潛先生早年譯過此書。譯家大概都有這種經(jīng)驗(yàn):如系重譯,動(dòng)筆前最好不要先讀舊譯本,更忌把舊譯本放在案頭,隨時(shí)參照,否則舊譯將似怨魂附體,處處糾纏不清。倒是全書或一章譯畢后,可與舊譯對照,互參得失,既免剽竊之誚,復(fù)得他山之助。譯者對朱譯著實(shí)做了一番消化功夫,推陳出新,同時(shí)決不抹殺其精彩之筆。如第十七章《狄那斯》,好友卡埃敦陪同特利斯當(dāng)去偷窺隨國王出獵的伊瑟王后。他們先是看到國王的隨從,然后是王后的儀仗。此段文字搖曳多姿,極盡鋪張之能事。試以金圣嘆評《水滸》之法評之:
浣婦,侍婢,勛貴的妻女走過之后,來了一匹駿馬,上騎一位麗人。卡埃敦乍見之下,驚為天人,乃嘆道:“啊,真王后也!”特利斯當(dāng)告訴他,來者不是王后,乃她的貼身婢女嘉湄。是為春云一展。“接著,又過來一位騎銀馬女郎,皮膚比陽春白雪還白,櫻唇比三月玫瑰還紅,眼睛亮得如同清泉里閃爍的星星。”卡埃敦以為這回該是王后本人了,特利斯當(dāng)又告訴他,此乃她忠心的伴娘白蘭仙。是為春云再展。然后,“此刻路上猛然間現(xiàn)出一片奇彩,仿佛枝葉間突然迸出萬道霞光:金發(fā)伊瑟終于駕臨!”是為春云三展。“此刻路上猛然間現(xiàn)出一片奇彩”,乃沿用朱譯“那條路上猛然間現(xiàn)出一片奇彩”,特為表出之。
譯者潛心翻譯理論與實(shí)踐多年,平素服膺傅雷與錢鍾書先生。傅雷善用“一字二譯”法,如《貢第德》中:“瑪丁下了斷語,說人天生只有兩條路:不是在憂急騷動(dòng)中討生活,便是在煩悶無聊中挨日子。”“討生活”與“挨日子”,原文中是一個(gè)詞,直譯應(yīng)作“人生……不是在憂急騷動(dòng)中,便是在煩悶無聊中過日子”,而漢語的行文習(xí)慣,此處宜用兩個(gè)同義詞。譯者偷得此法,時(shí)見應(yīng)用。如該書第六章《大松樹》,馬克王聽信讒言,欲監(jiān)視其妻,但白蘭仙早有覺察,提醒特利斯當(dāng)與伊瑟注意。“故馬克屢試其妻,伊瑟亦未墜其彀中。”此亦一字二譯,蓋從原文直譯,應(yīng)作“國王徒然設(shè)計(jì)考驗(yàn)伊瑟”。譯者乃剖一句為兩句,前句用“妻”字指伊瑟,以免重復(fù)。又,錢鍾書《談藝錄》引鄧南遮言,一字在三頁后重出,便刺渠耳。譯者亦注意此道,盡量避免在相鄰兩頁中有重出的動(dòng)詞和形容詞,讀者自可驗(yàn)證。
遇到人名,譯者喜歡音義兼譯。《列那狐的故事》中,他譯狐貍太太的芳名為“艾莫麗”(Hermeline),兩只烏鴉分別為“黑爾懵”(Ermande)和“吉失靈”(Tiercelin),母雞名為“牝特”(Pinte),綿羊名為“裴羚”(Bélin le mouton)等。該書譯愛爾蘭巨人名為“莫豪敵”(le Morholt),忠心的伴娘名為“白蘭仙”(Brangien),宮娥名為“嘉湄”(Camille)、“薄履娥”(Brunehaut),矮子名為“伏僂生”(le nain Frocin),特利斯當(dāng)?shù)膼廴麨椤坝锐Y騰”(Husdent),等等,亦小慧可嘉。可能是為了與朱譯有別,男主人公的名字譯成“特利斯當(dāng)”而不是“愁斯丹”,而這個(gè)名字本有“愁郁”的意思在內(nèi)。反之,“白蘭仙”這一類譯名,音雖近似,義與人也相配,但是原名沒有似花如仙的含義。翻譯之道,不是過于原文,就是不及。原作于譯文白得一筆利息,如曹禺譯莎士比亞名劇為《柔蜜歐與幽麗葉》,有意使讀者望文生義,作者當(dāng)欣然笑納。
至于特利斯當(dāng)與伊瑟的故事本身,據(jù)說愛情與死亡是文學(xué)的永恒主題,那么這對男女雙雙殉情,愛情加死亡,可謂雙料主題了。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臺(tái)、特利斯當(dāng)與伊瑟,普天下有情人當(dāng)為他們一灑同情之淚。人過了浪漫、感傷的年齡,雖不敢以大丈夫自居,倒也不輕易濕眼眶酸鼻子,于文學(xué)作品當(dāng)別有會(huì)心,賞鑒于牝牡驪黃之外,或直承寡情者與不賢者同識(shí)其小,亦無不可。讀凡羅那情人的故事,可能對那場瘟疫更感興趣;對化蝶的梁祝,倒愿意考證他們的籍貫履歷。關(guān)于特利斯當(dāng)與伊瑟的傳奇,說不定更注意從中窺見凱爾特舊俗與中世紀(jì)的古風(fēng)。書中屢屢言及馬克王的寢宮,不但外間有勇士值衛(wèi),就是內(nèi)室御榻之旁,也有人陪宿——不是嬌媚的宮娥,而是赳赳武夫。想起趙匡胤那句名言:“臥榻之側(cè),豈容他人鼾睡”,馬克王真雅量矣。又,中世紀(jì)的騎士階層乃至國王都不識(shí)字,立言命筆是教會(huì)的專職。特利斯當(dāng)致書國王,須由隱士代筆;國王獲書后,須由祭司開讀。
第三章《金發(fā)美人》,特利斯當(dāng)前往愛爾蘭尋找金發(fā)美人,愛爾蘭國王為表示不計(jì)較他殺了妻弟莫豪敵的前仇,應(yīng)伊瑟之請,吻了特利斯當(dāng)?shù)淖齑健橄笳骱徒狻捤《游鞘菤W洲中世紀(jì)的風(fēng)俗,起源于原始基督教信徒之間互祝平安的“神圣之吻”。周作人譯丹麥尼洛普博士的《接吻與其歷史》(見《永日集》)舉了幾個(gè)法國的例子,未提愛爾蘭國王給特利斯當(dāng)?shù)奈恰4孙L(fēng)中世紀(jì)后極為罕見,僅能找到兩例。1563年法國天主教徒的首腦德·吉斯公爵被暗殺,他的寡婦遇見新教徒的領(lǐng)袖科利尼大將,后者立誓說他并未參與暗殺,于是雙方接吻,互釋前嫌。1792年法國大革命期間,立法議會(huì)內(nèi)部斗爭激烈,而普奧聯(lián)軍正向巴黎進(jìn)逼。議員拉穆萊特在議會(huì)上發(fā)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呼吁大家忘記一切爭執(zhí),團(tuán)結(jié)對外。于是議員們立刻互相擁抱,交換和解的接吻。不過到了第二天,爭執(zhí)又復(fù)生起。
特利斯當(dāng)與伊瑟不同于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臺(tái)。后兩對是純情的少男少女,前者當(dāng)時(shí)有背封建倫常,在今天也是一種通奸關(guān)系。騎士對他崇拜的貴婦人本應(yīng)發(fā)乎情而止乎禮,事實(shí)上精神戀愛更是“不可能的愛情”。騎士文學(xué)作者寫到越禮行為時(shí)都有點(diǎn)心虛,總想為主人公找點(diǎn)辯解,“藥酒”乃成為騎士傳奇中常用的關(guān)目。第十二章《神判》,馬克率群臣在兩國交界處的荒原與亞瑟王相會(huì)。亞瑟王的圓桌騎士中以湖上騎士郎世樂最有名、最驍勇,他與王后桂乃芬相愛。法國國立圖書館收藏的一幅15世紀(jì)版畫上,桂乃芬和郎世樂,與特利斯當(dāng)和伊瑟一樣,也在一條船上共飲藥酒。英國作者馬羅禮于15世紀(jì)寫定的《亞瑟王傳奇》中無此情節(jié),但該書第十一卷寫郎世樂被人敬了一杯藥酒,頓覺春情蕩漾,把握不住,遂把伊蘭公主誤作情人桂乃芬王后,與她同房,后來生下最純潔的高朗翰騎士,完成取回圣杯的宏業(yè)。這里藥酒又用來開脫郎世樂背棄桂乃芬的行為了。中國古代小說、院本乃至當(dāng)代影視亦有一俗套:男方對女方有欲念而女方無意,男方便設(shè)法把女方灌醉或在酒里下麻藥或安眠藥,在女方無力反抗時(shí)得逞。歐洲古代的藥酒當(dāng)是被夸大了效用的媚藥。中土非無此物,但在文學(xué)上未扮演重要角色:才子佳人定情,以詩,以扇,以香羅帕、描金鳳、玉蜻蜓。此物不祥,偶爾出現(xiàn),必致人死命,如《趙飛燕外傳》中的漢成帝,又如清河縣開生藥鋪的西門大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