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遠濤讀《到婚禮去》|伯杰筆下的婚禮哪年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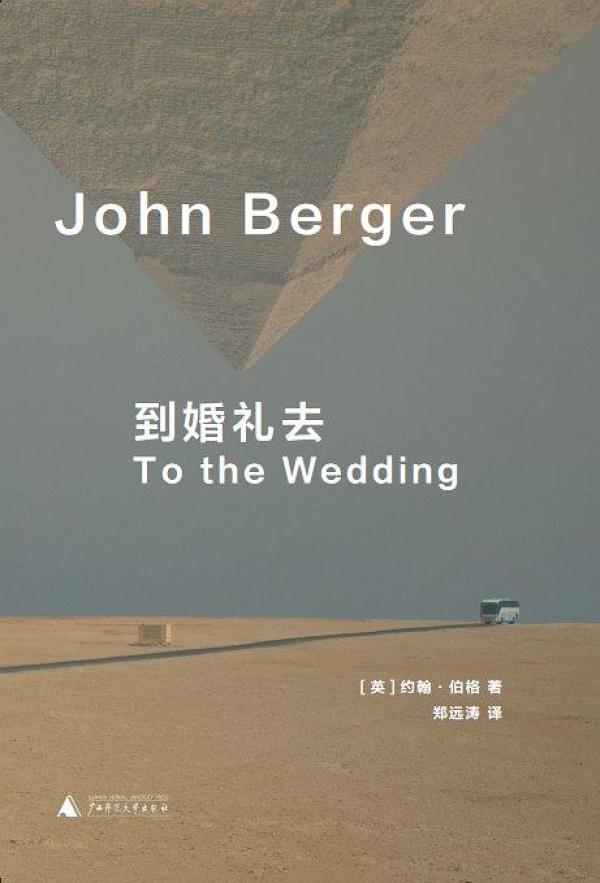
《到婚禮去》,[美]約翰·伯格著,鄭遠濤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272頁,52.00元
但凡詹姆斯·喬伊斯的書迷,不會不知道6月16日這個日子。1904年6月16日,喬伊斯初次約會諾拉·巴納克爾(Nora Barnacle)小姐,后來的喬伊斯夫人。出于紀念,作家把曠世之作《尤利西斯》的背景設定在此年此月此日,以小說男主角布盧姆在都柏林街頭游蕩十八小時的經(jīng)歷和意識流動開創(chuàng)出文學里活色生香的一天。每年世界各地均有讀者慶祝“布盧姆日”。
曾經(jīng)有一個十四歲的倫敦小伙子,在連接1940年與1941年的那個冬天航行于《尤利西斯》的詞語海洋,迷途忘返,當時他不知道,此書作者喬伊斯正在瑞士蘇黎世奄奄一息。當二十世紀列車骎骎行駛到世紀末,那個十四歲小伙子約翰·伯杰(John Berger, 1926-2017,又譯約翰·伯格)早已是著名作家,六十九歲寫成一本以時間為母題的小說To the Wedding(1995)。他同樣透露給讀者一個日子:妮農(Ninon)的婚禮會在“六月七號,禮拜五”舉行。我因為翻譯《到婚禮去》記住了這個日子。
故事梗概倒也簡單,因“冷戰(zhàn)”而分隔于異國多年的父親尚·菲列羅(Jean Ferrero)和母親澤德娜(Zdena),一西一東,同時穿越半個歐洲,去出席女兒妮農的婚禮。在講述旅途的同時,小說穿插以尚、澤德娜、妮農等人物的往事,各人自己的嗓音逐一浮現(xiàn),憶及往事多采用過去時態(tài),但也不盡如此。美麗又活潑的妮農,愛上了年輕的意大利人吉諾(Gino),但她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絕癥病毒,一度萬念俱灰。最終妮農和吉諾決定結婚來慶祝尚在最美時候的青春。兩人商量著婚禮地點和日期:“吉諾知道全年的每一天是禮拜幾。這是他趕集練就的本領。”他們準備在“六月七號,禮拜五”,在波河(Po)入海口的一個意大利村子結婚。
婚禮一幕是全書的華彩段落,它以將來時態(tài)糅合現(xiàn)在時態(tài)來敘述。敘述者這樣告白:“……婚禮尚未發(fā)生。但是正如索福克勒斯知道的,一個故事的未來永遠在當下。婚禮尚未開始。我會給你講它的事。”將來之中又有將來:在婚宴狂歡的敘事主體中,插敘著如同電影閃進一般的場景,妮農預先想見了自己未來病重的情形,小說在狂喜里交織大悲。
譯竣后意猶未盡,于是把文學教授拉爾夫·赫特爾(Ralf Hertel)講它的論文也一并譯介出來,赫特爾將婚禮日期寫為“六月八日”,不是我已熟悉的“六月七號,禮拜五”。詢之于教授本人,方知不是筆誤,他依據(jù)的英國版確實另有一個婚禮日期。我感到震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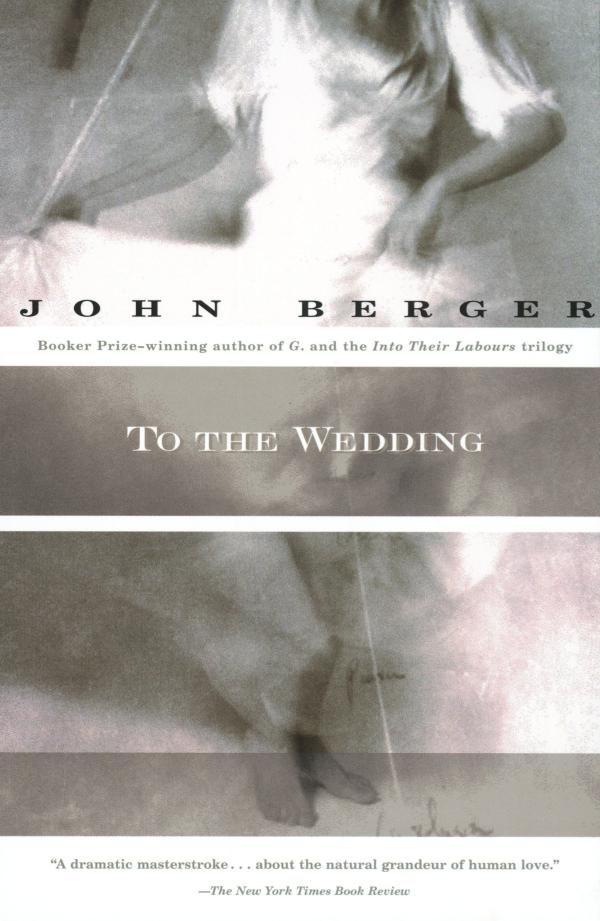
《到婚禮去》
英語名家的原著通常分為美、英兩個版本,由不同出版社發(fā)行,在各自地區(qū)的市場銷售。我住在美國,本來順理成章地采用了紐約Pantheon出版社1995年美國版作為工作樣書;英版同年由倫敦Bloomsbury出版社推出,我手邊也有。英語國家發(fā)行的《到婚禮去》至今還是這兩個版本的重印。英、美版頁碼相同,版式也大致相同,除了美版別出心裁,在每章開頭多放了一個塔瑪(tama)許愿牌圖案之外,似乎沒有區(qū)別。那“六月八日”卻推翻了想當然耳。身為譯者,我不得不追究兩版的差別,最終發(fā)現(xiàn)英、美版的文本有好幾處時間歧異:
(一)第十六頁(英文原著頁數(shù),下同),澤德娜憶及自己離開愛人尚·菲列羅和女兒毅然回國的往事,思緒中有一句:“十七年前那天晚上,她對尚問及簽證的時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英版)此處美版為“十年前”。
(二)第七十五頁,妮農剛確診感染艾滋病時,英版內心獨白為:“爸爸,你能聽見我說話嗎?我二十三歲,就要死了。”美版“二十三歲”作“二十四歲”。到第八十三頁,妮農去監(jiān)獄探望將病毒傳染給她的露水情人,憤然對他說:“二十四歲我就要死了。”此處英、美版則一致。
(三)第一百十一頁出現(xiàn)全書最耐人尋味的版本差異。英版將婚禮日期定為“六月八號,禮拜三”,美版則作“六月七號,禮拜五”。兩個日子一望而知不同年——一場婚禮,兩個年份?
討論時間歧異(一)(二)(三)之前,讓我們先找到參照時刻,來搭建一個結實的框架,這種時刻包括布拉格之春。
約翰·伯杰落筆細致,兼用明寫、暗寫來交代妮農成長不同階段的歲數(shù)與年份。非但如此,他還提供足夠的線索讓我們追溯妮農父母尚·菲列羅、澤德娜生命中的一些關鍵時間點。小說提及不少歷史大事,比如原著第十四頁(中譯本頁碼同)寫澤德娜“二十五年前”在布拉格讀書,時值1968年布拉格之春;而小說中提示的最晚發(fā)生的歷史事件,當為斯洛伐克變成獨立共和國(1993年1月1日):中譯本一百八十四頁,去婚禮途中的澤德娜,手袋里有“新辦的斯洛伐克護照”。據(jù)伯杰自己在紀錄片《恩典的輕觸》(A Touch of Grace, 1996)中回憶,他花了兩年寫《到婚禮去》(1995年出版)。綜合上述可以推測:作家在1993年動筆寫這小說,并將現(xiàn)實生活的當下,用作故事里的當下時間。換言之,小說動筆之初把故事當下設定為1993年。
同樣第十四頁,澤德娜1969年圣誕節(jié)逃亡國外,輾轉到達巴黎,其后和未來的妮農爸爸尚·菲列羅邂逅于聲援捷克難民的晚會,晚會時間可推斷為1970年。值得一提,原著第十二頁(譯本同頁)還交代“二十六年前”尚·菲列羅和妻子妮戈爾(Nicole)一起住在法國市鎮(zhèn)莫達訥,妮戈爾無法忍受丈夫對社會運動的熱忱,棄他而去。參照布拉格之春為“二十五年前”,可知妮戈爾1967年出走;三年后,尚與澤德娜相遇。
第十四到十五頁還講了1970年10月的事:智利政治家、社會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贏得大選,就任總統(tǒng),使戀愛中的尚、澤德娜動了遷居圣地亞哥的念頭。11月,澤德娜告訴尚她懷孕了,兩人決定留住孩子。孩子就是妮農,她肯定生于1971年。
女兒妮農六歲時,澤德娜從電臺廣播得知一百個捷克公民聯(lián)名請愿,政治氣候出現(xiàn)轉機,決定回去看看,當時她出國已有八年(15頁,各版本同)。小說雖未道破,但這無疑是指《七七憲章》發(fā)表那一年,1977年。
上一段的基礎讓我們能夠探明時間歧異(一)。
美版“十年前”與女兒分離,明顯有誤,因為1977年再加上十年才1987年,到不了當下(前述小說動筆之初,它設定為1993年)。英版“十七年前”,計得故事當下為1994年,以小說1995年出版而言,是合理的。美版“十年前”犯了編校錯誤。
現(xiàn)在來談時間歧異(二)。英版先二十三歲,再二十四歲;美版始終二十四歲。英版未必自相矛盾。從發(fā)現(xiàn)感染到探監(jiān),妮農中間經(jīng)歷了一些事:她取消和男友吉諾的約會,用明信片告知他去做血檢,并向監(jiān)獄寄材料申請?zhí)奖O(jiān),經(jīng)等待,方才獲得獄方的批準。在此期間,且不說妮農是否度過了生日,她至少是更接近二十四周歲了,在獄中沖口而出“二十四歲我就要死了”,合情合理。此時她對青春流逝的感受肯定特別強烈。可是,如果英版“二十三歲”系作者有意為之,美版為什么偏偏要用兩個“二十四歲”呢?我們稱它為疑問(I),押后討論。
輪到時間歧異(三),不可能位于同一年的“六月七號,禮拜五”(美版)和“六月八號,禮拜三”(英版)。它顯然要求我們探究:“婚禮在哪年舉行?”
先來探討故事的當下設在哪一年。中譯本附錄的赫特爾論文總結了故事的當下時間框架,它開始于復活節(jié)禮拜天(通常為3月底4月內),終結于當年6月上旬的婚禮(婚禮以現(xiàn)在時態(tài)糅合將來時態(tài)敘述,效果恍如當下)。故事的當下未曾跨年。所以,問婚禮哪年舉行,等于問:哪年是故事的當下?
前面講過小說動筆之初把故事當下設定為1993年。它和兩個事實不接榫:
(a)故事中妮農1971年生,現(xiàn)年二十三/二十四歲;
(b)由萬年歷查得,1993年6月7號、8號為禮拜一和禮拜二,與美、英版的婚禮日期均不符。
看來伯杰疏忽了:小說兩年寫成,這已不是動筆時的1993年。筆下“二十五年前”“二十六年前”云云,本應與時俱進才對。既然妮農生于1971年、年滿或將滿二十四歲,按理,故事當下該是1995年。然而查對萬年歷,1995年6月7號、8號卻是禮拜三、禮拜四,與美、英版的婚禮日期也均不相符。
伯杰計年是不夠周密,但意圖足夠清楚:他提示了女主角的生年,說明了她的年齡,又以“幾月幾號,禮拜幾”的相交之點,使婚禮年份能夠被讀者錨定。既然婚禮不在1995年,我們且看周邊年份。依據(jù)萬年歷,1994年的六月八號確是禮拜三,和英版婚期相符。1996年的六月七號,則果然是禮拜五,讓美版的婚期也有了著落。
現(xiàn)在可談談疑問(I):英版妮農的當下年齡從二十三歲進展到二十四歲,較顯年輕,令1994這偏早的年份更為可信。其實,英版故事梗概講明妮農“二十三歲,將死于艾滋病”(為中譯本的文案所沿用)。英版妮農偏年輕,與該版把當下+婚期定于1994年的事實互為佐證。美版的兩個二十四歲稍后談。
通觀時間歧異(一)(二)(三),英版處處合理,美版則在(一)有明顯差錯(“十年前”)。英版表現(xiàn)更佳,況且,伯杰是英國作家。我至此決定,把英版當作翻譯所依據(jù)的“善本”,鄭重地修改婚期為“六月八號,禮拜三”,并囑咐編輯在中譯本前面加上:“據(jù)英國Bloomsbury出版社1995年版本譯出。”
美版稍有紕漏,我們無須把嬰兒連洗澡水一起潑掉;它的“六月七號,禮拜五”仍可能意味深長。首先要明確,這不可能是筆誤、印錯,鑒于約翰·伯杰的盛名,也決不會是編輯擅改。對此,赫特爾教授回復電郵表示,如有更改也肯定是伯杰自己所為,婚禮日期看來對作家很重要,至于為何要兩版不同,則不得而知。上文談時間歧異(三)為求簡練,只說到英版婚期為禮拜三、美版為禮拜五,其實差別不止于此,書中還存在用其他“禮拜幾”信息與相應版本的婚期相配合的做法。比如尚·菲列羅開摩托車前往婚禮時,從法國山區(qū)進入意大利地界,清晨在山路遇見牧羊人并交談,牧羊人問他今天是否禮拜天,英版摩托車手答“禮拜一”,美版答“禮拜三”(原著42頁),各與相應婚期之間留空兩天。進入意大利后,摩托車手在波河邊幾個網(wǎng)絡黑客少年的小屋過了一夜(可推斷,英版為禮拜一夜晚;美版為禮拜三夜晚);循另一路線前來的澤德娜,同一天夜晚則在跨境大巴上度過。次日,在英版該是禮拜二,在美版該是禮拜四,摩托車手在碼頭接到了澤德娜。這天晚上即婚禮前夜,兩人已抵達目的地,小說言明澤德娜是在舉行婚禮的村子下榻的;婚禮那天拂曉,她被面包車的聲響吵醒了(譯本202頁)。此外還有一處歧異,在禮拜三結婚的英版十一頁,摩托車手在電話里向未來親家公說:“禮拜二咱們就在一起了”,顯然將兩人在婚禮前夜(禮拜二)的碰頭也算作“在一起”;美版為“禮拜五咱們就在一起了”,即禮拜五婚禮那天才正式算作大家“在一起”。各種細節(jié)珠聯(lián)璧合,無疑是作者手筆。
所以“六月七號,禮拜五”有何微言大義?即便它(或者英版的“六月八號,禮拜三”)像喬伊斯的“六月十六”一樣是個暗碼、私人紀念日,我們也無從知曉,就讓我們專注于有實證的年份問題吧。前述和它吻合的年份是1996年。然而妮農生于1971年,她二十四歲是在1995年——小說的出版年。把1995用作故事當下,難道不是最合理的嗎?美版偏偏繞路而行,一腳跨進未來,把當下+婚禮設定為1996年。美版著重于故事的未來性。
回到疑問(I):前述英版妮農先二十三歲、再二十四歲,年齡偏小,向較早的一年1994年靠攏。同理,美版妮農兩次二十四歲,年齡偏大,為較晚的一年1996年增強說服力。
伯杰沒有同時改動“二十五年前”發(fā)生布拉格之春事件(14頁)等指涉故事當下的時間說法,導致居于時間軸較遠一端(1996年)的美版故事當下,比英版含有較多矛盾。但請注意,他在任何版本都從未寫出婚禮的年份,一切都是隱含著的,那一處二十三/二十四歲的歧異也是很微妙的差別。雖然“二十五年前”云云是計少了,一般讀者并不會看出漏洞。

約翰·伯杰
我無意煞有介事。除了我這樣的特殊讀者因工作需要以外,試問有多少人會兼讀英美兩版,并且注意到當中的細微差異?作家明知讀者難以察覺而照樣予以安排,可以稱之為匠心獨運,也可以叫做任性。伯杰的“任性”,是想告訴讀者什么嗎?他這樣處理近乎瞞天過海,也許是更想告訴自己一點什么,并杜絕好事的記者追問。要知道,《到婚禮去》在他是個分外切身的故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艾滋病仍是世紀絕癥,無數(shù)人因而身陷地獄般的苦難,也令親友痛徹心肺;在歐美一些大都市的同性戀男性群體中,病魔奪走的是整整一代精英。蘇珊·桑塔格有感于此,寫了《艾滋病及其隱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伯杰作為桑塔格的好友,同樣有朋友罹患艾滋病,他說這疾病對他“并不是那么遙遠的事”,他感到自己也要做些什么,開始寫起《到婚禮去》來。豈料小說寫到一半,想象竟與現(xiàn)實悲哀地交集相會:他從事電影導演的兒子雅各布(Jacob)之妻確診感染了HIV。由于此事,他一度考慮放棄這小說,后來才決心繼續(xù)寫完,一邊從旁照料兒媳。出書不久,兒媳就因艾滋病去世了,那是1995年。
所以,英、美版近乎隱秘的時間差異,在出版那一年,令讀者當下走進一條他們難以發(fā)覺卻畢竟存在的語義歧路,故事在這里神奇地分岔:它要么回顧1994年,已經(jīng)發(fā)生;要么前瞻1996年,尚未來臨——猶如古羅馬的雙臉門神雅努斯一般,既面向過去,又面向將來(說來也巧:Janus和Jacob第一個音節(jié)拼寫相同)。雅努斯司掌過渡、產生、旅程、流通(exchange), 均屬《到婚禮去》的主題,伯杰自己就說,To the Wedding題目的關鍵詞是介詞to。雅努斯是開始與終結之神,一月一號為其圣日(沿用至今表示“一月”的單詞January意即Janus之月);他也是古人締結婚姻時崇拜的神明,而關于妮農,吉諾不是說過他們倆“結婚那天會是她重生的開始”嗎(210頁,譯本,下同)?小說只有一次提到羅馬,因為婚禮廣場上有一棵懸鈴樹:“許久以前,在一棵懸鈴樹的挖空的樹樁里,有位羅馬執(zhí)政官舉辦過十八名客人的晚宴”(221頁),雖然僅此一次,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舉行婚禮的地方正是意大利,小說也強調意大利人活在當下(“天才全部發(fā)揮在享受上”“和斯拉夫人正相反”,173頁)。既然這是一部蘊藏無數(shù)神話典故與文學象征的小說(參見赫特爾,亦見拙文《〈到婚禮去〉的重負和恩典》),伯杰可能暗用了雅努斯象征來喻示這婚禮既在過去又在未來的二重性。這么說當然是我的猜想,絕非考證,但也不妨以王爾德的理論視之:評論是在作品之內創(chuàng)造(a creation within a creation)。如赫特爾所言,小說征用了古羅馬以降西方文學里恒久不衰的一個主題——carpe diem:把握今朝、及時行樂。雅努斯身處當下,掌控著時間,過去未來之門同時對他敞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在過去,妮農有過一個給她帶來死亡前景的露水情人,可哀可嘆;但是在未來,她依然會擁有一個予她生命希冀的丈夫,又何其幸福!然而,我們也不該忘了《到婚禮去》的元小說(metafiction)性質,它被設定為一個希臘盲人懷著深情擬想出來的故事,是各種嗓音合成的祈禱、寄盼,而激發(fā)盲人想象的、作為故事模特兒的妮農,其真實人生際遇興許和小說截然相反:她似乎患了重病,預定的婚禮已告吹(第4、5頁)。“在音樂里,希望和失落雙生”(227頁),一如生死、福禍之相倚,一如想象與現(xiàn)實之交織互成,一如靈性與物質之不可分割:這種種辯證關系,本來就內蘊于《到婚禮去》,是故事的精神張力所在。莫非,伯杰舍棄最順理成章的當下一年(1995),利用1994/1996作雙重安排,是暗示著當下時間之門兼向過去和未來洞開?我不禁想起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帶有玄學色彩的電影《薇若妮卡的雙重生命》(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片中波蘭少女登臺演唱時突發(fā)心臟病死去,而那個和她面貌畢肖、心臟也一般脆弱的法國姑娘在冥冥中似有所感,決定停止學聲樂,仿佛因而避免了自己的夭折。伯杰稱贊基氏為“電影小說家”;我思索他筆下的妮農擁有雙重婚禮日期及年齡歧異這一點時,總會隱隱感到她好像是極為相似的兩個女子,代表兩種命運。基氏電影另一個譯名是《兩生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或許可以說,伯杰用一枝悼念綻放并凋謝于過去的逝者,另一枝是未來之花,獻給生者,可能預示著一顆希望的果實、一次命運的逆轉:畢竟,美版中1996年結婚的妮農,比1994年結婚的她多了整整兩年,而那兩年極其關鍵(因為婚期將近時醫(yī)生對吉諾說,可以指望妮農前面還會有“兩年、三年、三年半的好時光”)。不同于英版文案,美版只字未提妮農“將死于艾滋病”,也許并非偶然。
恰也是1996年成了艾滋病治療史上的轉捩點:這一年,發(fā)明雞尾酒療法的華裔美籍醫(yī)生何大一當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云人物。該療法的推廣令艾滋病發(fā)病率在歐美很快降了下來,漸漸地,艾滋病感染在世界發(fā)達地區(qū)成了一種可控的慢性病。文學創(chuàng)作以想象力介入現(xiàn)實,科學進步也干預著小說的天地。伯杰肯定欣慰于人間悲劇的減少,但是他這本杰作并沒有隨著舊聞埋沒,卻因其超越性的文學品質而常讀常新:每次重讀,便是再次進入那個當下。
在一篇寫于1991年向詹姆斯·喬伊斯致敬的散文里,伯杰這樣寫道:“今天,五十年后,我繼續(xù)過著喬伊斯以巨大力量為我準備的生活,我成了一個作家。在我尚且懵懂無知的年紀,是他向我展示了文學敵對于一切等級體系,而去區(qū)分事實與想象、事件與情感、主角與敘述者,便是停留在旱地上,永不起航。”《到婚禮去》從創(chuàng)作到傳播,從作者那一端到讀者這一端,都有種種“事實與想象”始終在交織不已、難解難分。本來妮農是死是生,皆屬小說,和我們有什么相干?然而她不是向壁虛造的人物,她代表著千千萬萬曾因艾滋病受苦的當代女子。我們覺得她近在眼前,才會念念不忘,而正是這種縈懷,方能使一部文學作品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