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與艾米莉·黑爾千余封信件公開:一段獨特而激烈的感情
1月2日,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公開了著名詩人T.S.艾略特與其知己艾米莉·黑爾(Emily Hale)之間的千余封信件。
這些信件揭示了艾略特和黑爾之間的親密關系和深厚情感,也為研究艾略特詩歌創(chuàng)作和生活提供了新的一手材料。艾略特和黑爾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書信往來,一直到1957年艾略特二婚為止。
艾略特的信件副本應他的要求被一位同事銷毀了。而黑爾把她的信件捐贈給了普林斯頓大學,在他們?nèi)ナ?0年后進行解密——艾略特于1965年去世,黑爾于1969年去世。這1100封信于去年10月首次從木箱中取出,并于1月2日向公眾公開。

此次公開的艾略特與黑爾的通信
這些熱情洋溢的信件揭示了兩人之間的深刻情感
黑爾一直被認為是艾略特一些最杰出的詩句的靈感來源,包括《四個四重奏》的《燃燒的諾頓》的第一段:
現(xiàn)在的時間和過去的時間
也許都存在于未來的時間,
而未來的時間又包容于過去的時間。
假若全部時間永遠存在
全部時間就再也都無法挽回。
過去可能存在的是一種抽象
只是在一個猜測的世界中,
保持著一種恒久的可能性。
過去可能存在和已經(jīng)存在的
都指向一個始終存在的終點。
足音在記憶中回響
沿著那條我們從未走過的甬道
飄向那重我們從未打開的門
進入玫瑰園。我的話就和這樣
在你的心中回響。
北卡羅來納大學的艾略特研究學者、倫敦T.S.艾略特國際暑期學校的主任托尼·庫達(Tony Cuda)告訴《衛(wèi)報》,這些信件的公布講述了艾略特生活中隱秘的愛情故事。“這是他職業(yè)生涯中丟失的一部分,當然也是我們對20世紀的一位重要詩人的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他說。
“他們的通信充滿熱情,”艾略特研究學者弗朗西斯·迪基(Frances Dickey)說,他是第一批看到這些信件的人之一。“這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多。艾略特聲稱是黑爾啟發(fā)了他的很多詩歌,她顯然在他的詩歌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迪基說,鑒于這些信件所揭示的內(nèi)容,在艾略特最著名的詩歌《荒原》中,“風信子女孩”黑爾的形象也變得更加明顯。
“如果你知道我現(xiàn)在沒有寫下的是哪一頁和哪一頁的溫柔,我想你會相信我的。雖然我有很多熟人,但我沒有真正親密的朋友,”艾略特寫道,他懇求黑爾接受他的熱情,“這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我祈禱我沒有冒犯你。因為在這混亂之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羞愧的。我的愛如此純潔……就像任何愛情一樣。”
他總結道:“如果這是一封情書,那將是我一生中寫下的最后一封情書。而我會簽上我的名字。”
黑爾對這封信的回復并沒有保存下來,但她接受了艾略特的懇求。于是艾略特開始了與她充滿熱情的通信。當時黑爾在波士頓,而艾略特住在英國。
那一年的11月,艾略特在寫信中表示,他已經(jīng)痛苦了一個月。
“你讓我感到非常幸福,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余生中我唯一可能得到的幸福現(xiàn)在正伴隨著我,雖然這種幸福同時也意味著我最深的失落和悲傷,但它是一種超自然的狂喜。”
他繼續(xù)寫道:“我試圖假裝我對你的愛死了,雖然我只能假裝我的心死了。無論如何,我接受了獨身生活。”
他形容自己處于“一種狂熱的情緒中”。到12月時,他承認,“我的痛苦愈加劇烈了,但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不感受到這種痛苦。”
對黑爾來說,情況要復雜得多。1969年,在她生命的盡頭,她提供了一份3頁紙的報告,描述了她和艾略特的關系。
根據(jù)黑爾的陳述,1922年,當艾略特向她表明自己的心跡時,她非常驚訝。“他告訴我他是多么關心我,而當時我對他并沒有這樣的感覺”。
黑爾承認,她了解到艾略特的婚姻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但她拒絕了“這個有天賦的、情緒化的、熱愛探索的人”的懇求。她寫道:“當他再次見到我后承認,他對我的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時,我感到沮喪。”
他們的友誼一直持續(xù)到1935年。“我們見過面,了解彼此的生活——盡管除了艱難而忠誠的友誼之外,我對他沒有其他感覺。”
然而,艾略特對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的責任限制了他與黑爾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直到他的妻子被送進精神病院。
1935-1939年,艾略特和黑爾一起在英格蘭格洛斯特郡的坎普登度過夏天。對那段時光,她寫道:“在如此反常的情況下,我和他變得非常親密,因為我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我也變得非常喜歡他。”
“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愛好,我們的反應,以及對彼此需求的情感回應——那種快樂,以及我們和我們生活之間平靜而深刻的聯(lián)系,非常豐富……更重要的是,我們保持了一種體面的、被人尊重的關系。”
黑爾寫道:“他的朋友和家人,以及我的朋友圈子里,只有少數(shù)人知道我們是相互關心的;而婚姻,如果他的妻子去世了,也會變成一種渴望得到滿足的權利。”

T.S.艾略特與艾米莉·黑爾
艾略特試圖淡化和否認他對黑爾的感情
然而,他們的關系注定要破裂。艾略特的第一任妻子薇薇安·黑格-伍德·艾略特于1947年去世,但艾略特并沒有一心執(zhí)著于黑爾,而是娶了另一個人——他的第二任妻子瓦萊麗。
黑爾對此表示,艾略特決定不與她結婚的決定在情感上對她來說非常難以理解,“這令我震驚和悲傷”。
“也許我不可能成為他所期望的婚姻伴侶,也許這一預期將我倆從極大的不幸中拯救了出來——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
黑爾總結道:“我和他討論了他態(tài)度的轉變問題,但并沒有從交談中得到任何收獲。”
在艾略特寫給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封聲明(日期為1960年)中,他簡要解釋了自己決定不向黑爾求婚的原因。“艾米莉·黑爾會扼殺我身上的詩人氣質;薇薇安幾乎要了我的命,但她讓那個詩人活了下來。”
艾略特說,他后來意識到,他的婚姻帶來了“《荒原》的精神狀態(tài)”,“它使我沒能和艾米莉·黑爾結婚”。“回想起來,我和薇薇安在一起的17年的噩夢般的痛苦,似乎比一個平庸的哲學老師的沉悶的痛苦更可取。而后者可能是另一種選擇。”
他接著說:“我希望我給黑爾小姐的信一公開,我的這封聲明就公之于眾……1912年我愛上了艾米莉·黑爾,當時我還在哈佛研究生院。1914年我在啟程去德國和英國之前,告訴她我愛上了她。”
艾略特在聲明中說,盡管他給黑爾的信寫得很親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意識到“艾米莉·黑爾和我之間的共同點是多么的少”。此外,他寫道:“我從未與艾米莉·黑爾發(fā)生過性關系。”
“我已經(jīng)注意到她不喜歡詩歌,自然她對我的詩歌也不怎么感興趣。這讓我已經(jīng)開始擔心我的不敏感和糟糕的品味了。”他寫道,“她喜歡的是我的名聲,而不是我的作品,這未免太苛刻了。”
艾略特學者安東尼·庫達告訴美聯(lián)社,這是一個“冷酷和不真實的聲明”。
“是他追的她,”他說,“他最早的書信是熱烈的愛情宣言。又不是她追的他。”
1947年第一任妻子去世后,艾略特說他開始意識到自己不再愛黑爾了。“在我看來,我對艾米莉的愛是一種鬼魂對鬼魂的愛,當我給她寫信時,這些信的書寫者其實并不存在,我只是在徒勞地假裝自己仍是1914年的自己。”艾略特說道。
普林斯頓大學英語系名譽教授邁克爾·伍德(Michael Wood)在10月份信件被拆封時在場。他告訴《紐約時報》,艾略特“如此憤怒”是一個“大驚喜”。
“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伍德說。“他試圖重新講述一個故事,他認為這個故事可以糾正信件本身的錯誤。他似乎改寫了與艾米莉的整個關系。”
迪基說,艾略特不得不否認自己對黑爾的感情,這是“不幸的”。“這似乎有點冷酷,”迪基說,“她是他多年的繆斯女神。”
庫達說,艾略特之所以寫下這樣冷酷的聲明,是因為他擔心這些信件會在約定日期之前就被發(fā)表。艾略特已經(jīng)要求銷毀了他從黑爾那里收到的信件。
“當他回首往事時,他為自己當時所表現(xiàn)出的開放和脆弱感到尷尬和羞愧,”庫達說,“他試圖控制損失。”
庫達說,艾略特還想保護他的第二任妻子瓦萊麗,他說她“改變了”他的世界。
“但這是一種奇怪的保護欲,”庫達說,“他非常愛瓦萊麗,瓦萊麗也非常愛他。艾米莉·黑爾的信件所揭示的僅僅是——(瓦萊麗)并不是他生命中唯一的愛。在她之前,他有過一段獨特而激烈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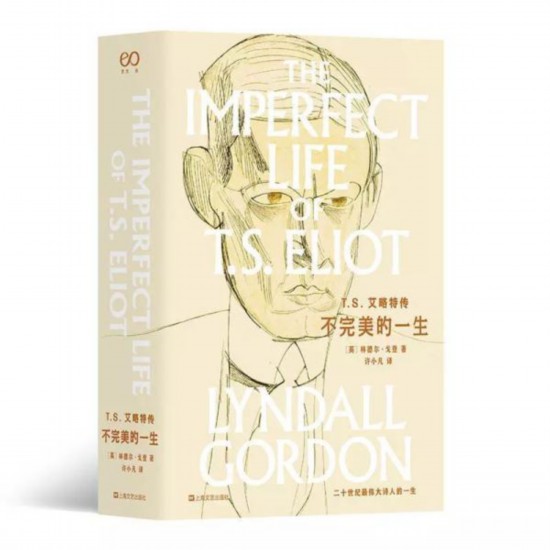
《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
這些信件還透露了艾略特生活的其他私人細節(jié),包括他對酒精的渴望。
這些信件可能會更多地揭示艾略特的私人生活和詩歌生活,并已在文學界掀起波瀾。庫達稱它們“正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全部”。
“作為他人生活的消費者,我們想做的僅僅是理解他們,”他說,“和往常一樣,艾略特不會被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