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逆襲原生家庭的成功絕非偶然,也不盡是努力前提下的必然

從斑駁的原生家庭出走,成功實現(xiàn)教育逆襲的故事,仿佛一碗熬好的雞湯。莉絲·默里出生在紐約的貧民窟,當(dāng)她在母親肚子里時,她的父親還在監(jiān)獄里,母親因為懷孕被提前釋放,而她的姐姐被暫時送往寄養(yǎng)家庭生活。孩童時期,父親出獄與家人團(tuán)聚,全家四人靠每月的救濟(jì)金生活,她看到父母總在卷聞起來不像香煙的香煙抽,內(nèi)心不愿離開寄養(yǎng)家庭的姐姐,則對日復(fù)一日的雞蛋餐發(fā)怒,也遷怒與她不和自己一起,向父母爭取更好的生活。這條父母鋪陳好的墮落之路,她從童年走到了青春。母親的去世直接導(dǎo)致了家庭的崩潰,卻也終于有機會,讓莉絲將維持家庭的權(quán)力轉(zhuǎn)移到她自己身上,她成功地用2年完成了4年課程,走向她早知存在于自己生活以外的、光明的世界。這段破曉的人生被她記錄下來,她稱之為“從無家可歸到哈佛的旅程”。(《風(fēng)雨哈佛路》)

莉絲式的成功絕非偶然,也不盡是努力前提下的必然。如同一張顯像的膠片,也受動力、決定、時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些家庭視教育為優(yōu)待而非權(quán)利,但這還不算最大的阻力,求學(xué)后不能雙棲在家庭舊秩序和個人新世界之中,這是他們更大的困境。與其神化逆襲,如何在此困境下適應(yīng)和進(jìn)化,才更體現(xiàn)受教育的價值和意義。
經(jīng)歷過偷東西、撿垃圾的絕境,在地鐵站學(xué)習(xí)或是在連夜運行的地鐵里過夜,對莉絲來說都不是問題,反而是一張借宿的沙發(fā)一條柔軟的毛毯,消磨著她出門去上學(xué)的意志。如她遇過的一個男孩所說,從貧民窟出來混很不容易,但你必須保持清醒,做夢可以,但不能睡著。命運是場綿長的抗?fàn)帲皇寝D(zhuǎn)折后半小時就結(jié)束的超級英雄電影,此處和別處的生活像水流入水,無法劃清界線。逃出原生環(huán)境的人,依然很難擺脫重心般的家庭影響力。
埃萊娜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逃離充斥著暴力的那不勒斯,拋下無可戀的童年,尤其是避免自己與母親的一切相似性。但當(dāng)她被比薩高等師范錄取,掌握了精致優(yōu)雅的意大利語,嫁入了書香門第,甚至有了一位能為她的事業(yè)助力的婆婆,她仍會在情急之下操那不勒斯方言破口大罵,更惶恐地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時的步態(tài)像極了瘸腿的母親。而如果有人假想過,自己留下來會過什么樣的生活——她的天才女友莉拉就是她的平行世界。莉拉啟蒙了她對外部世界的好奇渴望,激發(fā)了她的好勝心,自己卻選擇守著(或者說掌控)這座小城。對埃萊娜來說,這又成了一種煽動,她感到自己缺席了這一時期的家鄉(xiāng)。(《我的天才女友》)
混亂中成長起來的人,因為優(yōu)異的成績?nèi)チ舜蟪鞘校藗兞?xí)慣在他們身上施加光輝和想象,但真實的人生不是媒體投下的一片閃光燈。他們的原生家庭是人們眼中的異類,求學(xué)深造并非這些家庭的理想,更像玩笑般的念頭,沒有人想真的實踐它,除非自己被逼到了絕境,借此出逃。而從教育中得到的秩序感令他們與混亂格格不入,他們反而成為了家庭中的異類。如果說求學(xué)是對原生家庭的拒絕,那它必然也要遭到原生家庭的拒絕。埃萊娜的母親為自己女兒取得的成就自豪,但同時她也會粗魯?shù)貙ε畠赫f,別自以為太了不起,如果這么聰明的人是從我肚子里出來的,那么我至少一樣聰明,甚至更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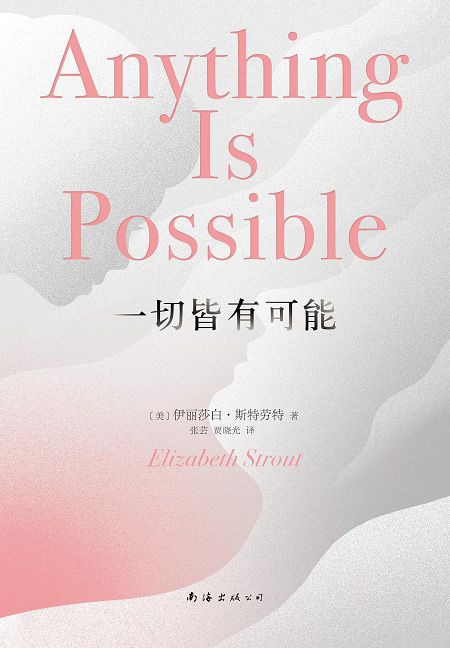
露西小時候住在丁點大的村鎮(zhèn)的一間車庫里,會在操場上被同學(xué)指著說“你們一家都臭烘烘的”;她的姐姐二年級的時候,被老師當(dāng)著全班的面說“窮不是耳后有污垢的理由,沒有人窮得連一塊肥皂都買不起”;她和姐姐沒有朋友,只能用打量世界的懷疑眼光打量彼此;高中時她因為夢到自己身在大學(xué)而不敢再入睡,原因是害怕再次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還在這間屋子里、并永遠(yuǎn)在這間屋子里。得償所愿,她念了大學(xué)、談了戀愛、結(jié)了婚,如今是一位生活在紐約的作家,17年她沒有再見過任何家人。小鎮(zhèn)上的人對她有形形色色的說法,有人覺得她高傲冷漠,一走了之,也有人記得她小學(xué)時候為了取暖,一直留在圖書館,必不得已才回家。而她的婆婆在她的婚禮上,向自己的朋友介紹她時,補了一句:從一無所有中來的露西。(《一切皆有可能》)
搭新書宣傳的順風(fēng)車,露西終于要回去和哥哥皮特見一面,姐姐維姬也不約而至,問她怎么從廣闊的世界回到了這里。直到露西的恐慌癥事隔多年再次發(fā)作,無法停止大哭,消解了維姬對她的嘲諷。“她不停地說,我來也是錯的,走也是錯的,都是我的錯。”維姬對皮特說,“她只是受不了回到這里。這對她太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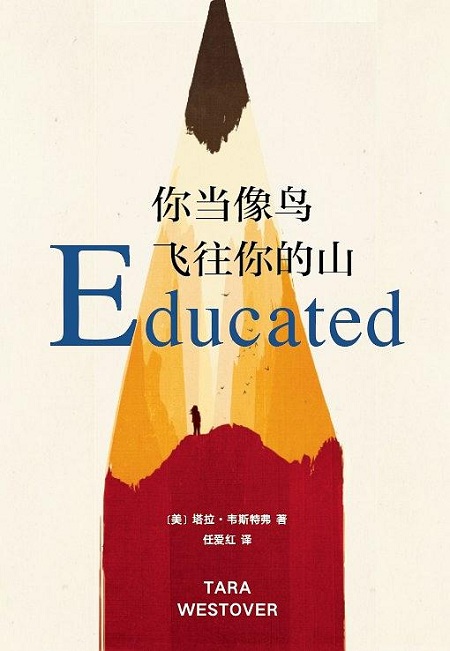
我是“一個叛徒,羊群中的一匹狼”。塔拉是這樣定義逆襲后的自己與家人之間的關(guān)系的。她與六個兄弟姐妹、一家九口人生活在山間,因為父親的信仰,所有孩子都不去上學(xué),所有人都不去醫(yī)院。不去醫(yī)院的意思是,從助產(chǎn)護(hù)理到燒傷墜落,都由母親用草藥和精油療愈。不去上學(xué)倒不能和絕對的愚昧劃等號,父親會為全家朗讀《圣經(jīng)》,幾個孩子在幫工之余也可以去鎮(zhèn)上買課本和書來看。但不去上學(xué)必然導(dǎo)致了她的落后,對她來說,拿破侖和冉阿讓一樣,都是從未聽說過的人。當(dāng)她走出這座山,她無從辨別虛構(gòu)的故事和真實的事件。(《你當(dāng)像鳥飛往你的山》)
恰恰是知識,為她提供了理解現(xiàn)實的工具,她為此感到驚奇和著迷:零散、反覆、不穩(wěn)定的物質(zhì)世界,可以被捕捉、理解和預(yù)測。知識讓她相信外面有一個“規(guī)則而理性的世界”,與從理論到實踐的認(rèn)識順序逆行。在嶄新的世界面前,理解成了要務(wù)。一開始,這并不容易。盡管通過了入學(xué)考試,盡管進(jìn)入了高等學(xué)府,塔拉自知“我不是唯一感到迷茫的人,但我比任何人都迷茫”。她犯低等的錯誤,比如不理解備考的方法和考試的法則,不理解“大屠殺”這個單詞是什么意思,但她高強度地瘋狂學(xué)習(xí),竭力留在學(xué)校,為了把自己和家分開,成為一個比自己更好的人。她找到了精英社會的節(jié)奏和自我融入的切口,拿到了學(xué)位,又被導(dǎo)師推薦至更好的教授,攻讀更高的學(xué)位。但這些常人眼中的果實,于她只是受教育過程中的表征。她“懸浮在對過去和未來的雙重恐懼中”,真正的難題是自我救贖,真正的教育是自我發(fā)現(xiàn)和自我創(chuàng)造。
對塔拉而言,接受教育和回歸家庭是個進(jìn)退兩難的選擇,只不過求學(xué)反而成了一條退路。家人都有存在自己生活中的價值和理由,只是當(dāng)他們聚在一起,生活就成了泥潭。父親被(他們不愿承認(rèn)的)被迫害妄想操控,成為一個執(zhí)意建造方舟的諾亞,在上帝并沒有讓洪水泛濫的時代,顯得荒謬。母親堅持塔拉是家里“沖出熊熊大火走出去的人”,斬斷她顧及父親反對而對上學(xué)的遲疑,催她趕快離開;又拒絕獨自出席她的畢業(yè)典禮,不敢相信她會期待一個人女人在丈夫不到場的情況下出現(xiàn)。更不用說幾次對她實施身體暴力和精神羞辱的哥哥,她向父母揭穿他的暴力行為后(依然得到了包括其他受害者在內(nèi)的眾人的包庇)間接和直接受到了他的死亡通牒,最后被他從生活中完全隔離出去,在絕交的謾罵電子郵件最后,他卻傷感地寫道,愛家人勝過一切,愛你勝過家人,你卻在我背后捅刀。他們出自天性地愛她,也同樣出自天性地傷害她。家庭中愛的型態(tài)令人生疑,家人的情感充滿不確定性,每一次溫情的發(fā)生都像奇跡。奇跡會出現(xiàn),但人無法僅僅依靠奇跡活下去。她愿意離開家,接受學(xué)校的催眠。
通過接受教育,塔拉窺見了人類的歷史并思索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對顯而易見的事實漸漸覺醒,對自我形成了基本認(rèn)知。當(dāng)她假期回家,父親或哥哥一如既往地向她開著玩笑,他們的語氣沒變,動機沒變,但她的耳朵變了,它聽到的不再是其中的玩笑,而是一個信號。沿著求學(xué)這條路,她退出了父權(quán)的邊界。理解。理解身在其中的沖突,理解對自己的譴責(zé),理解通往辯解和發(fā)聲,不再沉默或白白陣亡。過去塔拉身上除了無知,還有無知帶來的羞恥感。旁人對此困惑、心怯,但“困在過去的自我”,只能親手將她“送往別處”。受教育改變了她看待世界的方式,她不再活在別人的講述中,洗刷莫須有的羞恥感,承擔(dān)剝離原生家庭的痛苦。推翻舊信仰才能搭建她的新生活,才不負(fù)她為此付出的全部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