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jì)匈牙利文學(xué)在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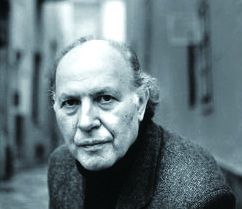
凱爾泰斯
匈牙利文學(xué)譯介歷史回顧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匈牙利即與我國建立外交關(guān)系。建交后,兩國友好關(guān)系全面發(fā)展,領(lǐng)導(dǎo)人互訪等各種形式的往來密切,各領(lǐng)域合作不斷加強(qiáng),兩國人民的友誼進(jìn)一步加深,雙方在國際事務(wù)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受到當(dāng)時的文化策略導(dǎo)向,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們主要譯介能夠體現(xiàn)民族斗爭意識的無產(chǎn)階級作家的作品。這其中,最多的要數(shù)匈牙利民族主義代表詩人裴多菲。
早在1907年,魯迅就將裴多菲同拜倫、雪萊、普希金等大作家相提并論,并稱他為“立意在反抗,旨?xì)w在動作”、“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fā)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從上世紀(jì)二三十年起直到21世紀(jì)初,中國對裴多菲的研究從未停止。50年代開始,國內(nèi)譯介了一大批匈牙利無產(chǎn)階級作家的作品,包括費(fèi)雷斯·彼得的《考驗》(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3年)、納吉·山多爾的《和解》(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3年)、約卡伊·莫爾的《金人》《鐵石心腸人的兒女》(作家出版社,1953年)、《黃薔薇》(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0年)。此外,我國譯介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和無產(chǎn)階級作家查爾卡·馬特的《查爾卡小說選》收錄了三類作品:描寫帝國主義戰(zhàn)爭、描寫蘇聯(lián)國內(nèi)戰(zhàn)爭以及揭露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本質(zhì)的作品。另一位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伊雷什·貝拉的兩部作品《祖國的光復(fù)》和《蒂薩河在燃燒》則分別由俄文和德文轉(zhuǎn)譯。現(xiàn)如今,當(dāng)我們回望歷史時不難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特定的國際形勢和意識形態(tài)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譯介匈牙利文學(xué)時的選擇,同樣,當(dāng)時中國了解到的匈牙利文學(xué)也不全面。這一時期的匈牙利文學(xué)譯介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大多通過其他語言轉(zhuǎn)譯;二是選擇作品傾向性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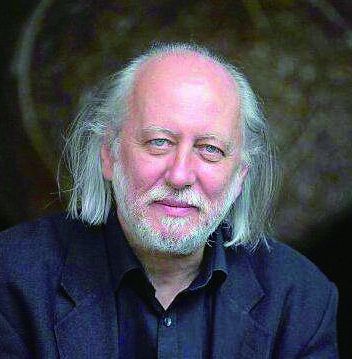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1976年之后,經(jīng)過了10多年的沉寂,對西歐與北美文學(xué)的譯介日漸成為外國文學(xué)譯介的主流,中東歐文學(xué)的譯介傳統(tǒng)也很快得以恢復(fù)。這其中,有一批作品是經(jīng)典重譯,比如興萬生譯的《裴多菲文集》。另外,選譯文學(xué)作品集的趨勢日漸明顯,收錄有匈牙利文學(xué)作品的集子有《東歐短篇小說選》(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9年)、《東歐短篇小說選》(馮植生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匈牙利民間故事選》(孫小芬編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匈牙利現(xiàn)代小說選》(德里·蒂博爾著,外國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神秘的王后:匈牙利民間故事》(徐汝舟編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東歐劇變后,我國對東歐文學(xué)的譯介面臨許多的挑戰(zhàn),東歐文學(xué)的譯介和研究曾一度走向沒落,最顯明的例子便是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外國文學(xué)研究所東歐文學(xué)室解散,這個曾經(jīng)人丁興旺、業(yè)績輝煌的團(tuán)隊建制不復(fù)存在;再加上出版行業(yè)的過度市場化,無法盈利的東歐文學(xué)作品最終沒有逃過被邊緣化的命運(yùn)。然而,即便如此,東歐文學(xué)的翻譯和研究仍在進(jìn)行,只是動作放緩了些,經(jīng)過時間的積累和打磨,最終呈現(xiàn)出系列成規(guī)模體系的翻譯和研究成果。收錄有匈牙利文學(xué)的成果有:《世界反法西斯文學(xué)書系》中的“捷克—匈牙利”卷、《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東歐卷》《世界經(jīng)典戲劇全集·東歐卷》《世界經(jīng)典散文新編·東歐卷》《東歐國家經(jīng)典散文》以及《祖國母親愛情:匈牙利著名詩人詩選》等。
新世紀(jì)以來匈牙利文學(xué)在中國的譯介
進(jìn)入21世紀(jì)后,隨著凱爾泰斯·伊姆雷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匈牙利文學(xué)在中國逐漸受到重視。如果說中國讀者通過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認(rèn)識了匈牙利文學(xué),那么,閱讀凱爾泰斯·伊姆雷才讓中國讀者真正地靠近匈牙利文學(xué)。凱爾泰斯的諾獎授獎辭稱,他的作品“以個體的脆弱體驗反抗歷史的野蠻強(qiáng)權(quán)”。裴多菲和凱爾泰斯,一位是捐軀沙場的民族烈士,另一位則是看透了“屈從即生存”的弱勢公民,遙遙相隔一個世紀(jì),雖然他們的生活年代、個體經(jīng)歷、創(chuàng)作內(nèi)容都不一樣,但兩人的創(chuàng)作主旨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反抗強(qiáng)權(quán),這也是匈牙利文學(xué)史的精神寫照。

艾斯特哈茲·彼得
2002年,當(dāng)瑞典學(xué)院宣布凱爾泰斯獲得當(dāng)年的諾貝爾文學(xué)獎時,全中國幾乎沒有人知道誰是凱爾泰斯,這個在此之前從未走入過中國人視野的作家,激起了所有文學(xué)愛好者和研究者的好奇。不過,人們迅速行動起來,2002年底時,對凱爾泰斯的介紹便逐漸展開。《世界文學(xué)》2002年第6期率先公布了凱爾泰斯獲獎的簡訊,隨后,高興在《外國文學(xué)動態(tài)》2002年第6期撰文介紹了作家的生平以及他的幾部重要著作。凱爾泰斯獲獎,讓中國讀者的目光重新聚集到匈牙利文學(xué)。匈牙利著名文學(xué)評論家瑟雷尼曾說:“以前我們的文學(xué)旗幟上寫著裴多菲的名字,現(xiàn)在什么人也沒有了。”這話雖有夸張的成分,但不得不承認(rèn),二十世紀(jì)下半葉以來,匈牙利確實沒有再出現(xiàn)像捷克的昆德拉、波蘭的米沃什那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作家。不過,凱爾泰斯獲獎后,匈牙利文學(xué)譯介在中國被邊緣化的狀態(tài)開始逐漸得到改變。這首先體現(xiàn)在對凱爾泰斯作品的翻譯和研究上。作為一份譯介外國文學(xué)的前沿雜志,《世界文學(xué)》在2003年第2期推出了由旅匈學(xué)者李震翻譯的《偵探小說》《慘敗》《無形的命運(yùn)》《苦役日記》《另外的我》五部作品的選譯以及作家的獲獎演說辭,這是凱爾泰斯的作品第一次與我國讀者見面。
2003年開始,一批從奧斯維辛之于作家的生活、創(chuàng)作等角度出發(fā)探討凱爾泰斯作品的文章相繼發(fā)表;凱爾泰斯的早期創(chuàng)作不被世人認(rèn)可、其作品推出后不受重視的遭遇也被研究者挖掘、剖析。而凱爾泰斯代表作Sorstalanság的題目翻譯也曾一度成為學(xué)界的探討熱點。該作最早被譯成《沒有命運(yùn)》,應(yīng)該來自英文標(biāo)題Fatelessness。2003年的一眾評論文章中,又將該譯名改成《無形的命運(yùn)》。《一步一步——凱爾泰斯·伊姆雷和他的〈一個在命運(yùn)之外的人的傳奇〉》一文的作者楊宏芹為德語研究專家,她根據(jù)該著的德文題目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將中文題目譯成《一個在命運(yùn)之外的人的傳奇》。2004年,此書以《命運(yùn)無常》為題出版單行本,這應(yīng)該是目前為止最廣為人知的譯名。不過,匈牙利文學(xué)專家許衍藝在她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凱爾泰斯曾在《苦役日記》中對“命運(yùn)”做過這樣一番詮釋:“我將什么稱作命運(yùn)呢?當(dāng)然是悲劇的可能性。然而外部的決定,那恥辱的烙印將我們的生命擠壓進(jìn)了特定的集權(quán)主義的一個處境中,一種無能為力之中,使這種可能成為虛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強(qiáng)加給我們的決定當(dāng)成一種事實自始至終地生活在其中,而不是生活在我們自己的(相對的)自由所帶來的必然性中,我便稱之為無命運(yùn)”。因此,許教授認(rèn)為,該著應(yīng)該被譯為《無命運(yùn)的人生》。2010年,許衍藝翻譯的《無命運(yùn)的人生》問世,這也是凱爾泰斯這部代表作的第二個權(quán)威譯本。2004年,凱爾泰斯的《命運(yùn)無常》《英國旗》《另一個人》《船夫日記》四部作品陸續(xù)翻譯成了中文。2014年,《清算》和《偵探故事》又被譯介進(jìn)來。
2006年以后,隨著凱爾泰斯第一批作品的中文版推出,對作家的研究也轉(zhuǎn)向了縱深。《西西弗斯的神話中的石頭——評凱爾泰斯·伊姆雷的小說〈慘敗〉》(侯景娟,2007年)對小說《慘敗》中貫穿始終的母題——西西弗斯的神話的發(fā)展演變進(jìn)行討論,并具體分析了小說《慘敗》對這一神話的獨(dú)特運(yùn)用。凱爾泰斯身上背負(fù)的奧斯維辛烙印,總是能引起研究者對其作品中“大屠殺”主題的興趣。《凱爾泰斯生存哲學(xué)探析》一文(闞興韻,2007年)一文揭示了凱爾泰斯認(rèn)為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所有人都只是功能性的人,并對凱爾泰斯的這一思想進(jìn)行溯源,進(jìn)而分析了作家對于現(xiàn)代性和集權(quán)主義之間關(guān)系的探索。《凱爾泰斯創(chuàng)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初探》(商金艷,2010年)一文關(guān)注的是在奧斯維辛的集權(quán)統(tǒng)治下,作家的人道主義思想形成過程,及其在作品中的呈現(xiàn)。基于“無命運(yùn)”這一結(jié)構(gòu)性詮釋《論凱爾泰斯小說的自傳性書寫》(孫燕君,2013年)一文考察了凱爾泰斯小說“集中營”主題與其創(chuàng)傷記憶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同時通過對個體“無命運(yùn)”性的探析,呈現(xiàn)出對集權(quán)制度的反思。《無命運(yùn)的存在性建構(gòu)——試論〈無命運(yùn)的人生〉的主體性反思》(李安斌、張凡,2017年)一文從對《無命運(yùn)的人生》的隱喻性解讀、主體性解讀兩個方面,對作品中人的“無命運(yùn)性”進(jìn)行反思,并認(rèn)為,人的主體性反思可以超越“無命運(yùn)”,具有荒誕感的現(xiàn)代人不必選擇非生即死的窮途末路,而是能夠通過真正意義上的反思達(dá)到對自我的肯定,安撫時代帶給一代人慘痛的回憶。
凱爾泰斯獲獎后,作為東歐文學(xué)重鎮(zhèn),有好幾位匈牙利作家都進(jìn)入中國讀者的視線。艾斯特哈茲·彼得是當(dāng)代匈牙利文學(xué)中一個繞不開的作家,他的兩部作品《一個女人》和《赫拉巴爾之書》在2009年和2010年被引進(jìn)中國。這位作家出生在19世紀(jì)歐洲最顯貴的家族中,有人說,一個歐洲人,即使沒讀過彼得的作品,也不會不知道艾斯特哈茲伯爵家族。這個家族曾經(jīng)走出過匈牙利的大臣、將軍、主教和大主教。艾斯特哈茲的祖母曾是一位法國公主,他的祖父莫里茨伯爵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末期擔(dān)任過匈牙利總理。但1950年作家出生時,這個家族早已衰敗,艾斯特哈茲成了一位被剝奪爵位的農(nóng)民的兒子。一個整天踢足球的數(shù)學(xué)系青年,成為寫作領(lǐng)域的領(lǐng)頭標(biāo)兵,這樣的事情在任何人看來都頗為離奇,卻被艾斯特哈茲視為理所當(dāng)然:“我覺得寫作、足球還有數(shù)學(xué)之間是有一定聯(lián)系的,都是一個場地,這個場上有特定的規(guī)則。”艾斯特哈茲在寫作時善于創(chuàng)造新式詞匯,經(jīng)常串用拉丁語、德語、法語、英語和各種諺語、俚語,還曾經(jīng)創(chuàng)作過一部名為《懸》的實驗性作品,該作兩百頁的篇幅,從頭到尾只有一句話,并以半個前括號結(jié)尾,以示作品的開放性,正因如此,艾斯特哈茲被稱為“匈牙利的喬伊斯”,他在世時曾多次獲得過諾貝爾獎提名,是匈牙利文壇的領(lǐng)軍人物。我們從《一個女人》和《赫拉巴爾之書》這兩部作品中,看到了作為數(shù)學(xué)家的艾斯特哈茲在各種對立的矛盾中追求著細(xì)膩的平衡,比如男人和女人、荒謬與嚴(yán)肅以及冷峻的寫作技巧與形而上學(xué)的敏感。這是多年來,他作為一個受過專業(yè)數(shù)學(xué)訓(xùn)練的創(chuàng)作者為自己建構(gòu)的文學(xué)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艾斯特哈茲在不停破壞、重建。而對艾斯特哈茲的作品進(jìn)行中文翻譯,也是對譯者文字功底、學(xué)養(yǎng)和耐性的一種挑戰(zhàn),需要他們用中文建構(gòu)一種全新的、與原文相對應(yīng)的文學(xué)語言。
蘇契·蓋佐在中國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太陽上》是一個選集,前半部分是詩歌,后半部分選自他的兩部故事集《假如章魚在克羅日瓦爾喘息》和長篇政治寓言小說《林普普》。2017年,蘇契以詩人的身份出席首屆“成都國際詩歌周”,他在詩歌周的開幕式上朗讀了詩歌《太陽上》。蘇契本人擁有多重身份,他出生在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qū),在歷史上曾歸屬于匈牙利,一戰(zhàn)后被劃到羅馬尼亞,因此這個地區(qū)也成為20世紀(jì)匈牙利人尋找身份與激情的土壤。上世紀(jì)70年代后,面對齊奧塞斯庫的獨(dú)裁統(tǒng)治,蘇契是當(dāng)時少有的敢于站出來的反抗分子,這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yù),也為他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礎(chǔ)。現(xiàn)在,他也是惟一一位能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兩個國家的高層政治舞臺上扮演角色的政治家,也是他,在匈牙利政治思想領(lǐng)域率先提出了“打開東大門”,成為高度重視與亞洲關(guān)系的倡導(dǎo)者之一。他頻繁出訪中國,不僅在政治貿(mào)易領(lǐng)域,也在文化、知識領(lǐng)域為兩國的關(guān)系體系打下了新的根基,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蘇契的作品中,會不時出現(xiàn)與中國相關(guān)的元素,比如《假如章魚在克羅日瓦爾喘息》中的一篇《屠龍的圣喬治克羅日瓦爾兄弟》提到了克盧日龍和中國龍的不同:“在我們這里跟在中國不同,中國人的龍日是在春節(jié)之后。”作家說的應(yīng)該是我們的農(nóng)歷二月二吧。同樣的,在《林普普》中,一篇《關(guān)于靈魂、中國皇帝和長城》讓人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說殘篇《中國長城修建時》。卡夫卡文中對中國長城修建的想象與奧匈帝國的政治現(xiàn)實之間存有一定程度的隱秘關(guān)聯(lián),這正是卡夫卡自身對國家認(rèn)同方式的表現(xiàn)。同樣的,在這個短篇中,蘇契用中國長城的意象,表達(dá)了他努力追求理想,但卻無法達(dá)到理想的現(xiàn)實。他說,不論是政治家還是文學(xué)家,都是在為同樣的問題尋找答案,有朝一日,這些問題會受到關(guān)注。蘇契在第二部中文版詩集《憂傷坐在樹墩上》收錄的一首詩歌《一位宇航員的日記摘抄》中向李白等唐朝詩人致敬:“在一家名為‘死亡詩社’的北京酒吧……李白正在談?wù)撍劳?我插言說:——詩人們,你們對月球都知道些什么?”
談到李白,就必須提起另一位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他也是李白的崇拜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曾來過中國三次。1998年,作家被歐洲的一家新聞組織選為世界范圍內(nèi)十二位有影響力的作家,來到中國。按照要求,他選擇了自己最崇拜的李白,沿著李白的足跡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陽、西安、成都、重慶等近十座古城,所到之處,他利用一切機(jī)會與中國的作家、學(xué)者談?wù)摾畎祝踔猎诼飞吓c普通行人談?wù)撨@位“詩仙”。旅程結(jié)束后克拉斯諾霍爾卡伊說,他所記錄的并不是詩人生前的地理行蹤,而是作為詩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記。作家的散文體游記《只是星空》便展現(xiàn)了一個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詩人形象。中國讀者讀到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第一篇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說《茹茲的陷阱》,刊登在《小說界》2006年第2期;兩年后,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說《狂奔如斯》再次與中國讀者見面。直到作家2015年獲得了布克國際文學(xué)獎后,他的成名作《撒旦探戈》才被譯介到中國。
匈牙利作家群與“藍(lán)色東歐”
20世紀(jì)的匈牙利歷史決定了這個國家有許多作家走上了“流亡”的命運(yùn)。他們有的從匈牙利前往海外,有的從被分割出去的土地上回到匈牙利,而“分離”是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無法拭去的一抹生命底色。這些年,國內(nèi)的匈牙利文學(xué)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這一現(xiàn)象,翻譯了一批這類作家的作品,這里面有馬洛伊·山多爾的六部作品:《一個市民的自白》《燭燼》《偽裝成獨(dú)白的愛情》《反叛者》《分手在布達(dá)》《草葉集》。1948年,在國家的政治文化面臨巨大轉(zhuǎn)折的關(guān)口,馬洛伊去國離鄉(xiāng),開始了逃亡的漂泊生活。他在瑞士、意大利生活過,最后客死美國,其作品曾在匈牙利文壇消失達(dá)40年。馬洛伊去世多年后,作品才在匈牙利出版。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展現(xiàn)了他對一個理想“市民”的追求:平靜、鄭重,充滿尊嚴(yán)。這令人聯(lián)想到《布達(dá)佩斯大飯店》里的一句經(jīng)典臺詞:“那個世界早在他進(jìn)入之前就已經(jīng)消逝了,只不過他極為優(yōu)雅地維持了那個幻象。”難怪有中國讀者感嘆:馬洛伊的文字中最令人感動的不是一個人內(nèi)心暗潮和時代浪潮的暗合,而是一個作家對自己命運(yùn)的確認(rèn)。
另外還有一些流亡作家來自羅馬尼亞境內(nèi)的匈族區(qū),比如德拉古曼·久爾吉和巴爾提斯·阿提拉。這兩位作家的身世非常相似:80年代中后期,他們隨家人從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qū)逃到匈牙利,當(dāng)時羅馬尼亞社會的高壓生活,為作家的青少年時期涂上了一層晦暗的色彩。我們在德拉古曼的《摘郁金香的男孩》中看到了一個十歲孩子對苦難的記憶,也在巴爾提斯的《寧靜海》中看見了社會制度對人造成的戕害,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正一點點地喪失掉靈魂和人性,淪為只為制度而存在的僵尸。對于這些作家來說,流亡成了思考的土壤,苦難成了寫作的養(yǎng)分,懷疑成了觀察的方式。
自從匈牙利“向東開放”和中國建設(shè)“一帶一路”和“16+1”經(jīng)貿(mào)合作以來,中國與匈牙利之間不僅在政治、經(jīng)濟(jì)等領(lǐng)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在文化交流上也更為頻繁。與此同時,國內(nèi)的翻譯者也對早期的東歐文學(xué)譯介進(jìn)行了深刻反思。《世界文學(xué)》主編高興說:“在我國,東歐文學(xué)譯介一直處于某種‘非正常狀態(tài)’。很長一段歲月里,東歐文學(xué)被染上了太多的藝術(shù)之外的色彩……為了更加客觀、全面地翻譯和介紹東歐文學(xué),突出東歐文學(xué)的藝術(shù)性,有必要顛覆一下這個既定的概念。” 因此,花城出版社自2012年起,推出了“藍(lán)色東歐”系列,希望讓中國讀者從中讀到一個另一種色彩的東歐。在“藍(lán)色東歐”系列中被譯介的匈牙利作家作品有瓦莫什·米克洛什的《父輩書》、查特·蓋佐的短篇小說精選《遺忘的夢境》、馬利亞什·貝拉的《垃圾日》和《天堂超市》、薩博·瑪格達(dá)的《壁畫》和《鹿》。《父輩書》的作者瓦莫什·米克洛什被稱為匈牙利的國寶級作家,他的這部著作是一部宏偉的家族傳奇,時間背景縱跨三百多年,記錄了整個民族國家的社會變遷。馬利亞什·貝拉既是作家,也是一名畫家,他的藝術(shù)作品總會給人一種“瘋狂”的感覺,曾被人拿來與查特·蓋佐的小說作類比:“馬利亞什畫畫,就像查特·蓋佐寫日記:低調(diào)但刻意地表現(xiàn)粗暴,幾乎是用變態(tài)的方式。”我們?nèi)绻プx查特·蓋佐的《遺忘的夢境》中的《弒母》和馬利亞什的《垃圾日》,就會明白這句評語的真正含義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作品均是在中國第一次被譯介,且都譯自匈牙利原文。這些作品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要算薩博·瑪格達(dá)——從新文化運(yùn)動介紹匈牙利文學(xué)以來,這是惟一被譯介的匈牙利女作家。從20世紀(jì)60年代開始,薩博·瑪格達(dá)的作品已被譯成40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fā)行,在之后的半個世紀(jì)中,無論冷戰(zhàn)中還是冷戰(zhàn)后,“薩博·瑪格達(dá)”都是匈牙利文學(xué)的一張國際名片。
自2006年起,文學(xué)雜志《小說界》的“外國新小說家”欄目先后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凱爾泰斯·伊姆雷、塔爾·山多爾、帕依·安德拉什,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詩人沃洛什·伊斯特萬、德拉古曼·久爾吉、納吉·蓋爾蓋伊、蒂薩·卡塔、馬利亞什·貝拉、巴爾提斯·阿提拉、馬洛伊·山多爾、桑多·T. 卡波爾、帕爾蒂·納吉·勞約什等人的短篇小說或是長篇選譯,這個“外國新小說家”欄目,是由旅匈翻譯家余澤民主持的。在新世紀(jì)的匈牙利小說譯介方面,余澤民功不可沒,2017年的布達(dá)佩斯國際書展上,他被授予“匈牙利文化貢獻(xiàn)獎”。頒獎詞稱“他一個人相當(dāng)于一個機(jī)構(gòu),當(dāng)代匈牙利文學(xué)通過他得以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他在這個領(lǐng)域扮演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但與匈牙利思想巨擘輩出的情況相對的是,除了余澤民等數(shù)量極少的匈牙利文學(xué)專業(yè)譯者以外,我們很少能夠找到愿意將身心扎根在文學(xué)土壤中的譯者。同樣的,在對引進(jìn)作品的后續(xù)研究方面,目前看來是明顯不足的。我們不缺需要介紹和研究的作品,我們?nèi)鄙俚氖窃敢鈱⒆约悍瞰I(xiàn)給兩國文學(xué)交流的優(yōu)秀譯者和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