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的新活力 ——讀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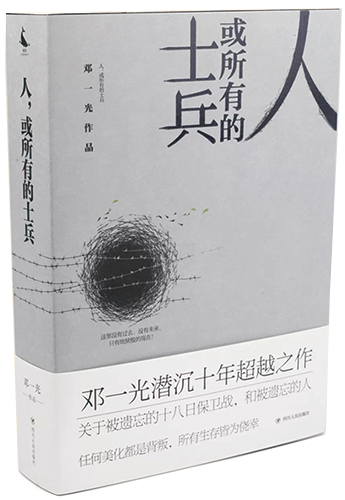
2019年,作家鄧一光提供了一部具備經(jīng)典化潛質(zhì)的長篇巨制《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文藝出版社7月出版發(fā)行)。這部作品以1941年香港保衛(wèi)戰(zhàn)為背景,通過對香港淪陷后日軍D戰(zhàn)俘營131號戰(zhàn)俘郁漱石被關(guān)押期間“通敵罪”的審判,以法庭自辯、法庭質(zhì)證、庭外調(diào)查、證人證詞、庭外供述、法庭陳述、結(jié)案報告等多人多角度敘事,沉靜地講述一個戰(zhàn)俘的悲歡恐懼和希望,勾勒出郁漱石不同尋常的一生,揭露了主人公內(nèi)心鮮為人知的隱秘世界。作品既有歷史的觀照與洞見,也有對現(xiàn)實的審美與燭照,展現(xiàn)出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的新活力。
首先,是情感力量的匯聚與釋放。鄧一光曾說:人最可貴的不是英雄品質(zhì),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軟弱和恐懼之心,這是上蒼給予人類阻止自我毀滅的最后法器,正是因為有了它,我們才有可能,或者說最終不會成為魔鬼。擁有捍衛(wèi)恐懼的權(quán)利,人類才能繼續(xù)前行。作者將戰(zhàn)爭的殘酷和戰(zhàn)后的苦澀交織在一起,以觸目驚心之惡激發(fā)的情感力量和善惡兩端不停轉(zhuǎn)換帶來的波瀾起伏,推動讀者不斷進(jìn)行角色置換,在一場簡單而紛繁的審判中直抵人心的柔弱,使作者情感、人物情感和讀者情感化合聚焦。作品沒有刻意營造敘事氛圍,而是依靠語言勢能激發(fā)敘事予以自然推動,在語言勢能中攜裹著巨大的情感力量。郁漱石在開篇陳述:“我要說,我沒有什么可辯護(hù)的。我不知道為什么辯護(hù),為什么站在這兒接受審判。”借主人公真誠決絕的語言,作品的敘事格調(diào)和敘事張力纖毫畢現(xiàn),奠定了全書的情感基調(diào)。圍繞對郁漱石的審判與辯護(hù),作者將屈辱、正義、構(gòu)陷和熱愛予以熔鑄,匯聚起一股強(qiáng)大的情感力量,與閱讀者共同釋放相通情感而完成閱讀旅行,讓讀者感觸到郁漱石、審判官封侯尉、養(yǎng)母尹云英、上司梅長治、李明淵、戰(zhàn)俘營次官矢尺大介、律師冼宗白、戰(zhàn)俘營戰(zhàn)友亞倫等眾多人物的鮮活與溫度。在內(nèi)在情感的起伏跌宕中我們看到了“講述者”若隱若現(xiàn)的影子,這個影子憂郁地注視著我們,在講述他人故事中飽含自己的悲憫與痛苦,與文本融為一體。這種超越故事而依靠情感的匯聚與釋放形成的互動,內(nèi)含對人生和命運(yùn)的由衷關(guān)懷,具有難以抵擋的情感重塑力,推動著作品的最終完成。
其次,是“球瓣”結(jié)構(gòu)的獨(dú)創(chuàng)與開合。作品故事開始于對一個戰(zhàn)俘的審判,終于主人公遺書,圍繞郁漱石是否在香港淪陷被俘后“通敵”,通過近百人物的陳述、調(diào)查、舉證和審判,將反法西斯時期香港淪陷前后各色人等生動展現(xiàn)出來,具有深廣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全書每一個小章節(jié)中每一人物的陳述,都以時間線性方式構(gòu)成一根弧形的線段,每根弧線首尾兩端相連,而在兩根弧線段形成的“球瓣”間寄居著一個歷史生活場域。它們既有所隔離又兩端相連,在100多根弧線段形成的“球瓣”鋪展中,將1945年前后在這些弧線段之間和兩端相交相織的生活場域真實地打開,不斷獲得“球瓣”體驗的循環(huán)疊加,一端指向開篇的自我辯護(hù)“我應(yīng)該活著”,另一端指向結(jié)尾的遺書“媽媽,我堅持不下去了”,構(gòu)建了作品與閱讀的緊張互動,由讀者將這些或?qū)捇蛘佌沟摹扒虬辍本蹟n成球體,清洗“球瓣”可能帶來的混亂,形成兩條清晰的線索,一為郁漱石留學(xué)日本、美國工作及回到國內(nèi)卷入香港戰(zhàn)役最終被俘,一為D戰(zhàn)俘營的3年8個月生活。兩條線索勾連起的廣闊背景構(gòu)成新的意蘊(yùn)空間,作者創(chuàng)造的“球瓣”文本結(jié)構(gòu),將日記體和環(huán)形結(jié)構(gòu)推到立體成熟的新高度,其由作者鋪展由閱讀合攏的探索,是構(gòu)建文本敘事與閱讀內(nèi)在互動的標(biāo)志性案例。
第三,是文學(xué)本身的辨識與標(biāo)志。一個有才能的作家,他的使命就是克服文體的自發(fā)慣性,創(chuàng)造新的標(biāo)準(zhǔn)和新的范式。關(guān)于虛構(gòu)與非虛構(gòu)的結(jié)合由來已久,在我看來,《人,或所有的士兵》正是將虛構(gòu)和非虛構(gòu)元素融合在一起,每一個陳述者的記錄,都以案卷記錄形式呈現(xiàn),這種記錄具有非虛構(gòu)的紀(jì)實特點(diǎn),腳注和參考資料則對其非虛構(gòu)性予以強(qiáng)化,它使每一個人物都獲得了歷史性真實。在這部作品中,歷史人物和虛構(gòu)人物交織,歷史事件和虛構(gòu)情節(jié)融合,虛構(gòu)的故事具有非虛構(gòu)的真實和沉重。這正是這部作品的貢獻(xiàn),用非虛構(gòu)獲得的真實講述 “或然”事實,盡管這一“或然”事實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也不應(yīng)該被人遺忘。這一基本邏輯在于,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基于人的觀測、參與和思維,人對客觀事物的觀測與描述并不等于客觀事物本身,必須承認(rèn)真實的某些虛構(gòu)性。
第四,是對現(xiàn)實主義的重申與拓展。從故事來看,作品抒寫的是過去時歷史,但作品并沒停留于對彼時彼刻的摩畫,而是呈現(xiàn)出強(qiáng)大的歷史精神性,郁漱石從法庭陳述開始,他不僅被一系列調(diào)查和舉證所推動而走向比戰(zhàn)俘更悲劇的命運(yùn),同時作為這場審判的參與者,也在審判中通過這些調(diào)查和舉證獲得了對人的命運(yùn)和價值尤其是恐懼的感知,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審判,這一審判超越了作品預(yù)設(shè)的法庭,用歷史性和未來性構(gòu)建其永恒的現(xiàn)實性,這是對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某種重申。同時,這部作品的現(xiàn)實性也具有寬廣視野,將中、英、印、美、荷、加、菲7國戰(zhàn)俘集中于島上,在宏闊的空間將每一個人物與其背后的國家、文化、時代等背景濃縮,突破了單一族群、地域、文化的現(xiàn)實性,將歷史豐富性展現(xiàn)到現(xiàn)實的深刻性與心靈的共振性方面,更真實地體味到現(xiàn)實主義精神所蘊(yùn)含的人性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