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陳寅恪哪些書不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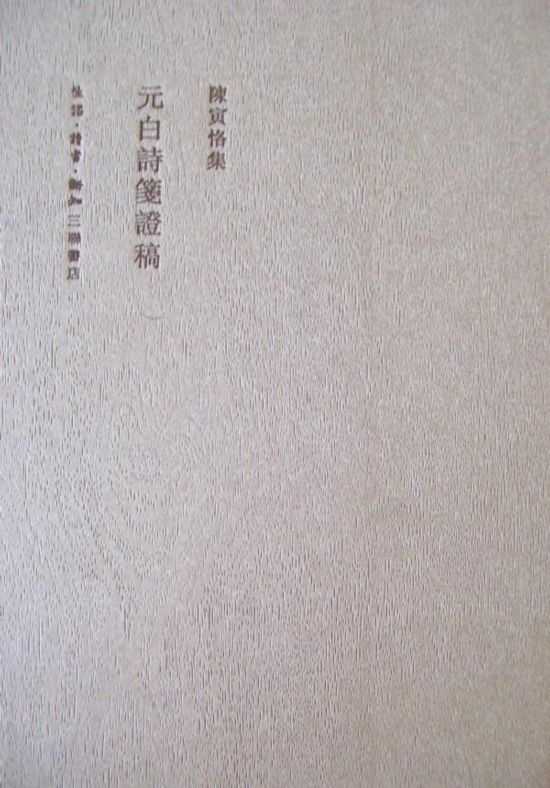
《元白詩箋證稿》(“陳寅恪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8月出版
新見劉夢溪先生主編《中國文化》今年秋季號胡文輝兄《陳寅恪征引史料未盡之例及其它》一文,舉證詳贍,見解平實通達,極有說服力。
后人對陳寅恪史學(xué)成績的敬意,其實主要不在史料周全,而在他的“巧”與“妙”(史學(xué)亦可視為高級智力游戲)。網(wǎng)絡(luò)時代,發(fā)現(xiàn)陳先生引書不周之處似乎并不很難,但在史學(xué)研究中有陳先生的“巧”與“妙”卻極不容易。他的“巧”與“妙”,簡單說就是:“他怎么會想到那樣的問題?”“他怎么能把表面完全不相關(guān)的事聯(lián)在一起?”“他怎么能在歷史中發(fā)現(xiàn)和今天結(jié)構(gòu)、事實極為類似的現(xiàn)象”,等等。陳先生研究的是大問題,但從來不失趣味。
陳先生早年有一篇文章《元微之遣悲懷詩之原題及其次序》,很能見出他的思維習(xí)慣,他在已知史料中用自己獨特的思維發(fā)現(xiàn)問題,然后解釋,雖然此文后來因白居易和詩寫作時間確定而不成立,陳先生舍棄了此篇論文,但陳先生發(fā)現(xiàn)問題的邏輯與視角,也就是他“巧”與“妙”的思維習(xí)慣卻還是能看得出來。另外,陳先生引書不周,可能還有個習(xí)慣問題,明以后的類書,印象中陳先生就不引。
中國老輩讀書人對類書的評價一般不高,他們認為這些書都是東抄西抄湊成的。往前的類書尚有價值,如唐代《藝文類聚》《初學(xué)記》等,宋代《太平御覽》《玉海》等,因為收古書多,這些古書又沒有保存下來,后世只能依賴類書中的史料,明以后的類書則基本不看了。陳寅恪可能也受這個習(xí)慣影響,他著作中一般不用明以后類書中的材料,比如郎瑛《七修類稿》是很有名的書,但印象中陳寅恪沒有引過(或引過我沒有注意到),而《藝文類聚》《初學(xué)記》《太平御覽》《玉海》等,則是陳寅恪常引的古書。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中講白居易《七德舞》時說過,類書為便利屬文,白樂天尤喜編纂類書,可知陳寅恪對類書體例及功用非常留意。
沒有引不等于沒有看過,因為不引明以后類書中的材料,有時就會出現(xiàn)同樣歷史現(xiàn)象,陳寅恪的判斷和類書史料相類的情況,試舉兩例:
陳寅恪講元白詩,經(jīng)常提到唐代女子很多用疊字為名,如“九九”“鶯鶯”之類(見《元白詩箋證稿》113、375頁,三聯(lián)版,2009年),陳寅恪的判斷是“鶯鶯雖非真名,然其真名為復(fù)字則可斷言,鄙意唐代女子頗有以‘九九’為名者”。
《七修類稿》有《唐雙名美人》條,原文如下:
元稹妾名鶯鶯,張祐妾名燕燕,柳將軍愛妓名真真,張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錢塘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氏曰燕燕,天寶中貴人妾曰盈盈,大歷中才人張紅紅,薛瓊瓊,楊虞卿妾英英,不知唐時何以要取雙名耶?(《七修類稿》361頁,臺灣世界書局,1984年)
陳寅恪注意到的現(xiàn)象與《唐雙名美人》為同一現(xiàn)象,雖強調(diào)唐女子多“九九”為名者與《七修類稿》略異,但《七修類稿》舉例頗富。
陳寅恪講《長恨歌》,特別注意考證“霓裳羽衣舞”(同上,26頁)。陳寅恪認為“自來考證霓裳羽衣舞之作多矣”,遠以宋代王灼《碧雞漫志》“所論頗精”,近以日人遠藤實夫《長恨歌研究》“征引甚繁”。陳寅恪總體認識是重要材料均出《唐會要》和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他依此思路進行了詳細舉證分析。舉證過程未及《七修類稿》,而此書有“霓裳羽衣曲舞”條,抄出如下:
霓裳羽衣曲舞
霓裳羽衣曲舞不傳于世久矣。雖學(xué)士知音之流。亦徒求想象而已。予以讀過詩書有關(guān)斯曲者。會萃成文。述注于左。其舞律呂節(jié)奏。庶亦可知過半矣。按明皇游月中。見仙女素衣奏樂極妙。記其音。歸而制之。(《漁樵閑談》云。與羅公遠游回。令伶人作。鄭嵎詩注。與葉法善游。歸于笛山寫其音。)會西涼節(jié)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diào)相符。遂合二者而制。名為霓裳羽衣。(《碧雞漫志》云為創(chuàng)于敬述。潤色于明皇。沈存中云。用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楊曲為腔。諸書皆同。)其音屬黃鐘。其調(diào)屬商。(見前漫志。沈存中亦引。辨為商調(diào)。)其譜三十六段。(見《渾成集》。)其奏樂用女人三十。每番十人迭奏。而音極清高。(見《齊東野語》。樂天詩亦曰由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其舞服之飾。樂天詩曰。虹裳霞帔步搖冠。鈿音累累佩珊珊。奏曲之數(shù)。白詩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八拍。繁音急節(jié)十二遍。唳鶴曲中長引聲。(前漫志云。飾奏有二十二遍。余皆同。)惜文人往往指為亡國之音。(如杜牧詩曰。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故棄而不傳。然周草窗述之。真有注云落水之意。非人間曲也。(見《齊東野語》。)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七修類稿》362頁,臺灣世界書局,1984年)
陳寅恪未引《七修類稿》,但所擴展史料方向和《七修類稿》有相合處。陳寅恪解“驚破霓裳羽衣曲”,認為“破”字除一般“破散破壞之意”外,還是一個樂舞術(shù)語,但舉例時未及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中“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而《七修類稿》已引。
最后附說一句,錢鍾書常引《七修類稿》,《容安館札記》中時有所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