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最早結識的唐代大詩人是孟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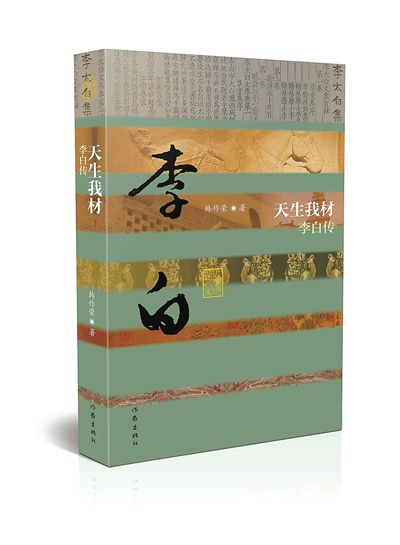
《天生我材——李白傳》 韓作榮著 作家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李白最早結識的唐代大詩人,是孟浩然。就一千多年來,流傳至今的唐詩而言,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春眠不覺曉”與太白的“床前明月光”之句,恐怕是不分長幼,所有粗通文字的人都能隨口背誦的五言絕句。或許是太熟悉的緣故,背得爛熟的詩句本來頗有意味,如之平白淺顯、通俗易懂,二十個漢字常常掛在嘴邊,太熟之后反倒不再深究其意,說不出好在哪里了。但詩有如此大的影響,能代代相傳,讓我想到詩能千古流傳,首先要寫得有意思,能吸引人;再就是平白如話,毫無滯澀之處,人人都能明白;自然還要精短,讀一兩遍就能記住,能背得下來。
若論詩之藝術水準之高,太白詩該首推《蜀道難》,可多數讀者只能記得住個別語句,能逐字逐句讀懂讀透已不容易,更別說背誦了。而孟浩然之詩,被詩人及研究者所稱道的,恐也不是《春曉》。
孟浩然堪稱五言絕句的圣手。他三十歲所作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詩中有這樣的句子:
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
這兩句詩自唐代殷璠編之詩選《河岳英靈集》卷中,被“孟浩然詩序”引用以來,一直被歷代詩話譽為古今絕唱之名句。就我看來,誠然詩之對偶精妙,但卻是一般詩人都可為之的技法,也不僅是兩個動詞用得好,妙在煉字、煉句之上的煉意。區(qū)區(qū)十個字渾然生成一種由獨特的內在感受而達成的境界,言他人眼中之無,讓不可能成為可能。這和現代詩中主體意識的滲入,重感覺和情緒的詩觀有異曲同工之妙。
《新唐書·文藝傳(下)·孟浩然》中,曾引《唐摭言》卷十一的一段文字,說的是孟浩然之詩亦被另一位大詩人王右丞王維所激賞。王維詠之“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句,“常擊節(jié)不已”。王維待詔金鑾殿,常應召商較風雅,一日玄宗忽臨幸王維宅第。其時恰巧孟浩然在王維處,錯愕之中拜伏于地。王維奏聞圣上,玄宗稱朕素聞其人,遂命浩然賦詩。浩然奉詔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玄宗聽了卻說:“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孟浩然雖終身未入仕途,但在唐時已詩名甚高。他與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滎陽鄭倩之、太守河南獨孤策,已結成“忘形之交”。唐代的諸多詩人都對其十分尊崇。
對于孟浩然的生平及其評價,歷來論家認為,與孟浩然同鄉(xiāng)的處士王士源所編《孟浩然集》三卷之序言最為精當、權威。序文系孟浩然歿后數年后,最熟知孟浩然者王士源于天寶四載(745)所作,言及了孟浩然的風貌、性格、言行、詩風等,其詳盡多面為他人所不及。故唐代韋韜于天寶九載(750)《孟浩然詩集》重序中言:“天寶中,忽獲浩然文集,乃士源為之序傳,詞理卓絕,吟諷忘疲。”
孟浩然為襄陽人,為孟子后裔。王士源稱他“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
由此看來,孟浩然該是位高潔清正、風儀動人的高士,且性格隨和爽朗,結交重義,樂于為人排憂解難,閑時種菜養(yǎng)竹,得自然之情趣。對朋友敞開心扉,心無芥蒂,率真且機敏。學問則不奉儒家,取眾家之精華;詩文不拘古法,而善于獨創(chuàng)。其五言詩稱天下獨步,盡善盡美。
李白對孟浩然心儀已久。浩然大太白十二歲,兩人相識時,浩然已名滿天下,而太白則是剛出蜀中的青年詩人,尚無大名。但心高氣傲的李白真正佩服的詩人實在不多,若非詩作真的令其佩服,不會對其如此尊崇,況且又是同一時代的詩人。正如太白《贈孟浩然》詩所言——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
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此詩系太白成名后所寫,對孟浩然詩兄仍如此親近,那大抵也是兩人氣味相投,都以清酒為圣人,濁酒為賢人,醉月迷花;尤其浩然不以乘軒服冕為上,云臥高隱,不事君王,如此清高如蓍草之德,確令人如高山般景仰。
太白寫給孟浩然的詩現存五首,為《游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淮海對雪贈傅靄》(另題《淮海對雪贈孟浩然》)及《贈孟浩然》《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春日歸山寄孟浩然》。另有疑為兩人互贈之作,有論者為之探討,可不計。
其實,孟浩然一生并非不想求取功名。在盛唐,文人士子都以能入仕為官、盡展才學以求宏達作為終生追尋的價值取向,孟浩然也不例外。正如他詩中所言:“心跡罕兼遂,崎嶇多在塵”(《還山貽湛法師》),為了謀取功名而到處奔波。故“少小學書劍,秦吳多歲年”(《傷峴山云表觀主》),為此曾在長安、吳越漫游多年。
太白與孟浩然相交,固然有慕其高潔、愛其人品、才華之意,但更重要的原因大抵是兩人命運相像,都有宏偉的建功立業(yè)之心,有高遠的抱負,都從對方看到了自己的理想與人格。孟浩然的“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昔有鹡鸰心”(《洗然弟竹亭》);“杳冥云海去,誰不羨鴻飛”(《同曹三循史行泛湖歸越》);“謂余搏扶桑,輕舉振六翮”(《山中逢道士云公》);“再飛鵬擊水,一舉鶴沖天”(《峴山送蕭員外之荊州》);“安能與斥,決起但槍榆”(《送吳悅游韶陽》)。這樣的詩句,與太白的“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及其《大鵬賦》何其相似乃爾!只不過因性情不同,太白之詩更為豪闊、博大,氣勢更為凌人而已。
兩人相像之處還在于雖入世心切,但皆懷才不遇,仕途坎坷無路可通,郁郁而不得志。卓然傲世、清高獨立者,雖然“沖天羨鴻鵠”,可又“爭食羞鳴鶩”。孟浩然想入世為官,又不愿意同雞鴨一樣的小人爭食。面對媚俗的世風,相知甚少,因無知己乏故親而郁悶,所謂“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帶異抽簪”(《京還贈張維》)。用陶潛不肯為五斗米折腰,與嵇康自稱“七不堪”的典故,表達自己不愿卑躬屈膝、喪失人格而趨炎附勢的心態(tài)。
李白與孟浩然相遇應當是開元十四年(726)秋日。其時孟浩然入京之前在吳越曾滯留三年之久,其詩《久滯越中》“兩見夏云起,再聞春鳥啼”可證。而李白辭親遠游初游吳越時,在溧陽與之相見初會,太白有《游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一詩為證。此詩一般選本為“贈同旅”,可在兩宋本、繆本、《文苑英華》《全唐詩》中俱云“一作《贈孟浩然》”。可知該是兩人相遇同游而作。或許是同游者不只兩人,還有新朋在側,李白贈詩給諸友,所傳皆以贈己為題,故不相同,后人才以“贈同旅”命名。而孟浩然為其中名氣最大者,因此原因多本之中才有“一作《贈孟浩然》”之說吧。
溧陽距金陵很近,太白于此得遇大名鼎鼎的孟浩然,神交已久,見面自然相互尊重,親如兄弟。其時正是太白縱酒攜妓、散金三十余萬的浪游之日,免不了品酒賦詩,盡名士之歡。太白任性率真,氣度非凡,任俠情豪;孟浩然亦率性真誠,為人排憂重義,亦書劍兼修;兩人性情趣味相投,一見如故,做傾心之談,一起游歷吳越,吟詩懷古,酬唱作答,友情日深。孟浩然善五言詩,太白贈之詩作,亦多為五言,多少亦受孟浩然體之影響。不過太白雖用孟體,但其詩一氣舒卷,“質健豪邁,自是太白手段,孟不能及”(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不過就我看來,孟之清絕,太白亦難及。詩恐各有其特色,難分高下,該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誰喜歡其詩,在誰眼中就是最好的詩了。
太白《游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之詩,有“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秋風還”之句,點明同游之時已近中秋佳節(jié)了。隨之孟浩然與李白同游金陵,太白的《金陵城西樓月下吟》有“白云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該是同時所作皆為天清白露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