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如何翻譯羅曼·羅蘭和巴爾扎克

傅雷舊照 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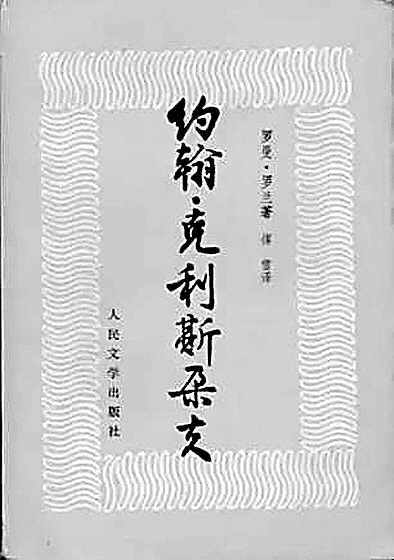
傅雷譯著書影 資料圖片

位于上海的傅雷故居 資料圖片

位于上海的傅雷圖書館 資料圖片
江聲浩蕩的背后故事
2006年我在準備博士學位論文的時候,江楓先生打來電話問我選了什么題目,我說是關于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就聽電話那邊江楓先生厚重而洪亮的聲音道:“‘江聲浩蕩。’傅雷的翻譯,好啊,很好。”這讓我想起,作家邰耕曾經說過:“羅曼·羅蘭的四大本《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令人難忘的著作,二十多年前我曾閱讀過,許多情節(jié)都淡忘了。但書中開頭的‘江聲浩蕩’四個字,仍鐫刻在心中。這四個字有一種氣勢,有一種排山倒海的力量,正好和書中的氣勢相吻合,……對閱讀者的心靈產生巨大的沖擊。”
1937年到1941年間,傅雷精耕細作,完成了《約翰·克利斯朵夫》一百多萬字的翻譯,于國破山河在的歲月出版,曾引起無數讀者的爭購傳閱。茅盾在1945年說過,羅曼·羅蘭的“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同是今天的進步青年所愛讀的書,我們的貧窮的青年以擁有這兩大名著的譯本而自傲,亦以能輾轉借得一讀為榮幸”。老作家阮波在傅雷著譯研討會上說,當年她作為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就是懷揣傅譯版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奔赴延安的。
其實,在傅雷之前,曾有敬隱漁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的前半部分;有黎烈文譯的第四卷《反抗》的片段;有靜子和辛質譯的第六卷《安戴耐蒂》;緊隨傅譯之后,還有鐘憲民和齊蜀夫譯的第一卷《黎明》。但由于這些譯者的藝術功力可能還有所不逮,或缺乏持久的意志,更沒有清醒的意識去思考民族危難中讀者的期待,沒有強烈意愿去完成歷史賦予譯者的使命,以上的版本最后都一一偃旗息鼓。只有傅雷那時意識到,“我們比任何時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都更需要堅忍、奮斗,敢于向神明挑戰(zhàn)的大勇主義”。傅雷為了“挽救”一個“萎靡”的民族,完成了《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譯,給黑暗里的人們點燃了精神火炬,促使當年的進步青年用“頑強的意志”去追求嶄新的天地,拼搏向上,攀登生命高峰。
“江聲浩蕩”是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的第一句,為什么能成為這部譯作的一個重要符號,留在讀者的記憶深處?我們不妨簡要分析一下,萊茵河與作品主人公的關系。在《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音樂靈魂譜寫的交響曲”(茨威格語)中,可以說,萊茵河有著這樣四層蘊意:一,它象征著主人公克利斯朵夫奔流向前的生命旅程;二,它象征著生生不息的人類的生命長河;三,它傳遞著吸收兩岸思想,融合法德優(yōu)秀文化,再生西方新文明的希望;四,它表達了作者以萊茵河為紐帶來包容共飲一江水的兩岸各國人民,實現人類之間的和諧共處的思想。概而言之,萊茵河的這四層蘊意構成了作品的主要精神,所以萊茵之聲便是作品主要精神的奏鳴,是作品的音樂主旋律。羅曼·羅蘭按交響樂的結構布局萊茵之聲,恰恰說明,萊茵之聲確實蘊意豐富而又重要,特殊而又意味深長。為了烘染一個英雄的誕生,為了突顯萊茵河的特殊蘊意,小說開門見山,奏響了作品的音樂主題,經過“呈示”和“發(fā)展”,最后又“再現”了萊茵之聲(作品開篇幾處譯文,從“江聲浩蕩”到“浩蕩的江聲”,又到“江聲浩蕩”,再到整個作品尾聲,回歸“江聲浩蕩”)。
我們通讀作品可以領會到,傅雷翻譯的“江聲浩蕩”傳達出了萊茵河的四層蘊意:一、克利斯朵夫任生命的波濤怎樣起伏顛簸,依然揚起遠航的風帆,百折不回;二、只有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兒女,像克利斯朵夫那樣去努力、去奮斗,才有希望重新締造一個理想的文明世界;三、“拉丁文化太衰老,日耳曼文化太粗獷,但是兩者匯合融和之下,倒能產生一個理想的新文明”,傅雷這樣的闡釋可以說是他精彩傳神的翻譯的依憑;四、唯有胸襟像長江大河那樣寬宏的人,方能有浩蕩的情懷,方能在心中培育出大愛人類的情感。所以,“江聲浩蕩”傳達出了這部恢宏巨著的主要精神。“江聲浩蕩”譯句的重復,就是這部音樂作品的主旋律在重復、回旋、再現。
傅雷早在1937年的《譯者獻辭》中就提出,這部作品“是貝多芬式的一闋大交響樂”。從交響樂的角度看,可以說,“江聲浩蕩”傳達出了波瀾起伏、令人心潮澎湃的樂思,傳達出了那融和歐洲文明的美妙的和聲。“江聲浩蕩”一句的翻譯,是傅雷深厚的文學功力和高超的藝術修養(yǎng)在其火熱的激情下的絕妙的融合。“江聲浩蕩”,聽來不但音節(jié)鏗鏘、清晰響亮,而且音律和諧,平平仄仄,自然而又勻稱,最大限度地彰顯了音樂效果,給讀者帶來了融視覺與聽覺于一體、符合這部作品創(chuàng)作特色的藝術享受。多少年來,它之所以撞擊讀者的心靈,給讀者留下深刻難忘的感受,就在于它著實太傳神了!借用傅雷自己的話說,它確實“含有豐滿無比的生命力”。它給讀者描繪出的是一幅意象深遠、蘊意豐富、“包藏無限生機”的宏圖;它那略含陌生化的搭配,使得讀者不由得稍作停留,來感受語言的張力;它自身的音樂感,又洞開了一個音響的天地,給這部作品的主要精神,賦予了一個回蕩在讀者心海的不息的強音。讀罷作品,細細品味后感覺,一部激昂著“英雄”的精神和生命的活力、蕩漾著不同文明的和聲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洋洋百萬余言,似乎全都濃縮到了“江聲浩蕩”之中。也正因為“江聲浩蕩”濃縮了這部音樂長河小說的激情與活力、氣勢與氣度、精神與靈魂、藝術與風騷,它才能穿越歷史,常駐讀者心間。
打開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們首先讀到的是《譯者獻辭》:“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所以在你要戰(zhàn)勝外來的敵人之前,先得戰(zhàn)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也許,不少讀者的內心在這里已被傅雷攫住,因為每個讀者應該都有,或者都有過英雄夢,而英雄原來并非高高在上的完人,蕓蕓大眾都有可能成為英雄。這是非常接地氣的話,樸實而又真誠,想必可以觸動幾乎每一個讀者,讓他們內心剎那之間產生“自拔與更新”的力量。
1934年,傅雷致函羅曼·羅蘭,向他討教了英雄主義。羅蘭在復函中說:“夫吾人所處之時代乃一切民眾遭受磨煉與戰(zhàn)斗之時代也;為驕傲為榮譽而成為偉大,未足也;必當為公眾服務而成為偉大……”羅曼·羅蘭告訴傅雷:為公眾服務,才是真正的偉大、真正的英雄;作為一個藝術家,應當把為公眾服務和為民族乃至全人類之忠仆,作為自己應當追求的“崇高之社會意義”與“深刻之人道觀念”。傅雷在回信中說:“不肖雖無緣拜識尊顏,實未誤解尊意。”傅雷與羅蘭雖天隔東西,但倆人思想是相通的,精神是契合的,所以這樣的《譯者獻辭》才能和作品的內容產生同頻共振的效果,讓讀者情不自禁地“以虔誠的心情來打開這部寶典”。傅雷后來也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的那樣,“潔身自好之士惟有隱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以從事文學翻譯來服務大眾,振興民族,以大勇無功的姿態(tài)為社會的文明奉獻一生。傅雷后來對好友宋淇說:“我回頭看看過去的譯文,自問最能傳神的是羅曼·羅蘭,第一是同時代,第二是個人氣質相近。”
1952年,傅雷又推出了《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使得作品“風格較初譯尤為渾成”,但我們發(fā)現,“江聲浩蕩”依然如故。
關于《高老頭》和《于絮爾·彌羅埃》的糾紛
傅雷也是巴爾扎克在中國的忠實代言人,一生譯有巴氏作品15部(出版14部,“文革”期間遺失翻譯手稿1部),其中《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貝姨》《幻滅》等作品由于傅雷的傾力翻譯,深受讀者喜愛,至今不衰。不過在傅雷那個年代,還有兩位巴爾扎克的譯家:穆木天和高名凱,前者是曾經的創(chuàng)造社成員,翻譯工作最早,約有10部;后者是我國知名語言學家,譯得最多,約21部。傅雷的巴爾扎克作品譯介既非最早也非最多。
不過,程代熙在介紹《巴爾扎克在中國》的史料時,權威性地指出:“在翻譯介紹巴爾扎克的作品方面,態(tài)度嚴肅認真、譯筆生動流暢,在讀者中影響較大的,要推傅雷。”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趙少侯,也曾直言不諱地比較指出:“讀過之前版本的巴爾扎克小說,再來讀傅雷先生的譯本,實在有爬出步步荊棘的幽谷走上康莊大道的感覺。因為再也碰不到疙疙瘩瘩、彎彎扭扭的句子,再也遇不見稀奇古怪費人猜想的詞匯了。”
早在1938年,傅雷就開始打巴爾扎克的主意,或許因為巴爾扎克的浩瀚博大,傅雷需要假以時日,準備醞釀,才讓巴氏作品構成他后半期翻譯的重心。此外,《人間喜劇》描繪了19世紀上半葉法國社會方方面面的風貌,也十分對應傅雷的翻譯觀,即:“文學既以整個社會整個人為對象,自然牽涉到政治、經濟、哲學科學、歷史、繪畫、雕塑、建筑、音樂,以至天文地理、醫(yī)卜星相,無所不包”。傅雷曾對好友宋淇說過:“鄙見以為凡作家如巴爾扎克……,譯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順,因原文冗長迂緩,常令人如入迷宮。我的譯文的確比原作容易讀。”
1952年,趙少侯在《翻譯通報》第7期上發(fā)表了《評傅雷譯〈高老頭〉》。趙少侯也是法國文學翻譯家。他的評論一分為二,三個譯例點贊,三個譯例質疑。但即便質疑,也有肯定的某個側面,也是用一種商榷的口吻,什么“不知譯者以為如何”,“是否正確,希望譯者以及讀者加以討論”以及“原則上還是無可非議的”等等措辭,顯得十分謹慎。他知道傅雷的脾氣,也知道他的真才實學,開篇褒揚道:“傅雷先生的譯品,一般地說,都是文從字順,流暢可誦……本書因為是譯者修改過的重譯本,曉暢、犀利更是它的顯著優(yōu)點”,但隨后話鋒一轉:可讀者“卻又另外有了一種不大放心的地方……那便是這樣流利自然的譯筆是否仍能完全忠實于原文?是不是為了追求中譯文的通順暢達,有時也多少犧牲了原文的形式?”
兩年后,傅雷在致宋淇的信中,提到了趙氏對他的評論:“趙少侯前年評我譯的《高老頭》,照他的批評文字看,似乎法文還不壞,中文也很通;不過字里行間,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同時傅雷也反評他道:“去年他譯了一本四萬余字的現代小說,叫作《海的沉默》,不但從頭至尾錯得可以,而且許許多多篇幅,他根本沒懂。甚至有‘一個門’‘喝我早晨一杯奶’這一類的怪句子。”
不久之后,又發(fā)生了一件事。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作品《于絮爾·彌羅埃》同樣遇到趙少侯的審讀。趙氏肯定了傅譯“是認真的,忠實的,對原文的理解力也是極其深刻的”,但同時也指出:“惟譯者的譯文風格,似乎已稍稍落后于時代。最突出的地方,即喜歡用中國的陳詞……傅雷先生的譯筆自成一家,若由編輯部提意見請他修改,不惟他不同意,事實上也有困難。”他提出:“關于他的譯筆及似是而非的譯法……請領導決定。”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的樓適夷,慎重地請傅雷的好友錢鐘書再來審讀,不料錢的意見,傅雷也難接受,而且還向錢“開火”,使錢陷入尷尬之中。于是樓適夷又決定請語言學家葉圣陶從中文角度提提意見,葉老次年二月回復:“這部譯稿是我細心看的,詞語方面并無不妥適處。看了一遍,僅僅做這么一句話的報告,似乎太簡單,可是要詳細地說,也沒有什么可說了。”至此,有關《于絮爾·彌羅埃》的糾紛案塵埃落定,譯本最終出版。
“翻譯工作要做得好,必須一改再改三四改”
需要指出的是,傅雷在1963年第三次翻譯《高老頭》時,對譯文自然又做了修改或調整。所以,傅雷致宋淇信中提及此事時,所表現的不買賬甚至不在乎的樣子,可能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文人的表象常態(tài)。但他也并沒有以趙氏的優(yōu)劣評判為轉移,即便趙氏當時大加贊賞的譯句,傅雷覺得還是欠佳,后來照樣做了修改。
傅雷后來說:“我自己常常發(fā)覺譯的東西過了幾個月就不滿意;往往當時感到得意的段落,隔一些時候就覺得平淡得很,甚至于糟糕得很。當然,也有很多情形,人家對我的批評與我自己的批評并不對頭;人家指出的,我不認為是毛病;自己認為毛病的,人家卻并未指出。”但總體說來,傅雷對別人改動他的文字,是很光火的,那些相關出版社的不少編審都領教過傅雷的脾氣。因為傅雷筆下的文字,通常都是他經過認真的思考、琢磨,幾經推敲才選定的,所以他不會認為別人的選字用詞比他更準確、更到位。
當然,這不等于說,傅譯就是完美無瑕;就沒有可以商榷、改進的地方了。至少,傅雷歸化傾向的翻譯對中國讀者就有溺愛之嫌。但無論如何,求真求美的傅雷,發(fā)現自己不妥當不完善的翻譯時,不會不改,因為他始終把“學問第一、藝術第一、真理第一”作為自己的追求。
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的最后說:“這次以三閱月工夫重譯一遍,幾經改削,仍未滿意。藝術的境界無窮,個人的才能有限:心長力絀,惟有投筆興嘆而已。”同樣,傅雷雖這么說,但他也沒有真的撂下手中的筆,從此放棄他的追求。他只是道出了一個求“真”的藝術家與“真”之間永遠存在的客觀距離。但他“對自己的工作還是一個勁兒死干”,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因為他明白:“藝術的高峰是客觀的存在,決不會原諒我的渺小而來遷就我的。”他對自己的譯作總有再上一層樓的要求,十分執(zhí)著,所以到了晚年,才會有“正在經歷一個藝術上的大難關”的境況,“眼光比從前又高出許多”。
傅雷曾對宋淇說:“無奈一本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高老頭》正在重改,改得體無完膚,與重譯差不多”;他對傅聰說:“翻譯工作要做得好,必須一改再改三四改”;他對梅紐因說:“巴爾扎克《幻滅》,譯來頗為費神。如今與書中人物朝夕與共,親密程度幾可與其創(chuàng)作者相較”;他在《翻譯經驗點滴》中說:“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常年感到苦悶”;等等。這一切,都因為他“視文藝工作為崇高神圣的事業(yè),不但把損害藝術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樣嚴重,并且介紹一件藝術品不能還它一件藝術品,就覺得不能容忍”。
傅雷對自己的翻譯活動還有獨特的認識,他說:“譯者不深刻的理解、體會與感受原作,決不可能叫讀者理解、體會與感受”;又說:“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領悟。”其實,他是在向我們傳經送寶:文學翻譯不只是理解原文意義,還要去體會、感受、領悟原文的妙處、原文的韻味;“理解”之外,還要有“體會”“感受”“領悟”,這樣翻譯過來的東西才有文學味道。傅雷的翻譯,耐讀、耐回味,既能把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都咂摸出來,又能出神入化地表達出來,這與他對翻譯活動的這種認識有極大關系。
因為傅雷的翻譯作品質量好、品格高,人民文學出版社才把《巴爾扎克選集》的翻譯任務交給他,“種數不拘——傅雷說,由我定,我想把頂好的譯過來”。因為傅雷在譯介巴爾扎克上面作出的重要成就,他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學會吸納為會員。他與宋淇談翻譯時說過:“我的經驗,譯巴爾扎克雖不注意原作風格,結果仍與巴爾扎克面目相去不遠。只要筆鋒常帶情感,文章有氣勢,就可說盡了一大半巴氏的文體能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傅雷翻譯手稿和校樣修訂稿整理與研究》〔19BWW011〕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