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說者的旁觀與逃離
在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小說《解說疾病的人》里,生活在美國,回印度度假的達(dá)斯夫人在得知導(dǎo)游卡帕西的另一份工作——將病人口述的病癥翻譯給醫(yī)生后,向這個(gè)土生土長的印度人透露了自己出軌的秘密,兩人隨后產(chǎn)生了這樣一段對話——
卡帕西先生,你真的沒有話說?你不是干這個(gè)的嗎?
我的工作是導(dǎo)游,達(dá)斯夫人。
不是說這個(gè)。你還有份工作,做譯解。
可是我們沒有語言障礙啊,有什么要譯解的呢?
我不是那個(gè)意思。你要不是做這個(gè)的,我絕對不會告訴你。告訴你那些秘密對我意味著什么,你明白嗎?
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天天這樣痛苦不堪我受夠了!八年了,卡帕西先生,八年來我一直在忍受煎熬。我盼著你能讓我感覺好點(diǎn),講一些寬慰我的話。你說我該怎么治才好?
對卡帕西來說,達(dá)斯夫人的意圖和這番話讓他不知所措,他不能提供給她治療的方法,他不是醫(yī)生,沒有這個(gè)能力,他只能像往常一般,成為他人痛苦與秘密的傾聽者、旁觀者。對達(dá)斯夫人來說,秘密的重量早已成為身體的一部分,自己難以承受,他人也無法分擔(dān),她不得不面對這種傾訴與回應(yīng)之間的落差。

裘帕·拉希莉
這場無疾而終的對話像是裘帕·拉希莉的小說里一個(gè)等待發(fā)現(xiàn)的病癥,不斷擴(kuò)散、發(fā)育,蔓延至其他小說里那些離開故土、前往美國的印度移民身上。相比達(dá)斯夫人的秘密,群體面臨的落差更龐大也更無形,它來自地域、社會和文化,又都在異國被迫細(xì)化成一個(gè)個(gè)難以割舍的習(xí)慣,餐桌上的咖喱和豆蓉、額頭象征婚姻的朱砂痣、信件和電話上的家鄉(xiāng)話。
這些習(xí)慣跟隨美式房屋里的美式家居,等待著自己的主人:被父母包辦婚姻的印度夫婦,丈夫高學(xué)歷,在大學(xué)供職;妻子留守家中,從廚房到臥室,奔走在丈夫和孩子之間。他們默許東方式的家庭關(guān)系在更獨(dú)立、更開放的異國扎根、生長,共同庇護(hù)的習(xí)慣和身份改變、流失,直到病癥顯露,在慌亂和矜持中,又被匆匆掩蓋,以便這種努力維持的家庭生活能夠繼續(xù)。
祖籍印度,生于倫敦,三歲隨父母移居美國羅德島,成年后在紐約和波士頓等地求學(xué),取得了包括文藝復(fù)興研究博士在內(nèi)的多個(gè)學(xué)位,父親是圖書館員,母親是藝術(shù)學(xué)碩士。
將裘帕·拉希莉的這段成長背景和經(jīng)歷拆解來看,跟她小說里寫到的移民角色沒什么區(qū)別,作家在成為角色的創(chuàng)造者之前首先是故事的親歷者,或許這就是為什么裘帕·拉希莉能以老練、信手拈來的筆觸記錄下移民生活中的變化,捕捉到特定時(shí)刻的那份慌亂和矜持。《解說疾病的人》里,達(dá)斯夫人在對話結(jié)束后,打開車門,走向山上的達(dá)斯先生和孩子,嘴里呼喊著:等等我!我來了。平靜得好像什么都沒有發(fā)生過。
《解說疾病的人》也是裘帕·拉希莉第一部作品集的名字,2000年,她憑借這部短篇集成為普利策文學(xué)獎迄今最年輕的得主,短篇集包括的九篇故事里,有寫第二代移民的婚姻和戀情的,《停電時(shí)分》《性感》《福佑之宅》;有用第一人稱寫第一代移民剛到美國的景況的,《第三塊大陸,最后的家園》,據(jù)說來源于裘帕·拉希莉父親的經(jīng)歷;《真正的門房》和《比比·哈爾達(dá)的治療》是兩篇寫契訶夫式小市民的,前者寫孟加拉難民布梨大媽在一棟破舊的居民樓里當(dāng)門衛(wèi)謀生,最后被對自我不滿的居民們拿來泄氣,趕上街頭。后者講無父無母、身患頑疾的單身女如何在周圍人自吹自擂的善良和一次突如其來的暴力中被迫成為母親的。
與那篇《解說疾病的人》類似,《森夫人》也是一篇關(guān)于旁觀者的小說。單身母親把兒子艾略特托付給來自印度的森夫人,男孩得以走進(jìn)這對異國夫婦的家門,他目睹森夫人用一條從印度帶來的刀片把食材收拾得干凈利落,看上去勤快又能干。他也聽森夫人拿著信件講印度的親人,抱怨待在美國郊區(qū)多么孤寂。
在男孩身上,也有著跟森夫人類似的遭遇,他的單身母親像森先生對待森夫人一般,極少過問,她把男孩交給森夫人就像森先生要求森夫人學(xué)車,首先是為了自己便利。森夫人抱怨周圍沒有說話的鄰居,男孩跟母親則住在海邊的屋子,閑暇時(shí)只能一個(gè)人在海灘玩。
男孩的懵懂恐怕不能完全知曉森夫人話語里沉重的鄉(xiāng)愁和孤獨(dú),森夫人自然也不指望一個(gè)男孩明白她的心境,她甚至沒有心思了解男孩內(nèi)心的想法。年齡和身份在裘帕·拉希莉這里是一種現(xiàn)實(shí)性的阻隔,情感無法交匯,兩個(gè)生活狀態(tài)類似的人只能扮演彼此生活的旁觀者。
在小說后段,裘帕·拉希莉?qū)懮壬蝗灰獛蛉撕湍泻⑷ズ_叄蛉颂氐卮┥霞t莎麗,森先生要給森夫人買冬衣,表現(xiàn)出小說里從未有過的關(guān)心,男孩跟著這對夫婦買魚、吃點(diǎn)心、在海灘上一起拍照。森夫人不再消沉,夫婦之間變得恩愛,男孩得以回到那種健全的家庭環(huán)境,在這個(gè)場景里,乏味的生活短暫回避,角色們第一次能共享快樂和自由,仿佛正經(jīng)歷出逃。
而在回程路上,森先生強(qiáng)迫森夫人練車,發(fā)生了車禍,男孩從森夫人家回來。裘帕·拉希莉替角色打開的這道門,又重重地關(guān)上了,生活重新返回到門背后那股無法訴說的孤寂和乏味,只是這份孤寂和乏味,男孩和森夫人不再能替彼此觀看。
小說結(jié)尾,男孩沒有再找保姆。森夫人曾傾訴給他的感受,他要在往后的日子里從自己身上知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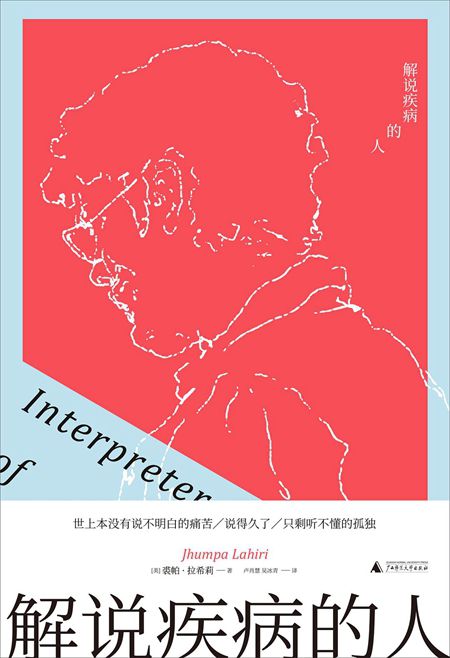
對于《解說疾病的人》里的第一代移民來說,故土在他們的精神世界里依舊留有一個(gè)難以撼動的位置。在2008年出版的另一部短篇集《不適之地》里,裘帕·拉希莉?qū)⒛抗饣財(cái)n到像自己一樣的第二代移民,他們生長在異國,比起父輩,故土在記憶里只是家庭生活中殘留的舊習(xí)和遠(yuǎn)渡重洋的一次次探訪,他們需要迫切面對的,是內(nèi)心不夠堅(jiān)實(shí)的故土情結(jié)和一個(gè)全然不同的外部世界之間的關(guān)系。
在同名短篇《不適之地》里,女兒露拉在母親死后,糾結(jié)于自己和父親間冷漠的關(guān)系,這段關(guān)系的疏遠(yuǎn)多少也暗含著露拉與故土的距離,父親即是故土;《純屬好意》里,姐姐蘇妲勤奮好學(xué),最后離開父母遠(yuǎn)嫁倫敦,弟弟拉霍爾違背父母意愿,淪為一名酗酒者、失敗者。姐弟兩人都在不同層面上割斷了與父母的聯(lián)系,姐姐是距離上,弟弟是精神上。
旁觀者不再能輕易地置身事外,在目睹父輩生活的同時(shí),第二代移民開始上演自身的掙扎和逃離。
三個(gè)章節(jié),兩個(gè)家庭,短篇《海瑪和卡西克》是《不適之地》里篇幅最長、敘事結(jié)構(gòu)最獨(dú)特的一篇。小說里,海瑪和卡西克分別是兩個(gè)印度移民家庭里的孩子,因?yàn)橐淮巫児剩ㄎ骺穗S父母搬進(jìn)海瑪?shù)募依铮粋€(gè)月的短暫相處中,海瑪對比自己大四五歲的卡西克產(chǎn)生了依戀,隨著卡西克和家人搬走,這段隱秘的單戀被迫擱置。
小說的第一個(gè)章節(jié)是海瑪?shù)淖允觯v述兩家人在一起的那段經(jīng)歷,她對卡西克的愛慕,對他母親的記憶。而卡西克的回憶里并沒有太多關(guān)于海瑪?shù)摹T诘诙鹿?jié)里,他傾訴更多的是母親病逝前后的那段日子,自己如何割舍不了對母親的懷念,難以融入父親組建的新家庭。
裘帕·拉希莉?qū)r(shí)間跨度的處理嫻熟又自然,讓人想起短篇大師愛麗絲·門羅。第三章節(jié)里,當(dāng)海瑪和卡西克再次相遇,已是數(shù)十年后。海瑪經(jīng)歷了一次失敗的戀情,默許了一段跟父輩一般的包辦婚姻。卡西克脫離父親的新家庭,游蕩在南美大陸的邊境和戰(zhàn)場。
兩個(gè)早已分屬不同世界的人,重新延續(xù)舊時(shí)的戀情。裘帕·拉希莉?qū)巧倪@一安排,使得彼此生活的旁觀者在對共同記憶的回望中,有了創(chuàng)造共同生活的可能,病癥似乎也要消除。只是這種被延續(xù)的共同記憶里,依舊存在著落差。對海瑪來說,它或許可以幫助自己逃離即將步入的婚姻,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而無所依靠的卡西克在海瑪身上尋找的,是母親去世前那段可以稱之為“家”的生活狀態(tài),似乎只要跟海瑪在一起,母親就能繼續(xù)活下去,自己也不會離開父親。海瑪最后拒絕了卡西克,也是因?yàn)樗宄ㄎ骺藢ψ约翰]有愛,那種對過去的依戀不能支撐他們維持更長久的生活。
故事結(jié)尾,海瑪在成婚的周末,收到了卡西克因意外死去的消息,裘帕·拉希莉的這個(gè)結(jié)局為前兩章的自述添上了后知后覺的告別意味。卡西克的回歸告終,海瑪回到美國開始新生活,逃離在此形成了困局周而復(fù)始的一部分,病癥或許才剛剛開始,它將在生者身上延續(xù),又因?yàn)樗勒卟辉倌芟?/p>
作為三十來歲出名、寫作生涯二十余年的作家,裘帕·拉希莉算不上高產(chǎn),除了兩部短篇集,她還有兩部長篇,兩部隨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作家似乎秉持了與作品同質(zhì)的氣息,沒有瑰麗宏大的敘事,撇棄技巧和結(jié)構(gòu)的修飾,他們的書寫和呈現(xiàn)難以在讀者心中喚起強(qiáng)大的感召力,而是在恰當(dāng)距離外維持一種無聲的照應(yīng),一種經(jīng)驗(yàn)的預(yù)示,他們需要讀者在現(xiàn)實(shí)中感受過這種經(jīng)驗(yàn),進(jìn)而在閱讀中消除彼此間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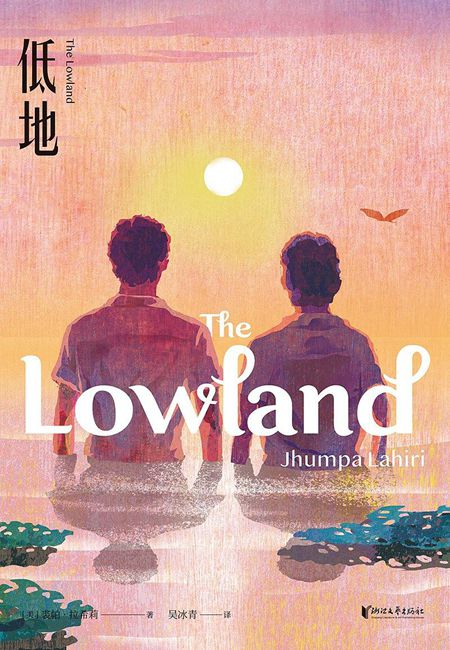
如果說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完美地實(shí)現(xiàn)了這種狀態(tài),那么她的長篇則開始偏離這種狀態(tài)。無論是2003年的《同名人》,還是耗時(shí)多年,在2012年寫成的《低地》,都有一種自然之物被精心修飾過的觀感。《同名人》里,第二代移民果戈理從父親鐘愛的俄國作家那里繼承了這個(gè)名字。《低地》開場,一對印度兄弟穿行過家門口的那片低地,多年后,他們共同擁有過的妻子從美國返回低地。短篇里難以訴說的病癥以更加具象、附帶命運(yùn)感的樣貌出現(xiàn)在長篇里。而裘帕·拉希莉從果戈理的父親寫到果戈理的女兒,寫《低地》里印美兩地四代人的生活歷變,復(fù)雜的代際關(guān)系背后,大概也有她嘗試在跳出距離之外的記錄和觀察,厘清病癥的意圖。
長篇《低地》依舊有裘帕·拉希莉短篇中慣用的人物結(jié)構(gòu)。一對年紀(jì)相仿、性格各異的兄弟,哥哥蘇巴什沉穩(wěn)內(nèi)斂,很少透露內(nèi)心的想法;弟弟烏達(dá)安性格叛逆,投身于當(dāng)時(shí)的印度革命。結(jié)果卻是蘇巴什離開印度,烏達(dá)安為了自己熱愛的故土選擇繼續(xù)抗?fàn)帲c自己不被認(rèn)可的妻子高麗留在了父母身邊。
兄弟二人都為此付出了代價(jià),烏達(dá)安被槍決,蘇巴什回到印度后,帶著高麗前往美國。蘇巴什的這一選擇可以看作是《海瑪和卡西克》里,卡西克重逢后對海瑪?shù)膽B(tài)度。唯有在高麗比肩弟弟的學(xué)識和對革命的熱衷上,蘇巴什才可以找到弟弟殘留的影子。
而對高麗來說,她對烏達(dá)安懷有無法遺忘的愛,烏達(dá)安死后,她也清楚自己寄人籬下不會有未來。但如果跟隨蘇巴什,她就有了創(chuàng)造新生活的可能,只是她的新生活里,永遠(yuǎn)都不會有蘇巴什的位置。裘帕·拉希莉?qū)⑦@一角色置入到情感與現(xiàn)實(shí)上都無法回避的困境,這種困境之下不只有高麗,還有為了緬懷弟弟放棄情感自由的蘇巴什,又或許在高麗和蘇巴什背后,站著更多來自裘帕·拉希莉小說中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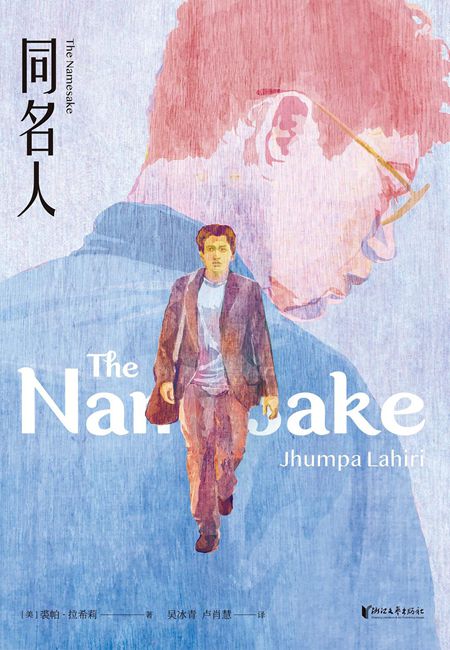
身份與記憶是塑造生命的方式,《同名人》里的果戈理一生中的大多數(shù)時(shí)間都想抹掉父親給予自己的名字,高麗在離開烏達(dá)安和蘇巴什后,重新回到低地。被塑造的也將是被限制的。2012年,裘帕·拉希莉?qū)懲辍兜偷亍泛螅x開美國定居羅馬,她開始學(xué)習(xí)用意大利語寫作。在接受《紐約客》的采訪時(shí),她形容用新的語言寫作“就像把我的右手故意綁在背后,我只能用左手寫作”,“就好像我放棄了我人生中賴以生存的、表達(dá)自我的一種語言,忽然有了另一重空間”。
現(xiàn)實(shí)中的“疾病解說者”將掏空后的自我獻(xiàn)給一種全新的經(jīng)驗(yàn)。在裘帕·拉希莉的這番話里,可以察覺到她那種接近笨拙的真誠,而真誠或許正是她作為寫作者的信條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