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龍訪談錄:中國詩歌英譯的現(xiàn)狀與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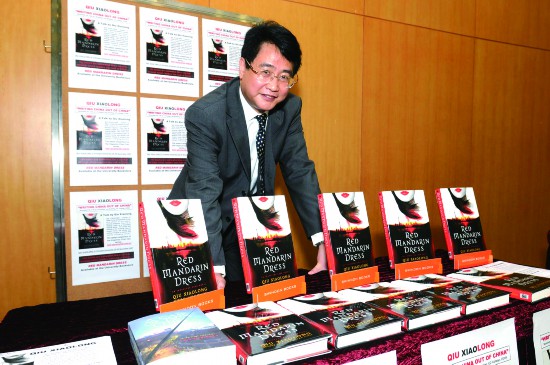
裘小龍
張智中:您在《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學(xué)術(shù)季刊》1989年第1期上刊登的論文《中國古詩與現(xiàn)代主義詩歌在翻譯中的感性交流》,文章提出了“凸顯原詩感性的翻譯原則”,其中的關(guān)鍵詞,就是“感性”。但是,在論文中,您似乎沒有對“感性”做具體解釋。您能詳細(xì)解釋一下關(guān)于漢語詩歌“感性”的概念和定義嗎?
裘小龍:謝謝你找出這么多年前的文章。你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回顧這些年的翻譯“思路歷程”。關(guān)于文中所提到的“感性”(sensibilities),簡單地說,就是一種語言獨特的感受和表達(dá)方式,這涉及語言的深層結(jié)構(gòu),也因此影響、甚至決定這一語言使用者的認(rèn)知過程以及世界觀的形成。詩歌正是把語言的可能性發(fā)掘、發(fā)揮到極致的一種藝術(shù),最能凸顯這一語言所特有的深層文化感性。如果說這些年我這方面的想法有了什么變化的話,或許可以說是在“凸顯原詩感性”的基礎(chǔ)上,又發(fā)展到怎樣“把原詩和譯詩中不同的語言感性凸顯融合在一起”。換句話說,這也是把詩歌與雙語寫作結(jié)合起來的嘗試,翻譯中不僅僅凸顯原文感性這一層面,同時也要像創(chuàng)作一樣,在目標(biāo)語言中也要充分發(fā)掘其感性,從而呈現(xiàn)出混合了不同語言感性的文本。這些年國內(nèi)的翻譯、研究都有長足進展,我想自己這種翻譯/雙語寫作的嘗試,對怎樣把中國文學(xué)、文化真正譯介出去,促進跨文化的理解,或許會有一定的意義。
張智中:您的《中國古詩與現(xiàn)代主義詩歌在翻譯中的感性交流》一文,先談了漢詩英譯,后面又談到了英詩漢譯。您覺得英詩漢譯與漢詩英譯,這兩者之間有著怎樣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對譯者有著怎樣的不同的要求?
裘小龍:我覺得就一般翻譯而言,如果目標(biāo)語言是譯者母語的話,可能會相對容易一些。但無論是英譯漢還是漢譯英,其實是互補的,要能在兩個方面都做些嘗試,對兩種語言不同的感性都會有更直接的感受、理解。至于對不同目標(biāo)語言的譯者有什么具體要求,這讓我想起卞之琳先生給我的第一次研究生作業(yè):寫詩。在他看來,要譯詩、評論詩,最好自己也寫詩,這樣才能真正知道兩種詩歌語言感性中轉(zhuǎn)換的甘苦,得以在其中騰挪自如。這里適用的,自然并不只是詩歌而已。
張智中:您在《中國古詩與現(xiàn)代主義詩歌在翻譯中的感性交流》一文說到,當(dāng)代的文學(xué)交流是多層次的,你也并非主張所有的作品都用“凸顯原詩感性的翻譯”原則去翻譯。既然文學(xué)交流或文學(xué)翻譯是多層次的,是否就意味著同一首漢詩,可以有不同手法的翻譯再現(xiàn)?您是否覺得漢詩英譯存在一些不同的翻譯流派?他們的存在是否合理?
裘小龍:確實,我依然不認(rèn)為有什么可以適用于所有文類的翻譯原則;僅就詩歌而言,也應(yīng)該有不同風(fēng)格、流派的嘗試。同一首中文古典詩,有不同理解、審美、處理的側(cè)重點,這本身說明了詩無達(dá)詁,也是詩歌翻譯的“困難魅力”所在,從而可以進一步互相比較,其實是挺有意義的事。例如格律體的譯詩,如果譯者能得心應(yīng)手地駕馭英語詩歌韻律,不去生搬硬套表面形式而損害詩的意義或意象,或僅僅為了湊韻,把句子寫得七顛八倒、不忍卒讀,格律體譯詩也未嘗不可一試。許多年前,我自己也曾用格律體翻過一本魯迅詩選,現(xiàn)在還能想起來的,就只有兩句似乎還稍工整一些。“How can I be as passionate as of yore? /Let flower bloom or fall, I care no more.”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只是,現(xiàn)代英語中,有多少人還在用of yore呢? 當(dāng)然,自己沒有這份功力,并不意味著其他人在這方面也不行。但如果說我有一個什么自我設(shè)定的標(biāo)準(zhǔn),其實簡單,翻譯的詩在目標(biāo)語言中讀起來也應(yīng)該是詩,而且是當(dāng)代英語讀者讀起來“不隔”的詩。
張智中:在您的英文小說創(chuàng)作、英文詩歌創(chuàng)作與漢詩英譯之間,您覺得這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您的創(chuàng)作與您的翻譯之間,如何互動和影響?您寫詩的狀態(tài)與譯詩的狀態(tài)是否一樣?有何聯(lián)系或區(qū)別?
裘小龍:近20年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在英文小說的寫作上。這與英文詩歌創(chuàng)作以及中詩英譯之間的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也陰錯陽差。我原想寫一本關(guān)于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社會的英文小說,主人公是知識分子,喜歡思考,也喜歡詩歌。但小說卻意外地寫成了偵探小說,主人公也成了一個“思考的探長”,雖然仍喜歡吟詩。只是,他在辦案過程中引用的英文詩,給我的美國編輯刪掉了,因為她說這樣做,要付的“版權(quán)費用太高”。結(jié)果只能在這些空出來的段落中,改用我自己翻譯的中國古典詩詞——早就過了版權(quán)年限,不用付費。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卻也更進一步意識到,在英文小說中放入中國古典詩詞的英譯,必須不影響到一般讀者閱讀的流暢性,就像他們平時讀現(xiàn)當(dāng)代英文詩一樣;與此同時,又必須能讓他們感受到中國古典詩歌的獨特感性和詩意。在小說中寫詩和譯詩,這同時也讓我或多或少有意識地承襲了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個傳統(tǒng),即小說中有詩,使敘事更富有不同的抒情強度,節(jié)奏變化。此外,小說中還有一部分不是譯詩,是我自己借著陳探長名義寫的詩,這樣做也可帶來一個意外好處:仿佛讓我戴上了陳探長的面具,進入了他的“自我”,寫出了我自己原來不會去寫的詩。
張智中:幾十年來,您在漢詩英譯方面的翻譯理念和翻譯原則有無變化?具體情況怎樣?
裘小龍:我在上面提到了在漢詩英譯中翻譯理念和原則的一些變化。因此在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也在從事其他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同時,盡可能多地把有關(guān)中國古典詩歌的譯介融合進去。最近幾年,我更受到了歐美相對語言學(xué)理論的一定影響。按照歐美語言學(xué)家,如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 、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觀點,人們的世界觀是由語言形成的,不同語言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影響、甚至決定了人們的思維、認(rèn)知方式。一種語言文化的獨特感性所凸顯的,正是在另一種語言文化中所難以真正理解的深層組成部分,因此在詩歌翻譯中,不僅僅要凸顯,也要在兩種語言中融合這種異質(zhì),甚至進一步嘗試,怎樣來構(gòu)成一種包含著不同語言感性的文本。最近一段時間,正好有機會來廣西大學(xué)作學(xué)術(shù)訪問,我想就此較深入探討下去。
張智中:當(dāng)下的漢詩英譯,在國內(nèi)似乎風(fēng)生水起,無論是翻譯實踐者還是理論研究者,都人數(shù)眾多,格律派明顯占據(jù)壓倒多數(shù),而且主要是押尾韻。您對于漢詩英譯的用韻怎么看?這是否在英語世界早已是落伍的東西?還是仍有市場?中國譯者的漢詩英譯,在英語世界,比如美國,是否有讀者?情況如何?
裘小龍:我自己寫詩,中文英文都寫。就英美詩歌創(chuàng)作的現(xiàn)狀而言,格律體肯定不是主流。我的朋友摩娜·凡丹 (Mona Van Dunn),美國第一個桂冠女詩人,也是新形式主義流派的領(lǐng)軍人物,就曾對我說過,格律體在英美詩歌界現(xiàn)在已很少有人寫了,對非母語詩人來說更難,力所不及,難免有畫虎不成反類犬之慮。就中國古典詩歌翻譯而言,情況更難、更嚴(yán)峻一些。因為寫格律體,作者可能出于對某個韻的考慮,來這樣或那樣處理一行詩,甚至因為這個韻而寫出一行詩,但譯者卻沒有這樣的自由。原文的意義、意象都不能妄加改動,要湊韻而加字減字,都是不能原諒的。這里恐怕不僅僅是畫虎不成的問題,拉格律大旗作拙劣譯詩的虎皮,其實是更為下者。至少在美國的書店里,人們根本看不到這些中國古典詩詞的“詩體”翻譯譯本,因此難免像有些評論者所說的,成了關(guān)起門來“自娛自樂”的游戲,離向世界介紹中國古典文學(xué)的目標(biāo)背道而馳。問題的另一面自然是,那么用現(xiàn)代英語自由體詩歌形式翻譯的中國古典詩詞,能否傳神地再現(xiàn)原文的意境?我個人認(rèn)為是可能的,尤其是在凸顯原詩感性的基礎(chǔ)上。
張智中:談起漢詩英譯,無論是翻譯實踐者還是理論研究者,往往都指的是中國古典漢語詩歌的英譯。漢語新詩的英譯,似乎比較冷門,您覺得原因何在?
裘小龍:我翻過一些現(xiàn)代中文詩歌。例如我在《洛杉磯時報》上寫過一篇關(guān)于當(dāng)代中國詩人王小龍的評論,同時也譯了他的幾首詩。此外,在小說中我也引用過徐志摩、卞之琳、吳興華等人作品的片段。不過總的來說,現(xiàn)當(dāng)代中國詩歌的翻譯,我確實做得不多。這里有版權(quán)方面的顧慮,也因為這些年太忙了一些。你說的漢語新詩的英譯比較冷門的現(xiàn)象是存在的。不過,你自己在古詩新詩英譯的兩個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這其實相當(dāng)不容易。
張智中:您說過,經(jīng)典作品每過二三十年就應(yīng)該有新的翻譯。在漢詩英譯方面,您的語言觀如何?怎么看待原詩的語言與譯詩的語言?比如,李白的語言顯然不同于李商隱的語言,如果同一個譯者來譯,是否可行?譯者如何調(diào)整自己的語言?是否需要調(diào)整自己的語言?他應(yīng)該采取什么樣的語言策略?
裘小龍:這是有意思的問題。關(guān)于經(jīng)典過二三十年就應(yīng)該有新譯這一點,其實最主要是因為語言本身就一直在更新、演變中,古英語詩歌Beowulf在后來的年代里有多少新的英語譯本不斷問世,就已說明了問題。關(guān)于后一點,在理想的翻譯中,譯者自然應(yīng)該盡可能追求接近原作者的風(fēng)格,但就中國古典詩歌翻譯而言,還真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宋詞中有婉約、豪放之分,但一個詩人可能在自己不同的詩里呈現(xiàn)這兩方面不同的特征,譯者只能落實到具體每一首詩的翻譯。再換一個角度說,如果在目標(biāo)語言中,一首譯詩讀起來甚至都不像詩,不是詩,又怎樣談得上譯詩中去保留不同詩人的語言風(fēng)格呢?
張智中:有人主張,漢譯英最好的翻譯模式,就是中西合璧,最好中國人和外國人結(jié)婚,兩個人合作翻譯,就像楊憲益和戴乃迭、葛浩文和林麗君等。那么,作為單獨的中國譯者,他們是否有希望在漢譯英方面取得成功?他們是否有前景?另外,您覺得中國譯者應(yīng)該向西方譯者學(xué)習(xí)什么?西方譯者的優(yōu)勢和不足之處體現(xiàn)在哪里?
裘小龍:這當(dāng)然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模式,如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合作。事實上,這樣的例子在漢詩英譯中也不在少數(shù)。龐德也是在其他人漢譯的基礎(chǔ)上再翻譯、再創(chuàng)作,同樣取得了成功。這樣合作的模式或許得有一個前提:合作者之間的反復(fù)交流、切磋,在原文本的理解與目標(biāo)文本的處理之間達(dá)到真正統(tǒng)一。要做到這一點,可能并不容易。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譯者一人獨自承擔(dān)的漢譯英工作,并非沒有自己的優(yōu)勢。還是回到龐德的例子,盡管他是個十分出色的詩人,但他并不能真正閱讀中文,因此他的譯詩在對原文意義的把握上,不是沒有欠缺的。也難怪美國的一些文學(xué)選集,把他翻譯的李白的“長干行”列為他自己的詩作。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中國的譯者應(yīng)該能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