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七版:從西方中心論到全球史觀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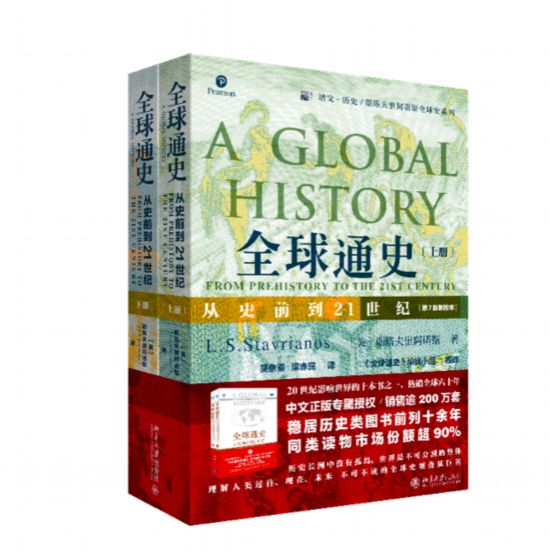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也是“全球史觀”的倡導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出版了《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這部書在全球暢銷2500萬冊,中文簡體版已經銷售600萬冊,并不斷更新再版中,第七版新校本近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全球通史》著眼于人類起源之初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上下數(shù)百萬年間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以及種種事件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與影響。該書將世界歷史視為一個整體,突破“西方中心論”的窠臼,書寫了全球人的全球史。此次新校本是根據(jù)中文版出版十余年來,讀者不斷反饋的意見整合的基礎上,對譯文中出現(xiàn)的錯訛和原著中的疏漏進行修訂后推出的,也是對新時代新史學的回應。
《全球通史》在其中文版出版十余年來修訂七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毅認為,該書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響,主要是因為它用一種讀者喜聞樂見的語言,深入淺出地把人類社會從哪里來,將來又會走向哪里的情況做了一個描述。高毅進一步解釋道,它的讀者在今天來看是頗具貴族氣質的,“在物欲橫流的社會把關注點放在全球社會上,這需要有一點心氣。”
除卻其語言的通俗性與敘述的可讀性,該書所體現(xiàn)的時代感與現(xiàn)實感也賦予了它不同的氣質。在高毅看來,斯塔夫里阿諾斯并沒有一味地把讀者拉向遙遠的過去,而是試圖讓讀者用過去的經驗反觀現(xiàn)實生活中的問題,從而更加清楚自身在時間洪流中的位置,進而認識到在未來我們該為何而繼續(xù)奮斗。
從“全球史觀”眺望“大同世界”
如若將斯塔夫里阿諾斯置于整個西方的學術脈絡中,他留名至今的原因或可部分歸于將歷史學從廟宇和殿堂推向了民間和草根。《全球通史》恰似這樣一扇門,將讀者帶入一個如萬花筒般的世界體系中,上承前代學者之探索,下啟此后的一股浩蕩的“全球史觀”之潮流。
追溯“全球史觀”的淵源,不得不回顧歷史長河中幾個階段的演變。從十八世紀歐洲對中國文化的崇尚,轉至十九世紀工業(yè)革命的完成致使“歐洲中心論”的產生,兩次世界大戰(zhàn)重塑了世界的格局,終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歐洲中心論”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定,歐洲人開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自此開啟了“全球史觀”的路徑。
在如何看待《全球通史》從“西方中心論”向“全球史觀”的轉變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健評價該書在這樣一場轉變中,可謂是率先做出了“壯士斷腕的決心”。
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曹寅則認為,斯塔夫里阿諾斯帶著一種自我批判精神,嘗試從一個中心走向全球視角,這同樣啟示中國讀者在閱讀中不應該通過批判歐洲中心論來加強中國中心,陷入從一個中心到另一個中心的桎梏,而應該對“普世性的中心觀念”保持警醒。
從歷史出發(fā),人類又將要走向何方?《全球通史》中流露出通往“大同世界”的可能性。在高毅看來,所謂的“大同世界”即是一個沒有戰(zhàn)爭、永久和平的世界。這一點在東西方是有共識的,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歐洲也萌生出了類似的向往,幻想中的烏托邦寄托了他們的理想。雖然這一理念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一個愿景式的存在;但是,“即便它是一個烏托邦,那也是大家應該為之奮斗的烏托邦”。
走向聯(lián)系、流動、共享的全球化未來
全球史強調聯(lián)系與共享,而非排他。當今戰(zhàn)爭的本質往往在于身份政治的激化,而《全球通史》中所展現(xiàn)的共享空間,使得讀者具備更為廣闊的世界觀,從而避免陷入這樣的激進之中。
回顧歷史是從另一層面關照現(xiàn)實。從該書的核心觀點出發(fā),曹寅認為今天社會的技術變革與社會變革同樣值得讀者重視。隨著新技術的加入,二十一世紀資本的形式并非工業(yè)資本亦或是殖民時期的資源資本,而是所謂的“監(jiān)控資本”。將人視為一種個體的數(shù)據(jù),每一次不經意間的行動集合構成了關于每個個體獨特的數(shù)據(jù)庫資源,而這與人工智能直接相關,“AI背后邏輯是資本,而資本內置的邏輯是賺錢。”
對于技術變革,在熱情擁抱的同時仍應保持必要的審慎與警醒,從歷史角度打量,尋找支撐,這也是《全球通史》中體現(xiàn)出的價值傾向。
作為一部理解人類歷史過往、現(xiàn)在與未來的經典著作,《全球通史》流露出的時代感與現(xiàn)實感時刻提醒我們認清所生活的現(xiàn)實世界與歷史的內在聯(lián)系,從而使我們的思想能夠跨越時空的限制,看到歷史的傳承性。
閱讀《全球通史》的意義在于,我們只有透過過去,才能看到歷史對今天的啟示,才能看到人類的未來。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每個時代都要編寫它自己的歷史,而每個時代的人也需要閱讀屬于這個時代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