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作者阿特伍德推出續(xù)集《證言》 就像她愛的莎士比亞悲喜劇,荒野的孩子終將找回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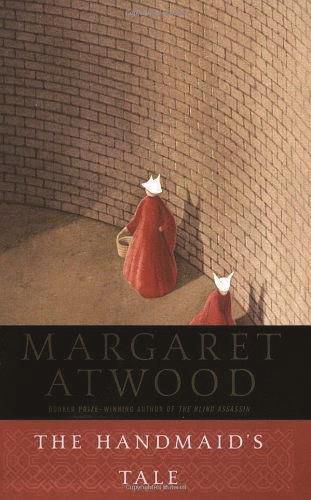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書封。 (出版方供圖)
《使女的故事》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半個月前度過了她的80歲生日。在世俗人們覺得“只能頤養(yǎng)天年”的年紀(jì),這位加拿大老太太給全世界的女人——包括女作家——打了一針強心針:如果你有熱愛的事業(yè),不要過早地放棄,堅持做下去,你到80歲仍然有可能制造出撬動地球的爆款。
蜂擁而至的讀者,見證阿特伍德“出圈”記
今年9月中旬,《使女的故事》小說續(xù)集《證言》在倫敦上市前夜,書迷們和同名劇集的劇迷們蜂擁到皮卡迪利街的水石書店,他們穿戴著故事里使女們的紅袍白帽,等待零點鐘聲敲響時由阿特伍德親自賣出第一本《證言》。滿頭灰白卷發(fā)的阿特伍德站在人群中,如同喚起午夜魔法的巫師。倫敦的書店很久沒有出現(xiàn)這樣的盛景,上一次能達到同等轟動規(guī)模的新書午夜發(fā)售,還是《哈利波特》系列的大結(jié)局。
時間倒推到1985年,《使女的故事》小說出版時,并沒有在書市制造大的反響,作家本人回憶:“只在出版人的小圈子里小小慶祝了一下。”“小小慶祝”是因為這部小說獲得了布克獎提名,可惜最后未能獲獎。此后十年里,阿特伍德又因《貓眼》和《別名格蕾絲》兩獲布克獎提名,但她最終拿到布克獎,要到2000年的《盲刺客》。直到當(dāng)時,阿特伍德的聲譽仍局限于小范圍的知識分子和文學(xué)愛好者中。2000年以后,阿特伍德因《珀涅羅珀記》和《女巫的子孫》兩次進入公眾討論的視野,她從女性主義的視角故事新編地重述了荷馬史詩的《奧德賽》和莎士比亞的《暴風(fēng)雨》。到了2017年前后,她決定續(xù)寫當(dāng)年的《使女的故事》,也就是在這一年,根據(jù)她的《使女的故事》和《別名格蕾絲》改編的兩部劇集先后上映,一夜之間,原作者阿特伍德真正意義上地“出圈”了。
苦難降臨時,女性和孩子總是被迫承受更多
阿特伍德遲來的聲譽未必是影視改編推波助瀾的結(jié)果,至少不全是。英國科幻作家尼爾蓋曼在讀過《證言》之后的這段感言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在我讀《使女的故事》時,曾以為她過分悲觀。時隔30年,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自己過分天真。面對現(xiàn)實,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總是不夠清醒,不夠警惕。”阿特伍德本人接受《衛(wèi)報》采訪時,直接說:“過去的30年里,我們本來有希望遠離‘基列國’,但現(xiàn)在眼看一步步地回去了。”
1984年,阿特伍德在柏林開始構(gòu)思《使女的故事》,那是一個被認為“樂觀的年代”,婦女解放運動在全世界展開,幾代人的持續(xù)抗?fàn)帲瑩Q來社會結(jié)構(gòu)的一點改善,“第二性”逐漸發(fā)出被壓抑的聲音,爭取著被父權(quán)剝奪的權(quán)利。在那樣的大環(huán)境里,阿特伍德敏銳地察覺到始終存在強悍頑固的保守力量,時刻準(zhǔn)備著把女性的身體、聲音和自我意識,一樣樣地重新封鎖到黑匣子里。為此,她寫下了《使女的故事》——如果在北美,存在著一個威權(quán)運作的政治體,權(quán)力對“人”的征用,最顯見也最終極的表現(xiàn),是對女性的物化和工具化。
《使女的故事》上承《可以吃的女人》,后接《別名格蕾絲》和《盲刺客》,阿特伍德在寫作中堅持一條明確的信念:為什么要從女性的視角出發(fā)?為什么女性處在風(fēng)暴的中心?因為苦難降臨時,作為弱勢者的女性和孩子,總是被迫承受了更多。
嚴酷和希望、毀滅和新生的復(fù)調(diào)貫穿全書
阿特伍德拒絕認為“基列國”是想象的產(chǎn)物,她說:“即便我創(chuàng)造一個想象的花園,那里面一草一木連帶一只烏龜都是真的。《使女》故事里的所有細節(jié),來自清教徒時期的北美,我是把真實發(fā)生過的事件重新排列組合了。”
《使女》聚焦的是在殘酷的、非人的環(huán)境里,個體怎樣活下去。“活著”可能是奧弗瑞德那樣向善的、向著明亮方向的掙扎,也可能是莉迪亞嬤嬤那樣,來自弱勢一方卻成為強權(quán)者的幫兇。“生存”的命題延續(xù)在《證言》中,在這個故事里,莉迪亞嬤嬤的聲音清晰起來。小說標(biāo)題“證言”,其實也是莉迪亞嬤嬤的遺囑,在這個多聲部的文本里,莉迪亞的聲音指向過去,她的聲音成為基列國土崩瓦解時凄厲的背景音。阿特伍德認為,莉迪亞嬤嬤的意義在于她提供了內(nèi)部洞察的視角,她把這個角色定義為“女版的克倫威爾”“一個被權(quán)力吞噬的人”。莉迪亞是一個被厭棄的反面角色,一個同流合污者,但也恰恰在她身上,阿特伍德把普通人從受難者走向加害者的過程透明化了。
阿特伍德的寫作,既是出于對現(xiàn)實的洞察,所以她從莉迪亞嬤嬤的視角呈現(xiàn)了系統(tǒng)的崩潰;但同時,恰似奧弗瑞德留下的聲音,“敘述”也可以是一種寄托著希望的行動。于是,在《證言》里,少女阿涅斯和黛西的聲音是和莉迪亞平行展開的聲部,阿涅斯成長于瓦解前的基列國,黛西是在襁褓中隨母親逃到了加拿大。嚴酷和希望、毀滅和新生的復(fù)調(diào)貫穿了整本小說,男權(quán)和女性的對峙逐漸退隱到背景中,前景中清晰的是少女的出走和回歸,很多時候,這個故事就像阿特伍德鐘愛的莎士比亞晚期悲喜劇,它幾乎是帶著童話色彩的——荒野的孩子終將找回家園。
也許是年邁讓作家變成了布道者,但也正像她形容的,站在迷宮路口的人類仍然是有選擇權(quán)的,也許打開對的那扇門,門后就有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