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xué)是怎樣煉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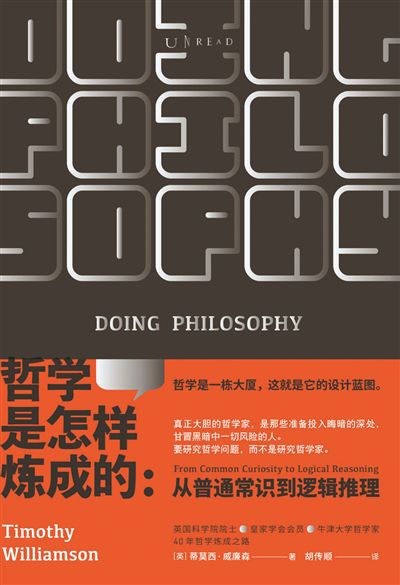
作者:[英]蒂莫西·威廉森 譯者:胡傳順 出版:未讀·思想家 |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上市時間:2019年11月
所有的學(xué)科都是從人類最初的好奇開始的,哲學(xué)思考的種子也誕生于每個普通人的好奇。我們從常識中逐漸推理出了各學(xué)科的精密體系,也建造出了人類的哲學(xué)大廈。英國牛津大學(xué)哲學(xué)博士蒂莫西·威廉森教授的《哲學(xué)是怎樣煉成的》近日由“未讀”出版,書中,作者向我們展示了這座由科學(xué)哲學(xué)、分析哲學(xué)、數(shù)學(xué)哲學(xué)、語言哲學(xué)、形而上學(xué)、邏輯學(xué)等學(xué)科鋪展出來的設(shè)計藍(lán)圖。跟隨作者的思考,我們會推翻自己對科學(xué)與哲學(xué)關(guān)系的刻板印象,會認(rèn)識到哲學(xué)是用什么工具讓人們從業(yè)余走向?qū)I(yè),從興趣走向?qū)τ篮闩c無盡的思考。
哲學(xué),起源于驚異,致力于未確定之一切。在它之下,誕生了數(shù)學(xué)、天文學(xué)、心理學(xué)……但仍有無數(shù)人問哲學(xué)有什么用?我們學(xué)習(xí)和研究哲學(xué)有什么意義?一談起用處,人們的第一反應(yīng)就是那種可以立竿見影的,最好還能夠兌換成金錢的用處。所以一點(diǎn)都不奇怪,在一般人的眼里,哲學(xué)壓根就沒有什么用。
其實哲學(xué)并非如此。蒂莫西·威廉森教授還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讓-皮埃爾·里夫是橄欖球聯(lián)合會的傳奇人物,是偉大的法國橄欖球國家隊1978—1984年間的隊長。在一次新聞采訪中,他談到了他對戰(zhàn)術(shù)的思考:關(guān)鍵在于,對你要試圖獲得的東西保有一個清楚和明白的觀念;然后,你應(yīng)該把每一個復(fù)雜的動作分解為最簡單的組成部分,讓它們易于直觀,再從此處返回以建構(gòu)整體。里夫雖然沒有點(diǎn)出法國標(biāo)簽式的哲學(xué)家笛卡爾的名字,但他遵從了笛卡爾對清楚和明白這兩個標(biāo)語的需求和強(qiáng)調(diào),也遵從了他的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導(dǎo)原則》中的原則之一。法國的學(xué)校教授哲學(xué)課程,這讓哲學(xué)有了意料之外的用途。
這個案例說明,哲學(xué)并不是某種完全與我們不相容的東西;它已經(jīng)以各種瑣碎和重要的方式深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
如果你走進(jìn)一所大學(xué)的哲學(xué)系,不久你就會發(fā)現(xiàn),在某處,或者說大部分地方,正在有許多哲學(xué)史課程被教授。與之相反,在數(shù)學(xué)系或者自然科學(xué)系,就很少甚至沒有數(shù)學(xué)史或自然科學(xué)史課程被教授。偶爾,數(shù)學(xué)家或科學(xué)家的名字與他們的發(fā)現(xiàn)聯(lián)系在一起,但是,學(xué)生們并不期待知曉他們是如何得出這些成果的。學(xué)生們也很少去閱讀他們的原始著作,因為,在原始著作中,這些結(jié)論很可能難以辨別,對于閱讀者是陌生的見解和語言。而與此同時,哲學(xué)系的學(xué)生卻必須閱讀已經(jīng)死去很久的偉大哲學(xué)家們的著作,或者是其中的大部頭,至少也得閱讀譯本。哲學(xué)與其過去的關(guān)系似乎不同于數(shù)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與其過去的關(guān)系。
很少有哲學(xué)家愿意把哲學(xué)史放到歷史學(xué)系。當(dāng)過去的哲學(xué)家在歷史學(xué)系被研究時,被稱為“觀念史”。“觀念史”更多關(guān)注的是哲學(xué)家們的生活:他們的社會、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背景和約束;他們成長、寫作、教育的環(huán)境;他們讀了什么以及誰影響了他們;他們認(rèn)為理所當(dāng)然的東西和他們所反對的東西;他們?yōu)檎l寫作;他們的著作在當(dāng)時意圖具有的或?qū)嶋H上具有的影響等等。當(dāng)同樣的哲學(xué)家在哲學(xué)系被研究時,被稱為“哲學(xué)史”。哲學(xué)史主要聚焦于他們的研究本身,而不是其與那個時代周遭環(huán)境的相互關(guān)系。這一目的就是要把內(nèi)容理解為一種鮮活的、一貫性的思想體系,它對今天的我們?nèi)匀挥幸饬x。
哲學(xué)史是哲學(xué)的一部分。然而,將一個理論當(dāng)作是某個哲學(xué)家提出的,和將一個理論當(dāng)成是真理,這兩者之間是有區(qū)別的。就學(xué)術(shù)上而言,哲學(xué)史學(xué)家通常很清楚這種區(qū)別:他們追問的是,這位哲學(xué)家堅持的是什么理論,而不是什么理論是真理。不幸的是,還有另一種廣泛存在的哲學(xué)寫作方式,它模糊了這條界限。一些令人高山仰止的思想家,例如,偉大的德國哲學(xué)家伊曼努爾·康德,他通常都會這樣撰寫著作。當(dāng)你讀到“我們不可能認(rèn)識物自體”時,你不清楚作者是否只是在主張康德認(rèn)為我們不可能認(rèn)識物自體,還是作者以自己的話語主張我們不可能認(rèn)識物自體,而實際上正支持康德的觀點(diǎn)。混淆這兩種主張在辯護(hù)上是實用的,因為它使作者能夠把針對第一種主張的批評斥為沒有抓住第二種主張的關(guān)鍵點(diǎn),把針對第二種主張的批評斥為沒有抓住第一種主張的關(guān)鍵點(diǎn)。如果你論證,它作為歷史是錯誤的,回應(yīng)就是要討論事情本身。相反地,如果你論證它作為哲學(xué)是錯誤的,回應(yīng)就是要討論康德。通常情況下,諸如此類的寫作方式既不是好的歷史學(xué),也不是好的哲學(xué)。
有一種觀點(diǎn)是,哲學(xué)就是哲學(xué)的歷史,因為除此之外,它沒有什么其他的東西。這個觀點(diǎn)具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歐洲大陸地區(qū),不過,現(xiàn)在這個觀點(diǎn)正在逐漸失去它的土壤。我的一位朋友,一位意大利的哲學(xué)家,于20世紀(jì)70年代后期第一次參訪牛津大學(xué)。她發(fā)現(xiàn)這里的人們?nèi)匀辉谠噲D解決哲學(xué)問題,這是多么的天真可愛。她解釋到,她是在這樣一種哲學(xué)文化中受到教育的,這種文化理所當(dāng)然地認(rèn)為根本不同的體系之間沒有以之為基礎(chǔ)從而作出決斷的共同根基。根據(jù)這個觀點(diǎn),我們不可能富含深意地追問,它們之中的哪一種客觀上是正確的。我們只能在一種歷史上給定的體系或另一種體系范圍內(nèi)進(jìn)行思考,即使當(dāng)我們試圖從體系內(nèi)部來顛覆它時。有時我被問到,我研究哪位哲學(xué)家,好像這是任何一位哲學(xué)家都必須做的。我以牛津的風(fēng)格回復(fù):我研究哲學(xué)問題,而不研究哲學(xué)家。
哲學(xué)就是哲學(xué)的歷史這個觀點(diǎn)是在自掘墳?zāi)梗旧砭褪且粋€有爭議的哲學(xué)選項,我們沒有義務(wù)必須接受它。它沒有證據(jù)的支持。在哲學(xué)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哲學(xué)家,如本書提到的那些哲學(xué)家,是自己寫哲學(xué)史的。他們的目標(biāo)并不是解釋其他哲學(xué)家的理論,或者甚至是他們自己的理論,而是首先建構(gòu)這樣的理論。例如,關(guān)于心靈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這與科學(xué)理論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這同樣適用于今天仍然在發(fā)展的大部分哲學(xué)理論。而且,如同我們已經(jīng)看到的,有很多在諸種理論之間進(jìn)行合理決斷的方法。把哲學(xué)與哲學(xué)史看成是一樣的,這是一種及其不歷史的態(tài)度,因為它違背了歷史本身。雖然研究一個哲學(xué)問題的歷史(例如自由意志)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一種方式,但還有許多研究問題的方式并不是研究其歷史,正如對數(shù)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問題的研究,就典型的不是研究它的歷史。幸運(yùn)的是,哲學(xué)史可以被研究,但并不是以讓它接管整個哲學(xué)的帝國主義的野心來研究。
當(dāng)我們意識到那個地區(qū)的人已經(jīng)忍受了長期人權(quán)濫用的歷史時,哲學(xué)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能這么做,是因為我們有人權(quán)的觀念。哲學(xué)家則在這個觀念的發(fā)展中起到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在笛卡爾同時期,還有著名的胡戈·格勞秀斯、約翰·洛克,以及其他哲學(xué)家。
哲學(xué)并不是某種完全與我們不相容的東西;它已經(jīng)以各種瑣碎和重要的方式深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但哲學(xué)究竟是什么?哲學(xué)家又在試圖獲得什么?
傳統(tǒng)意義上,哲學(xué)家以一種非常普遍的方式想要理解每個事物的本質(zhì):存在與非存在、可能性與必然性;常識的世界、自然科學(xué)的世界、數(shù)學(xué)的世界;部分與整體、空間與時間、原因與結(jié)果、心靈與物質(zhì)。他們想要理解我們的理解能力本身:知識與無知、信仰與懷疑、表象與現(xiàn)實、真理與謬誤、思維與語言、理性與情感。他們想要理解和判斷我們與這種理解能力是什么關(guān)系:行為與意圖、手段與目的、善與惡、正確與錯誤、事實與價值、快樂與痛苦、美與丑、生與死,以及更多。哲學(xué)極具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