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復(fù)興:重讀朗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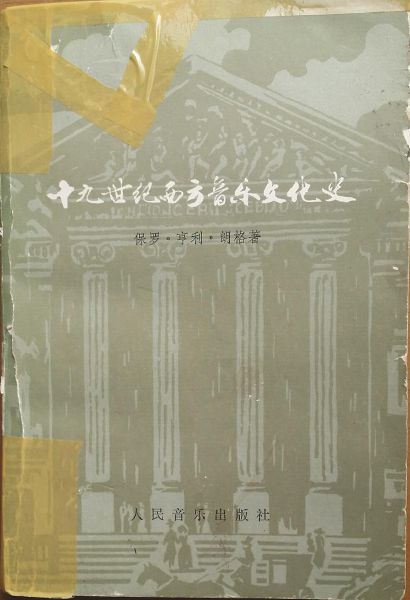
朗格著《十九世紀(jì)西方音樂文化史》,一九八二年版
最近,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要將我的《音樂欣賞十五講》重版,要求在書中的每一條注釋后面添加引文的頁碼。這是2003年出版的一本舊書,當(dāng)初是作為通識講座的一種,我并非學(xué)音樂的專業(yè)出身,勉為其難,倉促上陣,書寫得很不規(guī)范。如今,16年過去了,重新找回當(dāng)年曾經(jīng)查閱過的那些書籍,猶如重拾舊夢,真非易事。
讓我意外的是,那些書大多數(shù)是當(dāng)年自己買的,居然都還在書架上,雖已經(jīng)塵埋網(wǎng)封,卻并未相離相棄。重新翻閱舊書,如同老友重逢,別有一番滋味。發(fā)現(xiàn)其中引用最多的是一本叫作《十九世紀(jì)西方音樂文化史》的書。想起這本書是上世紀(jì)90年代初,在琉璃廠榮寶齋對面不遠(yuǎn)的一家專門賣音樂書籍的書店買到的。這家書店很小,被左右兩家店鋪擠在中間,像一塊茯苓夾餅。但是,它里面銷售的有關(guān)音樂的書籍不少,這是我買到的其中一本。
這是一本1982年的舊書,作者是保羅·亨利·朗格,譯者張洪島。說老實(shí)話,當(dāng)時(shí)見識所限,我并不知道這本書,也沒聽說過這本書的作者朗格和譯者張洪島,是書名吸引了我,讓我毫不猶豫地買下它。它靜靜地躺在書架上已經(jīng)有幾十年的光景,紙頁粗糙,業(yè)已發(fā)黃,定價(jià)只要二元一角。現(xiàn)在想來,真是恍然如夢。如今,為添加注釋頁碼,不由得重新翻看這本已經(jīng)破損封面和被水浸濕印漬斑斑的書頁,依然興趣盎然,還有新的收獲,不禁想起桑塔格說過的話:最有價(jià)值的閱讀是重讀。
這本書的原名為《西方文明中的音樂》(《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原書一共20章,《十九世紀(jì)西方音樂文化史》翻譯的是原書的最后六章。集中在19世紀(jì)。書名起得比原書名要好,將朗格以文學(xué)和文化為背景和底色書寫音樂史的特點(diǎn)彰顯。起碼對于我這樣一般的音樂愛好者,這樣截取的斷代史,比從猿到人的寫法,顯得更接近,更親切。21世紀(jì)之后,我國出版過這本書的全本,書名恢復(fù)原名《西方文明中的音樂》,但是,不如這本舊書影響大。
這本書囊括19世紀(jì)幾乎所有歐洲重要的音樂家,論述了浪漫主義時(shí)期從發(fā)生到鼎盛到衰微的全過程。對于這些耳熟能詳?shù)囊魳芳遥矢窦日摷八麄兊淖髌罚植秽笥谧髌罚欠旁诖蟮臍v史與文化背景下進(jìn)行比較,在前后發(fā)展鏈中進(jìn)行考察,其褒貶臧否,顯得格外舉重若輕,很多地方頗有見地,而不是一般的音樂鑒賞辭典,也不是學(xué)究式的學(xué)術(shù)術(shù)語的列陣馳騁。對比一些音樂史,如《牛津音樂史》或朗多爾米的《西方音樂史》等書,朗格的這本書,更為吸引我。
他批評柏遼茲,一針見血,毫無扭捏:“缺乏對于精神事物的理解,他沒有沉思冥想的能力……他的管弦樂隊(duì)沒有一刻停歇。它經(jīng)常在變動,從這一種色彩到另一種色彩,有時(shí)清澈而優(yōu)美,有時(shí)則粗糙而庸俗。”
對于大名鼎鼎的李斯特,他說:“進(jìn)行著鋼琴家,作曲家,指揮家,技師,哲學(xué)家,音樂學(xué)院院長以及僧侶等多種活動;所有這一切都妨礙了他的藝術(shù)達(dá)到成熟所需要的平靜。因此,他的作品是不平衡的,偉大的作品很容易為許多應(yīng)時(shí)之作所掩蓋。”這樣的批評,至今依然具有現(xiàn)實(shí)的警醒之意。
也有表揚(yáng),比如他高度評價(jià)瓦格納,說他的作品“是一種劇院的語言,它不適宜狹小的場所,它是一個(gè)民族的聲音,日耳曼民族的聲音”。
他說德彪西的“音樂反映了世紀(jì)轉(zhuǎn)折時(shí)期的過度敏感、坐臥不安、心慌意亂的分裂的精神狀態(tài),但是它卻擺脫了那個(gè)時(shí)代所激起的強(qiáng)烈的情熱,淚汪汪的多愁善感和嘈雜的自然主義”。
前者,他著重于瓦格納音樂的民族地位;后者,他著重于德彪西對浪漫主義晚期藝術(shù)弊端揭竿而起的意義。朗格說得都高屋建瓴,頗有撥云見日的感覺,而不糾纏一般的作品演繹。
最有意思的,也是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對于19世紀(jì)音樂兩位保守派的評論。一位是布魯克納,朗格開門見山指出其是一個(gè)矛盾體:“布魯克納的藝術(shù)是紀(jì)念碑式的,但又是墨守成規(guī)的……嚴(yán)肅但又樸素,深幸但又常常是不幸的。”他進(jìn)一步分析集中在布魯克納身上和作品中的這種矛盾的價(jià)值和意義:“像他這樣完全不合時(shí)代的藝術(shù)家是少見的,但是像他這樣集中地反映了其時(shí)代的善與惡的藝術(shù)家也同樣是少見的……他試圖清除浪漫主義強(qiáng)加在音樂上的音樂以外的文學(xué)成分。”我見識淺陋,沒有見過曾經(jīng)有人這樣剖析布魯克納的。
另一位是勃拉姆斯,朗格極其肯定地說:“這位浪漫主義最后階段的大音樂家,是在舒伯特之后最接近古典時(shí)期諸音樂家精神的。他的藝術(shù)像成熟的果子,圓圓的,味甜而有芳香。誰想到甜桃會有苦核心呢?寫下《德意志安魂曲》的這位作曲家看到了這偉大的悲劇——音樂的危機(jī)。他聽到當(dāng)代的進(jìn)步人士的激昂的口號‘向前看,忘掉過去’,而他卻變成一個(gè)歌唱過去的歌手;也許他相信通過歌唱過去,可以為未來服務(wù)。”唯新是舉,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都是有誘惑力的;而“向前看,忘掉過去”的口號,對于我們更不會陌生。從這樣兩個(gè)方面,朗格強(qiáng)調(diào)了勃拉姆斯的意義,今天重讀,并不過時(shí),仿佛是朗格貼近我們的耳語。
重讀朗格,不僅讓我重溫19世紀(jì)歐洲音樂史,也讓我重新審視和面對如今的音樂和包括文學(xué)在內(nèi)的一切當(dāng)下的藝術(shù),期冀我們擁有更多對于藝術(shù)純潔而熱情的信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