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與詞語》:只有書與我們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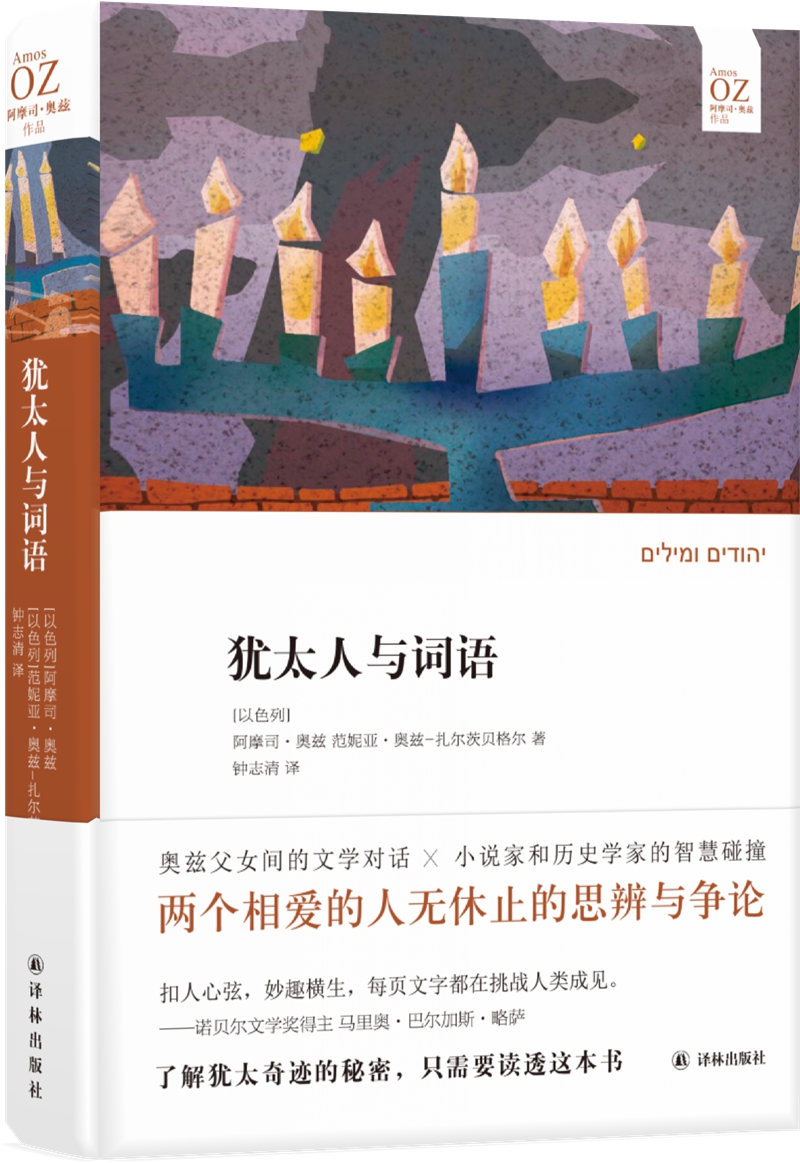
最初承諾翻譯《猶太人與詞語》是在2016年6月,當時奧茲應邀前來中國人民大學領獎,假道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參加《鄉(xiāng)村生活圖景》首發(fā)式。晚宴間,他提到與女兒合寫的這本書,譯林出版社當場拍板購買版權,而我再次責無旁貸,答應翻譯。星移斗轉,這幾年因為科研壓力大,翻譯相對做得少了。2018年11月,我忽然收到奧茲郵件說他的女兒、海法大學的范妮亞教授要來中國開會,希望屆時能看到此書的中譯本,我因此意識到此書的翻譯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了。世事難料,2018年12月28日奧茲竟然撒手人寰。我在哀痛與負疚中向奧茲家人承諾盡快將此書翻譯成中文,并與出版社商定力爭在范妮亞教授來中國時將此書付梓。
不料想,就在奧茲逝世十天后,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與我相依為命數(shù)十年的母親猝然離世。由此我步入人生中最艱難的一段歲月。每位經歷喪母之痛的人都會理解,那是一種永遠無法化解的痛,痛失,痛悔,痛悼,痛徹心扉。終日伴隨我的是無數(shù)個如果與假設,以及她臨終前的話語與身影。別說翻譯,就連每天堅持吃飯、起居、生活都需要巨大的恒心與努力。是親人、朋友與師長各種方式的關愛與慰藉: 陪伴、探望、電話、書信、交談等,讓我逐漸感受到在這個世界上,我不是孤零零一個人,我還有許多未竟之事需要完成,那樣才算對母親有個交代,才可以慰藉她的在天之靈。逐漸,我選擇了堅強面對,從不能自持到每天能翻譯幾十字、幾百字、上千字,最后數(shù)千字。直到3月底完成了一件可以說不可能為之的事,一部將近十一萬字的譯文初稿。而后便是每天三個時段的校譯。
回想這三個月來的生命歷程,是《猶太人與詞語》一書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我,讓我在文字轉換中慢慢平靜下來,用文字寄托對奧茲、對母親刻骨銘心的紀念。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力量左右著人生與機緣,這是二十年前在翻譯《我的米海爾》時寫下的文字,如今這種感覺更甚。2017年初夏,去耶路撒冷寧靜之居(Mishkenot Shaananim)會議中心開會時,奧茲悉心安排我和他的女兒范妮亞教授見面。2018年至2019年嚴冬,我們在十天當中成了一對沉浸在喪親之痛中的姐妹。在這個生命中的特殊時刻,我們相互致哀,在相同的悲傷中以只有孤兒才能理解的深沉與親密相互理解(范妮亞 語),相互攙扶,患難與共。這部譯作見證了我們的姐妹情誼與心路歷程。
必須要說的是,本書是一部文化隨筆,既不能像翻譯純文學作品那樣保持原作的句式與詞法,因為許多極其復雜、在思想與文法上均十分雜糅的句子確實難以轉換;也不能像翻譯純學術著作那樣一板一眼,因為奧茲父女經常使用幽默、調侃甚至抒情的口吻。也許,這便是奧茲父女在《猶太人與詞語》結尾時所說的“語言不可譯”。我們只能盡力為之。很感謝譯林出版社的合作伙伴。姚燚在受傷之際,忍受病痛操勞本書的出版細節(jié)和范妮亞訪華的具體事宜。彭波更是事無巨細,悉心校對原文,對文本中不符合中國讀者習慣之處進行編輯與個別刪節(jié),付出了極大心血。尤其是那句“鐘老師,盡管時間緊迫,我還是希望能把這本書做好”,讓我感受到一位年輕編輯對出版事業(yè)的執(zhí)著與熱忱。感謝幾任譯林出版社的領導,尤其是顧愛彬先生,在過去二十多年里執(zhí)著地支持出版奧茲。而以后,永遠離開這個世界的奧茲不會再寫作品了,因此出版奧茲中譯新作的機會愈加珍貴。無論是編輯還是我,都會珍惜這樣的機會。
最后,僅以此書,獻給偉大的以色列作家奧茲,我在以色列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位謙和的師長、重要的引路人和出色的合作者。獻給我親愛的母親,那位把我?guī)У竭@個世界、培養(yǎng)我能用文字為溝通這個世界上的兩個古老文明略盡綿薄之力的堅韌女性。獻給所有幫我度過艱難歲月的人。
本文是《猶太人與詞語》的譯后記,題目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