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洛威爾:我自身便是座地獄,此處空無(wú)一人
只有臭鼬,在月光下
搜索著一口食物,
它們闊步行進(jìn)在大街上:
白條紋,狂亂眼神中的鮮紅火光
在三一教堂那白堊色、干燥的
圓柱尖塔下面。
我站在我們
后踏板頂部,吸入那濃烈的臭氣——
一只母臭鼬帶著一群幼崽在垃圾桶里大吃大喝。
它把楔形腦袋插入
一只酸乳酪,垂下鴕鳥般的尾巴,
毫無(wú)畏懼。
——節(jié)選自羅伯特·洛威爾《臭鼬時(shí)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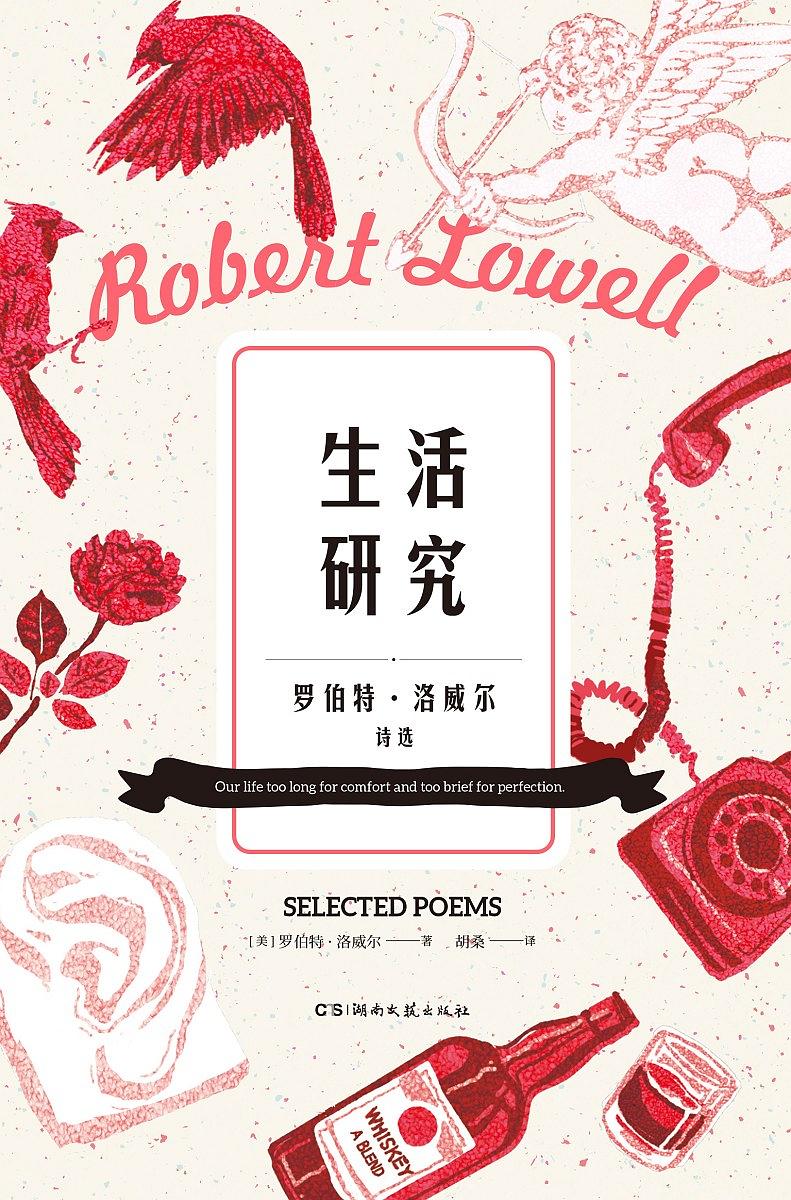
《生活研究》 (美)羅伯特·洛威爾 著 胡桑 譯 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9年10月
為什么只有臭鼬
這首《臭鼬時(shí)光》意義非凡,它是美國(guó)詩(shī)人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 1917-1977)的代表作,也是自白派詩(shī)歌的里程碑作品。
原詩(shī)有八節(jié),因篇幅關(guān)系,本文只引述了最后兩節(jié)。這部分的寫作,很有畫面感。月光之下,一群臭鼬,在大街上,闊步行進(jìn),搜索食物,在垃圾桶里大吃大喝。發(fā)生在三一教堂的圓柱尖塔下面的這場(chǎng)狂歡盛宴,本質(zhì)上是僭越,是反對(duì)宗教的,詩(shī)人歌詠的對(duì)象,是母性的愛與無(wú)畏,為了生存,母親帶領(lǐng)她的子女,向陌異的世界發(fā)起了挑戰(zhàn)。
兩段十二行,傳達(dá)了激昂的情感,讓人顫栗,讓人不安。讀整首詩(shī),回顧前面六節(jié),會(huì)有更深的體會(huì)。臭鼬是在最后出場(chǎng)的,之前的都是什么呢?從“鸚鵡螺島上的隱士/女繼承人在簡(jiǎn)樸的屋子里度過冬天依然存活下來(lái)”講起,詩(shī)歌描述破敗的、衰朽的人境。“這季節(jié)病了——我們失去了夏日的百萬(wàn)富翁”,古玩店裝飾家販賣著無(wú)用的商品,“他勞作,卻身無(wú)分文,他不如去結(jié)婚”,“我的都鐸福特車攀爬在山的顱巔”,望下去,“車身緊挨車身,仿佛墳場(chǎng)疊在城鎮(zhèn)上面”,車中的收音機(jī)在怨訴著,而“我”覺得“我”的手仿佛卡在了喉嚨……
縱使物質(zhì)富有,孤獨(dú)無(wú)邊無(wú)際,城市被棄在身后。詩(shī)人嘆息道:“我自身便是座地獄,此處空無(wú)一人”。他人即地獄。前面六節(jié)的主體是人類,最后兩節(jié)是臭鼬。心靈的荒涼凄寂與精神的勃?jiǎng)踊顫姡纬闪缩r明的對(duì)比。臭鼬,唯有臭鼬,以生的斗志與健康的欲望,行進(jìn)在空曠的大街上,成群結(jié)隊(duì),彼此信任,沖破了枷鎖,獲得了自由。
《臭鼬時(shí)光》是羅伯特·洛威爾的詩(shī)集《生活研究》的壓軸之作。這部詩(shī)集寫于1954-1959年。在這期間,洛威爾的生活發(fā)生了很多改變:1950年父親去世,1954年母親也離世了。重視親情的洛威爾在1952年和1954年先后兩次患上抑郁癥。在1957年,洛威爾成為父親,新的家庭與情感連接,撫慰了他的憂傷,也讓他有了新的體悟。洛威爾開始回望家族的經(jīng)歷,反思為人父母的職責(zé),審視個(gè)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的邊界。
洛威爾詩(shī)風(fēng)的轉(zhuǎn)變
浦睿文化的這部《生活研究》,不是洛威爾同名詩(shī)集的全集中譯,而是從《生活研究》(1959)《威利老爺?shù)某潜ぁ罚?946)到《日復(fù)一日》(1977)《最后的詩(shī)》(1977)等十部詩(shī)集的精選,主要是中晚期作品。洛威爾的早期與中晚期詩(shī)風(fēng)有很大差異。
謝默斯·希尼說過:“如果有一個(gè)術(shù)語(yǔ)可以用來(lái)形容開始于火成而終止于沉積的過程,則這個(gè)術(shù)語(yǔ)就很適合形容羅伯特·洛威爾的詩(shī)歌。”從前的洛威爾是一頭不馴服的公牛。他在1943年因拒服兵役而坐牢,這起事件讓他被符號(hào)化,也讓他的詩(shī)歌與政治結(jié)緣。作為帶著抱負(fù)卻被社會(huì)辜負(fù)的年輕人,洛威爾嚴(yán)厲批評(píng)他的國(guó)家,把噴火的憤怒訴諸于筆端。
《威利老爺?shù)某潜ぁ罚?946)是洛威爾的早期詩(shī)集。選了六首。來(lái)讀《圣嬰》。它化用了《馬太福音》里的故事。希律王為殺死嬰童耶穌,屠殺了伯利恒城的嬰孩。“希律王尖叫著,向正在空中嗆咳的/耶穌那蜷曲的膝蓋復(fù)仇。”詩(shī)歌象征意義明確,節(jié)奏短促有力,激情充沛。權(quán)威的《黨派評(píng)論》評(píng)價(jià):“他(洛威爾)的世界就是我們的世界——政治的、經(jīng)濟(jì)的和謀殺的世界——被殘酷地堅(jiān)持寫下去,而我們一切新鮮而蒼白的希望卻消失了,希望的位置被盲目而血腥的天堂所代替了。”隨著1945年戰(zhàn)爭(zhēng)的結(jié)束,壓抑的情感尋找釋放的渠道。詩(shī)人站在廢墟之上,用詩(shī)歌吶喊,用詩(shī)歌控訴。
或者,極力反對(duì)的往往恰是因?yàn)闊釔郏钥隙〞?huì)失望。洛威爾漸漸轉(zhuǎn)向更私密的內(nèi)心探索。《生活研究》就是在這種情境下誕生的。
《臭鼬時(shí)光》有之前的風(fēng)格遺痕,但已不是抗議的口吻,追索個(gè)體的存在意義。《丹巴頓》追溯家族起源,“我外祖父發(fā)現(xiàn)/他外孫大霧籠罩的孤獨(dú)/比人類社會(huì)更甜蜜。”在這里,祖先曾經(jīng)參與獨(dú)立戰(zhàn)爭(zhēng);在這里,祖先曾經(jīng)非法自制紅葡萄酒,“甜得就像裝在蠟封/平底玻璃杯里的葡萄果凍”;在這里,家族的墓地埋下時(shí)代的遺骨。洛威爾寫著《父親的臥室》,寫著《高燒時(shí)》躺在嬰兒床上的小女兒,寫著《男人與妻子》,寫著《“談及婚姻時(shí)的煩惱”》……這些詩(shī)歌有我們熟悉的家庭場(chǎng)景和生活細(xì)節(jié),普通人的歡喜與煩惱,是一個(gè)人的生活自白。在詩(shī)風(fēng)上,更加接近日常用語(yǔ),更強(qiáng)調(diào)心理的真實(shí)表達(dá),自由隨意,開放不隱晦。
評(píng)論家羅伯特·霍爾伯格說,洛威爾取得了兩項(xiàng)成功:《威利老爺?shù)某潜ぁ泛汀渡钛芯俊贰杀緯牟煌c(diǎn),特別是風(fēng)格的差異,意味著整體知識(shí)文化的情趣和情感的劃時(shí)代的轉(zhuǎn)變。1946年恪守格律,1959年寬松的格律、自由詩(shī),甚至散文;1946年華麗的宗教狂熱,1959年溫雅世俗的自傳。在從前,洛威爾以對(duì)有意義的歷史性變化抱希望的啟示錄式空想家的身份創(chuàng)作,而《生活研究》的作者一掃往昔的信念:一首重要的詩(shī),為誰(shuí)而作?
自白,向著內(nèi)心的追問
洛威爾的轉(zhuǎn)型,提出了一個(gè)問題,即詩(shī)歌的功能。《生活研究》因此格外重要。在它的推動(dòng)下,“自白派”蔚為潮流。
譯者胡桑在譯后記里,起筆就開列了一個(gè)長(zhǎng)名單。美國(guó)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那些最為耀眼的詩(shī)人:洛威爾、畢肖普、普拉斯、金斯堡、默溫……他們共同發(fā)動(dòng)了對(duì)艾略特及由新批評(píng)派倡導(dǎo)的那種冷峻、晦澀、玄秘的學(xué)院風(fēng)格的反叛。這一代的詩(shī)歌不斷書寫個(gè)人的經(jīng)歷,披露私人化的隱秘情感,掀動(dòng)被壓抑的心靈的絕望反擊,他們毫不忌諱地談?wù)撃切﹤鹘y(tǒng)詩(shī)歌回避的主題,比如離婚、流產(chǎn)、藥物、性、精神的疾病、自殺的沖動(dòng),等等。這些詩(shī)歌與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的社會(huì)思潮相結(jié)合,反映了戰(zhàn)后中產(chǎn)階層的藝術(shù)觀和生活觀,徹底摧毀了高雅嚴(yán)肅文學(xué)規(guī)矩得體、正派嚴(yán)謹(jǐn)?shù)臏?zhǔn)則,一意追求個(gè)性的解放。
洛威爾是“自白派”的開風(fēng)氣者,也是其中成就最大的詩(shī)人之一。在《生活研究》之后,直至1977年逝世,洛威爾一直繼續(xù)他的“生活研究”。
洛威爾經(jīng)歷了三次婚姻,《在大洋附近》(為E.H.L而作)描摹“最后的激情/透過她的肉身震顫。英雄站立……”,甚至還出現(xiàn)了對(duì)經(jīng)血的描寫。《初戀》與《一九三〇年代》系列作品,回憶少年時(shí)代的激烈青春,“后來(lái),我們知道了投射我們藏紅花色/精子的更佳地點(diǎn),領(lǐng)會(huì)了智慧所恐懼的,/胸部高聳”。有好幾首詩(shī)是寫給小哈麗特的,女兒是洛威爾的珍寶,在女兒身上,洛威爾重新發(fā)現(xiàn)了母親,與親情的溫?zé)帷B逋栭L(zhǎng)期為躁郁癥所困擾,通過《癥狀》《在病房》《十分鐘》等詩(shī)作,我們可以領(lǐng)略詩(shī)人的痛苦、恐懼與孤獨(dú)。自白詩(shī)的視角是內(nèi)向的、自我的,采取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學(xué)說的分析應(yīng)用,很多自白派詩(shī)人都有精神疾病,或許,靈魂的損耗就是他們必須為詩(shī)歌付出的代價(jià)。
自白派的主題大多是個(gè)人生活,但并不等于說,這些詩(shī)歌就總是寫瑣細(xì)的日常。還有友情,還有閱讀,還有思考,還有個(gè)體置身的社會(huì)與大世界。比如,《臭鼬時(shí)光》就是為伊麗莎白·畢肖普而作,洛威爾后來(lái)說,“重讀她(畢肖普)的詩(shī)為我開啟了一條道路,使我得以沖破我的舊模式的束縛”。洛威爾與畢肖普的友情延續(xù)了一生。自白派之所以成為一大流派,詩(shī)人之間的相互借鑒,是一大原因。洛威爾還有很多詩(shī)歌,寫給他的同時(shí)代的“隊(duì)友”。讀《為聯(lián)邦軍陣亡將士而作》(1964),很顯然是對(duì)越戰(zhàn)的抵制。當(dāng)洛威爾寫下詩(shī)集《歷史》(1973)時(shí),一切歷史都是他的當(dāng)代史。這些公共性的詩(shī)歌,比起早期的作品更有同情心。
1977年8月31日,羅伯特·洛威爾離世。《夏潮》是最后的詩(shī)歌,寫于他去世前三天。獻(xiàn)給第三任妻子卡羅琳·布萊克伍德。在結(jié)句部分,洛威爾寫道:“我想起我的兒子和女兒,/還有三個(gè)繼女,/他們?cè)谶b不可及的暗礁上,/可怕的嘩嘩作響的波浪沖刷著暗礁……/逐漸侵蝕著我所站立的防波堤。/他們的父親缺少慈愛的撫觸/在疏松的圍欄上顫抖。”在這時(shí)候,洛威爾似乎尚未獲得心靈的平靜,仍然被自疚感包圍。愿他在天堂能逢親人,他的祖先與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他愛的人們,愿他安息。


